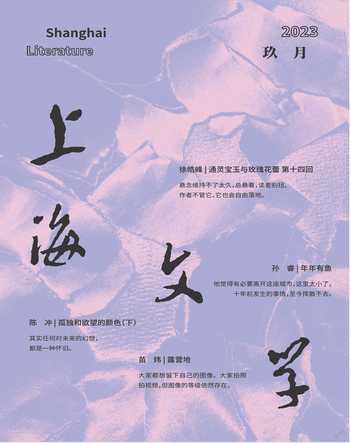散落的足迹
小雅
小夜曲
这是一条长长的寂静的街道
——奥克塔维奥·帕斯
1
呵,又是华丽落幕的一年,
隆冬之夜张开嘴,吐出纠缠不清的日子!
当它把日子一股脑倾吐到街道上,对岸大厦
便附身识别这十几年来熟悉的河流的气味,
——时常将水汽铺于行者的双足
又接纳了水鸟和浮萍、月光这固体露水的天使,
宁静却令它失眠,它的皮肤过于潮湿,
它一直在等待可以晾干它身体的某段舞曲。
2
突然遇见一个伽罗瓦——或者
某种类似的天才,咳嗽得像朵水母,
在彩色礁石间扑腾着倒退。
天才,我们都在期盼,头脑中猛地长出智慧,
就像戴了顶帽子,有着柔软的白色帽檐。
就这么简单,没有风,偶尔有人
晃动轻飘飘的身体,举着路灯小跑,
犹如牢牢系住地球的飘带,仿佛分不开的恋人。
3
风,老朋友,提醒你隔着玻璃能看见的
朦胧景物,也许都是真实的,
快樂,一如既往,这条小路尽头,
行道树在彩色面具后闪烁,到底发生了什么?
它们最清楚,用枝条替代祝福的手足,
一年一度的节日——治安那么好,
喝酒或者切蛋糕,你捂嘴吃下甜甜的一块,
我们终究能自主地享受:刀锋的冷峻味道。
4
这儿是南方,下雪的日子已经过去,
那么雪下在何处?与泛白的波涛有何关联?
坐在炉前回忆我们曾与美德共处一室,
内心不寒冷,裹着羽绒外套的身体亦不寒冷。
他们在过生日,庆祝数十年前消灭的苍蝇,
值得欢呼的年龄,在温暖祥和的节日里来临,
戴眼镜的人,知识分子们,地图上
乳白色的蝇卵——皆是可控的变量。
5
理智因读书太多而滑到?而美德
通过胞衣来传承!我们谈到一位死去多年的
老人,他用诗歌怀念更多的死者,
后来他果真脱下了那张黑瘦的红色皮囊,
这风中旋着笔尖的老头儿,
不给疾病充当模特,他将皮毛风干,
晾晒在两个美洲之间,鼓起的风中大鸟
穿越一片微光,却拒绝用右手写出病毒的名字。
6
有人在大笑,说着削足适履的故事,
然后说乌鸦和猫头鹰,哪种鸟类的内心更黑?
羽毛更沉重?而荒诞没有法则,
我们和世界隔着玻璃,这就挺荒诞,
更荒诞的是窗外行道树又将在春风里
吐出熟悉的味蕾,而我们所失去的歌声,
它是否真是永恒的遗失,湿漉漉的水边,
我们生命的晾衣绳上,结起白霜似的冰片?
乌程张氏宗谱·家族墓地
年月日。一掌可握的小镇上,
一个人的死亡过程仿佛带电球体滚滚驰过
深蓝色夜空,落在桑树与流水之间,
撞击地面形成椭圆形的坑,是死的安居之所。
这蚁穴般不断壮大的家族,正在失去
皮肤上的水分,被泥土推动的白色卵异常耀眼。
此地泥土接纳了一个世代显赫的家族,
他们以沉默为语言,种植松柏和万年青,
桑树手指天空桑叶簌簌鸣响是彗星陨落时刻,
同样沉默不语的是石头,是渐增的青绿色
纹理,
沿着石碑进入地底寻找连成一体的树根,
遇到石头便打成结,彼此的触手已无法区分。
记住和遗忘,哪一个是耗时的胜者?
一代代落叶覆盖的小径被一代代的脚印替换。
夜枭,猫头鹰……更多鸟雀在月下飞过,
远处稻草人扎着表示善意的领结分享祭品,
流水日夜不息从河岸带走散落的泥土,
灯笼果爆裂的果浆和泪水一样对抗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