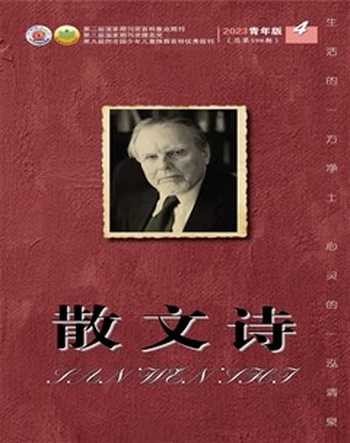怀念辞
野乔
怀念辞
祁连山变成钱塘江,牧群变成鱼群
黄土变成黑土,小麦变成水稻
沙土路变成青石板,洋芋花变成桐子花
在钱塘江,云,缺少高度,山无法承受太多,只满足人间落日
我怀念群山和白雪,也怀念高原和秃鹰
没有到过这里,你理解不了谦卑和庄严
钱塘江时而有雨,我远方的故乡,河床干涸龟裂
对尘世的理解,变成塔克拉玛干的一口古井
风雨辞
栾花旺盛的时候,黄土高原,正在等雨
农夫和牧马人前世也是船夫,这里也曾沧海桑田
风,代代相传,锉碎了300万平方公里的铜质大地
把荒芜留给青山,把高寒留给白雪
夕阳不肯落下,变成倒扣的金碗,留给乡亲们
一生要惦念的事物太多,我惦念麦田,出走半生的你,姐姐的婚礼
还惦念塔克拉玛干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
那里的风,能把故乡吹小
贺兰山下
天空越来越低,风声越来越小,人间越来越安静
在西海固,云不下雨,山的悲凉,猫儿刺和打碗花最理解
小麦的黄,和落日同色,这是大地献给生命的金黄
一周后,熟透的小麦变白,又和大地的颜色一致,白得荒凉
收小麦的人,一言不发,承受着整片天空
他们的影子,日日下沉,连同红寺堡,一起老了
父親更是坦言,跟在他身后,我回头,他的脚印已看不见
再看父亲,他的头上已顶起贺兰山的白雪
忆故人
觉得她就是碌曲水,从六十年代,淌到壬寅年四月
古井已被填平,高大娘跳过,后来种了二亩梨
在碌曲水边,有灰色的大地,灰色的房子,灰色的男人和女人
还有甘南高原,住着落日和鹰,他们相依为命
这里只长股子蔓和冰筋草,对它们来说
是幸运的,拥有的世界太广阔
对河西走廊人来说,他们是悲苦的,拥有的荒芜不可丈量
她说留恋人间的灯火,胜过星星
她说永恒的事物,都会被忘记
只有梨花会想起她,每年四月,按时开,又按时败
只有昆仑的冰雪,在夜里,轻轻拍打她的墓碑
走洮水
上辈子一定是棵树,一棵栾树
和谷物,牧群,长在鹿儿塬,放马塬
因此,懂得了五十年代的洮河水
大风吹尘世,男人引渠
女人守麦田,男人引渠
为此,乡亲们准备了河床
准备了渡口,准备了船,甚至莲,鱼苗
土地托起的洮水,承受了人间的悲与喜
陇中在等的洮水,从黑夜,翻山越岭,开枝散叶
引洮的男人,满头黄土,月光下,像天山的雪
我开始敬畏天山,他头顶的雪,百年不融
念祁连
风把大地压得很低,河流并没有因此升高
我不说话,和万物一起,失去了言语
你能从我的眼里,看到小麦如何生长,雨如何丢失
牧群如何绕着黄草梁一圈,顺着干涸的河床归来
这一生,要理解的太多,接受的也多
我在二十岁,接受了雨的角色,和故人无异
能让乡亲们大喜,大悲
我会在四十岁,理解落日,一盏深黄色的孤灯,日日抚慰人间
大风歌
还是大兴安岭和阴山的风,因此,八百公里荒芜
族人挪动不了祁连的雪,因此,走廊南山,托来山,疏勒南山.
无比高寒
黑河是流动的时间,带着族人的希望,冲进了巴丹吉林沙漠
这里有一万个村庄,他们的河床,空了十年,又十年
上天欠大地的雨,一场未落
人间星起,星落;灯起,灯落。在风中
只有灯火读懂了村庄;只有河床,读懂了天
在鄂尔多斯高原
在河套人眼里,他承受了更多天空
被风敲碎,落下的群星,变成人间的灯火
倔强而坚硬的烈日,经燕山,太行,行至鄂尔多斯高原
麦田和牧群,在这样的烈日中苍老,父亲也是
一生一直在理解水,从祁连到贺兰山,再到阴山
这一次是因为,黄河向北折转,去了河套平原
而我一直信任的事物,在鄂尔多斯高原更高处
鹰,能带走人间的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