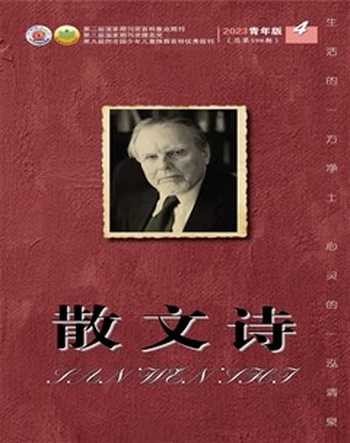冯家湾
弟弟
秋雨
雨水,经常在梦里落下来。
当一切变得寂静,它们才能保持体内的纯净。
远处的街道,只有几片稀稀落落的树叶,在风中旋转。
更多的叶子,已经被清扫路道的清洁工倒入垃圾箱,它们黄灿灿的一生,就以这种极为简单的方式结束了。
而雨,似乎没有怜惜万物的慈悲心。
来不及成熟的果子在枝头腐烂,卷心菜上卧满了晶莹的露珠,仿佛一面冰冷的镜子,在无人问津的泥土中,自我审视,自我怀疑和肯定。一条菜青虫,蠕动娇小的身体,想要离开,攀附到更高的枝头去。而缓慢,注定它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秋天的寂静中,它只能做一条小小的虫子。而蝴蝶,早在某些跌落的树叶中,化为乌有。
电线杆上,两只无家可归的麻雀,相互依偎,秋天的萧瑟,让它们变得寡言少语。
几朵野菊,开得十分耀眼。
蜜蜂、蜂鸟蝶、松鼠,都忙碌了起来。它们和众多的父母一样,缺乏安全感,在冬天来临之前,它们需要贮存更多的粮食。
秋天里的父亲
此刻,我能想象到的,是乡下院子中的梨树和一头老牛。
犁——被秋天的雨水和泥土擦得雪亮。
麦子,在晨雾中冲开种子柔软的身体,她们用绿油油的生命力回馈大地,给予自己的垂怜。
而父亲的头发,白如雪屑。
他和一个季节有着无法割舍的牵绊。
秋天,对一个乡下人来说,无非是采摘梨子、割草、喂牛、种麦子。
秋天,对一个父亲来说,无非是抽一棒卷烟,擦擦生锈的犁,想一想自己的孩子。河岸的格桑花
吹过来的风,仿佛绕开了她们的身体。
当萧瑟的冷气顺着河道涌来,芦苇发出簌簌声,一些说不出名字的花朵,已经垂下高昂的头颅,像一位失去家园的老人。
只有格桑花,摇晃着细小的身体,与寒风做着最后的抗拒。
白色、紫色、红色的花朵,像一轮随时都要熄灭的烛火,在风中摇曳。而对于垂钓者和经过这里的人们来说,她们,无疑是最美的风景。
秋天的寧静无处不在。
当我们口中呼出的气息清晰可见,当我们穿上厚厚的毛衣,戴上红色的围巾,我们的视角,也将变得狭隘。
格桑花——用力绽放,她们惧怕的,不是寒冷,而是桥上刚刚拥抱的一对恋人,散去后,留下空无一人的寂静。
永恒
时间的齿轮在不经意间辗过路口,当我们再次回首,草木还在那里,开出一成不变的花朵。而后院的老牛,不知是我们童年时光里那头牛的第几代子孙。
风,从山峦袭来,野菊花摇晃轻盈的身体,没有暗香的季节,苹果和梨在上了年岁的树下,默默接受腐烂的结局。
腐烂是另一种重生。
甲壳虫放弃了飞翔的愿望,在一片枯萎的树叶上,它们已经选好自己最终的目的地和归宿。
一阵风,从残垣断壁中传过来,它们放下爬行的夙愿,用一种永恒的姿态,躺向大地的某一部分。
来不及脱落的果子,在空荡荡的枝头敲响暮钟,像一场告别。而祷告,开始于一只长尾喜鹊,鸟鸣触碰到屋檐,深秋的消逝,也随之爬上墙壁。
老的已经足够老了,枯萎的核桃树,宛如一尊雕像,矗立在门前的十字路口,迎接来来往往的人群。
当经过那里的年轻人,用异乡的方言问路时,她枯干的根茎,仿佛有了几秒钟的微颤。而后,温暖的光透过枝叶,一棵树在照耀前,还要望一望,将自己带向这个世界的人。
消逝,也是另一种永恒。
小花猫
我们跨过放学后的河道,秋天的石头有了些许冰冷的触觉。
这是12岁那年的秋天。
我和远方侄儿在离家不远的村校读书,因为对一只小动物的喜爱,我们要走很远的路,去另一个村子,见一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猫。
我们看到了她——一只闭着眼睛,在母亲怀中和兄弟姐妹吮吸乳汁的小花猫。
生满冻疮的手,捏了一路的纸币,变得皱皱巴巴。
一张破旧的十元纸币,和一只长着圆溜溜眼睛的小东西做交换时,我们觉得物有所值,丝毫没有在意过父母结满老茧的双手的劳作,和一只小猫临别母亲时,不舍的嘶叫。
暮色一点一点铺满大地。
我们抱着小花猫,离开一个叫了中川的村子,再经过我们学校所在的小河村。
天黑之前,我们回到了冯家湾。
小花猫——
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
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伙伴。
苹果的味道
暮色,再一次降临。
古老的四合院内,母亲正在淘洗土豆淀粉,梨树固执地摇晃着身体,想要将最后几片叶子也抖落在地上。
枯黄和颓败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众多的惊喜。比如,当我们一放学回来,正房的门窗里就会飘来扑鼻的苹果的味道。一斤麦子换一斤苹果,无需过秤,也无需讨价还价,童年的每一次交易,都是真诚的,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的祖先穿过黄河,带着贝壳,去不同的部落换取食盐,那该是一种多么诚恳的交流。
天色晚了。
所有的屋子都有一座烟囱,扫来的树叶烧在炕洞里,吃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新闻联播——在黑白电视机里响起最初结束的声音。
昏暗的老式电灯泡上沾满了灰尘,满屋子苹果的香味,萦绕季节。
秋天的梦里,肯定有一片苹果园,父亲和母亲在树下采摘,我和侄女,在田里奔跑追逐。
喜鹊
天气暖和的时候,把自己放在麦场里晒一晒。
几只麻雀落在附近的地面上,也许是因为太冷的原因,它们的羽毛,缩成一团,圆溜溜的身体,像一小块滚动的风滚草。
你没有赶走它们,尽管它们偷走了你晾晒在院子里的葵花籽。
坐在板凳上,你杵着拐杖,闭上慈悲的眼睛,像一尊苍老的木根雕像。
突然,喜鹊的声音从屋后的古树上传来,苍凉如箭的悲鸣,抖落秋天的最后一片叶子。而你,依旧杵在屋子前,享受着太阳的抚慰。
你的耳背了——
那样明显的声音,在只有一个人的院子中,你却忽略了它们的存在。
晚年
太阳下山之前,一切又变得安静起来。
麻雀叼着一颗葵花籽,踩在瓦片上,飞走了。
最后一声喜鹊的回音,在山野中荡漾开来,炊烟——从远处的屋子升起来,直挺挺冲向暮色。
这个时候,你才从板凳上站了起来,颤巍巍地往门外的草垛走去。
一个人的晚年,是一道巨大的谜题。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你怀中的枯草是用来煮面条的。
可你把它们放在了炕洞里,划燃的火柴,照亮你的眼睛。
也许,你需要的只是一团火。
雨
雨水,会顺着童年的路面,从打麦场流到湖坝里。
邻居家养了八个月的年猪,在吃完一顿可口的胡麻杂后,死在那个寒冷的雨天。
她心里难过极了,边抹泪,边往炕洞里烧树叶。
丈夫,将那头还散发着体温的白色年猪丢在野地里。
嘴馋的嫂嫂们,顶着大雨,去遥远的柳樹下,卸了四条猪腿回来。
厨房散发出扑鼻的肉香味,我们围在门口,像几只等待投喂的小猫。
雨点打在院子的积水里,滴答滴答——
一点一个雨泡,三天不揭帽。
雨,掩盖了一些悲伤。
也洗亮了一些喜悦。
冯家湾
那里,有我寄托的爱和信仰。
为了不让自己过早地被放逐,我努力融入到每一颗饱满的玉米和谷子中去。所以,在每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时,我体内的雨水和雪还尚有丰盈。
在一个叫冯家湾的地方,人们已经懂得将过去的一切放下,在那里,我们彼此有过口角、爱和帮助。
村民善于种植土豆和玉米,她们经常在秋日的某个午后或者暮晚,开始准备食物,在铁锅里煮玉米和土豆,而她们习惯将这两种植物,叫做苞谷和洋芋。
电线上往往停落着几只燕子,有时候,那上面也会落满露珠和雪花。
在长久的守望中,村庄一天天老去,风雪包裹的土屋子,随着年轻人的一天天长大和离去,也开始倒塌。断壁残垣下,月光依旧清亮。
眼中布满光泽的老人,在村口的田中挖掘一棵绿头萝卜,我们互相问候,重新介绍自己,告诉彼此的姓名和住址,在一个并不大的村庄,我们已经需要用这种方式去重新认识一位长辈,这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
土地庙和山神庙依然守护着村子。
山上的树已经高出所有的房屋。
我们在杂草丛生的小径通过,寻找走向自己家乡的捷径。
想象
当暮色从山边袭来之时,我就有了众多的想象。
和你一起去乡下走走,看看那里破败的房子,在村口的杏树下看小小的蜜蜂。
许多说不出名字的野花,在树下开出灿烂的色彩,无尽的香味混在一起,万物在彼此的喜悦中给予大地回赠。
村里的人大多都走了,可众多的树木和花草依旧怒放着。山上有可食用的野果,野兔和松鼠在田间跑过,它们在群山中见到了我们,会惊慌成一道闪电,倏忽不见踪影。
此刻,我要做的是,教你辨别一颗野果与另一颗野果的区别。
野草莓微甜,野枸杞微涩,满树的槐花长在树上。
此刻,我想用柳条编织一顶帽子,戴在你的头上。
这算不算一场盛大的约定?
风——从山口袭来,让山谷有了一种甜蜜的晃动。
如果在这世界所有的秘密背后,我们将自己的余生交付给寂静隐秘的山村,山上沉默的树木,会不会因为两个相爱的人的到来,重新枯木逢春?
岁月
岁月的容颜,最能让一个人失去安全感。在渐渐老去的时光中,我们注定要失去一些东西。
曾经的理想,也被生活的琐碎打碎。
亲人们在日子的倒影中渐渐老去,我们头顶的风,有时吹来雨水,有时吹来雪花。云点缀着天空,可终有一天,它们会带来一场巨大的暴雨。
我们在雨中遐想,想象月光的温凉和阳光的温暖,渴望被这个世界热爱。
于是,我们可以冒着淋湿自己的风险,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和商贩讨价还价。
日子的盐,从一个人的成长开始,扮演起人生一道调味品的角色。
我们在生活织就的网络中,开始渐渐认清自己。
家中的老人,需要我们赡养。
膝下的婴儿,需要我们去抚养。
那些青绿色的蔬菜,各有来处,各有各的用途。
收割之前,它们也曾热爱阳光、雨露和早晨的太阳。
直到它们被送往菜市场的各大超市,它们才真正明白过来,自己的使命——无非是被那些匆忙的人们选中,提回家去。
让生活,更加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