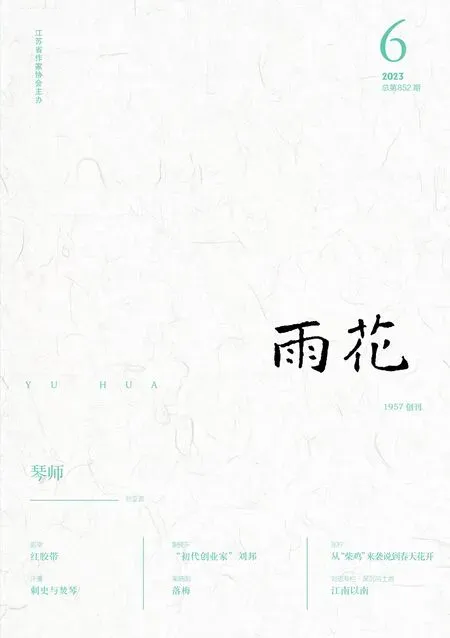皖人歌
黄亚明
暂坐
园中很多白车轴草,随意洒在坡间隙地,花朵就长得到处灰白青绿,几不可察的小蜜蜂骑在花蕊间,或许有采蜜时振翅的“嗡嗡”演奏声,但乐器的丝弦实在太小了,我完全听不清音乐的走向,它在无视一个旁听者的孤独?路边,几十棵金丝桃,瓣丝细而绵长,去年我在这里所见也似乎如此。微风吹处,几百个花瓣挨挤点头你亲我侬,神态各有异趣,一些被夏光催老的瓣丝尚悬垂于花下,金穗一般柔弱。左边的天人菊,长长叶茎顶着迷你版向日葵,黄瓣中簇着一团深红,像极了童话中小姑娘徐徐挥动的五彩小帽子。
忽然,一只短尾鸟在白车轴草间蹦跳,我很想拍好它的美妙,它似乎睃了我一眼,一下子飞到了林间高树。几只鸟同时“叽叽喳喳”起来。
昨日端午,下了几场暴雨。半下午初晴,在园子转了一圈,偶见有老太太手拿艾草,缠成人状。《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四民“采艾以为人悬于门户上,以禳毒气”。艾人,又名健人,多用于悬门户。宋人又称它为豆娘儿,宋无名氏《阮郎归·端五》:“门儿高挂艾人儿,鹅儿粉扑儿,结儿缀着小符儿,蛇儿百索儿,纱帕子,玉环儿,孩儿画扇儿,奴儿自是豆娘儿,今朝正及时。”其中端午风情,诸般物事,如晴日暖风,百花莺声,难可名状。晚饭后,又和家人绕着园子转了一圈,一家人喜乐吉祥。
现在我在数火车,砀山梨、骆驼奶、青花郎,各色广告一晃而过。不再是绿皮火车缓慢刺耳的“咣咣”,而是“嗡呲嗡呲”一瞬间就飞闪向异乡。这里距合肥南站很近,火车声是日夜的伴奏,那些外乡客,旅途中并不会过分关注一个小坐在城市公园的男人。我在数火车,一列、两列、三列、四列……安静的早晨,我像是回转到了懵懂美好的少年……
虎形记
虎形的油菜花开得略带浪荡,山田中去年的稻茬约莫半尺深,枯败而色泽灰白,不经意田土上竟冒出一层层绿。绿意是很淡,却有几分绵绵,绵绵不绝。许是前几日冷湿下了雨,又或是上头挖机在给新建的民宿挖土,溪流涨大了些,微有混浊。溪边不远处的洗衣妇在捣衣。这是难得一见的古景色,如今几乎没人在河畔捣衣了。捣衣只在山里,或者南方之南,纯净的山水和老画中。也没什么遗憾,前尘而已。溪边坐一个钓客,纹丝不动,似乎自己就是肉质的钓竿。他身边三三两两红男绿女,在一堆卵石上撒欢。待久了,钓客偶尔动动身子,溪水似乎也颤抖了一下,一条溪就被这些人弄活了。山里就是这样,晨昏寂寂,不知其所来,不知其所终。来时我经过新结对户王业华家,是第一次见面,自报家门,他热情地散烟。这是个精干爽朗的老人,儿子在浙江丽水做项目经理,以前承包过车队。我们边抽烟边闲扯,小楼房在我和他背后,门前有葱蒜之气,一畦畦溢出来。然后我往更深的山里走,去结对户杨全友家。靠山,很高的山,费劲抬头看,最上面是老树,各门各类,也叫不出名字。之后是悬崖,特陡峭。再下面有好几畦菜地、茶园,山脚、田堤边角摆放了几十箱子土蜜蜂,几万只蜜蜂飞来飞去,“嗡嗡嗡”,金晃晃,并不令人觉得可怕。真是好天,天色很蓝,哪家的牛“哞”了几声,河对面人家的电锯似乎在咬啮松木,“呼哧呼哧”,松香被阳光弹到了天空。电锯声像一排排五线谱,那些下乡搞批发送货的车子,那位目不斜视读报纸的颇为骄傲的杂货店主,以及摩托车、电动车、黑色白色红色轿车,间或有从村部探头出来的村民,乳娃的啼哭,都像五线谱上守规矩或者捣蛋跑调的音符……现在我站在村部大门口,正对着“某某婚庆”背后的大山。不见山色,只见漫山竹色青黄,无风自动,有风,也动……
早晨静得比一天漫长
云不会随便指挥一只鸡叫,鸡叫通常会在煞黑的天空中先垒一个鸟窝。这个鸟窝不断扩散,越来越大。我知道太阳就是个鸟蛋样的东西,只有鸡叫才能将它孵化。这时候鸟窝快变成了云朵,一朵一朵地劝说太阳。阳光就开始像一头黄狗,穿过浩浩荡荡的群山。
一座坡总是在静默中回想,大地猜不透云的心思。
幸好一只松鼠打扰了木窗,“吱呀”一声。
在黄泥坡,早晨静得比一天漫长。
斜坡
斜坡是春天的一个切面。
我在斜坡上慢走。在斜坡上慢走,一人一狗。天气白亮,天气白亮得像一只狗,在斜坡上慢走。
日头挂在山坳,青油油的日头,清幽幽的山头。一阵冬风吹刮,日头快掉落山头。日头被一捧雪捧住,慢慢往下落。
像种子慢慢落进了地里,不久之后,春天来了。
妖气
樱桃熟了,红果璨璨。这是春的气象,冶溪河的风吹得山里红一片,青一片,绿一片,蓝一片,肥美丰腴一片,红红绿绿紫紫白白粉粉黄黄。暮春的风带有强烈的肉感,似乎妖气炯炯,那些古树还在河边,树上有种种乱啼的鸟,飞一会儿东,飞一会儿西,山色水色随之流溢。
金黄的油菜如大妖,喷涌之液已然融入大地,踩在田亩间,酥酥簌簌。联庆村的莲荷未开,还是花苞的点点初萌之态,但小家碧玉型小妖的意思已在。
情侣树下,杜鹃海中,一行中年女人,妖精一样,欣欣跃跃。她们活得妖精一样,也许几百年,都是元气饱满的妖精。妖而不乱,妖而不冶,是妖精的大境界。《山海经》里,说到上古十位妖女,均弱柳扶腰,美艳不可方物,但法术通天,行善者有,作恶者有。
《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句曰九凤……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说的是凤凰,第一本领是“能吃”。《西山经》云:“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青鸟女妖,仿佛是为情“殷勤探看”。
花妖多柔弱之态,多美丽动人,“风动花枝探月影,天开月镜照花妖”(明唐寅《花月吟效连珠体》之六),有莫名之妙。志怪小说《集异记》说到一位书生夜宿寺庙,晚间散步,在花丛中遇到一位美女,容貌清丽,谈吐不俗。临别之际,书生将自己的白玉戒指相送。书生再回此地时,却遍寻不见女子,行至花间发现一株百合格外清雅别致,枝上居然挂着白玉戒指……
古籍旧事渲染得好,比如《封神榜》《聊斋志异》,也不全然是坏妖。好妖亦有冲天妖气,妖媚生成,乃内功精湛粲然。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身边的女人妖妖,也是人间好景。
老婆她们建了个群,群名“七妖八怪”。年长为妖,年稚为怪,普遍妖而不怪。七个妖,八个怪,嘱我写篇小说,需将她们描摹如西施,美丽百年,喜事乐事伤心事,都不算个啥事。挂怀无碍,念头通脱,三四十年的小妖也会成为女神。
今日老婆生日,作此礼赞小文,天下诸女妖同喜同乐。
吃了几颗冶溪的樱桃,酸甜可口,犹如年轻时,夫妻卿卿我我、吵吵闹闹,是热闹,是情爱。人过中年,情爱变为情义。有情有义,朴素中蕴大道,也是妖怪成仙的应有之义。
元旦登花果山
年年登山,年年登高。
春来花发,秋来果硕,这是花果山的美处。好几年没登花果山了。住在深山皱褶的小县城,花果山像一幅国画小品,三十多年前我在小城读普师,时不时上花果山看书看花看树看人,烂漫之心是一簇簇野花。十多年前我调到小城,偶尔也走走花果山,兴致一来就走走,心情不好也走走,鸟粪很多,鸟鸣悬在大枞树上,“吱吱”“嘻嘻”“叽叽”“咕咕”,水墨一样让人心里静,静到澄澈。
冬至甫过,小寒大寒在即,然山中冬意似超然节外,倒是春气渐浓。今日元旦,早晨天色雾蒙蒙,到十来点钟,日光开始浩大。如此日色是宏大叙事,在好日色里携家人登山,乃除旧迎新的心头美事。
妹妹一家、妻侄一家、妻侄女一家、我一家,有小娃三个、大娃两个,黄发垂髫,燕语莺声,铺下一片盎然绿意。听见花骨朵萌发的声音,灰喜鹊睡梦里咕哝的声音,心情为之一荡。山中绿色被日色浸染,浮光耀金。金色里有温暖,有幸福,有吉祥,闪耀光明。
人往高处走,新年平安喜乐,是一种美好的愿力。
写作也如登山,步步登高,步步见高处的风景。
同行者,老黄家老刘家十来人,人与小狗载欣载奔,水塘边,草坪上,披一身金光,步步登高,步步旺相。
同行者,有熟悉者、不熟悉者,数十人,均扶老携幼,自在逍遥。
龙潭记
初秋入潜山,见了七分秋色。山里秋色清奇,亦有春色的娇俏,随山色赤橙黄绿肆意变幻,曲里通幽。曲里通幽之外,又是明明暗暗的山色重重,空山层层荡荡,在胸间空蒙回环。
九月好天,如小阳春,阳光潋滟。阳光打在车窗上,车窗里映出一车人的影子,斑斑驳驳。阳光好时才有斑驳的层次。山里的阳光带有草木气,披挂在身上如铠甲,守护人心。
车过余井镇,未见长春湖,但有一路苍翠,像辛劳持家的农妇,从水缸舀到了一幅蘸浓的油画里。
车过龙潭乡,一片久违的詹荡,秋色的层次不甚分明,颜色驳杂蓊郁,似是混杂了十万亩的颜料。
龙潭乡在天柱山北门之下,沿路的柳树、桃树、栗树,枝枝杈杈间,晃动古老而年轻的漆蓝,烁光熠熠。那些青枫、枞杉,彼此簇拥,捭阖纵横。
渐渐是竹。有些衰黄,有些深绿,有些与其他灌木乔木迥异的激荡。这种激荡还潜藏在内部,而非广为人知。但不仅是一棵两棵三棵五棵,已经族居群聚,像天空的印泥掉落偌大的一块。风还没吹来,若吹来了秋风,往深里一定是竹海涛涛,一种南北过渡地带呈现的变形、战栗的莫名韵律。
龙潭拥有我沧桑的初始青春记忆。少年的足迹曾在竹海间跋涉,迷茫惘然。我一直以为龙潭有蛟龙飞升,溅起无边白浪。少年就是梦幻的白浪。
路边人家,丝瓜青长,毛茸茸的藤蔓探出朵朵黄蕊。那些瓷砖砌就的乡村水泥白墙,被经年的雨水日头侵蚀得驳黄半黑。大门有一联,大红不减:
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庆有余。
墙上挂了红红的干辣椒,与春联同辉,可为积善人家注脚。
往左拐是万涧村,有古戏楼、齐云道院、杨家祠堂,我去年曾游过半天。但车子顺溜儿往右一拐,拐到了槎水镇的路上。
群山遍生竹林,一时间秋意荡漾,又穿行在竹海合围的喧杂汹涌中,目标:一个古老的时光盆地,塔畈乡。
入户
山中松影入户,柏影入户,一段段的鸟声虫籁,次第入了户。
晾在窗台上,依稀有梦的爪痕。月亮肯定来探访过,山里的泉水如跳丸,何时蹦到了窗边树上,变成悬垂的露珠,似小鱼静伏在梦中。
户外小溪白亮如银线,蜿蜿蜒蜒,皖西南的夜都是如此白亮。
天空幽蓝,星子有好几粒,摇摇欲坠。
在板仓,夜晚的意味是一点一点加深的。草丛、灌木、阔叶林,都屏息静气。静气深了,有时会被一声“嗷唔”的兽语惊醒。旋即,静气更深。
倚床翻书,一阵从宋朝来的风,入了户。
把蘸满虫鸣的松柏影折下一枝,寄给苏轼,寄给承天寺。
中庭月色如积水,如户外小溪,一夜白亮,夜夜白亮。
欲飞
十月中,在半山居饮茶,风来饮,夕光来饮,月色来饮。
半山居居半山。半山好,花半开,酒半醺,日光半照,邀风来扫,月色来扫,剩下都是斑驳的影,疏影多横斜,有溪水叮当、月上树梢的意趣。一群人,青阳人、潜山人、岳西人,影子如茶瓣,落在偌大的来榜镇盆地。秋气清寂,亦有花影、鸟影、人影、树影,所有的影子晃动起来,是一杯茶牵引一条秋溪的晃动。茶杯里似有清淡人影走动,是谓茶人。
茶人瘦。茶亭中竹瘦,风瘦,雨后黄花瘦,秋来万物均清减了几分。
明前茶也瘦,雨前茶则渐渐丰腴。想来春日的半山居是雨前茶,一山斑斓空翠,山花浪荡,在风里醉得东倒西歪。宋人黄庭坚有诗:
花上盈盈人不归,
枣下纂纂实已垂。
又云:
仰看实离离,忆见花纂纂。
说不得道不明的旧影陈迹,盈盈离离纂纂。看过黄庭坚行书《花气诗帖》,中年笔墨却有水流花开的少年气。“风前横笛斜吹雨,醉时簪花倒著冠。”(《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十年前读来一时惊诧,颇合我意。
这几年我白发渐苍然,已无簪花心事,心境多如苦茶。
这一段太忙,也没心思品茶。
这一段也没闲绪,去看一座山,去访山问仙。
黄昏的半山居是红茶。夕阳金红挂在山头,夕光照在半山腰的木屋上,流光漫漫。
早晨的半山居是绿茶。早晨的风清爽爽,略带寒意。是秋意,也是春意。
我喜喝红茶。
今日霜降,庭前草木落黄,忆得半山居一晚,曾梦里恍惚:一山树,一山叶,一山乱石鸟啾,如茶人数十,宽袍大袖,肉身清癯。
以天地为壶,捉箸举杯。兴至酣处,双臂生了翼,欲飞,欲飞……
大事
下午窗前枯坐,忽然,就想起了胖子饭店。那个讨喜的并不十分胖的胖子厨师,喜气堆在脸上,如红辣椒堆在饭尖。
胖者最不耐烦横肉,横肉里有匪寇气。如《水浒传》中鲁达,如鲁达几拳头打死的屠户镇关西,如满口腌臜话挥斧杀人的李逵。铜梁老画家秦廷光,曾绘李逵和武松两大煞星做门神,画中李逵形状和水浒原著大有不同,虽不算慈眉善目,戾气却消减了好几分。秦廷光和油画家罗中立,曾是四川美院附中的同学。罗中立画过《父亲》,苍如黄土高原沟壑林立。秦廷光做过电影院画工,心里多是老重庆旧影。其实二人殊途同归。
我少年时看水浒,以为戾气是勇力。少年人多戾气,无所畏惧,心中无山无栅,一缰野马。如今觉得头顶三尺神明,压得人战战兢兢,敬畏使然。但水浒偏要破敬畏心。打打杀杀,水上马上,刀棒相交,端的痛快。痛快是痛快了,想破旧呈新,难哉。
破而后立,是革命之道,是为文之道,也是美食之道,难哉。
胖子厨师不是李逵、鲁达,估计他杀鸡、杀羊,肯定没杀过猪,没杀过牛。好在他有羊肉火锅。我对羊肉的嗜好几乎偏执,却又颇不喜几瓢寡水,添些火锅底料,那种千篇一律的滋味。胖子烧的手撕羊肉,能吃出地道的葱蒜姜干辣椒味,且熟烂,对于一贯牙口欠佳的人,喜欢得真是无以言表。
喝过皖北羊肉汤,淮北的、蚌埠的、宿州的、阜阳的、亳州的,都觉得大差不差,膻气在外。虽删繁密,多有简淡,却少了山峦重重凛冽的起伏。
胖子羊肉的葱葱蒜蒜,是直抵内心的旧时故园滋味,是肚腹洪荒饥饿中的几滴猪油。想来一锅里藏幽曲之妙,拥大块之美。
文章大事,火锅大事,一样少不得。
好合
秋风骀荡,金阳灿灿,因女儿婚事从岳西赶往芜湖。潜山、怀宁、桐城、巢湖、含山,秋色一路丰腴明艳,青青红红。入秋已有些时日了,地气依旧喧腾,青绿不减,犹若盛夏的元气少年,猛发充沛。大别山山势则渐渐低伏,变化为余脉、丘陵、平原,待到得巢湖、含山,入目的都是大片金黄的沃野了,间或有人家菜园子,篱边探出的丝瓜绵绵长长,悬垂了一份恬静的富足。
真是奇妙。山也富足,水也富足,岳西的山,芜湖的水,是老戏台中的喜相逢,中国画里的牡丹会。
芜湖好,好在有湖。平芜尽处是春山,春山草木有狂草的葳蕤。如今一湖秋意,七分月色,亦合我中年心绪。芜湖好,揽湖入江,湖是镜湖、九莲塘、凤鸣湖、龙窝湖、怡龙湖、响水涧、陶辛湖、奎潭湖,江是青弋江、水阳江、长江,有凤鸣龙吟之音,亦有莲塘响水的意境。我曾在宣城桃花潭见过青弋江,在敬亭山下见过水阳江,均清癯如宽袍大袖的古人。想必再过些日子,秋风起处,荻花纷飞,这些江上少有舟楫渔人,可得一篇《秋江荻花赋》。荻花飞处,亦是洋洋洒洒。月光飘来,亦是无声的大珠小珠落玉盘。
芜湖古称鸠兹,鸠鸣在兹,兹地美好,好花好天。想起王维诗:
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
一派喜乐,真璞,恬然,是旧时乡村的本源之味。
又想起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
屋上鸠鸣谷雨开,
横塘游女荡船回。
鸳鸯湖,亦名南湖,在浙江嘉兴市南三里处。鸠鸣咕咕,棹歌荡荡,春游的妙处在十月天看来,倒是有些恍惚了。
一时无言。恍恍惚惚中,我已到了沈巷镇。鸠江区一个新旧林立的镇子。
当晚的家宴叫作“暖房酒”,多用于敬舅舅,敬舅舅就是敬母亲。各方亲戚、本家到场欢饮。新事新办,但沈巷的古风犹存,老人坐在主位,上了硬菜,先请老人。下首陪客的三人,彬彬斯文,人情十分,每每举杯敬客,姿仪宛若古人。
翌日晨起,见朝阳初生,其道大光。沈巷镇的鞭炮阵阵响起,大吉日。
婚礼上,女儿梓童和女婿孙辉,一对璧人,青春逼人。“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这是《诗经》里的美好。昨日美好,今日美好,愿明日美好,明年美好,年年美好,安然静好。
回到岳西,气温骤降,秋衣两三层,立即有入秋之味了。但秋气不是萧瑟悚然,是内敛,是贮藏,是厚积薄发。秋气里亦蕴有勃勃生气,万物成熟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