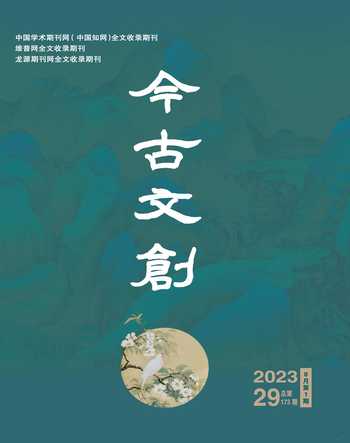《愤怒的回顾》中的空间对峙与身份建构
【摘要】《愤怒的回顾》是英国剧作家约翰·奥斯本的著名戏剧,剧作塑造了吉米这一“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人物。本文试图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分析剧作中如何构造出具有强烈对比的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生存空间,并在空间中进一步构建不同身份的角色。以吉米为代表的愤怒青年代表了奥斯本的观点,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不公的愤慨,也展示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关切。
【关键词】《愤怒的回顾》;空间;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9-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9.002
《愤怒的回顾》是英国剧作家约翰·奥斯本于1956年创作的戏剧。在剧作中,奥斯本成功塑造了吉米这一反英雄人物,成为二战后“愤怒的青年”一派的代表性作家。奥斯本所创作的剧作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主题主要批判社会的不公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对自由性格的向往,以及反对社会对人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作品的整体基调为“愤怒”。《愤怒的回顾》是一部三幕剧,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中部。剧作主要讲述了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主人公吉米和他来自上流社会家庭的妻子艾莉森之间的重重矛盾。吉米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这种灰暗的人生使得吉米变得异常的愤怒。他对资产阶级出身的妻子嬉笑怒骂、反复无常,喜欢嘲讽激怒她来表达自己对上流社会的愤懑不屑。同样来自下层阶级的克里弗是维护这段关系的天平,负责安抚艾丽森的情绪,同时按捺吉米无时无刻的愤怒情绪。这三人组合成一种极其畸形的家庭关系,在中部一个拥窄的阁楼中居住。吉米厌恶现存的社会秩序,但又无力改变,只能在愤怒中消耗生命,表现了英国战后一代青年对社会和人生的不满情绪。戏剧表现了英国普通人的生活和人们面临的各种现实困境,给人们提供了思考生活的机会。《愤怒的回顾》掀起了英国戏剧改革的新浪潮,之后的戏剧开始从描写中产阶级生活转变反映下层人民生活。
国外对于《愤怒的回顾》主要从精神分析学、吉米的个人形象诠释以及社会阶级矛盾等角度进行研究,也有学者将其与奥斯本其他戏剧进行比较,国内学者亢泰、刘润清等早在1980年就发表文章对《愤怒的回顾》进行评析,此后有学者从现实主义角度研究剧作的写作风格,以及从多角度剖析吉米愤怒的原因,或研究吉米的人物形象,还有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解读吉米的愤怒等。由此可见,国内外研究虽然对主人公形象或“愤怒”的原因源头进行多角度深入研究,但还未有学者从空间理论的角度对剧作进行深入解读。文本中空间建构对于塑造人物身份,反映人物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借用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剖析剧作如何通过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的对比来体现《愤怒的回顾》中存在的空间对峙,以及分析如何在空间对峙中建构人物身份,以此来表达奥斯本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底层人民愤怒、无助情绪的深切关注。
一、空间对峙——难以跨越的社会阶层
长久以来大多数文学理论都有注重时间问题,忽视空间问题的倾向。自20世纪后半叶起,空间理论逐渐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批评理论出现了“空间转向”,许多学者也对文学作品中如何体现空间艺术进行深入研究。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理论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他提出,空间不是抽象的自然物质,而是体现社会关系的交织物,它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控制、主宰和权力的手段”(Levebrve,26)。在此基础之上,列斐伏尔提出了著名的“空间三一论”,即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以及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空间指的是由意象以及联想体验所构成的空间,空间实践是感知的空间,是联系表征空间与空间表征的纽带,空间表征则是概念化的空间,涉及知识、符号,嵌入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形成空间秩序。
《愤怒的回顾》中通过空间表征的构建,展现英国社会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生存环境的对比。在剧中,吉米、艾丽森和克里弗三个人居住在一间顶楼的阁楼中,在第一幕前的环境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艰难的居住环境。“一件相当大的阁楼。天花板从左到右急剧倾斜。右下方是两面低而小的窗子……大部分家具都很简陋,而且相当破旧”(奥斯本,3)。“门这边是一口不大的衣柜。一面很高的长方形的窗子占去了左墙的大半。窗子正对着楼梯口,但光线却是通过窗外的一个天窗照进来的。衣柜下边是一个煤气炉,煤气炉旁边是一口木质的食品柜……饭桌前面,一左一右放着两张腿短背高的破旧的皮垫扶手椅”(3)。阁楼相较于一般的房间,因为位置较高,冬季寒冷且夏季炎热,居住条件很差,由此可见,吉米三人的生活环境十分贫困,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租住公寓,且只有满足基本生活条件的日用品。“我管他媽什么屈瑞瑞小姐……就这么个破地方,她每星期向咱们要去了多少钱”(奥斯本,29)。从下文吉米口中得知,这处阁楼还是在屈瑞瑞小姐那里租来的地方,可见他们困窘的经济状况。狭窄的阁楼,粗略摆放的家具,这是下层阶级的生活空间,而另一方面,奥斯本又建造起一个与吉米等人所处的下层社会完全不同的上流社会空间,这在剧作中并没有直接的正面表现,而是通过吉米、艾丽森之口,以碎片式的描述勾勒出资产阶级生活空间的整体印象,比如“那些地方在他们看来就是敌区,我呢,我刚才说过,就是他们弄到的人质……打着我的名号,我们就到处去撞吃喝——鸡尾酒会,周末宴会,甚至有一两次还闯进了人家在别墅举行的私宴”(奥斯本,58)。艾丽森同海伦娜抱怨吉米和他的朋友休因对资产阶级不满去艾丽森的亲戚朋友家中大行胡闹之事,但同时也揭露了中产阶级生活空间的一角,高档别墅象征着财富的聚集,时常举办的晚宴,派对,这些显然与下层阶级生活的窘迫产生鲜明的对比。还有在吉米讽刺自己与艾丽森的相恋过程时所打的比方:“妈咪把她锁在她们的那个八间卧室的城堡里了,不是吗?”(奥斯本,70),从“八间卧室的城堡”的比喻也可一观中产阶级的奢侈。通过人物之口,剧作建构起下层阶级与中产阶级两个迥然不同的空间,下层阶级居住的生活环境潦倒窘困,而上流社会掠夺巨大财富,过着下层阶级难以想象的高级生活。
二、身份建构——环境造就的人物形象
身份最先是社会学中研究的一个概念,身份一词与角色,类别相联系,揭示了生活在社会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身份认同指的是对自己或者对与自己有相同性的事物的认知。“认同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心理过程,它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身份建构是一个过程,是不断变化而非一成不变的”(王,50)。《愤怒的回顾》戏剧中主要塑造了由吉米为代表的下层阶级以及以艾丽森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在第一部分中,通过空间表征,即“别墅”,“阁楼”等概念符号,划分出了上流社会与下层阶级两个对立的地理空间,而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人物的成长历程不断塑造人物性格,建构出不同人物形象。
即便同属下层阶级,但吉米和克里弗的形象也迥然不同。“他急躁、固执、更兼目中无人,因而不论感觉锐敏或感觉迟钝的人都同样不愿和他交往。令人难堪的诚实……他似乎敏感到了令人憎恶的程度。”这是第一幕前对吉米外貌的描述,从这里可以一观吉米的人物建构,这是一个暴躁敏感,十分易怒的青年,反观克里弗:“克里弗和他年岁相仿,黑黑的面皮,身材矮小,骨骼粗大,穿着一件棉毛衫……他神情安闲懒散,简直显得有些痴呆,脸上却透着专心自学的人的那种略含悲愁的深厚的性灵。”这种差别极大的人物性格不是生来被赋予的,而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克里弗没有像吉米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经常被吉米嫌弃,不允许他阅读自己的报纸。他和休的母亲一样,都属于朴素的下层人民,靠自己的劳动赚取微薄的钱财勉强为生,他们不像吉米一样,通过学习知识接受教育开阔了眼界。而吉米能够产生“愤怒”情绪的原因也是因为接受高等教育,开阔眼界之后,看到的却仍然是社会的不公以及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因此他时常是愤怒的,只因自己郁不得志。除却社会环境,家庭也同样塑造吉米的个人身份。吉米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劳动者,母亲却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富家小姐,父亲在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战争中负伤,但吉米是家中唯一一个敬佩和关心他的人,他的母亲极其势利,“只顾结交少数精明、时髦的人……对于自己的婚姻常常悔恨不已,因为这样一来,她就将自己的命运和一个似乎事事犯错儿的男人拴在一起了”(奥斯本,46)。吉米的母亲打心底看不起她的丈夫,她认为丈夫所做的都是错误的决定,和这样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在一起对她的人生是一种耽误,因此她对丈夫从西班牙战场上负伤归来也不抱有自豪感情,而更加努力地去攀附上流社会的人。“当我10岁时,在12个月中我目睹了父亲慢慢走向死亡的过程……每次,我坐在他床前听他说话或者读书,而我只得抑制住满眶的泪水。当12个月结束时,我已被磨炼成了一个老兵。”(奥斯本,46)这对于吉米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背叛,在这样的家庭中塑造了吉米对资产阶级更加深刻的恨意,因此他对资产阶级的情绪比克里弗这样的下层阶级更加强烈,也更加反感。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共同塑造出吉米这样一个身处下层阶级,对上流社会抱有强烈的反感情绪,郁郁不得志,愤世嫉俗的年青一代形象。
艾丽森来自一个中上层阶级家庭,父亲是在印度驻扎多年的高级军官,母亲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身份,十分鄙视像吉米这样的下层阶级试图攀附权贵的行为,因而极其反对吉米与艾丽森的婚姻。生活在这样家庭中的艾丽森自小衣食无忧,难以感受到下层阶级的生活不易,因而对爱情充满幻想,不顾家里的一切反对嫁给吉米,却发现阶级的巨大差异难以忽视,吉米将对上层阶级的不满全部宣泄在艾丽森的身上,这令她感到十分痛苦,但又无力反驳。“艾丽森又已经回到熨衣服的案子边。她抱着两臂站着,一边抽烟,一边呆呆地出神”(奥斯本,18)。“这时,除了艾丽森的熨斗落在案子上的啪啪声外,再没有任何声息。她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手上的活儿”(奥斯本,22)。艾丽森的身份性格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特点:作为笼络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者,面对下层阶级的诘问,他们表现出的状态或像艾莉森的母亲那样不屑一顾,或像艾丽森一样不发一言的沉默,只能不停地熨衣服。
三、充满矛盾——不可避免的人物冲突
一边是笼络社会财富的上层阶级,一边是艰难生存的普通劳动者,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双方必然爆发尖锐的冲突。艾丽森是这场冲突的战利品:“他们俩都把我看成是从社会的另一些阶层弄来的人质,而对那一部分社会他们早已公开宣战了。”(奥斯本,57)吉米无力改变自身现状,因此靠言语发泄怒火,他对艾丽森极尽讽刺、挖苦,恶毒的诅咒她的家人,目的就是为了激怒艾丽森,打破她努力营造的和平景象,撕下她温吞冷漠的面具:“你见到过她哥哥吗?那个从桑德赫斯特来的直脊梁的……流出过那么多有教养的废话。外层空间废话专家……他跟他的那一伙子好几代以来都一直在愚弄着所有的人,掠夺他们的财富……他唯一能够做的——是依靠自己的愚蠢使自己过得心安理得”(奥斯本,22),“一个中年的妈咪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她怕不要像一头要下崽子的母犀牛一样大声吼叫……我说她早该死了。我的上帝啊,那些蛆虫有一天在她身上爬过一趟的时候,可真不知道得要吃多少泻盐!”(奥斯本,73)在吉米的发泄中,最使他痛恨的当属艾丽森母亲,原因之一在于艾丽森的母亲和吉米的母亲一样,都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富家小姐,她们都十分势利并且对下层人民的苦难不屑一顾,一味地想要攀附更高阶层的权贵,因此吉米在怒骂艾丽森母亲的同时也是在宣泄对自己母亲的不满情绪。而对艾丽森的哥哥不满则是因为对社会教育体制的不满,资产阶级给贫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却仍然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子女,即使是无能平庸之辈,像艾丽森的哥哥,反应迟钝,胆小如鼠,对待人全无尊重,却能够进入“公学——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大学,享受教育特权,还有着大好的前程和光明的政治前途,这让吉米感到不公。在初遇艾丽森的宴会中,吉米还遭遇一众资产阶级的白眼,淑女们更是把他视为怪物,一味地表示鄙夷不屑,这更让吉米对资产阶级的同龄人感到愤慨与仇恨。
除却言语攻击,吉米他们更是采取行动以表达他们“愤怒”,在艾丽森与海伦娜的对话中:“他们开始——通过我的关系——自己把自己往别人家里请,尼格尔和我的朋友家,爹的朋友家,哦,不管是谁:阿克斯顿家、塔勒特家、韦恩家——”(奥斯本,57),吉米和休“进攻”中产阶级的住宅,索要吃喝,肆意玩乐,这种无所顾忌的行为也表现了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吉米等人通过这样的“合法报复”手段来弥补自己认为在社会中被上流社会掠夺走的资源,而究其原因,仍是在于当时战后英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均的社会分配造成的悲剧。
四、结语
《愤怒的回顾》通过角色之口,构建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迥然不同的生存空间,又进一步在空间中建构不同人物身份,由吉米为代表的下层阶级,与上流社会激烈地斗争,以及以艾丽森为代表的中上层阶级,攫取了社会的极大部分资源,但在面对社会不公的问题时消极应对,坐享其成。并通过吉米、艾丽森、克里弗、海伦娜等人的纠纷展现了战后英国社会暴露的激烈矛盾,表达了奥斯本对当时英国社会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严厉批判,以及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与愤懑不满情绪的深切同情与理解。
参考文献:
[1]约翰·奥斯本.愤怒的回顾[M].黄雨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
[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3]朱叶.失却了事业的人——《愤怒的回顾》中的“愤怒的青年”[J].外国文学研究,1982,(01):103-108+36.
[4]贺爱军,胡伶俐.《我弥留之际》中的空间对峙与身份建构[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45(01):106-116.
[5]師琦.时空的囚徒——列斐伏尔空间理论视域下的《八月:奥塞奇郡》[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34(11):10-14.
作者简介:
王雨欣,女,山西晋城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