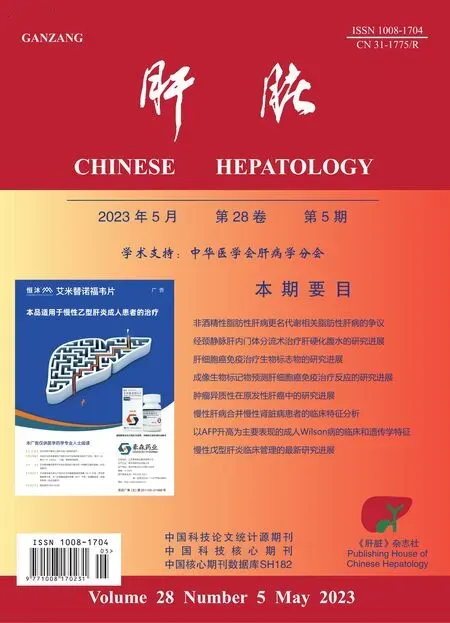转铁蛋白受体-2在铁稳态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谢超 王晓凡 丛敏
铁是人体内细胞代谢和重要生理过程所必需的元素,包括氧气运输、线粒体呼吸、核酸复制、氧化还原反应的催化和细胞信号传导等。然而,当存在过多的“游离”铁时会诱发芬顿反应(Fenton reaction)催化自由基的产生,从而破坏DNA、蛋白质和脂质,损伤细胞和组织器官。所以维持全身铁稳态,满足机体生理需要的同时限制过量铁的毒性显得十分重要[1, 2]。
一、全身铁稳态
由于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缺乏铁排泄机制,因此铁稳态取决于铁损失和铁吸收之间的平衡,以及从循环巨噬细胞和肝细胞储存中释放的铁与在生物过程中利用铁之间的匹配。红细胞生成是体内铁元素的主要消耗者,人体每天需要20~24 mg的铁元素来生成新的红细胞,以替代因衰老而失去的红细胞。在稳定状态下,巨噬细胞从衰老的红细胞中回收铁并以转铁蛋白的形式在体内运输供骨髓造血或者其他组织利用;而小肠和皮肤细胞脱落等造成的少量铁损失(每天1~2 mg)可通过饮食中铁的吸收得到补偿[2]。
血浆铁的主要来源是肠上皮细胞和巨噬细胞。膳食铁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即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这两种形式的铁都被小肠(主要是十二指肠)上皮细胞所吸收。膳食中大多数非血红蛋白铁是三价铁(Fe3+),Fe3+先被十二指肠细胞色素B(duodenal cytochrome B,DcytB) 等还原酶还原为二价亚铁(Fe2+),然后通过肠上皮细胞顶膜表面的二价阳离子转运蛋白-1(divalent metaltransporter 1 ,DMT1)转运入细胞内。血红蛋白铁的摄取也是通过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来实现,但具体的转运机制尚不清楚[3]。巨噬细胞通过吞噬衰老的红细胞获得铁,即红细胞被降解,其所含铁被回收。铁从肠上皮细胞和巨噬细胞通过铁运蛋白(ferroportin,FPN)释放到血浆中。FPN是哺乳动物中目前已知唯一能将铁从胞内转运出胞外的转运体,是由(SLC40A1)基因编码的产物[4]。通过FPN输出到血浆中的Fe2+,先被循环中的铜蓝蛋白和肠上皮细胞基底侧的亚铁氧化酶(hephaestin)氧化,然后与转铁蛋白结合(transferrin,TF)结合形成全转铁蛋白(holotransferrin,Holo-TF)。Holo-TF被运输到全身各个组织利用,主要用于红细胞生成。机体在稳态环境中,血浆中95%的铁来源于巨噬细胞回收的衰老红细胞中的铁,另外5%由饮食吸收,以补充皮肤、肠道上皮脱落等造成的铁丢失[5]。
二、铁稳态的调节
铁调素(hepcidin)是由HAMP基因编码的肝脏合成的一种小分子肽类激素,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天然FPN配体,hepcidin与FPN结合导致配体-受体复合物的泛素化、内吞和降解,从而减少铁入血[6]。由于FPN介导所有细胞的铁输出,因此从饮食中吸收铁的肠上皮细胞、参与衰老的红细胞或者其他细胞的铁循环再利用的巨噬细胞,以及参与铁储存的肝细胞,均受到hepcidin/FPN轴的调节。HAMP基因的转录调节涉及到几种途径,包括细胞信号传导对铁储备或转铁蛋白饱和度变化的响应。肝脏铁浓度增加导致肝窦内皮细胞产生大量肝细胞骨形态发生蛋白-6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6,Bmp6)。BMP6与其受体(BMPR)结合导致BMPR磷酸化,从而促使Smad蛋白-1(mothers against decapentaplegic homologue 1,Smad1)、Smad5或Smad8的磷酸化。这些蛋白与Smad4形成复合物,Smad4被转运至细胞核内,并与编码hepcidin的HAMP基因启动子上的BMP反应元件相互作用,导致HAMP转录和hepcidin表达。在BMP调控hepcidin表达的过程中,血幼素(haemojuvelin,HJV) 作为BMP的一种协同受体,与BMP-BMPR复合体结合参与此信号通路对hepcidin表达的调节[7-9]。另一方面,血浆转铁蛋白的饱和度也参与了hepcidin的调节,这一过程涉及遗传性血红蛋白沉着蛋白(HFE)、转铁蛋白受体-1 (TFR1)和转铁蛋白受体-2(TFR2)之间相互作用的转换。当Holo-TF与TFR1相结合时,HFE与TFR1的结合被破坏,导致HFE移位后与TFR2和HJV形成复合物来调节hepcidin的转录。HFE和TFR2可通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和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通路来增加HAMP基因的转录;HFE-TFR2复合物也可与BMPR-HJV复合物相互作用,通过Smad途径调节HAMP基因的转录。此外,hepcidin的表达也受其他因素的调节:如慢性炎症时,由炎症细胞产生的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介导的Janus激酶(Janus kinase,JAK)和转录激活因子-3(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3,STAT3)通路调控的hepcidin表达,以及红细胞产生的红细胞铁酮,与未知的配体相互作用,能降低HAMP的转录[2, 5]。
细胞内同样存在调控铁摄取与储存的元件。铁的细胞内流和储存都受铁反应元件——铁调节蛋白(iron responsive element-iron regulatory protein,IRE-IRP)系统的调控。当细胞铁水平较低时,IRP与IRE结合。当细胞铁水平升高时,IRP发生构象转移或降解,因而削弱了它们与IRE的相互作用。IRP与IRE的结合对靶蛋白合成具有的抑制或者促进作用,取决于IRP是与目的mRNA的非翻译区(UTR) 的5′端抑或是3′端结合[10-12]。在细胞缺铁时,IRP与TFR1 mRNA3′非翻译区的IRE核苷酸序列相互作用,IRE-IRP相互作用能稳定TFR1 mRNA,并增加TFR1蛋白的合成,以促进低铁条件下更多的铁摄取。与TFR1不同,铁蛋白mRNA的5′非翻译区存在IRE,当细胞内铁浓度降低时,IRE-IRP相互作用,抑制铁蛋白mRNA的翻译,导致铁蛋白减少。相反,当铁在细胞中累积时,IRE-IRP相互作用减少,导致TFR1表达减少,铁蛋白增加[13]。
三、TFR2在铁稳态中的作用及其相关的铁过载
TFR1一直被认为是哺乳动物体内唯一的TF受体。直到1999年,有研究报道了另一种TF受体,命名为TFR2,其一级结构与TFR1相似。TFR2基因通过不同的启动子至少可以转录出两种亚型:全长型TFR2α和较短型TFR2β。TFR2α是一种2型膜蛋白,在肝细胞和红系前体细胞中选择性表达,而TFR2β主要在各种细胞胞质中低水平表达[14]。尽管与TFR1一样同为膜蛋白,全长型TFR2也可以与holo-TF相互作用,但是其基本上不会促进铁的摄取,而是作为全身铁状态的感受器。因为TFR2 mRNA的表达在铁负荷或铁螯合下没有明显的变化,而TFR1在铁负荷下表达减少,在铁螯合存在的情况下表达增加。TFR1通过铁调节蛋白-铁反应元件(IRP-IRE)相互作用受转录后调控,而TFR2不受IRP调控,TFR2 5′和3′UTR区均不包含IRE元件,其表达主要受血浆中holo-TF的影响。血浆holo-TF可显著上调TFR2α,使其更加稳定。此外,TFR2对holo-TF的亲和力明显低于TFR1。这些TFR2表达模式均提示其主要功能不是细胞铁的摄取,而是机体铁感应机制的重要部分[15]。
上文提到,HFE-TFR1-TFR2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激活下游通路调控hepcidin的表达。有研究表明,在体内,影响了HFE与TFR1结合的TFR1突变小鼠体内hepcidin mRNA水平明显高于野生对照组,而影响了TF与TFR1结合的TFR1突变小鼠的表型与HFE基因敲除小鼠的表型类似,表明HFE在调控hepcidin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16]。此外,在体外重组肝细胞过表达TFR1后,并没有比野生对照组hepcidin 的表达升高[17, 18],这些结果提示TFR1水平对hepcidin表达调控的直接影响并不大。此外,有研究指出,仅破坏HFE/TFR1复合物不能调节hepcidin的表达,只有在TF和TFR2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hepcidin mRNA的上调,证明了TF/ TFR2/HFE复合物参与了hepcidin的上调;并猜测在高铁条件下,TFR1结合TF释放出HFE,随后HFE与TFR2和TF结合,该复合体激活下游信号而使hepcidin的表达增加[19]。尽管有研究表明:在体外培养系统中,通过细胞过表达HFE与TFR2,可以检测到HFE与TFR2相互作用,且holo-TF的存在会增强其结合[20]。但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在体外构建的HFE和TFR2稳定共表达体系中,经holo-TF作用后未检测到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且在体内未观察到HFE和TFR2的相互作用[21]。在体内,TFR2和HFE通过独立的途径调节hepcidin,即使在没有功能性TFR2的情况下,过表达HFE的小鼠也会增加hepcidin的表达。此外,在人和小鼠模型中,HFE和TFR2同时缺失比单独缺失都会导致更严重的铁负荷表型[22]。综上所述,TFR2与HFE既可以各自独立调节hepcidin的表达,也可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复合物影响hepcidin水平,具体的调控模式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有研究发现,TFR2与holo-TF的结合可以激活K562细胞以及肝细胞中的ERK信号通路,且ERK通路的活化在holo-TF诱导的hepcidin表达过程中是必需的。Holo-TF激活ERK后,磷酸化Smad1/5/8水平的增加,显示出BMP/HJV通路与ERK1/2通路之间调控hepcidin的交互作用[23]。此外,研究表明HFE和TFR2参与ERK信号转导,并伴有弗林蛋白酶(Fruin)表达的调节。Furin是一种原蛋白转化酶,在hepcidin表达中具有多种作用:它可以将prohepcidin加工成成熟的hepcidin,并参与BMP的成熟,从而诱导hepcidin的表达。它还可以裂解HJV产生可溶性HJV,并对hepcidin的表达发挥抑制作用。 沉默TFR2将导致Fruin表达的抑制,进而通过其对prohepcidin和BMP成熟的调控以及可溶性HJV的产生,进一步调控hepcidin的水平[24]。
上文提到,HFE/TFR2复合物与BMP/HJV复合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有研究采用不同的铁负载模型探讨HFE与TFR2对BMP通路调控进而对不同细胞类型铁沉积做出的反应。在膳食铁负载模型(铁沉积主要在肝实质细胞)中,与正常对照饮食相比,HFE和TFR2双基因敲除小鼠(HFe-/-/TFR2-/-)在高铁饮食刺激下,HAMP基因表达依然上调,但显著低于WT小鼠对高铁饮食刺激的反应。通过对HFE和TFR2单基因缺乏小鼠,即TFR2-/-和HFe-/-小鼠,与HFe-/-/TFR2-/-小鼠的比较,证实TFR2对BMP6以及hepcidin的表达发挥重要调控作用。而在铁-右旋糖酐铁负荷模型(铁沉积主要在肝非实质细胞)中,TFR2-/-、HFe-/-和HFe-/-/TFR2-/-小鼠中BMP6水平与野生型小鼠相当,表明在肝脏非实质细胞中,Bmp6的诱导独立于HFE和TFR2。尽管在铁-右旋糖酐铁负荷后,BMP6水平升高,但在TFR2-/-和HFE-/-/TFR2-/-小鼠中, hepcidin的表达明显低于野生型小鼠。这表明,肝内非实质细胞铁沉积诱导肝细胞内hepcidin表达依赖于TFR2[25]。
综上所述,TFR2对于不同细胞类型中铁沉积作出的贡献不同。铁沉积在肝实质细胞时,TFR2参与了BMP6相关通路的调控,当铁沉积在肝非实质细胞时,TFR2似乎独立于BMP6的诱导,但对肝细胞中hepcidin的诱导起一定的作用。有关TFR2与BMP6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分子机制和模式尚不完全清楚。
已有不同国家报道过TFR2相关的原发性铁过载(Ⅲ型遗传性血色病)病例,症状较经典的HFE突变病例更轻[26-28]。TFR2相关的铁过载主要是通过上述信号通路改变hepcidin的表达而导致的。此外, TFR2基因敲除小鼠或者TFR2突变小鼠,为人类研究Ⅲ型遗传性血色病的分子病理学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动物模型[29-31]。
四、展望
目前,虽然已知TFR2主要是通过以上几条通路调节hepcidin的表达,进而调控全身铁稳态,但是其中各通路及分子之间的关系、调控模式目前尚不完全清楚;TFR2与HFE之间是否始终存在相互作用,两者之间相互独立调控hepcidin的表达是因为建立的模型不同还是存在其他原因,这些问题需要更多不同的体内外模型来研究。关于TFR2对不同肝脏细胞类型铁沉积的反应及其扮演的角色,相关数据我们也是知之甚少;Smad4是否是TFR2下游ERK的靶点等问题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虽然铁摄取并不是TFR2的主要功能,却有研究发现TFR2促进培养细胞中holo-Tf的摄取,TFR2将holo-Tf转运至红系前体细胞的溶酶体以摄取铁[32]。因此,我们缺少TFR2的结构-功能数据来阐明TFR1和TFR2之间的受体功能差异。尽管TFR2在遗传性血色病中的影响不及经典的HFE,但它能够与其他分子相互作用在多条通路起作用,对TFR2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其对hepcidin的调控以及遗传性血色病的分子机制,最终服务于临床。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