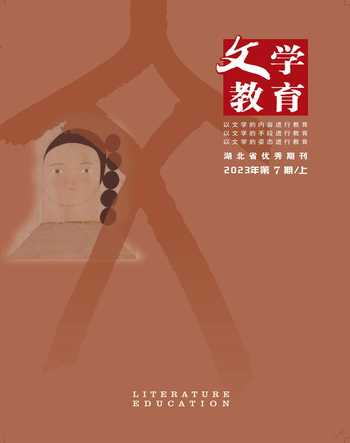论文学史书写的困境和出路
内容摘要:重写文学史是近些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最强势的话语行为之一。时下多元的价值标准体系,无所适从的荒原处境、冲突腾挪的时代氛围更刺激了文学史研究者寻找真正文学史的书写冲动。面对文学史书写的“迷雾重重”,只有破除一元论模式、重写树立人的价值、紧扣“审美性”和“文学性”、避免人为纠葛和奇幻化、夸饰化书写、把握健康理性有效的书写方式,才能为文学史书写找到坚实的基石,从而建构一种“现代性”个人主体的合法性和理论性的文学史。
关键词:文学史 书写 困境
自80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提出后,时至今日,学术界对文学史书写发言的热情似乎依然没有停息。而由这一口号所导致的理论推衍、思维更新、学术观念选择等问题,已经逸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视域,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引发思想的爆炸。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诉求和行为显然隐含着学人们对已有文学史不足之处的清醒认识和作为文学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学术承担。这一口号不早不晚在80年代末期提出,也正是学界对时代召唤的呼应。有研究者指出,“重写文学史”是一场充满浪漫主义想像的重述历史的运动,源于建构现代性个体合法性和理论性的热情和冲动。“重写文学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全景式俯瞰,还在于它呈现了富有意味的解读方式和阐释策略,以及新语境下的历史表达和文化焦虑。诚然,以往进化论等二元论文学史观既破坏了文学史的文学精神又伤及了文学史的历史性。而时下多元的价值标准体系,无所适从的荒原处境、冲突腾挪的时代氛围更刺激了文学史研究者寻找真正文学史的书写冲动。纵观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对文学史的无数次修正、重写、再阐释,无一不是研究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昨天或为迫切或为愤激或为清醒的发言。
虽然对文学史观、文学史价值尺度的把握各有千秋,立意旨趣各有偏重,但似乎研究者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文学史要回到文学本身,回到文学的本质那里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学是一种体现审美价值的审美活动,这是不容质疑的。好的文学史,既要正视过去,还要回应现在,更要前瞻未来。文学史书写经过了在歧途上的艰难跋涉,终于找到了真理之路。但是这并不代表文学史的书写是一片坦途。文学史的书写也只有廓清这一朝圣之路上的层层迷雾,才能为文学史书写找到坚实的基石,不致使文学史的高堂广厦成为空中楼阁。
一.文学史书写要破除“绝对之是”,正视“一家之言”
全景式的再现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轨迹和生态面貌,恐怕是每一个文学史撰写者心中一个巍峨的梦想。确实,从历史和学科的宏观视野出发,建立一种兼容并包的“通观”文学史,破除单一的文学史观和知识结构,走出舒适区和误区,是文学史研究的应有之举,也是文学史研究者的应有职责。无数学人也以可敬的精神和丰盈的学养在为这一梦想而汲汲追求。但是,有一个虽然无奈但是十分真实的学术现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那就是所谓的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类文学的整体形式、全面呈现物质和精神社会的整体原则、描述特定时期的全部面貌和所有规律的历史,其主题和可能性正在消失,而总体历史则是历史发展不可扭转的大趋势。福柯指出,很多研究者对全面历史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是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的:首先,在某一特别设定的时空层的全部事件之间,在人们重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可能建立某种同质的关系系统;其次,假设历史性唯一的同一形式,诸如经济结构、社会稳定性、心理形式、技术习惯等,均处于同一类型的转换中。再次,假设历史是由大的阶段和时期连缀而成,并体现出自身的内聚力原则。而显然,历史的形成不是同一而绝对的。这一方面是由历史本身的吊诡特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历史和历史阅读者的互动关系决定的。文学发生场域中的多种因素相互激荡碰撞,此消彼长,最终的合力才决定了文学史的不同样态。就像布尔迪厄所说,“文学场和权力场或社会场在整体上的同源性规则,大部分文学策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1]。
再者,文学史的形成是文学史料和撰写者本人两种视域的融合。过往、现时历史和其精神文本处于不断的转化过程中。历史事实研究最终要形成对文化的精神阐释和生命意义建构。所谓历史的客观性,其实是建筑在历史经验事实之上的人类生命世界的内在要求和意义追寻。撰写者的历史视野、价值判断、理论视角、审美趣味,乃至个人气质和好恶等都在历史精神文本生成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里,意义追问是始终贯穿着的纯粹关联。在这种时间转化的维度内,新出现的精神建构基于人的现时历史的价值建构意向,现时历史中的精神在直接的自我认识中,在与过去的精神对话的基础上,开启自己的本质的新维度。”[2]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要做的不仅仅是还原文学事实(姑且不论这种还原是否可能),更重要的是对文学史历史事实的精神意义建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任何绝对真实言之凿凿的论断都是颇有问题的,任何书写都是“一家之言”。且不說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学术眼光的偏颇,单单是研究者就以发言的史料也是残缺、片面、真伪待辩、有待进一步发掘的。研究者要穿过历史迷雾真正做到和历史合丝合缝的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尽可能无限接近于历史真实。钱理群先生曾经说过,作为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历史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有“绝对之是”。但我们所编写的历史,没有“绝对之是”。因此我们鼓励在文学史写作上的“一家之言”,并且我们确信这种“一家之言”是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探索历史多样性和个人独立性的必经之路,但我们无法原谅对历史唯我独尊的断言、片面的理解和不容挑战的学术态度。这无疑是由对文学史进行旧的拨乱反正的良好初衷出发,却最终又沿着旧的思维方式走上了另外一条歧途。
二.文学史书写必须回到人的价值,坚持“审美性”、“文学性”与社会性、历史性并重,防范新的审美和文学偏执
囿于意识形态评价的影响,文学研究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是理想主义地认为艺术具有语义和美学上的自由性;二是就历史延续性(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通常被视为是有结构性的)而言对艺术进行一种社会批评性的评价。”[3]曾经,现实主义文学一度是文学正典。这种文学史观以社会发展史作为文学的叙事框架,以现实主义原则和人民性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圭臬。我们不重视人的价值,或者片面地理解这一价值,从本质上说,这是人在文学领域对自身特质的漠视。对人的价值对其生存和历史的依托性,弗洛姆给予了精辟的概括。他说:“价值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生存诸条件之中,因此,正是依靠有关这些条件,亦即关于‘人类处境的知识,我们才得以建立其具有客观效准性的种种价值。显然,这种客观有效性仅当与人的生存相关时才会存在,在人之外则决无所谓价值。”[4]新的文学史写作就是要回到人的全面性、丰富性和多元性的价值向度。在重写文学史的学科实践中,诸多学者尤其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以全新的理论框架和学术思路,冲击和修正了传统文学史的政治一元化书写,在文学史的结构、形态和模式等方面带来新的气象。这种文学史观以人道主义和真善美价值评估体系作为指引,以现代新文化史观梳理文学发展和演变过程,重新整合文学格局和秩序。接受以往文学史盲目服从政治的教训,重写文学史的研究者们对文学史书写似乎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敏感。在具体的书写中,势必要重申“文学性”和“审美性”的重要意义,重估一切价值,以此为依据判定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运动的地位,甚至重新挖掘历史盲区,填补历史空白,形成文学史的新样貌。审美标准被重新确立和拔高,作为对以往“政治标准”的拒斥和反驳,成为一种新标准。在此过程中,“审美”本身容易被片面化和抽象化,其本身的丰富意蕴被稀释,其与社会政治历史的互动共生关系也往往被遮蔽。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强调其文学史的写作要将文学创作和文学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其“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审美的)做出臧否,”[5]从时代场域来看,文学史任何一发展阶段的样态并不是在一个真空里发展起来的,如果将文学的审美性抽离出来看,势必会陷入新的偏执和一元论旧窠。审美标准的产生,如重蹈“政治标准”诞生的覆辙,就会成为新的政治,被绝对化和单一化。而单一视角显然无法涵盖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相反,单一视角无视文学史这一对象的复杂和多义,最终会导致单向度偏狭文学史的产生。如果以文学性和审美性标准回溯文学发展史的话,那些散发人性的光辉的文学往事自然可以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可是那些在当时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具有时代进步性的作家作品有可能被漠视而无缘进入文学史。
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偏颇,文学史书写中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不容忽视。而且正因为历史性和社会性曾经有被片面夸大化的历史,才更应得到更理性化、适度化地重视,而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漠视。对那些曾经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文学史经典的作家作品,即使以文学和审美的眼光审视,不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文学经典,也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独特运行机制,作品背后隐含的权威话语意识,都是我们书写文学史的学术框架和研究基点。以作品为中心,捕捉作家对生活敏锐的感受力和独特的语言表达魅力,提升阅读者对美的鉴赏和感受能力,固然回到了文学史的正途。加之西方新批评学派文本分析的影响,近年来也诞生了一批侧重于文本细读、经典鉴赏的优秀著作。但是,文学史终究还是一门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学科,抛却了历史意识,文学史的整体性和贯通性就无从谈起。我们不能因为以往文学史片面追求整体性走到了板结化、僵滞化的极端,就因此因噎废食,放弃了对文学史的历史追求。诚如文学作品有殊异的叙事方式和角度一样,文学史书写也应该兼顾“大叙事”和“小叙事”。大叙事建构了历史理论和阐释框架,小叙事则从不同角度细温历史事实和关系,抒发史家感悟和真知,赋予历史鲜活具体的面目,拓展研究空间和历史透视的可能性,共同建立一种既宏观综合又多元开放的大历史。
三.文学史书写应警惕欲望的非正常裹挟和妖魔化、奇幻化、夸饰化的媚俗式书写
相对来说,当下的文学史书写相比以往进入了一个空前自由的时期。破除了政治、社会、历史等人为地加负在文学身上的枷锁,文学的步伐变得轻快而恣意。人们似乎急于撕掉文学道貌岸然的面孔,文学终于成为了人们心目中自由的人性释放之地。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知识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共识”的怀疑,这是造成人文学科叙事危机的主要原因。[6]各种各样的话语似乎都堂而皇之地取得了发言的合法性。一个光怪陆离、千姿百态的人性之场被铺陈开来——人们在金钱、女色、权利、地位、伦理中的颠仆浮沉也被穷形尽相、形态各异甚至无节制地表现出来。文学终于摆脱了被历史理性、政治意识形态奴役的历史,可以自由放肆地喘息,可是谁又能说对人性的无限纵容和原宥不是又一次沦为欲望的工具?诚然,在人人皆是欲望主体的时代,文学对欲望的书写和表达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对时代形态和众生百态的敏锐捕捉,是文学反映社会、传达时代精神、挖掘普遍人性的价值书写和表达。这是作为一个文学史书写者不可回避的认知。但是,文学表现不是对欲望的猎奇式展示,甚至对现实欲望的妖魔化、奇幻化、夸饰化,而是应该合于作品主题表现的深切,合于人物形象的饱满,合于作者本身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换言之,欲望不应成为文学的“噱头”,假文学之名,行从俗媚俗之道。文学对欲望的表现,理应建立在对社会的宏大关注和深层思考基础上,瞩目人类命运和处境、人性的复杂和纠葛。而很多对欲望横溢视而不见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者,却将这些都看作人性原有之恶,作家只是反映了這个时代而加以宽宥甚至纵容,甚至大张旗鼓地鼓励,反映出其背后价值评判标准的偏颇和浅薄。这就要求文学史书写者具有科学合理的史观、优秀的鉴赏能力、审慎的思维,去分辩扑朔迷离的文学现象和态势,分析文学热点和浪潮,对所谓文学“时尚”保持清醒的认知,捍卫文学的美学原则和秩序。同时,文学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变现,作为历史书写者,也要与时俱进,关注新媒介、新形式、新现象、新态势,关注文学热点和潮流,以此明晰文学史的多元形态和当下整合。
毋庸置疑,文学史书写的道路,颠仆至今依然任重而道远。但文学史书写和文学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绵延的过程。这不仅因为文学的不断发展变化、文学史料的不断被发掘,而且也因为文学史书写视角的拓展所导致的文学史多幅面孔。从这个层面上说,文学史被不断重写也是这一学科建构的必经之路和应有之义。没有唯一的、唯美的文学史,只有从不同角度、立场、方式建构的多元文学史。所谓“正确”、“权威”、“经典”的文学史,更多是我们的一种历史想象和希冀。但只要我们能把握文学史书写的健康、理性、有效的方式,那么,文学史书写所呈现出的纷纭话语言说和多家之言林立就不能说是一种多元混乱,而是一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探索。
参考文献
[1]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48.
[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3.
[3]约·舒尔特·萨斯.文学评价[A].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384.
[4]马斯洛等主编.胡万福等译.人类价值新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2.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
[6]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北京:三联书店,1997:11-15.
(作者介绍:张霞,文学博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