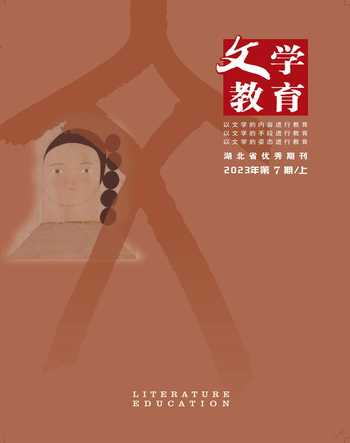重构自我之旅:《长日将尽》的空间政治解读
杜婷婷
内容摘要:《长日将尽》是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小说将空间、权力与身份建构交互融合,具有明显的空间政治特征。该小说中英国贵族管家史蒂文斯为期六天的乡村之行,这也是其重构自我之旅。史蒂文斯在达林顿府,乡村旅途和小镇码头三地的空间转换中,解构了过去三十五年权力规训下异化的“旧我”,在长日将尽时重建焕然的“新我”。本文将用空间理论分析小说的空间政治特征,解读在空间转换中史蒂文斯重构自我的心路历程,揭示其对昔日帝国的释怀与告别。
关键词:石黑一雄 《长日将尽》 空间政治 权力空间
《长日将尽》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第三部作品,也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小说以英国贵族管家史蒂文斯的视角讲述了其在新主人的准许下开启六天的乡村旅行,在达林顿府、乡村旅途和小镇码头三地的空间转换中穿插过去三十五年在达林顿府的往事回忆,最终在长日将尽时分释怀过去拥抱新生活。史蒂文斯的乡村之行也是其重构自我之旅,在达林顿府封闭空间的权力规训下,史蒂文斯已精神异化,在乡村旅途的流动空间中史蒂文斯逐渐解构“旧我”,最终在长日将尽的小镇码头实现“新我”的重建。作品的叙事呈现空间性结构,通过空间的转变推动整个叙事过程,小说将空间、权力与身份交互融合,具有明显的空间政治特征。本文旨在用空间理论探究小说的空间政治特征,解读在空间转换中史蒂文斯的自我重构,揭示在后帝国时期英国子民对昔日荣光的怀旧和身份建构问题,以期体会这首帝国挽歌背后石黑一雄的深刻见解和创作特色。
一.达林顿府——权力规训下的自我异化
达林顿府是英国政客交际的重要场所,内部的空间分布等级分明。在这个封闭的表征空间,史蒂文斯被权力的空间表征所规训,呈现完全顺应型的空间实践,麻木刻板,导致自我异化,思想和行为禁锢在陈旧虚幻的英式尊严之中。
“表征空间指真正意义上的物理生活空间,是居住者与使用者的空间”[1]。在小说中,史蒂文斯服务三十五年之久的达林顿府可以被视为其生活的表征空间,是所有生活实践的活动场所。“空间表征可以理解为对客观空间的主观再现”[2],是主流社会或强势群体所构想的主导空间秩序。达林顿府不止是英国贵族庄园,更是英国的政治轴心,英帝国尊贵的象征,体现了权力的空间表征,极具政治色彩。正如文中所说,“这世界就是个轮子,以这些豪门巨宅为轴心而转动,由他们做出的那些重大决策向外辐射到所有围着他们转的人”[3]。在达林顿府的内部,空间的分布井然有序:庄园内分为主楼和侧楼,主楼列有供主客人使用的起居室、书房、客厅等设施,宽敞高级;侧楼则是佣人的仆役厢房,逼仄而简陋。史蒂文斯的居所在达林顿府被边缘化,就像一间封闭的权力牢笼,将史蒂文斯的身体和精神囚禁在这狭小的空间。权力“把空间当作最为重要的政治工具使用来确保对空间的控制,并保持严格的等级、整体的同质性和各部分的隔离”[4]。空间的施展依赖于权力的运作,达林顿府邸的空间分配渗透着权力的空间表征。达林顿府成为令人窒息的权力空间,俨然成为福柯笔下的新型监狱,一台权力规训机器。达林顿府的权力规训通过空间渗透到史蒂文斯的身体和精神领域,促使其自我异化。
依据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表征空间”的居住者在“空间表征”的影响下,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对的空间实践,即“顺应型的空间实践”和“挑战型的空间实践”[5]。史蒂文斯的空间实践是顺应型的,史蒂文斯在达林顿府的规训下内化了权力空间表征,其空间实践完全顺从庄园的政治意识形态。三十五年来,史蒂文斯时刻以“伟大管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言谈举止到衣着打扮,都以绅士为楷模, 保持着一贯的刻板与矜持,压抑克制自己的情感,甚至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三十五年的管家生活将史蒂文斯规训为一个异化的劳动者,一个毫无精神需求的工作机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6],认为当劳动背离人的本质时,劳动的过程便沦为劳动者丧失主体身份的过程。“只有那些合乎美的规律、合乎人的目的的创造性实践才指向人的自我实现;反之,那些导致人的实存与本质相背离的行为就是异化劳动。[7]”史蒂文斯为了维持心中的“尊严”放弃照顾临终的父亲,认为这是职业生涯中“节制感情”的一次成功考验;为了贯彻职业操守,极力克制自己对肯顿小姐的感情,直到她嫁为他人才怅然若失。史蒂文斯活在帝国荣耀和绅士尊严的幻想之中,逐渐成为一个失去正常感情需求的异化自我。
“权力遍布于空间...权力已然将其领域扩展到了每一个人的骨髓之中,扩展到了意识的根源,扩展到了隐匿在主体性的褶皱下的‘特殊空间里”[8]。生活在达林顿府窒息的权力空间,史蒂文斯的空间实践完全服从其意识形态,俨然被规训成一个麻木的异化自我,沦落成為达林顿府这个权力牢笼的忠实囚徒。
二.乡村旅途——流动空间中的旧我解体
从达林顿府的封闭空间到流动的乡村风光,伴随着空间的移动,史蒂文斯也逐渐脱离异化的旧我。乡村旅途的表征空间呈流动开放性,呈现自由多元的的空间表征。史蒂文斯的空间实践也开始打破原有的刻板模式,促成新我的构建。
空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渗透了各种意识形态,影响着主体对于自我的认知。对于史蒂文斯来说,想要打碎旧我,首先便要逃离达林顿府这个权力空间,才能为构建新我创造契机。在新主人的建议下,史蒂文斯驱车开启六天的乡村旅行,也踏上了自我蜕变之路。对于三十五年未曾离开达林顿府的史蒂文斯来说,从熟知空间到未知空间的转换使得其心情矛盾复杂,不安中夹杂着些许期待。叙事学家普林斯提出,“物理空间可以影射人物的心理空间,并强调空间变换可以推动小说情节发展”[9]。伴随着空间的流动,越来越多的风景和人物涌入视野,史蒂文斯的思维也随之发生转变。绵延无际的乡村美景使得史蒂文斯心情开阔明朗起来,一扫旅途伊始的恐慌不安。史蒂文斯随着旅途进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空间,感受到来自普通人民的淳朴善良和思想碰撞,促使其开始反思自我。无论是热心帮助修理汽车的退休兵,还是在村里让他免费留宿的泰勒夫妇,亦或是旅店里围着吧台的当地居民,他们无不透露着善良淳朴,轻松自在的处世态度,这与史蒂文斯在达林顿府小心谨慎的空间氛围截然不同。这种别样的空间实践感染着史蒂文斯,成为他解放天性找回自我的催化剂。
史蒂文斯解构旧我的关键一步,就是在莫斯科姆村这一异质空间,打破了多年恪守的认知——对尊严的刻板理解和对爵爷的盲目愚忠,从而脱离精神异化的旧我。莫斯科姆村充满人间烟火气息,不像达林顿府等级森严,这为史蒂文斯构成了一个异质空间,这“既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空间,也是一种相对于现实空间的虚幻空间,具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偏离性等特征”[10]。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史蒂文斯认为尊严在于一位管家在任何时刻都能坚守其职业生命的能力。在莫斯科姆村,史蒂文斯聆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村民哈里认为尊严并非上流社会的特权,而是每位公民都可以凭自身努力争取得到的。哈里的见解使得史蒂文斯幡然惊醒,自己对“尊严”的想法太过狭隘,不过是在权力规训下的刻板执念。再者,史蒂文斯在服务于爵爷时,执行完全顺从型的空间实践,对爵爷持有绝对的忠诚甚至是盲从。不管是爵爺开除两名无辜的犹太女仆还是在政治决策不当时,史蒂文斯都选择自我欺骗,相信爵爷所有言行都是出于内心深处的正义和善良。在和村民的交流中,村民认为爵爷是战争爆发的祸因之一,这使得史蒂文斯开始正视自我,反思多年来的盲目顺从,打碎了对昔日帝国荣光的滤镜,实现思想上的重塑。
以空间流变为内核的乡村旅行不仅解放了史蒂文斯被禁锢的身体,而且预示着从一个既定的权力政治空间向一个开放的有利于自我建构的空间的转换。在空间流动中,史蒂文斯实现了主体思想的蜕变,绵延开阔的风光和随性自由的村民使得史蒂文斯在思想上跳出了权力规训的樊笼,超越了过去狭隘愚忠的思维,走向清醒鲜活的新我。
三.小镇码头——长日将尽时的新我重构
旅途的最后,在小镇码头这个开放的第三空间,史蒂文斯终于卸下面具,决定告别旧我,拥抱全新的生活。在这里,史蒂文斯坐观落日残光,感慨于时代的变化,释怀了与肯顿小姐的感情,在和退休男仆敞开心扉的交谈后与过去达成和解,实现了对自我的重新建构。
旅途接近尾声,史蒂文斯终于来到多年惦念的地方——韦茅斯小镇,西蒙斯太太也在《英格兰奇景》中称其为能让游客多日游兴不减的小镇,而小镇码头的落日将尽华灯初上之时正是其最美的时刻。“第三空间概念具有列斐伏尔始终要赋予社会空间的多重含义,它既是一个区别于其他空间的空间,又是超越所有空间的混合物”[8]。小镇码头正是小说中的第三空间,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在这个开阔的空间里,没有封闭空间的窒息感,权力与等级表征也在这里了无踪影。史蒂文斯在这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身心完全放松下来,学会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背靠长椅观赏海上的落日奇景,执行回归自我的空间实践。“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1]。眼前的落日黄昏就如同辉煌不再的英帝国,终究要像消失在海平面上一般退出现代世界的舞台。紧接着华灯亮起,人群欢呼,隐喻时代俨然转变,美国的法拉戴先生买下达林顿府,美国也已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等强国。眼前的一切都在提醒史蒂文斯时代已经变化,昔日的帝国同达林顿府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也不应该沉迷于过去固步自封,应该适应时代变化,改变自我。
开阔的空间和欢乐的氛围让史蒂文斯的思绪也随之放空,恣意飘散。史蒂文斯回忆起和肯顿小姐两日前的会面,反省了过去麻木的自我,对这段感情做出最后的告别。在与肯顿小姐的交谈后,史蒂文斯意识到自己为了恪守心中所谓的尊严而错过了一份珍贵的感情,如今已无法挽回。坐在长椅上,史蒂文斯终于释怀了这份感情,决定正视自己的内心,不再遮遮掩掩。“当空间成为无法掌控、捉摸不定的场域时,空间就超越了权力的掌控范围,于是自由、对话与共存就成为了可能”[11]。开放自由的空间让史蒂文斯卸下防备,敞开心扉与身旁的退休男仆聊天。年近七旬的退休男仆是不同时空里的另一个史蒂文斯,也是史蒂文斯重构自我的重要引路人,为史蒂文斯未来的晚年生活指引方向。他们工作经历相同,不同的是,退休男仆早已告别过去,开始学会享受生活,惬意自在。听闻史蒂文斯的心声后,他劝说史蒂文斯傍晚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史蒂文斯也应该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傍晚。这番话点醒了史蒂文斯,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他始终带着“尊严”的面具压抑自我,从没有为自己活过。“我的确应该不要再这么频繁地回顾往事,而应该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把我剩余的这段人生尽量过好”[3]。他终于明白频频地回首过往没有意义,人总是要向前看的。此时的史蒂文斯已经决定向旧我挥手告别,去享受生活的快乐,感知人间喜乐冷暖,顺应自己的内心而活。史蒂文斯转过身去,认真观察眼前的人来人往,家人团聚,朋友结群,热闹攀谈共同欢呼,自己也被这人间温情所打动,他的血液也再次鲜活沸腾起来,是重获新生的史蒂文斯。
小镇码头这个开放的第三空间摆脱了压抑的权力意识形态,史蒂文斯在这里反思了过去的自我,展望无限美好的未来,在这长日将尽时拥抱了全新的自我。此时的他彻底改变了在达林顿府时的空间实践,决定顺从内心,享受属于自己的美丽黄昏。
在小说《长日将尽》中,叙事随着空间的转换层层递进,极具空间政治特色,主人公史蒂文斯也在空间的流变中实现自我重构。在达林顿府的三十五年,在权力空间的长期规训下,史蒂文斯成为异化的劳动者失去自我。在乡村旅途的流动空间中,在开阔风景和形色人群的感染下,史蒂文斯压抑的自我也随之释放,开始自我反思。在开放的小镇码头,史蒂文斯终于勇敢地告别过去,卸下虚伪面纱,拥抱全新的自我。石黑一雄将空间、权力和人物的身份构建巧妙地钩织结合,勾勒出在时代巨变下小人物的成长流变,折射出对国际形势的深度见解,同时也为读者自身成长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不愧为世界文学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Lefebvre,Hen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Blackwell,1991:39,154.
[2]王桃花,林武凯.归来的“娜拉”:《湖滨旅店》的空间解读[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5):120-126.
[3]石黑一雄.长日将尽[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152,317.
[4]Shields.R.Lefebvre,Love and Stru
ggle:Spatial Dialectics.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9:169.
[5]王桃花,罗海燕.温特森《正常就好,何必快乐》的空间解读[J].湖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2020,23(6):49-55.
[6]周可.异化的扬弃与共产主义: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7(1):169.
[7]黄大军.西方空间理论的美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78.
[8]E.W.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9,79.
[9]Prince,Gerald.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M].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88.
[10]唐小霞.空间视阈下《觉醒》中艾德娜的形象新解[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6):62-68.
[11]胡蝶.空间视角下的薇拉·凯瑟《我们的一员》[J].戏剧之家,2019(6):197-198.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