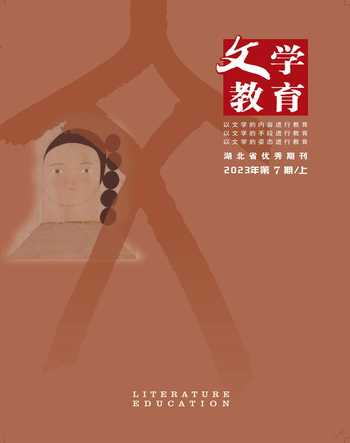施蛰存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与欲望书写
周唯
内容摘要: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在小说中挖掘和揭示人类本能欲望的复杂与幽深,而这一欲望主题的表达与作者塑造的空间形式密不可分。本文将以施蛰存小说中的街区、闺阁、乡野三种典型空间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与欲望书写之间的关联,兼谈这种表达对于小说美学风格的影响,以期提供有益的启发。
关键词:施蛰存 空间形式 欲望书写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1930年代创作的《梅雨之夕》、《将军的头》、《善女人行品》等小说集,表现出了自觉的文体创新意识,开创了一种独具实验技巧的小说形态。施蛰存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在小说中挖掘主人公的性心理和潜意识,揭示人类本能欲望的复杂与幽深,而这一欲望主题的表达与作者塑造的空间形式密不可分,无论是繁华绚烂的都市街区,幽闭寂寥的女子闺阁,还是空旷神秘的乡野山林,皆与小说中人物欲望的释放、压抑或变形构成了丰富的互动关系。本文将以施蛰存在小说中塑造的此三种典型空间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与人物欲望表达之间的关联,兼谈这种书写对于施蛰存小说美学风格的影响,以期提供有益的启发。
一.都市街区:欲望的激发
在施蛰存的小说中,都市空间呈现的典型代表是街区,人在街区中的流连与行走,既介入和占有了都市,也开拓和丰富了这一空间环境,使静态的空间成为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动态记忆;与此同时,借由街区漫游这一行动,小说中的人物得以观看都市景观,并经由后者生产和塑造情感与欲望,而都市街区的敞开性、匿名性也使得欲望的自由表达成为可能。
施蛰存小说中“都市漫游”的典型作品是《春阳》和《梅雨之夕》。《春阳》描绘了一个从昆山来到上海的中年妇女内心的情欲萌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流动、敞开的现代都市空间(上海),暂时取代了她日常生活着的那个充满“熟人”的稳定、封闭的小城镇空间(昆山)[1]。跟随婵阿姨“街区漫游”的行踪和视线,我们看到了绸缎、瓷器、化妆品、丝袜、糖果饼干等商品,继而见到了崭新的汽车、光芒闪耀的玻璃橱、摩天大厦、华丽的菜馆等都市景观,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中指出,消费的逻辑包括了强烈的视觉性维度,视觉作为“欲望媒介”刺激了人们的商品崇拜和想拥有的渴望[2],借由街区漫游时触目可及的商品景观,婵阿姨的欲望被激发了,“为什么到上海来不玩一玩呢?”“何必如此刻苦呢?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3]当占有商品和物质享受的欲望被刺激后,婵阿姨往常的步行路线便重新改道了,她去到了南京路、冠生园等以前不曾去过的地方,在行走的过程中,她压抑的爱欲也在这个春阳普照的上海启动,身体感知发生了从“孱弱”、“不济”到“身上又恢复了一种好象久已消失了的精力”的变化,看到街区上轻盈美丽的男女,她甚至开始“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着她在马路上走,手挽着手。”[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大都市的现代化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激发了她们的物欲和爱欲,而她们也因消费能力而在消费文化盛行的都市上海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都市街区成为了一个富有张力的表征空间。
在施蛰存的“意识流”名篇《梅雨之夕》中,一位男性也在街区漫游的过程中,发生了对女性身体的欲望审视。小说中的“我”喜爱雨中漫步,一次雨后,“我”从江西路南口走到四川路桥,不觉行至天潼路口、文监师路,与《春阳》中因温热的天气而微微出汗的婵阿姨不同,“我”的身体欲望复苏的象征性暗示是双脚因雨水的打湿而“觉得湿漉漉的”,就在此时,“我”遇见了一个从电车上走下来的姑娘,并不自觉地提出撑伞送她回家,这也再一次应证了理查慈·桑内特的经典定义——城市是“一个陌生人很有可能在此相遇的人类聚居地”[5]。“我”和女子共同迈向了都市的种种具象:商店、公共汽车、城市的天际线、办公大楼以及被霓虹灯照亮的夜空,在这一过程中,“我”潜意识里压抑的思绪和欲望也开始像雨水一样流溢:女子让“我”想起了自己初恋的少女,“我”甚至幻想她会不会是故意来同我接近,“我”凝视女子的眼光也充满了欲望的气息:她被雨淋湿的薄薄的绸衣、圆润的手臂,她鬓边颊上被潮润的风吹过来的粉香,小说中还有这样毫不避讳的“观看”:“一阵微风,将她的衣缘吹起,飘漾在身后。她扭过脸去避对面吹来的风,闭着眼睛,有些娇媚。”[6]“她屡次旋转身去,侧立着,避免这轻薄的雨之侵袭她的前胸。”[7]男性眼光的加入使得对女性体态的观察呈现出一丝亵玩的色调,这也契合了“我”被激发的欲望的流动和呈现。
《梅雨之夕》以大段的内心独白著称,而这种百无禁忌的宣泄式自陈所发生的条件,正存在于都市街区的漫游之中,正如西美尔所言:当人们在街区这一敞开的空间中相遇时,“人们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匿名的,也就不会有责任感”[8],短暂的相遇因此尤其容易诱使人们暂时忘却自我克制,进行率直而大胆的自我表达。由此,都市街区这一空间为人物情感和欲望的被刺激、被呈现并最终得以释放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二.闺阁空间:欲望的幽闭
施蛰存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而闺阁正是女性行动的主要场所之一。闺阁往往具有封闭性、私密性的特征,充满了神秘的氛围和情调,在施蛰存的笔下,闺阁空间不仅仅是单纯的空间概念,它也包含了幽居闺阁的女性日常的生活状态,隐喻了特定空间中女性的情感变化。从空间呈现与人物欲望的表达关系来看,这一空间幽闭了人物的欲望,并使小说具备了一种暧昧缠绵的美学色彩。
在施蛰存的早期小说《周夫人》中,中年的“我”忆起了自己还不谙世事时与邻居一位青年寡妇周夫人的偶然相遇,周夫人因为“我”与其逝去丈夫的相像而突然对“我”产生了爱恋,她带“我”走入了她的房间——作者并未对房间的装饰和陈设着墨过多,但其中有一个意象十分突出,即“四壁悬挂着的镜屏”。镜子具有自我观照和审视的作用,挂在孀居的青年妇人房间中,更添其孤寂自怜之感,而“屏”往往用以分割空间,表明了闺阁空间层层封闭的特征。在周夫人的眼中,“我”的长相酷似周先生,这引起了她压抑已久的情欲,小说借由“我”的视角看到了周夫人的媚态和温柔:“我睁着一双无知的眼瞧着她的严肃而整齐的美脸,她却报我以一瞥流转得如电光一般迅速而刺人的,含着不尽的深心的眼波。天啊!女人的媚态是怎样的,在那时我是懂得了,虽然我还没有认识那个字。”[9]周夫人难以自持的欲望最终被压抑了下去,小说写到“她走到窗边把窗推开了两扇,便倚在窗棂上望夜天的新月。”[10]开窗之举看似是对狭深的闺阁空间的突破,实则是另一种延申,户外空間依旧冷清幽深,夜天的新月更添寂寞惆怅,可视作“谢娘心曲”的“外物化”呈现,可见这重远境并未释放闺中人的欲望和愁闷,反而更唤起了与外界隔绝的孤独之感,作者将远近结合、内外相辅的两重空间进行叠加,打破了审美空间的单一性,增加了空间的张力,也深化了女性主人公的内在情感。
《薄暮的舞女》中素雯的心境变化也是依托闺阁这一空间进行呈现的。小说开头,我们得知素雯决定结束从前放荡的舞女生活,为此,她改造了自己的房间,此处颇具象征意味的表述是床单的变化,“她的眼睛忏悔似地凝住在新换上去的纯白无垢的床巾上。贞洁代替了邪淫,在那里初次地辉耀着庄严的光芒”[11]在与舞厅经理的通话中,素雯自陈“我愿意被人家牢笼在一个房间里,我愿意我的东西从此以后是属于一个主人的,我愿意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惟一的人能时常进来,”[12]可以见出,房间正是素雯本人或是其身体的象征,以往可以随意进出的房间代表“邪淫”,暗指身体和欲望的开放,而改造后的房间将独属一人,带有封闭性和归属性,意味着她将回归“纯洁”和欲望的守持。然而,素雯寄予期待的“良人”子平最终破产,女主人公对稳定与归属的期待就此破灭,“现在我看我的房间虽然改变了样式,可还是一个寄宿舍。”[13]舞女将不得不再度敞开闺阁,复归风尘。在这一过程中,闺阁的敞开抑或封闭,贞洁抑或邪淫,皆隐喻了女性身体与欲望的开合,展现出舞女身不由己的处境,也曲折地呈现了女性的隐秘情感和精神挣扎。
从闺阁空间延伸开去,女性在成为妻子之后所归属的“家庭空间”也呈现出了欲望的幽闭性质,施蛰存擅长书写都市男性在婚后对家庭的厌倦和疲惫,而作为妻子的女性则感到婚姻生活的寂寞、焦虑和欲望压抑。《狮子座流星》中的丈夫只关心金钱和股票,对生活麻木冷漠,最终卓夫人只能通过一场梦发泄无法纾解的情欲与内心的渴望;《残秋的下弦月》书写了卧病在床的妻子屡次打断丈夫正在进行的小说创作,只是为了和他重温两人相恋时的情景,而丈夫却不能体会妻子的感伤与渴求,最终妻子只能在病榻上独自看月光,“而不知过了多少时光,丈夫觉得冷了。他起来关了窗,下了窗帘,明了灯。”[14]这一举动意味着妻子的欲求再次被封闭。
整体看来,在施蛰存的小说中,闺阁往往是女子欲望甚或自身主体性的象征,闺阁的封闭意味着欲望的压抑和幽闭,而对闺阁这一空间形态的运用,也体现了施蛰存在古典意蕴中蕴含现代情绪的美学风格与写作特征。
三.乡野山林:欲望的变形
除描写现代都市外,施蛰存还有不少以乡土为背景的小说,在他后来创作的一系列被冠以“怪诞”和“哥特”之名的作品中,故事的背景常常设置于乡野和山林,在这一空间形态里,人物反常的心理现象和迷惘的精神状态频频出现,呈现出欲望的压抑、扭曲和变形。
例如,小说《魔道》中的“我”因“都市病”前去乡下朋友陈君家度假,当看到窗外自然的绿野和隆起的土埠时,“我”幻想里面会走出一个紧裹白绸、魅惑动人的王妃木乃伊,而这一欲望又实则与恐惧交织在一起,因为“我”在火车上曾将一位对座的普通老妇人幻异成妖婆,从此如坠魔道,觉得她如影随形,王妃木乃伊便也有可能“是这妖妇的化身”;当“我”来到古潭边散步,又依稀在竹林浣衣女身后见到“怪妇人的背影”,后来甚至将陈夫人也视作“善于变幻的妖妇”,而与此同时,“我”对陈夫人的审视又充满了色情凝视的味道:“今天,一眼看了她紧束着幻白色的轻绸的纤细的胴体,袒露着的手臂,和刳得很低的领圈,她的涂着胭脂的嘴唇给黄色的灯光照得略带枯萎的颜色,我不懂她是不是故意穿了这样的衣服来诱引我的。”[15]
“我”性格怯弱多疑、易于受惊而又耽于幻想,这种惊恐与幻想中又实则夹杂着被压抑的丰富欲望,正如施蛰存所言:“在《魔道》这一篇中,我运用的是各种官感的错觉,潜意识和意识的交织,有一部分的性心理的觉醒。”[16]主人公性的节制使力比多没有得以满足,一方面亟需发泄,另一方面又无法升华,使得性焦虑在恐惧的刺激下历经了扭曲和变形,与怪力乱神等形态复合在了一起,而并非如《春阳》、《梅雨之夕》那样自然舒展。
《夜叉》讲述的故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描写了神经衰弱患者卞士明在乡间休养时见到一位白衣女子,从此对之魂牵梦绕,为了摒除欲念,他将这位女子视作夜叉的化身,可即便夜叉令人惊恐,欲望的焦灼仍促使主人公不顾危险,追踪而去,以至最后竟因精神错乱而失手杀人。《夜叉》延续了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以“艳遇”为核心的传统模式,具有浓厚的聊斋气息。既风情万种又充满危险的女妖正是男性潜在欲望的投射,这种欲望隐蔽、克制、压抑,同时夹杂着恐惧和焦虑,急切寻求突破而不得,最终以诡秘妖异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乡野山林之所以成为这些惊悚怪诞的故事的背景,一方面是因为乡野往往是都市人出于疗养、休假等目的逃离城市而前往的去处,但在逃离的过程中,他们也将都市生活的压抑所带来的“神经症”和“焦虑症”投射在乡土之上,由此,乡土不再是理想的桃花源,却成为了城市梦魔的延续和妖魅丛生的“异界”,让渴望在乡土中寻找灵魂慰藉的都市人的幻想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乡野山林的空旷神秘也刺激了主人公的想象,例如《魔道》对陈君家周围环境的描写:“站在门檐下回看四野,黑黝黝地一堆一堆的草木在摇动了。”[17]又如《夜叉》中的乡野景观:“四面看黛色的群山好象堵成了一道魔壁,把我包围在一个表面上极美丽,而实在是极恐怖的魔宫中的迷园里。”[18]这一诡异的氛围易于刺激和制造人们惊恐不安的幻觉,同时也形成了阴森诡秘的美学效果。乡野山林背景下的“奇遇”故事既与中国传统的志怪小说具有美学上的承续,又与爱伦·坡《厄舍府的倒塌》、《黑猫》等作品有互相对照之处,施蛰存将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渗透融合进中国传统的题材,“使梦幻文学日益心理化从而挽救古代志怪小说”[19],展现出“传统质”与“现代性”相互融合碰撞的特征。
综上所述,施蛰存小说中的空间形态往往具有独特的表征意义和美学特征,本文从都市街區对于欲望的刺激,闺阁空间之于欲望的幽闭,以及乡野山林背景下欲望的变形扭曲三个维度,探讨了空间形式与小说中人物的欲望表达之间的关联,兼谈其对于施蛰存小说美学风格的影响,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对施蛰存小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宋晓萍.欲望、货币和现代都市空间——重读施蛰存的《春阳》[J].文艺理论研究.2015,35(04):104.
[2]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03-304.
[3][4][6][7][9][10][11][12][13][14][15][17][18]施蛰存.施蛰存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07-184.
[5]王爱松.施蛰存的三篇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空间[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4),138.
[8]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42.
[16]杨迎平.论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J].文艺理论研究,2004(01):15.
[19]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95.
(作者单位:广州南方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