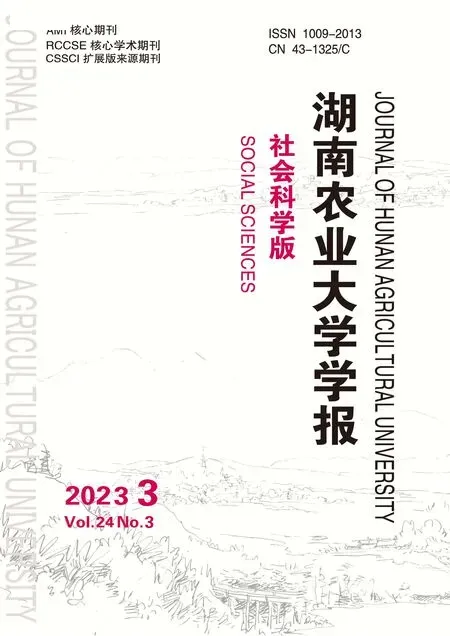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研究
任怡多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研究
任怡多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赋予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享有继承权能,不仅是当前中央政策文件精神的一致导向,还是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应当重点规范的内容。然而,目前在学理层面、地方实践和司法裁判中,均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存有争议。鉴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满足立法上对遗产的特征要求,且《民法典》继承编为其纳入遗产范围预留了制度空间,故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应当作为遗产继承。在此基础上,通过明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属于身份性权利、不承载社会保障功能、不同于其他涉农权利以及并非成员专属权益,对否认其遗产能力的观点进行辩驳,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充分证成。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遗产
为切实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央政策文件倡导赋予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权能,允许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死亡后,由其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其生前持有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为《集体产权改革意见》)明确规定,“保障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继承权,制定农民持有集体资产股份继承的办法。”原农业部等三部门出台的《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为《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指出,“重点探索具备法定继承人资格但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员继承集体资产股份的规则,以及继承人与集体的关系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区性的影响。”在中央的政策导向下,各地纷纷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丰厚的改革成果①。然而,伴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出现反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声音,这极大地阻碍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现实进程,影响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权能的顺利实现。为此,本文在全面把握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理论争议与实践分歧的基础上,从正面论证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具备遗产能力,并从反面辩驳否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可以继承的观点,从而充分证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具有可继承性,为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一、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现实争议
纵观我国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发展现状,目前在学理层面、地方实践和司法角度,都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存有争议。为此,需要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厘清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现实争议,展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争辩全貌,以全面审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正当性问题。
(一)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学理争鸣
关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是否能够继承,学者们展开了热议,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三种主流学说,其核心观点及主要理由归纳如下:
第一,肯定说。该学说主张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能够继承,应当纳入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由其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其中,房绍坤教授认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是一种财产性权益,应当遵循既有改革的政策逻辑,允许其通过合法的方式予以继承[1]。高海教授强调,继承权是集体资产股权权能的核心内容,应当充分认识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特别性,并基于其特性实现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规范表达[2]。刘云生教授指出,尽管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并非一项纯财产性权利,但其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故应允许该权利通过继承的方式得以延续[3]。王玉梅教授主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应禁止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继承,集体资产股权继承依据有关继承法律法规进行[4]。
第二,否定说。该学说主张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能继承,否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遗产能力,质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行为的合法性,代表性学者为韩松教授。其主要缘由在于,一方面,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从集体取得财产的资格性权利,是成员资格在集体收益分配上的具体化和形式化,本质上属于一种身份,不应当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5]。另一方面,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来自集体公有制下的成员资格,是实现集体给予成员社会保障的具体方式,不是成员个人的私有财产资格,无法纳入遗产之列[6]。因而,赋予成员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权能,存在将集体资产通过股份化达到私法之趋向。
第三,折中说。主张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需要根据继承人的不同身份作出区别处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继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而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则不能继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例如,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政策法规处方志权处长指出,为防止外部资本侵吞集体资产,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区性,应当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限定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7]。再如,宋志红教授强调,允许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会导致集体资产股权持有的非均等性和非封闭性[8],有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基于公有制逻辑所应体现的均等性和封闭性[9]。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实践纷争
尽管在中央政策文件精神的导向下,各地区均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持肯定态度,全然认可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并积极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改革实践。但是,通过进一步走访座谈发现,广大农民并非一致认可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行为的正当性,其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持有不同观点。结合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全部2745份有效问卷中,1912位受访农民认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具有继承权能,应当允许继承人依法继承集体资产股权;159位受访农民主张,鉴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涉农权利不能继承,故作为新型农村财产权利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亦不得继承;674位受访农民指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是成员享有的专属权益,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继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具备成员身份的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法继承②。据此,从农民意愿的角度看,目前实践中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存在纷争,分别形成了认可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否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和根据继承人的不同身份判定是否具有可继承性三种不同观点。
(三)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裁判分歧
为全面展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纠纷的司法裁判现状,本文利用“聚法案例”检索分析工具进行司法案例的全文检索,分别设置不同的检索条件进行了三次样本选取,最终筛选出有效样本5份③。通过分析上述司法裁判文书,发现在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问题上,不同法院之间存在着差异化的理解和认识。其中,部分法院以《集体产权改革意见》为政策依据,支持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行为,强调保障每一位继承人的正当权益④;部分法院认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属于人合性股份,伴随主体资格的丧失而自动灭失,故其不会发生继承问题⑤;另有部分法院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自身特性出发,主张其应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专属享有,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获得集体资产股权,当然亦不能继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⑥。由此可见,对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问题,司法机关尚未达成共识,其在立基于不同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三种迥然不同的裁判路径,分别对应学理上的“肯定说”“否定说”及“折中说”三种主流学说。
综上,关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能否继承,不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农民意愿中,抑或是在司法裁判下,均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目前主要形成了允许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不允许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以及根据继承人的不同身份决定是否赋予继承权能的三种现实样态。
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应当作为遗产继承
面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现实争议,当前亟须对其展开法理分析,明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正当性依据。为此,意欲证成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具有可继承性,应当依据《民法典》继承编的相关规定,充分证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具备遗产能力。
(一)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符合遗产的全部特征
《民法典》继承编第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这表明遗产具有如下五项特征:第一,时间上的限定性,即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的财产状况来确定遗产范围;第二,内容上的财产性和包括性,即遗产只能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并且作为遗产的财产包括财产性权利、财产性义务和财产性利益;第三,范围上的限定性,即遗产只能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第四,性质上的合法性,即遗产只能是自然人的合法财产;第五,可让与性,即遗产应当是能够转由他人承受的财产[10]。由此,只有全部满足上述五项特征,才能成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依法予以继承。
为此,意欲证成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具有可继承性,需要对其符合遗产的各项特征展开充分论证:
其一,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符合遗产在时间上的限定性。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死亡之前,其作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权利主体,依法享有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死亡时,其所遗留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转变为遗产,成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据此,当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作为遗产时,其既不是被继承人死亡之前依法享有的财产,也不是被继承人死亡之后遗留财产的增值,而是被继承人死亡之时合法遗留的财产。
其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符合遗产在内容上的财产性和包括性。从内容上看,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仅包括股利分配请求权、股份优先受让权等财产性权利,还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表决权、监督权等经营管理权利。着眼于团体法的视域之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行使表决权等经营管理权利的方式,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控制和管理,从而确保其财产性权利得以有效实现。表决权等实为实现自身财产权益之经营管理权利,而非承载人格或身份利益的人身性权利。据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本质上属于财产权⑦,代表着成员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所享有的财产权益[11]。
其三,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符合遗产在范围上的限定性。鉴于“农户”并非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不具有民事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12],且其内涵始终模糊不清,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自然人,具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民事主体地位,且其法律内涵明晰规范[13],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权利主体,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个人所有。据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属于被继承人个人所有,并不为其他人所共同享有,能够纳入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
其四,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符合遗产在性质上的合法性。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基于农村集体资产的折股量化而形成,是在对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将其量化为股份,再以确定的标准平等地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据成员身份无偿取得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无需另行支付任何对价。据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配置股权的合法方式而取得,属于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
其五,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符合遗产的可让与性。《集体产权改革意见》明确要求,不断激活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赋予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有偿退出等流转权能,发挥集体资产股权量化的最大效用,显现农村集体资产的潜在市场价值[8]。据此,允许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予以质押、有偿退出,表明可以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转让给他人。亦即,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具有人身专属性,是一项可以流转的财产权利,能够转由继承人予以承继。
综上,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符合《民法典》继承编所规定的遗产的特征,满足立法上对遗产的特征要求,具备作为遗产的各项条件,应当作为遗产予以继承。
(二)《民法典》继承编为其预留了制度空间
在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上,《民法典》继承编摈弃《继承法》“正面概括+列举”的模式,采用“正面概括+反面排除”的立法模式,以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契合财产权利范围日益扩大的现实需求。具言之,一方面,《民法典》继承编充分认识到,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财产的范围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现代社会的民事权利实乃一个开放的体系。因而,若遗产范围沿用《继承法》列举的方式,难免会存在一定的立法漏洞,进而增加日后修改法律的可能,有损于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为此,《民法典》继承编尊重财产权利扩张的现代趋势,采用正面概括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将个人的合法财产尽可能地纳入遗产范围。另一方面,《民法典》继承编特别考虑到,全国各地区的社会习惯存在较大差异,若仅对遗产范围作出正面规定,恐怕无法涵盖某些例外情形。因而,为确保立法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满足当前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民法典》继承编采用反面排除遗产范围的立法模式,将不属于个人遗产的部分予以反向排除[15]。
据此,针对遗产的范围,《民法典》继承编秉持开放的体系思维,对新型财产权利展现充分的包容性,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被纳入遗产范围预留了制度空间。亦即,尽管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属于一项新型民事权利,但《民法典》继承编采用的“正面概括”立法模式,体现了财产权利开放的立法理念,完全能够将其纳入遗产范围之中。由此,只要充分证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属于反面排除的范围,即可认定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正当性。具体来讲,不得继承的遗产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根据法律规定不得继承的遗产。由于现行法律规定并未禁止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作为遗产予以继承,反而存在大量政策性规定倡导赋予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权能,故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继承的遗产。第二类是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这主要是指与被继承人人身有关的专属性权利[16],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显然既不是一项人身性权利,不与被继承人的人身紧密相关,而更多地彰显出财产权益;也不是一项专属性权利,不由被继承人所专属享有,而可以转由继承人承继。因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既非依照法律规定不得继承的遗产,亦非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当然不属于《民法典》继承编反面排除的遗产范围。
综上,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是基于国家政策性规定建构而成的一项新型财产权利,将其列入遗产范围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契合《民法典》继承编的立法理念。
三、对否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可继承性的辩驳
在正面论证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具有可继承性的基础上,还须对否认其遗产能力的观点进行辩驳,以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充分证成。为此,笔者针对当前理论和实践中的反对理由,展开一一论述:
(一)对该权利属身份性质的辩驳
相比遵循资本所有制的理论进路,对基于出资财产所有权对价转化逻辑产生的一般工商企业股权来讲,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由农村集体资产的折股量化而形成,始终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下运行,具有取得的身份性和配置的无偿性等特性[17]。由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与“身份”的联系更紧密,而与“财产”的联系则较疏远,其属于身份性权利的呼声愈发强烈。然而,这仅代表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在初次取得时,应当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依据,严格遵循股权分配标准的身份性,并不意味着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本身是一项身份性权利。亦即,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初次取得的身份性不等于该权利本身的身份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于成员身份获得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代表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属于身份性权利。
同时,权利本身的身份性决定了该权利不能流转,一项身份性权利无法进行流转,而权利取得的身份性仅决定哪些人可以取得该权利,并不意味着该权利不能流转[18]。申言之,若以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属于身份权为由反对股权继承,那么在此逻辑体系之下,亦应当对集体资产股权质押、有偿退出等流转行为持否定态度。但是,在前述持“否定说”观点的论述中,普遍赞同赋予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和有偿退出权能。那么,其在倡导开展质押、有偿退出等股权流转行为的同时,却以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系资格权为由,否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行为的正当性。这恐怕存有体系矛盾之嫌,并不能自圆其说。为此,鉴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能够通过质押、有偿退出等方式予以流转,可以推知该权利本身并不是一项身份性权利,仅是在其初次取得时要坚持成员身份性。
据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不是一项身份性权利,而是承载成员所享财产权益的财产性权利。以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系身份性权利为由,否定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行为正当性的观点,因不具有理论依据而无法予以成立。
(二)对承载社会保障功能的辩驳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享有的三项重要权利,关乎每一位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涉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然而,从现有法律和政策规定来看,并非三种权利皆承载着社会保障功能,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承载社会保障功能,而作为集体收益分配权实现形式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肩负社会保障的职能⑧。
具体来讲,一方面,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尽管在实行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之后,农地产权的经济属性凸显,农地的财产价值被不断激活,但其始终坚持保障农民不失去对土地控制的法律底线,确保农民获得持久稳定的生活来源[19]。如此设计之根源在于,农村耕地仍然承担着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关系到农村村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水平紧密相关。据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关乎广大农民的生计,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20]。另一方面,就宅基地使用权而言,《民法典》第362条承袭了《物权法》第152条的规定,未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人相应的收益权能,其旨在强调宅基地使用权是一项用来解决农民基本居住问题的权利,财产增值功能并非其所应发挥的制度效能,而居住保障功能才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核心职能[21]。同时,现有法律及政策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流转等作出了严格限制,如《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一户一宅”原则⑨、《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的禁止向城镇居民转让宅基地等⑩,这些都充分表明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典型的社会福利属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成员提供的居住权益保障。据此,宅基地使用权关乎广大农民的生活,亦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22]。然而,就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而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集体产权改革意见》亦强调,着力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可见,赋予农民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意在增加农民额外的经济收入,实现农民更多的财产权益。据此,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肩负保障农民最基本生活需要的使命不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承载着财产增值功能,旨在确保每一位成员参与集体收益分配,并真正分享到农村集体资产收益[23],从而不断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其并不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退一步讲,即便是认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承载着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那么,允许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也不必然意味着阻碍农村社会保障。其主要理由在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对于具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发挥的保障功能,除非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有偿退出,否则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就一直由该成员享有,并且仅能由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因此,如果说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发挥了社会保障功能,其保障范围也仅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继承人通常也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继承人继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并不必然导致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脱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此,若农村集体资产收益仍然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分享,那么,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便并未消失。
据此,有别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并不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以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承载社会保障功能为由,否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可继承性的观点,因缺乏合法性依据而无法予以成立。
(三)对效仿其他涉农权利的辩驳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成为继承权的客体,无法作为遗产而被继承[10]。但是,因应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与其他涉农权利的继承有所不同,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不能予以继承的理由,无法成为否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可继承性的依据。申言之,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都属于涉农财产权利,但其产生于不同的制度背景之下,奉行不同的价值理念、权能构造和运行规则,故在判断其是否具有可继承性的问题上,不得采取类比推理的方法加以适用。
具体来讲,一方面,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理由不能类推适用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问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⑪。当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承包地仍由该农户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经营;而当农户家庭中的成员全部死亡导致该户整体消亡时,承包地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予以收回,并另行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农户家庭[24]。立法如此设计的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农村处于人多地少的背景之下[25],为有效缓解人地矛盾,避免出现符合条件的人无地可包或者一人承包数份土地的不合理现象,谨防侵害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的合法权益,因而否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26]。然而,由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存在上述现实问题,故其并不能同样适用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当然亦不能据此否定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另一方面,严禁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缘由亦不得类推适用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实行“一户一宅”的原则,具有典型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属性,其旨在保障农村村民的基本居住权益[27]。因而,为防止“一户多宅”的现象发生,避免宅基地资源被并不真正需要的人占用,现行法律规则回归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创设目的,不允许将宅基地使用权予以继承[28]。然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在份额享有上不存在“一人一股”的严格限制,其亦不存在占用土地资源等农村集体资产的情形,故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
据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同样作为涉农财产权利,却与二者遵循全然不同的制度逻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涉农财产权利不能继承为由,否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可继承性的观点,因缺乏正当性依据而无法成立。
(四)对其系成员专属权益的辩驳
与一般工商企业股权基于股东的出资作为对价而获得有所不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来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具体实现形式,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获得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前提和基础。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作为分配依据,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原始取得农村集体资产股权[29]。但是,这仅代表在初始分配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时,需要遵循成员身份的股权配置标准,并不意味着继受取得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亦应遵照上述规则。易言之,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取得上的身份性不代表其转让、继承时也具有身份性。财产权取得上的身份性不应当成为限制其转让性、继承性的正当理由。否则,势必会导致所取得财产权的权能和价值受到限制和贬损[30]。
事实上,《集体产权改革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等一系列中央政策文件已经清晰地指出,应当积极引入市场化机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深化集体经济市场化改革。可见,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固化走向流动[31]。由此,应当凸显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财产属性,不断提高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流动性[32],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对外流转[33],从而激活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市场价值[34]。相应地,应当允许不具备成员身份的社会主体通过质押、继承、有偿退出等股权流转行为,以继受取得的方式获得农村集体资产股权[1]。为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专属权益,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够基于股权流转行为继受取得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并可以此享受相应的财产权益[35]。
据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专属权益,其亦可流转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由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以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系成员专属权益为由,限制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予以继承的观点,因不具有合理依据而无法成立。
四、结语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基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而产生,是我国政策文件赋予广大农民的一项民事权利。通过将农村集体资产以股份的形式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保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促使亿万农民参与集体资产收益分配,真正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作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一项重要权能,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权能直接涉及股权的代际传承,能否实现集体资产股权的继承权能关乎广大农民的切实利益。为此,本文从正向论证与反向辩驳两个角度出发,充分证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具有可继承性,为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权能扫清理论障碍。至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具体操作路径,则有待未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作出相应的法律制度设计。
① 例如,北京市大兴区2065人发生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继承金额17795万元;上海市闵行区6494人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继承金额31175万元;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生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240宗,股权数达1242.3股。
② 笔者及所在团队于2019—2022年先后深入湖北、湖南、黑龙江、山东、重庆、四川、辽宁、广东、河南、甘肃、上海、福建、山西、云南、宁夏、浙江等16省份34个县(市、区)的118个村(社区)开展实地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2792份,收回有效问卷2745份。
③ 本文分析的裁判文书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截止时间限定为2022年12月7日。第一次检索以“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和“继承”为关键词在“全文”部分进行检索,获得37份裁判文书,筛选出有效样本4份;第二次检索以“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和“继承”为关键词在“全文”部分进行检索,获得11份裁判文书,筛选出有效样本0份;第三次检索以“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为关键词在“全文”部分进行检索,获得128份裁判文书,筛选出有效样本2份。其中,在第三次检索得到的2份样本中,有1份样本与第一次检索获得的样本重合。因此,通过进行三次案例检索,共获得有效样本5份。
④ 参见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13民终6806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行初9号行政裁定书、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9165号民事判决书。
⑤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4337号民事判决书。
⑥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21)浙0212民初18033号民事判决书。
⑦ 关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性质的论证思路,受益于冯果教授对于公司股权本质属性的观点的启发。
⑧ 伴随着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农村集体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由此,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成为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实现形式。
⑨ 参见《土地管理法》第62条。
⑩ 参见《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十)中的规定。
⑪《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第54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
[1] 房绍坤,宋天骐.“化外为内”与“以特为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制的方法论建构[J].探索与争鸣,2022(1):119-128,179.
[2] 高海.集体资产股份继承的特别性与规范表达——基于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22(2):112-121,131.
[3] 刘云生.农村土地股权制改革:现实表达与法律应对[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89.
[4] 王玉梅.从农民到股民——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基本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183.
[5] 韩松.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J].法学家,2014(2):36-41.
[6] 韩松.农民集体成员的集体资产股份权[J].法学研究,2022(3):3-20.
[7] 方志权,蔡蔚.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与继承的理论研究和地方探索[J].上海农村经济,2018(4):27-30.
[8] 宋志红.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关系重构[J].法学研究,2022(3):39-56.
[9] 宋志红.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J].中国法学,2021(3):164-185.
[10] 房绍坤.中国民法典评注继承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13-15.
[11] 房绍坤,宋天骐.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的特别性[J].山东社会科学,2022(2):45-55.
[12] 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76.
[13] 房绍坤,任怡多.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纠纷的司法实证研究——基于129份裁判文书的整理分析[J].河北法学,2022(4):2-17.
[14] 房绍坤,任怡多.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成员股的设置[J].学习与探索,2022(3):73-82.
[15]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495-496.
[16] 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19.
[17] 王洪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物权法底线”[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42-50.
[18] 刘凯湘.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J].北方法学,2014(2):20-28.
[19] 蔡立东,姜楠.农地三权分置的法实现[J].中国社会科学,2017(5):102-122,207.
[20] 陈甦.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机制及其阐释辨证[J].清华法学,2016(3):57-71.
[21]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评注物权编(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602.
[22] 郑尚元.宅基地使用权性质及农民居住权利之保障[J].中国法学,2014(2):142-157.
[23] 房绍坤,袁晓燕.关于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几点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70-81.
[24] 刘保玉,李运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探析[J].北方法学,2014(2):5-14.
[25]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899-900.
[26] 高圣平,王天雁,吴昭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167.
[27] 高飞.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否定论——一个解释论的立场[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4):125-134.
[28] 张建文,李红玲.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取得之否定——宅基地“法定租赁权”的解释路径[J].河北法学,2016(12):28-39.
[29] 任怡多.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管理模式[J].求索,2022(3):162-170.
[30] 管洪彦,房绍坤.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法理解构与制度重构[J].学习与实践,2018(11):76-85.
[31] 方志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殊法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J].科学发展,2018(1):94-105.
[32] 丁关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若干重要问题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64-75.
[33] 张保红.农民集体财产股份化的制度构造[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1):187-197,239.
[34] 房绍坤.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法治保障进路[J].求索,2020(5):14-23.
[35] 吴昭军.基于资产类型区分的集体资产股权法律性质界定与权能设计[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8):92-98.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bility of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equity
REN Yiduo
(Law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Granting farmers the right to inherit the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equity is not only the consistent orientation in the spirit of the current central policy documents, but also a key element that should be regulated in the futur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law. However, the inheritability of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equity is currently disputed in academic theory, local practice and judicial judgmen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equity meets the legislative requirement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ritage, and the inheritance part of the Civil Code has reserved institutional space for its inclusion in the scope of heritage,so the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equity should be inherited as heritage. On this basis, by clarifying that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equity does not belong to identity rights, does not carry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agriculture-related rights and is not exclusive rights of members, the view that denies its inheritance capacity is refuted,and sufficient proof of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equity inheritance is achieved.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equity; inheritanc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law; member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heritage
10.13331/j.cnki.jhau(ss).2023.03.009
D922.3;D922.5
A
1009–2013(2023)03–0075–08
2022-03-2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ZD202)
任怡多(1994—),女,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农业农村法治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法学、农村产权法治。
责任编辑:黄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