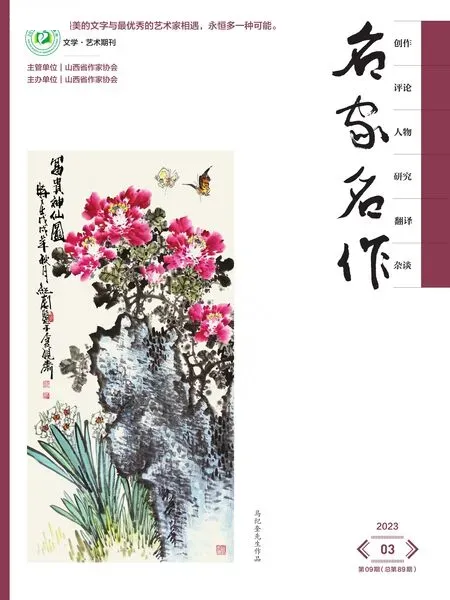赛博朋克影视中泛义肢化伦理浅析
潘乃维
赛博朋克(Cyberpunk),是“控制论”“神经机械学”与“朋克”的结合词。在赛博朋克影视文学作品中,不久的将来,现实和虚拟现实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人们借助脑机接口,实现侵入性的人体改造。在一个电子科技、人机互联高度发展的反乌托邦式未来社会,在后现代主义的赛博朋克式的数码幻境、泛滥的倾入性的人体改造和控制中,凸显了后人类主义的主体性焦虑。分别从泛义肢化的起源、困境、启示三个层次分析其伦理困境。
一、起源
亚当·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中对赛博朋克做如下阐释:它既是一种文体,是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又极具创造力的构成部分,又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构成。[1]纵观科幻文化发展史,赛博朋克这一文化类型超越了文本本体的框架,对不同层面的文化要素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发展出广域的泛义肢化现象。以下分别从赛博朋克的泛义肢化、泛义肢化的社会背景、侵入性人体改造的初衷三个方面阐述其起源。
(一)赛博朋克的泛义肢化
在谈及后人类主义时,“赛博格”与“赛博朋克”是两个重要概念。赛博朋克是文学影视艺术类型。而作为单词“控制论的”(cybernetic)与“有机生物体”(organism)的混合体,赛博格一词有效地唤起了人们在说明这种形象时所带有的特征:电子设备的熔断,带有生物形象的机器或机器人,所以赛博格也成为指代在未来社会中,人与机器融合后所形成的产物的代名词。[2]
譬如,在《战斗天使·阿丽塔》中,整个城市的人几乎全民进入侵入式人体改造的境遇,各式各样的脑机接口和机械义肢层出不穷,而赛博朋克影视中泛义肢化的机械属性义肢类型即是如此,针对不同工作领域需要的、可替换的机械义肢。
同时,义肢不仅具备机械属性,还具备信息属性。如在《攻壳机动队》中的巴特,一双高度信息集成的电子眼,在实现视力感知替换功用的同时,还具有多种人机互联、AI 分析等电子辅助功能。在赛博朋克影视中,侵入式的人体改造已全民泛化。
(二)泛义肢化的社会背景
赛博朋克影视的社会背景设定有着鲜明的后人类主义和反乌托邦色彩,即社会被顶层势力控制,这种社会层面的控制运转多由巨型资本、政府或人工智能所执掌。鉴于人类被信息技术侵占,如在《战斗天使·阿丽塔》中,整个社会被诺瓦财团所控制,不仅使社会控制更有人体控制技术,比如电影后期诺瓦能够通过脑机技术“附体”维克多。
赛博朋克世界是当代城市空间的极端形式,肮脏、危险、污染和黑暗在整个底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而上层城市空间的精英阶级则有享有高度智能现代化的干净、舒适、安全的生存空间。这种由科技垄断造就的两极反差的社会构成,无疑是人们对于未来后人类主义的主体性焦虑投影。
(三)侵入性人体改造的初衷
倾入性人体改造的初衷,最初是用于帮助残障人士恢复正常生理功能。随着脑机接口的发展和神经机械学的涌现,这一想法变得更有可能性。在设定于未来的赛博空间中,这种倾入性的人体改造就变得更加泛化,以至于生理正常的人为获得更高强度的身体机能,突破肉身局限而去做机械式替换性的身体改造,形成了赛博朋克影视中的泛义肢化现象。
正如哈维拉所强调,“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是重构我们身体的重要工具”[3]。脑机接口是一项将大脑活动产生的信号转化为不涉及周围神经和肌肉的技术,并利用这些信号来控制外部设备。[4]得益于脑机互联技术和神经机械学的高度发展,倾入性人体改造变得稀松平常,通过脑机接口从而来实现对机械义肢的控制。
在赛博朋克影视中,这种由控制而发展来的“赛博格”最终也越来越脱离仅仅帮助残障人群的机能修复初衷,而是跟随高度发展的信息机械水平,超出了其原有的范域,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泛义肢化的现象。
二、困境
在赛博朋克里,随着广域的泛义肢化现象蔓延,在便捷生活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伦理困境。一是由“赛博”式控制论带来的自由控制问题;二是在机体替换时自身主体性界限的模糊;三是由脑机互联带来的虚拟感官的达成下现实与虚拟的精神毒品问题。
(一)控制论与神经机械学的隐患
基于赛博朋克的控制论色彩,这种控制的影响随着义肢化的泛化也跟着广域泛化了。依附高度发展的神经机械学和信息技术,赛博格们也面临因控制论和信息互联而带来的潜在隐患,分别为机械控制论隐患和神经控制论隐患。
在赛博朋克影视里,机械是极易被干扰和控制的,尤其在信息网络技术相当发达的赛博朋克世界里,此为机械控制论的隐患。基于赛博空间是一个复杂的信息互联系统,加上高度的脑机互联,这种隐私的窥探便延展为对自由的控制,以至于衍生至心灵无隐私的境遇,此为神经控制论的隐患。随着科技发展和资本膨胀,尤其是对网络终端掌有者而言,更是造成了公众权利与自由的极端集中。这种控制极易被政府、财团和犯罪黑客势力所利用。
在《战斗天使·阿丽塔》中,格鲁就被诺瓦施以过行为控制,从而进行犯罪活动,也正影射了赛博朋克中的控制论隐患。同样,在《全面回忆》中,道格在被追杀途中也曾一度因掌中电话的漏洞被持续追踪。这些隐私的窥伺,其背后都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控制与自由的剥夺。这正是赛博朋克中,控制论与神经机械学的隐患所在。
(二)人的主体性的自我界限
人的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得以确立。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第一次将“理性”的人作为主体,康德进而提出了“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黑格尔指出主体性的四个表征:“被释放了的个人主义,批判的权利,行动自主性,理念化的哲学本身。”[5]因此,人的自我包含和自我控制,即自由与否成为人的主体性的重要衡量指标。自尼采以“上帝已死”作为现代主义分野以来,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身份忧虑伴随着科技迅猛的发展,也在赛博朋克中凸显出来。
在被“控制论”统领的赛博朋克世界,在身心面临巨大被控隐患时,自我存在的主体性又何以得到显现?当意识被控制抑或窥探,每个想法都受到信息干扰和诱导的时候,不同于观看广告时的被动信息诱导,而是基于脑机接口的意识电流层面的主动诱导,更有甚之的全面意识控制,在这种无法做到“我思”之时,也便无法凸显标志人的主体性的“我在”了。
在赛博朋克的泛义肢化中,人在获得了因侵入性身体改造而得以大幅提升的身体机能后,也面临着自身主体性的自我界限日益模糊的困境。尤其是在《攻壳机动队》中,少校因为只剩下大脑,其他身体来自机械制造,那么她如何去认知自己的存在?究竟哪个是我?身上义肢还是工厂里所有可能将被替换选用的下个义肢?推而进之,当大脑的功用也能被全部量化转换、信息化传输后,是否也有辗转于机械化替换脑的个体之间,抑或是活跃于信息空间的自我?如《超能查派》和《露茜》中的意识信息化转换。
诚然,在赛博朋克的泛义肢化背景下,人的主体性面临着庞杂的挑战,人我界限和物我界限将进一步模糊,社会伦理秩序也将面对空前考验。
(三)现实与虚拟的精神毒品
赛博格的广域泛化带来的另一个困境就是虚拟与现实的精神毒品。在赛博朋克中,这种现实真实与信息虚拟的边界日益模糊,带给人的无疑是精神毒品式的现实困境。
首先,这种虚拟来自两种类型。一是依附脑机接口的感官模拟,从而实现感受刺激的精神毒品。如《未来战警》中,玛姬使用的机械义肢上感官模拟的电子毒品,通过脑机接口将感官信号直接传输给大脑,实现精神沉迷的目的。二是依附赛博空间的虚拟现实式精神毒品。借助于脑机互联的信息技术,赛博空间高度真实,带来的虚拟现实的界限模糊,甚至是沉溺信息幻境,而产生对现实的厌恶逃避行为。如《全面回忆》中借助脑机互联技术,辉忆公司提供的虚拟幻境造梦业务,《头号玩家》中沉溺于赛博空间虚拟幻境的社会群体。
在《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中,错杂在霓虹灯影中的后现代主义都市景观和工业遗迹的具象描绘着光怪陆离的赛博朋克世界,虚拟影像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与现实交叉,在《银翼杀手》中更有利用科技投影直接生成的拟真人。虚拟现实和脑机互联的高度发展,日渐模糊甚至消弭了现实真实与网络虚拟的边界。
三、启示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反乌托邦式未来社会,后现代主义的赛博朋克式画风下,依附于脑机互联的数码幻境、泛滥的倾入性的人体改造,都指向了后人类主义对人类自身的拷问与焦虑。分别从自由的剥夺与隐私的入侵、人的主体性的指称与替换、伦理审视下的进化方向三个方面予以启示分析。
(一)自由的剥夺与隐私的入侵
后现代主义视域下失衡的社会矛盾,加上浓郁“赛博”式控制论色彩,泛义肢化带来了强烈的自由剥夺与隐私入侵的问题,人的权利与自由变得不堪一击。这也是脑机互联技术、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必然考验。如何去面临这场入侵,如何去正视这场考验,成为伦理反思中所需思考的问题。
在非赛博朋克式的现实世界中,自由与隐私的问题并没有如此复杂。社会面更多是外加施与性的政策法规及舆论宣传,而非赛博空间中高度的信息交互和全方位的机械控制及神经控制。通常,现实世界的控制难以侵夺人主体意识上的自由,而赛博朋克世界里的“赛博”式控制则是完完全全将人推向行尸走肉的边缘。
不难看出,在赛博朋克世界中,这种对人的彻头彻尾的控制是对人的自身权利让步于专政权力的过程。回看赛博朋克影视中“赛博”式控制的悲剧情感,也不免对技术进步产生反思。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借鉴赛博朋克影视中泛义肢化的伦理叩问,则是要求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要重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跨越脑机技术时的慎重性。
(二)人的主体性的指称与替换
人的主体性问题是贯穿在前瞻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当人的主体性的指称发生改变与替换时,个体自身能否接受?人类本身能否接受?这能否决定甚至改写自我本身存在的价值,抑或为直接否定自身的存在?这一系列问题向来都是未来类影视文学作品中带来的反思和拷问。
在赛博朋克世界的泛义肢化构象下,如何去界定人自身的主体性界限是一种相当棘手的伦理困境。因为在赛博朋克世界里,脑机互联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超出了当下科技带给我们的材料范围,也突破了当今社会常识所能认识和预料的限度。譬如,在财产的置换和抵当方面,把机械臂拆下来抵当置换与现实世界的抵当,二者是完全不可比拟的。
换言之,当人的身体成为单纯的财产,而失去其本有的自我存在属性的时候,亦即是说,当具身性向离身性偏离时,人自我存在的认识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梅洛·庞蒂在“具身主体性”中提到“为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既不把人视为离身的心智,也不把人看作复杂的机器,而是视人为活生生的、积极的创造物,其主体性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物质性互动而实现的”[6]。具身性强调认识过程中身体的核心作用,而在赛博朋克的泛义肢化现象中,因为义肢可替换的永久性和持续性,身体的概念也跟着模糊和泛化了。人将不再是具身性个体,而是转向离身性,这种离身性将超越人类认知的主体边界。
(三)伦理审视下的进化方向
在赛博朋克影视中,泛义肢化的出现是对科技发展的畅想与思考。赛博朋克电影作为一种科幻电影的类型,同时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投射的是对科技高速发展水平下后人类主义的主体性身份焦虑。
后人类主义是人类面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情形下的一种自我否定,人类一方面依助于强大的科技所带来的生活便利,另一方面又恐惧科技对人类的反噬。这种两难正是伦理审视下的科技发展困境。
后人类将人类和智能机器、肉体和信息技术糅合在一起,人类中心主义被后人类解构,因而后人类主义试图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绝对局限问题。除了解构整体性以及拓展人类潜能外,后人类的转向过程并没有走向终结,而是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在海勒的后人类主义观点中,身体是一种能够书写以及重写后人类形成的隐喻。她提到“后人类的观点认为,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7]
然而,对于赛博朋克泛义肢化的构想也不必悲观。因为无论后人类以何种形式到来,其最终都会导向人类对于自我认知的反思之中。影视中各式各样的“赛博格”也正是人类自身因为不同需要而制造的人机融合体。其问题关键就是人类自身在创造过程中充当“造物主”的角色,从人类自然生成过程来看,这与人类本身的自然属性相违背,其必然引发对自身认知的主体性焦虑。但因其从具身性向离身性的转向,大大超出了人类认知的主体边界,也在促使我们再一次把眼光转到人的本质上来,再次反思存在的意义,警醒着科技发展的慎重和人的本质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