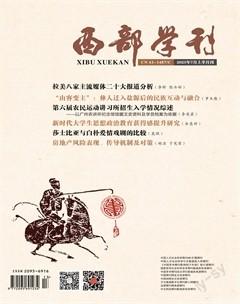斯摩棱斯克档案与西方苏联学研究
摘要:作为西方苏联学中的“极权主义流派”所主要依据的档案文献,斯摩棱斯克档案详细记录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共产党在斯摩棱斯克省等的机构设置、政治活动以及对当地民众生活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摩棱斯克档案受到多方重视,先后辗转于德国纳粹、苏联共产党、美国陆军部与美国情报局之手,造成了部分内容的遗失。最终,由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芬索德牵头,首次对斯摩棱斯克档案进行系统研究与利用。芬索德利用残存的斯摩棱斯克档案,重点关注苏联民众的日常生活,以此丰富了其对“苏联权力”和苏联政治体制的研究。斯摩棱斯克档案不仅对芬索德等学者反思和创新“极权主义流派”的相关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持,而且不断启发着此后西方苏联学领域“修正主义流派”的研究。
关键词:斯摩棱斯克档案;梅因·芬索德;西方苏联学;“极权主义流派”;“修正主义流派”
中图分类号:D73/77;K512.53;K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3-0083-07
Smolensk Archive and the Western Sovietology
Yin Qinqi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Smolensk archive, the main source of archival document on which the totalitarian school of Western Sovietology is based, contains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s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the Smolensk provinc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s well as of its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live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Smolensk Archive came under the scrutiny of many parties and passed through the hands of the German Nazis,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SR, the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and the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some of its contents. In the end, Merle Fainsod,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led the first systematic study and exploitation of them. By utilizing the remaining Smolensk archive, Merle Fainsod enriched his study of “Soviet power” and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by focusing on the daily lives of Soviet citizens. The Smolensk archive has not only provided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Merle Fainsod and other scholars to reflect on and innovate the theories of the totalitarian school, but also continues to inspire the study of the revisionist school in Western Sovietology.
Keywords: Smolensk Archive; Merle Fainsod; Western Sovietology; the totalitarian school; the revisionist school
西方學者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展开系统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形成了“极权主义流派”。对“极权主义流派”的发展史及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议的国内外研究不胜枚举。传统观点认为,“极权主义”理论的单一性和极端性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的脆弱性。因为要高屋建瓴,即以一个变量解读大量复杂且长期的社会现象,不可能面面俱到。“理论的层次越高,对现实的描述就越粗糙。”[1]但事实上,“极权主义流派”的相关理论与研究不仅没有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反而与政治学、社会学中的一些非苏联学理论进行结合,逐步完成了自身的赓续,由此不断启迪着西方苏联学学者的研究,并作用于欧美诸国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如今,苏联已然“作古”,苏联学亦不再是“显学”,但是西方苏联学中的“极权主义流派”却并未偃旗息鼓。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不仅需要跨学科的兼收并蓄与交流融合,更需要基于自身学科特性的、细致文献考证基础上的严谨史实作为“理论之基”。综观“极权主义流派”的诞生与发展,学者们对于斯摩棱斯克档案(Smolensk Archive)的不同解读,正是这“千变万化”的“筋骨”之所在。作为二十世纪唯一一批到达西方的苏联共产党档案,现如今保存在华盛顿州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斯摩棱斯克档案就像一面格外瞩目的明镜,启迪着每位对它感兴趣的研究者,透过其管窥和解释历史、关照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殷鉴现实与未来。
一、斯摩棱斯克档案的主要内容
斯摩棱斯克被“俄罗斯历史之父”内斯特(Nestor)称之为“通往罗斯的钥匙与大门”,这座边境城市也正如其档案所反映的那样,作为第聂伯河畔四面楚歌的前沿哨所,在历史上遭受过诸多征服者的蹂躏。苏联的斯摩棱斯克省成立于1937年,作为从华沙经明斯克到莫斯科铁路干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不仅是战略要地,也以富饶的土地而闻名。二战前夕斯摩棱斯克省的领土范围更为辽阔,一度包括战后的卡卢加省和布良斯克省等地。该省的人口超过650万,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重镇。
从1943年纳粹德国维尔纽斯“羅森伯格特别行动队”(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以下简称ERR)负责整理斯摩棱斯克档案的罗伯特·冯·伯格博士(Dr.Robert Von Berg)呈递给政府的报告来看,斯摩棱斯克档案中与苏联共产党相关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五个部分:“1.斯摩棱斯克省(中央当局)的记录,包括:a.斯摩棱斯克省的政府记录;b.斯摩棱斯克/西部在1920—1930年苏波战争期间的记录;c.斯摩棱斯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记录;d.斯摩棱斯克的共产党治理委员会的记录。2.斯摩棱斯克、卡卢加和普斯科夫等省的地方组织记录,包括:a.全省各个地区的共产党委员会的记录。3.1929—1937年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各级机关党组织的记录,包括:a.斯摩棱斯克省委员会的记录;b.斯摩棱斯克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记录;c.斯摩棱斯克省共产党治理委员会的记录。4.斯摩棱斯克省各地区组织的记录:斯摩棱斯克省和4个区级委员会的相关记录。5.苏联共产党的机构和组织的各种记录,包括:a.《真理报》的编辑记录;b.高级预备党课的记录;c.苏联共产党改造群众课程研究所的记录;d.拖拉机站管理部门的记录;e.西部铁路管理部门的记录;f.64个步兵团中的199个政治部门的记录。”[2]33-44
1943年德国纳粹档案局的专业人士初步将约17 000份文献材料进行整理归纳后,斯摩棱斯克档案的重要价值进一步凸显。这些资料涉及苏联地方一级共产党的机构与组织、职能和统治情况,主要包括:斯摩棱斯克省共产党委员会(1919—1928年);西部委员会(1929—1934年);群众宣传部(1929—1934年);干部处(1929—1934年);文化宣传处(1930—1936年);卫生委员会(1929—1936年);普通科(1931—1935年);组织部(1930—1933年);共产党的特殊部门(1931年,1935—1936年);工业部(1930—1935年);交通运输部(1930—1933年,1936年);秘书处(1930年,1932—1935年);农业部(1933—1935年);苏联贸易部(1932—1935年);共青团委员会(1929—1933年)等[2]36-37。总体而言,对于任何试图了解并攻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斯摩棱斯克档案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工具,苏联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传来时,苏联当局随即下令从预期的战争前线疏散指定的档案文献记录,以避免其落入敌人手中:“至少在许多地区,都被要求销毁那些不可能撤离的最危险的文件。”共产党机关的近期记录自然被列为最优先的行列。但是,由于纳粹军队入侵之快速突然,苏联方面缺乏既定的疏散计划和足够的运输设施、当局与社会对战争普遍缺乏准备,因此并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够执行这样的命令,疏散他们所有的高优先级文件。斯摩棱斯克的相关档案被德国纳粹截获的原因就在于此。当斯摩棱斯克在1943年9月25日被苏联红军解放之时,它一半以上的档案已经被纳粹转移,其他的文献资料也在战火中被摧毁。
二、德国纳粹对斯摩棱斯克档案的重视
德国纳粹出于从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方面“向东进军”、反共反苏反犹的考量,对于斯摩棱斯克档案的保护、转移、整理和研究可谓“煞费苦心”。在这方面,由纳粹政权意识形态方面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指挥的“罗森伯格特别行动队”发挥了重要保护作用,该组织在德国档案学家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Mommsen)的带领下对斯摩棱斯克档案进行了初步整理[2]16-18。如今馆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斯摩棱斯克档案”并非全部来自斯摩棱斯克,也包括纳粹从基辅或其他地方没收的文献资料。
入侵苏联还未开始,EER就已经为这场政治意识形态战争做好了准备。ERR于1939年分别在巴伐利亚和柏林建立了多所学校和中央图书馆,用以存放从苏联等二战同盟国掠夺来的藏品与文件,并以此为据点进行研究[2]19-23。1941年起,ERR在乌克兰、柏林格特劳登大街(Gertrauden strasse)等地建立了诸如“罗森伯格研究区”(Ostbiicherei Rosenberg)等特殊图书馆,进行主题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犹太人在苏联国家和政党中的参与、斯大林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中的‘世界革命或民族国家的构成,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和知识观”等方面的研究[2]15-20。1943年,德国纳粹政权成立了“罗森伯格特别行动队”拉蒂波尔研究中心(The ERR Ratibor Center),用于分析布尔什维克主义,以此准备向在苏战区占统治地位的苏联意识形态开战。在斯摩棱斯克档案于1944年夏末初秋到达ERR拉蒂波尔研究中心之前,ERR就已经与专业的纳粹档案当局合作,收集了四五套乌克兰其他地区共产党的重要档案。ERR拉蒂波尔研究中心也成为日后纳粹政权整理和研究斯摩棱斯克档案的主要阵地[2]16-18。
1941年9月14日至21日,由冯·沃尔登费尔斯(Von Waldenfels)率领的“赫尔萨契夫军事档案突击队”(A military archival commando unit from the Heeresarchiv)调查了斯摩棱斯克的档案保存情况。在汇报了“斯摩棱斯克是极少数完整保存了当地共产党档案的城市之一”这一情况后,德国纳粹政权派学者多次前往斯摩棱斯克调查档案的价值与完整性,以决定是否开展后续的转移和保存工作。1943年12月,ERR指挥部担心斯摩棱斯克离战争前线太近,轰炸袭击频繁,于是派蒙森把主要档案从斯摩棱斯克和明斯克转移至里加。但是由于政局和交通的不便,出于将所有从斯摩棱斯克查获的档案搜集在一起的原因以及提前利用这些档案的目的,最终在蒙森的建议和督促下,纳粹秘密警察当局同意了先将档案转移到维尔纽斯的提议。1944年5月初,斯摩棱斯克档案被完整、安全地存放在维尔纽斯的前本笃会修道院,在ERR的指示下,共派遣蒙森在内的6位专业人士参与对斯摩棱斯克档案的整理工作[2]20-32。通过阅读其最后形成的《关于斯摩棱斯克政党档案状况的报告》可知,他们已经将超过16 739份文件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并且做了内容摘要卡。在报告中,伊丽莎白·皮尔逊(Elizabeth Pirson)推荐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扎佳科夫斯基(Stanislaw Marian Zajaczkowski)的提议,建议通过以“苏联西部地区学生的思政教育和培训”“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等为课题开展研究,出版各种反布尔什维克的研究和宣传物。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在华盛顿的“斯摩棱斯克档案”中找到纳粹政权的这些研究和摘录,而后来的西方学者在其研究中也并无任何借鉴[2]38-48。
1944年4月底,纳粹军队从苏联领土继续向西败退的同时,计划转移斯摩棱斯克档案。里加、比亚韦斯托克、普洛斯、布雷斯特等多地都分散着斯摩棱斯克的档案,由于战事紧迫,到1944年3月为止,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档案被提取整理。在1944年年底的撤退中,只有此前提取的约17 000份档案文献被优先顺利转移。从现有的纳粹报告来看,斯摩棱斯克档案是纳粹发现的唯一来自于俄罗斯联邦的共产党档案,纳粹从斯摩棱斯克转移到位于波兰奥斯维辛以西的普洛斯的档案,无论从大小、数量、收藏种类,还是内容的深度來看,都比其他任何档案都更有价值。随着1944年年底德国纳粹的匆忙撤退,大约3.5到4车厢的斯摩棱斯克档案被撤退的纳粹军队遗弃在了普洛斯的普什奇纳(Pszczyna)火车站。1945年冬天,当苏联红军抵达拉蒂波尔地区,他们找到了被纳粹掠夺至普洛斯的大部分档案和图书资料,并且这些文献资料并没有遭到蓄意破坏,大多完好无损[2]42-48。
三、美国对斯摩棱斯克档案的占有
“二战”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冷战的阴云已经聚集于美国与苏联这两个战时同盟国的上空。当苏联将从纳粹手中追回的档案暂放于德国境内受美国管辖下的奥芬巴赫档案库(The Offenbach Archival Depository,OAD)时,美国陆军随即向驻法兰克福的美国陆军欧洲战区总部(U.S.Forces European Theater,USFET)发出秘密电报,内容是关于“存放在奥芬巴赫地下室大型图书馆中的苏联资料”。这封电报涉及有关档案资料的现状、体积、题材等多个方面,并且询问是否具有情报价值或对美国国会图书馆、胡佛图书馆等机构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如何处置等。此外,在给华盛顿的秘密电报中也汇报了斯摩棱斯克档案:“斯摩棱斯克地区共产党地方组织和有关党务及政府工作会议的记录和其他文件。这是共产党和政府实际运作的一个小型模型(非常重要)。盟军的一些资料被列为‘最高机密。”尽管笔者目前尚未找到美国方面明确的“取消归还斯摩棱斯克档案”的命令或解释,但是通过对上文引述的报告进行推断可知,后来美国陆军部确实是故意公开模糊自己所掌握的情报,这才导致了未归还斯摩棱斯克档案这一“意外事件”。其实,美国对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分裂早就做出了反应:早在1945年5月底,美国情报当局就指示,“要求将所附缴获的有关俄国军队的德国文件送交至华盛顿陆军部”[2]49-54。
“二战”后对德国纳粹所掠夺文物、书籍、文献、藏品等的整理与归还工作庞杂且无序。除一些具有明显属地特征的物品外,纳粹军事书籍、代表纳粹进行宣传的文学书籍,以及一些无法确定所有者身份的档案材料等,都被移交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总共5 957件物品从奥芬巴赫转移到美国陆军部情报文件科,其中就包括1946年留存的斯摩棱斯克档案。此外,一些其他的苏联档案材料——尤其是基辅犹太无产阶级文化研究所的文件和白俄罗斯一些面向犹太人的文件,最终也成为美国国家档案馆“斯摩棱斯克收藏”的一部分[2]49-54。战后初期,苏联方面并不知道被扣留在奥芬巴赫的斯摩棱斯克档案。由于苏联当局从未对斯摩棱斯克档案的残部提出正式的归还要求,且由美国军队在德国和东欧邻国找到的大多数其他档案材料和文化宝藏都根据归还计划条款归还给了苏联,因此至少在1963年,美国陆军部和美国国会都认为,适当地归还该档案是没有问题的。在1992年,美方也再次重申了这一点[2]57-63。
在日益浓厚的冷战氛围中,残存的斯摩棱斯克档案和奥芬巴赫的其他俄国档案材料被认为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被悉数带回美国以供情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斯摩棱斯克档案并未被列入1950—1951年的《美国陆军俘虏德国记录》。1947年9月,华盛顿的情报专家们已经开始整理斯摩棱斯克档案,编写了简要的卡片说明和一些摘要。这一系列工作主要由美国陆军部德国军事文件科(The German Military Documents Section,GMDS)负责。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机密的GMDS研究文件将该档案列为“第1056组共产党记录”,并在注释中提供了详细信息:“苏联斯摩棱斯克地区1917—1941年的494份文件,按下列分类整理:会议纪要、通信、指令、金融、犹太自治共和国、少数民族、宣传、福利、宗教事务、党的报刊、工业、农业、妇女活动、青年活动,党的控制、调查、活动报告,信息公报。”[2]64-66在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与美国空军部签署了赞助合同后,9个装有524份斯摩棱斯克档案原件的箱子被送到了德高望重的哈佛大学资深政治学教授梅因·芬索德(Merle Fainsod,以下简称芬索德)的办公室,他也因此得以雇佣助手对档案进行全面分析,展开后续的系统研究。在这些助手中,就包括芬索德的学生、当时在哈佛大学担任讲师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由于美国政府和兰德公司的保护,芬索德团队基于斯摩棱斯克档案的分析研究在当时的学术界一直是独一无二且颇具颠覆性的。在芬索德的指导下,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们专门举办了学习斯摩棱斯克档案的系列研讨会,这也为日后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芬索德对斯摩棱斯克档案的研究
1928年,芬索德在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1930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政府系,他仅用两年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主题与政治史相关:一战期间的国际社会主义导致了1919年共产国际的成立[3]。芬索德在毕业第二年就以教师学者的身份服务于美国政府部门。从芬索德此时期的一系列著述可知,他对现实政治的分析具有鲜明的历史学研究特点:采用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将自己的学术精力投入到对全面性的追求;收集典型的细节并试图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实现广泛覆盖,而非执着于抽象的理论突破。总体而言,从芬索德学术成熟期开始,就表现出“对理论化的谨慎和抵制”,直至去世[4]。作为1948年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发起人之一,与其他苏联学的研究者不同,芬索德更像一只有条不紊的“狐狸”,而非像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甚至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是有着自己鲜明观点理论与政治立场的“刺猬”。
芬索德研究斯摩棱斯克档案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与苏联人民的相遇。芬索德于1932年前往莫斯科,耗费近一年时间为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际社会主义的论文寻找档案文献。作为莫斯科的常驻民,他也因此更多地接触到苏联民众,感受到更为真切的苏联日常生活。对芬索德的治学路径最具影响的,是其于1949年夏天所参与的苏联移民访谈项目。芬索德由此对“苏联体系中的基本控制模式”和“紧张和不满的来源,以及它们在苏联社会中的分布”更感兴趣[4]。芬索德敏锐地意识到:“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正在被“对俄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依恋”所调和。芬索德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莫斯科的记忆形成了鲜明对比——“苏联内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锐气的下降”。令他震惊的是,甚至在苏联共产党党员中也普遍存在着“冷漠和漠不关心”,这意味着“信仰的丧失”——更多的野心家和更少的“热心奉献者”。芬索德据此认为这一“大转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业集体化、饥荒等所致,这些都造成了苏联公民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幻灭”。据此,芬索德激动地宣布:“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已经结束。”芬索德对苏联体制的看法在他1949年10月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有集中体现。四年后,在他基于斯摩棱斯克档案所著的《苏联是如何被统治的》一书中,芬索德依然坚持着这一观点:“尽管政权可以控制人民,但不能真正信任人民”;“如果冷战升温,苏联人民很可能会变成‘我们拥有的最有效的原子弹”[4]。
芬索德接触到斯摩棱斯克档案时,这批文献早已不似其在纳粹手中那般完整。在1953—1958年间,芬索德还阅读了其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档案文件。当他面对斯摩棱斯克档案时,还是以一位专业学者所应具备的素养,严谨认真地进行着整理、阅读和分析工作。1972年,作为芬索德学生的布热津斯基在其老师的讣告中,回忆了芬索德在研究斯摩棱斯克档案时的神情:“他带着真诚的兴奋之情投入到这些材料中——在他办公室旁边是两名助手的办公室,他经常走进我们的房间给我们看,甚至大声朗读一份特别有启发性的文件,毫不掩饰对其独特贡献或新颖见解的喜悦。”[4]美国收藏的斯摩棱斯克档案按照时间顺序一共收藏了170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件,122份集体化时期(1929—1932年)的文件,156份1933—1936年的文件,50份1937—1941年的文件。尽管档案文件的范围很广,芬索德也遇到了“许多令人恼火的空白”:对于从权力控制的角度研究所有这些地区的政治、权威和权力来说,最致命的就是缺乏政府和高层党组织的文献,因此无法将苏联高层的重要作用直接纳入地方层面进行考虑。正如芬索德所言,“也许斯摩棱斯克档案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对苏联中央政府决策过程的充分记录。”[4]
盡管如此,芬索德团队还是开展了对斯摩棱斯克档案的大规模细致翻译工作,并将初步翻译好的文件再用铅笔不断地补充更正。芬索德并没有像拥有大量档案资料的历史学家那样,将同一特定主题的许多文件拼凑在一起,而是对其所认为十分重要的文件进行格外细致地阅读。体现在具体的运用中,便是在芬索德著作的几乎每一章都基于档案给出了较长的引文,其中一些引文还以较小的字体占据了一页或多页的篇幅。由于缺乏严格相关的系列文献,芬索德便将注意力放在揭示反映苏联普通民众的个人生活、经历和观点的材料上[4]。从这个角度看,斯摩棱斯克档案的不完整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它促使芬索德将这些以文件语言表达个人故事的文献资料编织到他的整个叙述结构中,并唤起了苏联学研究者们对苏联普通民众的重视。
基于斯摩棱斯克档案的研究,芬索德进一步完善了他此前对于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权力”的观点。在《苏联是如何被统治的》一书中,芬索德对后斯大林主义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四个部分:“对权力的追求”“政党的角色”“统治的工具”以及“控制和紧张的局势”。这部著作阐明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假设,影响了“极权主义”观点在研究苏联历史方面的应用。这些观点包括“极权主义的胚胎会导致极权主义的全面发展”[5]59;认为集权政治下权力和恐怖的积累“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关键”[5]354,它压倒了其他力量,包括来自民众的不满;“极权主义制度并没有摆脱其警察国家的特征”,并且“当权力从其手中被夺走的时刻,该制度下的国家便会消亡。”[5]500《苏联是如何被统治的》用四个章节分别讲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调查范围和深度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卫·恩格曼(David C.Engerman)对该书如此评价:“在所涵盖的广度和细节的深度上,它远远超过了英语中的其他任何著作,并很快成为教室和教授书架上的常客。”[6]作为继芬索德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苏联学专家,丹尼尔·布劳尔(Daniel Brower)对芬索德的详实研究予以高度评价:“1953年《苏联是如何被统治的》,1958年《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使芬索德成为‘战后最具影响力的苏联学专家。”[7]
尽管1956年苏共二十大事件、匈牙利事件等对芬索德早期的观点造成了冲击,但是他并未完全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而是以斯摩棱斯克档案为基础,关注苏联民众的普通生活和他们的不满,并以此补充对苏联权力等级的结构主义分析。芬索德在《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的开篇概括了自己在1949年参与采访项目的心得:“(采访)档案中显示的是对更高生活标准的普遍渴望……档案揭示了它们在斯大林主义强制一致性的表象背后的发酵。”但是,通过阅读和分析斯摩棱斯克档案,在书的结尾,索芬德通过对“苏联民众个人生活”的重新关注也使其对自己此前的观点做了修正:“民众对苏联体制的怨怼本质上是源自不满而非愿望,这一点已经在1949年的采访中传达出来了。”[5]14诚如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凯特琳娜·凯莉(Catriona Kelly)所言,芬索德在1957年对苏联普通人经历的理解“读起来像是过去二十年许多学术成果的宣言”。她把芬索德这种立场的“转变”归因于其对普通生活的关注——从对“苏联是如何被统治”的冷漠抽象,转变为“非凡的,确实感人的”修正主义先锋文学[8]。
五、基于档案和芬索德研究的探索
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在西方苏联学领域成长起一批如希拉·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 Sheila)、斯蒂芬·科特金等(Stephen Kotkin)“修正主义流派”的先驱。这些“修正主义流派”的中流砥柱最初接触苏联学,便是在大学课堂从学习索芬德所著的教科书开始。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苏联学中关于修正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辩论愈演愈烈,一些苏联学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芬索德教科书中对极权主义控制的强调与其在《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一书中关于苏联民众生活和地方主义的丰富档案材料之间的矛盾[7]。2002年斯蒂芬·科特金在他该主题文章的开头便提到了斯摩棱斯克档案——“这是梅因·芬索德1958年专著中对极权主义论题的最佳经验主义阐述,也是20世纪80年代几个反极权主义论点的基础。”[9]
芬索德之前的西方苏联学研究虽然也关注“苏联权力”,但很少将权力本身作为研究焦点。索芬德结合自身专业特长,从体制、层级、官僚体系、制度框架等角度对于“苏联权力”的细致研究与探索,促使欧美学界对“苏联权力”本身的理解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芬索德基于斯摩棱斯克档案对“苏联权力”的下放问题格外关注,认为斯大林主义实际上靠着三个独立的控制机构得以维持——党、秘密警察和国家,而斯大林本人则主要操纵这“三重权力线”,以维持平衡。此后的苏联学学者们通过对相关苏联系列档案的研究,也证实了芬索德的洞察。
此外,芬索德本人对理论化的谨慎与抵制、对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强调,也使得其在参与哈佛大学的苏联移民访谈项目、前后多次赴苏调研的基础上,对于“苏联权力”的框架和苏联地方—中央的权力的制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尽管芬索德在他的著述中并没有使用过“群众动员”这类的词汇,但是其研究却表明:革命、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群众动员的巨大力量不仅影响到了苏联的党和国家体制,而且也波及苏联官方在意识形态(如后来福柯所理解的)层面的权威。芬索德的这方面探索为欧美诸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指引和经验。从对历史学和苏联学本身的影响来看,芬索德在其著作《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中将视角引向苏联民众的个人生活——在著作结尾,芬索德通过引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强调历史研究的主题是“人类的生活”,强调在斯摩棱斯克档案中“充斥着普通人,他们在不寻常和不正常的事件中拼命努力,试图过上正常的生活”。这不仅启迪了希拉·菲茨帕特里克1999年所著的《日常斯大林主义:非凡时期的平凡生活》[10]一书的副标题,促使后来的苏联学“修正主义流派”进行“自下而上”的范式革命,更以人文主义的关怀强调了历史学的最終旨归——对人本身的思考与探索。
芬索德基于斯摩棱斯克档案对苏联民众个人生活的关注,使他对于“苏联权力”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理解。在《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一书中,芬索德通过探讨苏联的行政等级,发现了“权力压迫从中央到省再到区的转移”。此外,芬索德还探讨了“地方腐败如何导致大清洗,大清洗如何进一步巩固苏共中央的控制,而这又缓慢且无情地将逃避和松懈的早期政党生活转变为‘顺从的斯大林主义混合体”[5]52。但是,芬索德在探讨这一系列问题时,由于文献材料的缺失而忽略了党中央、秘密警察和斯大林的确切作用,因而几乎完全是从中央集权的角度看待“苏联的权力”,而并没有从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等视角综合探讨这一时期的苏联政治,因此造成了芬索德对苏联1928—1932年“大转变”的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并不充分。这一点被后来的修正主义史家们发现,丹尼尔·布劳尔、斯蒂芬·科恩(Stephen F.Cohen)、希拉·菲茨帕特里克等学者就沿着索芬德未尽的事业,就苏联1928年的“大转变”做了许多具体的专题性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工作也依然是建立在前期索芬德对于斯摩棱斯克档案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其观点并非是推翻芬索德看法的标新立异,而是继往开来的证实和补充,所使用的史料以对斯摩棱斯克档案的重新解读为主。
六、结语
“史学就是史料学。”综观中外史学界,对于任何一位以书写“信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历史学者来说,无论是探赜索引地“秉笔直书”,抑或是钩深致远地“高屋建瓴”,都离不开对于基础文献史料的分析与解读。斯摩棱斯克档案在二十世纪四十五年代辗转多地,但是各方势力都对该套档案进行了细致地保护与整理,也因此才得以保存至今,成为珍贵的研究史料,成就了芬索德在西方苏联学研究领域的非凡贡献。通过该套档案,芬索德以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视角,对“苏联权力”与苏联体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丰富了“极权主义流派”的相关理论与观点。芬索德对该档案毫不偏颇地如实记录和使用启发了后来的修正主义史家们在其基础上进行范式革命与理论创新。时至今日,斯摩棱斯克档案依然造福着大批苏联学学者,包括美国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Edgar Pipes)、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康奎斯特(George Robert Acworth Conquest)等诸多历史学家都从中获益,以其为文献写作并出版了一系列知名论著。目前,得益于档案文献数字化的便利,学术壁垒逐渐被“开放存取”的趋势打破,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瑞典于默奥大学、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国家档案馆、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等都收录了斯摩棱斯克档案的微缩胶卷,以供对其感兴趣的研究者们阅读使用。
参考文献:
[1]于滨.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J].俄罗斯研究,2013(6):167-197.
[2]GRIMSTED P.K.The Odyssey of the Srnolensk Archive:Ploodered Communist Records for the Service of Anti-Communism[D].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5.
[3]FAINSOD M.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ld War[M].New York:Octagon Books,1966:1-238.
[4]DAVID-FOX M.Re-Reading Fainsod in Smolensk[J].Kritika: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2021(4):813-840.
[5]HOUGH J.F,FAINSOD M.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6]ENGERMAN D.C.Know Your Enemy: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10-230.
[7]FAINSOD M.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xiii.
[8]KELLY C.What Was Soviet Studies and What Came Next?[J].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2013(1):109-149.
[9]KOTKIN S.The State—Is It Us?Memoirs,Archives,and Kremlinologists[J].Russian Review,2002(1):35-51.
[10]FITZPATRICK S.Everyday Stalinism: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作者簡介:殷亲亲(1999—),女,汉族,陕西汉中人,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苏联史、国际关系史。
(责任编辑:冯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