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禹绩”之敷土、随山、刊木、濬川四事考
许兆昌 王一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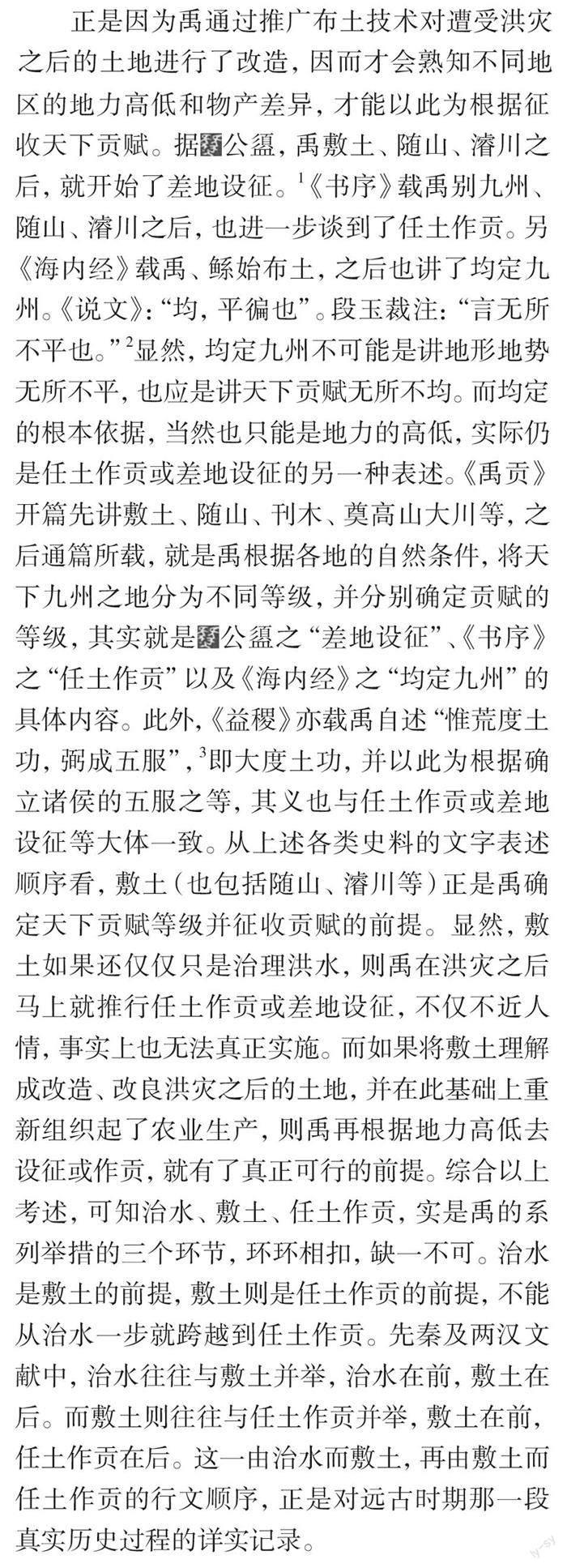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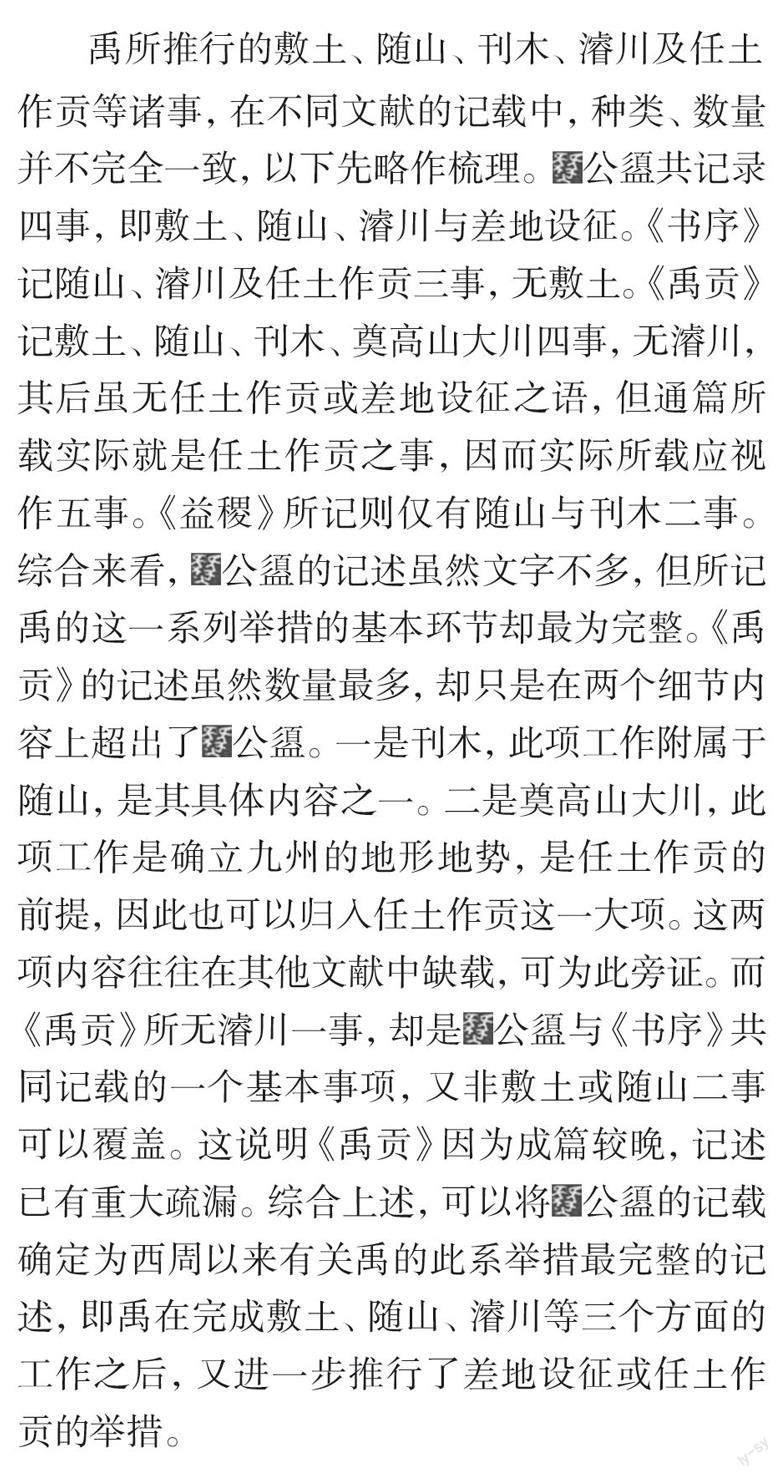
关键词:禹绩;敷土;随山;刊木;濬川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3.006
敷土、随山、刊木、濬川,语出《尚书》之《禹贡》《益稷》及《书序》等先秦古籍。《禹贡》首句即作“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1《益稷》中有“予乘四载,随山刊木”。2《书序》则作“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3此外,《大戴礼记·五帝德》还有“使禹敷土,主名山川”4的记述。上述文献的成书虽不一定很早,但西周中期公盨亦有非常相似的记载:“天命禹尃土,随山,濬川,乃差方设征。”5可见敷土、随山、刊木、濬川等辞,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是人们称颂“禹绩”的习语。然自伪孔传以来,敷土诸事往往与治水合二为一,被简单地视作治水的方式或手段。本文以为,禹绩之敷、随、刊、濬四事,所指是与早期农业修整、垦育土地相关的各类事务,并非治理洪水。尽管先秦文献有关“禹绩”的记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传说甚至是神话色彩,但神话与传说不会凭空产生,其后往往隐藏有真实的史实依据。上述禹绩四事,就是对华夏远古农业经济的如实记述。以下试做考辨,敬请专家指正。
一、“敷土”非“治水”考
最早将敷土与治水合二为一的,是伪孔传。《禹贡》首句所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就其本文看,其实并不涉及治水,甚至没有提到洪水一事。但伪孔传却为这些禹绩增加了一个洪水泛滥的前提,谓:“洪水汎溢,禹布治九州之土,随行山林,斩木通道。”1如此行文,则敷、随、刊等事就都成了治水的相关举措。唐孔颖达为伪孔传作疏,又对此有更为细致的描述:“洪水流而汎溢,浸坏民居,故禹分布治之……于时平地尽为流潦,鲜有陆行之路,故将欲治水,随行山林,斩木通道,”2这就进一步将敷、随、刊等禹绩的治水性质坐实。
伪孔传以前,自战国以迄两汉,学者们都是将治水与敷土述为二事,是禹绩的两个主要内容。例如,战国时期,《荀子·成相》云:“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3其文前言治水,后言傅土(即敷土。战国两汉文献中,或称敷土,或称傅土),显为二事。西汉时期,司马迁著《史记·夏本纪》,直引《禹贡》之文,仅依汉代学者的理解或用字習惯,改敷为傅,随为行,刊为表,称“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据太史公的前后行文,禹所行傅土、行山、表木、定山川诸事,都是其受帝命为司空之后的业绩。而禹之所以得任司空,是因为他已完成治水,立了大功:“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显然,太史公著《夏本纪》,也是视治水与敷土为二事的。至于禹为司空之后,太史公虽然有一段“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的对比记述,但却并不是在讲禹在治水时一变其父鲧之治水用堵而改为疏导,而是赞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的敬业精神。至于其后述禹绩: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4
其中唯“陂九泽”涉及水的治理,然郑玄《礼记·月令》“毋漉陂池”注云:“畜水曰陂”。陆德明音义:“漉,竭也”。5则陂九泽实为畜水用于农业灌溉,显然不是治理洪水。至于其他事务,就更与治理洪水无关。至东汉时期,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夏”时曾将“傅(敷)土”和“治水”并举为禹的两大业绩,称:“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6显然,如果郑玄将傅土视作治水的手段,即应表述为“傅土治水”,而不应表述为“治水傅土”。郑玄如此行文,只能是并举傅土与治水,视其为二事。自战国以迄两汉,敷土往往与治水并举,且其行文的一般顺序都是治水在前,敷土在后。这应是伪孔传以前学者有关禹绩的基本共识。
伪孔传视敷土与治水为一,从训诂的角度看,有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敷土的对象终归是土,不是水。伪孔传具体解释“敷土”时,仍仅作“布治九州之土”,实际是回避了治水与治土之间的差异问题。因此,如何将敷土解释成治水,成为唐代学者制作五经正义时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难题。孔颖达既然要将其坐实为治水,就只好在疏解伪孔传时有意无意地省去了这个土字,将“布治九州之土”省作“分布治之”。由于此语又紧承在“洪水流而汎溢,浸坏民居”之后,则其所谓“分布治之”的“之”字,就由伪孔传所讲的“土”偷换成了“水”。敷土也就实际上变成了敷水。除孔疏使用这种偷梁换柱的方式外,唐代学者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在敷土一辞中楔上一个“水”字。例如,贾公彦疏郑玄《周礼·大司乐》“傅土”即云:“案《禹贡》云‘敷土,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是敷土之事也。”1贾疏像搀沙子一样,将郑注的傅土解释成布治水土,语义中凭空多出一个水字。实际上,郑玄《大司乐》注本为“治水傅土”,有水有土,水土分言,而且方式也不同,对水曰治,对土曰傅。贾疏将傅(敷)土疏解为布治九州之水土,反而使郑玄注中原有的治水一辞没了着落,这当然是极不妥当的错误做法。从伪孔传的“布治九州之土”发展成贾公彦的“布治九州之水土”,可见唐代学者为了弥缝伪孔传治水、敷土为一事说中的漏洞,着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尽管视敷土与治水为一事只是自伪孔传以始的后起之说,唐代学者勉为其难的疏解中也存在着种种训诂问题,但在大禹治水的强势语境下,此说竟成定论,甚至成为后来学者讨论禹绩时习焉不察的前提性话语。例如,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夏本纪》“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并做解释时即云:“治水土非一人之力,故奉帝命兴人徒”。按孙氏此文,是解释何以傅土要“兴人徒”,但在引述傅土时,一如贾公彦,直接将《夏本纪》中的傅土转述成治水土,竟对其擅增一水字的问题毫不察觉。孙氏甚至还将贾公彦《周礼·大司乐》疏所谓“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这一唐初才出现的说法误以为即汉代郑玄所云。2
视敷土为治水说同样影响到当代学者的研究。上个世纪,顾颉刚先生撰《息壤考》3一文,利用《山海经》的记载,认为敷土就是鲧用息壤去填堙洪水这一神话的历史化。顾先生的文章避免了自伪孔传以来学者注解敷土时必须要将土转换为水或至少要在土之外搀入水的问题,直指敷土就是治水的一种手段,这才最终坐实了伪孔传以来敷土、治水为一事说。顾先生的文章影响很大,近至公盨公布,裘锡圭先生考释铭文,也仍以为铭文中的敷土即用息壤填堙洪水。4
先秦文献中确有禹堙堵洪水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北经》即云:“禹湮洪水,杀相繇。”5又《庄子·天下》亦称墨子曾言禹治理洪水,兼用堙堵和疏导两种方式:“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6此外,《汉书·沟洫志》也引《夏书》云:“禹湮洪水十三年。”7墨家既自称“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8其所述禹的事迹,可信度理应较高。《汉书》所引《夏书》,也能说明禹湮洪水确是先秦以来所传之禹迹。另外,远古神话往往是真实历史的曲折反映。《山海经》所载鲧用息壤填堙洪水的神话,当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为依据,9它也符合人们对于土能挡水这一常见自然现象的最一般的认识。顾先生认为禹治洪水也曾用过与其父鲧一样的堙堵策略,这一点当可成立。不过,远古时期存在着这种用土堙填的方式来治理洪水,甚至禹也用过这种方式治水,与敷土就是用息壤堙填洪水,是两个命题。不能因为前者成立,后者就一定也成立。由于顾文前提已基本是伪孔传以来敷土即治水说,因此该文的主要内容只是利用自然现象解释息壤堙填洪水这一神话中所包含的科学原理,而针对敷土即用息壤去堙填治水的说明,实仅举三条史料便遽下论断。这三条史料一是《诗·商颂·长发》所述“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1有关商人起源的诗文。二是《山海经·海内经》所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2的神话。第三条也是神话,为《淮南子·墬形训》所谓“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的记述。3其实,顾先生的立论不仅证据单薄,且对史料的理解也有一定的问题。
首先,顾先生所举第一条史料《诗·商颂·长发》“禹敷下土方”句,虽上承“洪水芒芒”,但诗句本身其实并没有明指这就是治水,故郑玄笺诗即云:“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夏,广大其竟界之时,始有王天下之萌兆。”4显然,在郑玄看来,诗文的后句“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才是“禹敷下土方”语义的自然发展,而洪水茫茫,不过是为敷下土方,正四方,定诸夏这一禹绩设置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已。郑玄之所以这样为诗作笺,是因为自战国以迄两汉,治水与敷土分为二事是众多学者的基本共识。郑笺当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淆乱。“敷下土方”与“大国是疆,幅陨既长”语义前后相承,除有前引《荀子·成相》所谓“禹傅土,平天下”为证外,即顾先生所举三条史料中的第二条《海内经》的记载同样可做一重要旁证。因为在《海内经》中,也明言“禹布土”的结果是“定九州”。显然,“定九州”就是“平天下”,而在《诗》中,也就是更具体的“大国是疆,幅陨既长”。而此三者的共同前提,就是敷土、傅土或敷下土方。郑笺对诗义的理解显然是正确的。因此,虽然《长发》篇中“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在形式上语句前后相承,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敷下土方就是治理洪水。其次,顾先生所举第二条史料《山海经·海内经》所述实为两个神话,一是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一是禹布土以定九州。就其本文看,前一个神话讲的是治水,后一个神话讲的是定九州。前举《诗》《荀子》《史记》等先秦两汉文献中,都是先述治水,后述敷土,两事相关,但又并非一事。《海内经》中的这两个神话,也应作如是观。顾先生将鲧、禹父子二人的不同神话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尤需指出的是,禹定九州的前提必須是通过疏导的方式治理洪水。因为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再度出现,所以才有禹定九州之事。《荀子》所谓平天下也好,《诗》所谓外大国是疆也好,都是洪水退后才需要也才能够做的工作。先秦两汉文献记载禹绩时这一治水在先,敷土在后的叙事顺序,并非众多作者有意为之,而且还能如此巧合,实是大禹所立功绩的本来顺序就是如此。若禹也仅像鲧那样用堙堵的方法治水,而不是导流入海,则洪水仍在,又何来均定九州,平天下,疆大国之事呢?顾先生以为禹可以通过堙堵洪水的方式来定九州,肯定是一种错谬。此外,从神话的细节上看,鲧所窃息壤固然是一种土,但不能反过来说后文的土就一定指息壤。据郭璞注,息壤是一种特殊的土,可以“自长息无限”。这与需要禹去人工布放的土显然不会是一物。第三,顾先生所举第三条史料《淮南子·墬形训》所述“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其实仅能证明禹与其父鲧一样,也曾用息土(壤)堙填洪水。前举先秦文献如《庄子·天下》《山海经·大荒北经》等,也都明确记述了堙堵曾是禹治洪水的方式之一。不过,前文已讨论过,禹曾堙堵过洪水与禹敷土就是治水,实为两个命题,不能因为前者成立,后者就一定成立。因此,《淮南子》的记述,同样不能证明禹敷土就是用息壤(土)去堙填洪水。
通过前文梳理,可知将敷土与治水合二为一,只是伪孔传所立之谬说。顾颉刚先生利用上古神话力证禹亦曾采用堙堵的方式治水,其说确当有据。但因受伪孔传敷土、治水为一说的影响,误将敷土理解成用息壤去堙堵洪水,对历代混淆敷土与治水的错误认识起到了进一步的推波助澜作用。
二、“敷土”事实考
剥开一千多年来治水对敷土的纠缠,为揭示这一禹绩的历史真相找到了正确的路径。敷土应是一项针对土地实施的工程,与治水前后相关,但并不是治水本身。就先秦两汉典籍看,土与水一直是记述禹绩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除前引《荀子·成相》分别详述禹绩中的治水与傅土两个方面外,更多文献是水土并举,以“平水土”一语来简要概述禹的功绩。例如,《尚书·吕刑》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国语·郑语》云:“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墨子·尚贤中》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西汉初成书的《淮南子·修务训》仍有称:“(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前引唐贾公彦《周礼》疏也曾“水土”并举,但他以为“布治九州之水土,是敷土之事也”,即将水与土都归入敷土一类,因此尽管与上举先秦文献并称水土在形式上一致,但意义相差却不可以道里计。另有需辨明者,即《尧典》亦称:“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维时懋哉!”其后《夏本纪》据以改作:“(舜)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据这两种文献的上下文,此两例“女平水土”句皆在禹完成治水之后,任司空之前,此时尚未涉及敷土之事,似有用治水一事兼容水与土的语义。不过,《尧典》实为东周时期作品,可能有一些远古传说为蓝本,其内容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其中所载远古时期人物之间的对话,绝不可能是当时实录。钱钟书先生曾谓《左传》记言“实乃拟言、代言”。1《尧典》此文,也大略如是,应只是其作者直接借用当时众多文献共同概述的禹绩“成语”以成文,实未做清楚辨析。因此,不能仅据《尧典》之文即以为治水能够包括水与土两个方面。

《说文》:“尃,布也。从寸,甫声。”1尃即布义。又《说文》、互训。即施。《说文·?部》:“施,旗旖施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大人赋》说旌旗曰:“又旖旎以招摇。”2旖旎即旖施,象旌旗招摇布展之貌,与尃字训布同义。是故《禹贡》《荀子》《大戴礼记》《史记》所述敷土、傅土或溥土,在《山海经》中则径作“布土”。其《海内经》云:“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又云:“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等等。按《说文》云:“布,枲织也。”3所释为用作名词之布,与训尃为布的动词之布不同。徐广、惠栋等皆谓尃即古布字。4按尃字从寸,甫声。从寸表义,象手之动作,甫、布又皆为鱼部帮纽字。是可知徐、惠等学者所谓尃为古布字,说的正是用作动词的布,故亦可与施同训。伪孔传释《禹贡》敷土为“布治九州之土”,犹存古义,但伪孔传对于布字在此具体用为何义、所指具体何事,应不甚了了,所以才会特地在布字后增加一个“治”字,事实上将敷字的意义最终落实在了“治”上。以泛指的治土训敷土,也很容易为人理解。由此“布治”一词,成为历代学者言敷土时常用之语。但何为布治,即布字的具体实义,自伪孔传以来历代学者都没能给出明确的解说。唯顾颉刚先生以为敷土即用息壤去堙堵洪水,才算是将布字落实,故而也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不过,据前文考证,敷土与息壤当分别为二事,不可混淆。
敷土作为一项针对土地的工程,其字面意义即“布土”。沈长云先生曾结合大禹治水的事迹,认为洪水排出之后,导致原来被水淹没的土地又重新暴露出來,甚至有可能比过去还有所扩大,这就好似“对土地重新布置了一番”,而民众亦由此得以“陆处”,重新获得生机。禹立下了这么伟大功绩,故而被人传颂为“布土”。5沈先生释敷土,直接针对土地本身,相较前代学者,可谓眼光独到,更为精准。而且他对治水与敷土二事先后顺序的理解,也完全符合先秦两汉学者必先称治水,然后再称敷土的一般行文顺序。按照这种行文顺序,虽不一定能够清楚地说明何为敷土,但敷土必不为一种治水的手段,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沈先生所释敷土,正是治水之后形成的一个结果,而非用于治水的一种方式。这一点显然更符合古文献记述的本义。不过,如果敷土仅是治水的一个副产品,并非禹主动完成的一项功绩,则古文献常常将之与禹的另一大功绩治水相提并论,又不免有些名不副实。事实上,先秦文献中,禹除了治水外,也曾主持过治理土地的工程,惜沈先生未予措意。《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6《大荒北经》亦载:“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7相繇即相柳氏,当为沼泽之神,故其所抵所尼,郭璞注:“抵,触也,”8“歍,呕……尼,止也”,9即为源泽。此种沼泽之地,既不能居住,也不能耕作,故禹对其实施改造、改良工程。工程的具体内容就是通过“三仞三沮”,营造众帝之台。仞即满,清人王念孙云:“仞读为牣。牣,满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云:‘充仞其中。仞、牣古通用。”10沮,郭璞注云:“言禹以土塞之,地陷坏也。”11又云:“掘塞之而土三沮滔(陷),言其血膏浸润坏也。”1沮即陷,但郭注释沮为地陷坏,则未尽文义。因为上两则记述于“三仞三沮”之后,皆有营造众帝之台等语。《海外北经》云“乃以为众帝之台”,《大荒北经》则云“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显然,如果仅是三仞而又三度陷坏,则何以为众帝之台?事实上,这里所记载的,正是禹运用夯土技术改造沼泽之地,使之变得适于人居的一项土地改造工程。所谓三仞三沮,应是指进行了多次夯实地基的工作。据《海内北经》,所谓众帝之台,指的是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及帝舜台等。这些远古之帝大多与禹同期,说明其时夯土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曾极大地改善了当时人的居住环境。因为夯实地基需要大量取土,因而同时又会出现深挖的沟池。是以《大荒北经》才会一方面记述“乃以为池”,另一方面又记述“是以为台”,这看似并不搭界的记录,恰是对远古时期人们大量取土以夯实地基,从而营建宜于人居的宫室这一历史真相的最完整描述。《山海经》的记述有充分的考古学证明。据考古发掘材料,夏王朝统治时期,夯土技术已经获得很大的进步。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夯土基址,为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5号基址。这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夯土基址,为一处四进院落。其夯土总厚度一般在1.2米左右,其中的2017VM11的夯土堆积竟厚达3.8米,可以划分出60余个夯土层。考古学者推测其夯土工序应是先挖一个大型基坑,平整坑底,铺垫垫土之后,再就近利用灰坑填土逐层夯筑。每隔一层或数层,又会在灰土之上铺垫黄沙土,以防止灰土粘连,在接近表面的地方再选用较纯净的红褐色土进行夯筑。《山海经》所述“三仞三沮”,正是对这种通过多次填满灰土再予以夯实过程的最简洁又最为形象的描述。夯筑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故《世本·作篇》载:“尧使禹作宫室。”2无论是营造群帝之台还是作宫室,都说明禹曾运用夯土技术改造建筑用地,加固建筑基址,为推动早期建筑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敷土也是禹所实施的一项土地改造工程,它发生在农业生产领域,是远古农业科技的一次重大突破。《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3其中的“禹、鲧始布土,均定九州”前文已经引述。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段记述远古时期农业及手工业各项技术进步的文字。其中,义均为巧倕属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其后的后稷播百谷以及叔均作牛耕都属农业技术的进步。“大比赤阴,是始为国”文义不可解,其中文字应有串乱。4袁珂校注以为“始布土”句应是“承上文播百谷,作牛耕之意而言”,5可谓至确。结合此上下文,可以肯定所谓“禹、鲧始布土”,也当是一项重要的农业科技发明,而且所针对的,正是一切农业经济的基础——土地。有关禹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具体贡献,目前所见仅《海内经》所载此条史料,看似孤证,但先秦文献确有不少记载,涉及禹在远古农业发展方面的成就,可以作为禹曾在农业技术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旁证。《论语·宪问》:“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6可见在春秋晚期的孔门学者眼中,禹与稷一样,同是躬行稼穑的远古帝王。稷的贡献是教民播种百谷,这是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能与稷并称,禹的贡献恐怕不能仅止于身体力行,主持甚至只是积极参加农业劳动,也需要有能够相提并论的技术突破和推广,才会令人信服,并为之传诵。又《诗·鲁颂·閟宫》亦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此段诗文前四组共八句,讲的都是后稷教民稼穑之事,而至第五组却突然终结为“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毛传:“绪,业也。”按禹并未传位于后稷,所谓缵禹之绪,显然不是政治领域的前后交接。结合《宪问》的记载,可知这里的“缵禹之绪”指的应是后稷继承了禹在农稼方面的事业。只有这样理解,该诗文的第五组才能与前四组文义相属,否则前面对稷的农稼成就的具体描述就都成了无的放矢。《国语·周语下》记周太子晋称颂禹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1韦昭注:“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万物也。”2所谓以嘉祉殷富生物,说的正是禹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另据《尚书·益稷》,禹确是洪灾之后恢复与重建农业经济的重要人物之一。禹自述云:“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又云:“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3这两段话都提到了所谓“鲜食”“艰食”等,又有“烝民乃粒”之语。伪孔传:“鸟兽新杀曰鲜”,“米食曰粒”。“艰食”,太史公以为“难得之食”,4马融以为即“根食”,“根生之食谓百谷”,郑玄则将“鲜食”“艰食”统释为“泽物、菜蔬、艰戹之食”。5根据这段材料,可知洪水退后,禹与益、稷一起致力于灾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从禹与益尚只能进奉各种鲜食看,此时农业经济尚未能完全恢复,因此还需依靠猎捕鸟兽供民充饥。而到禹、稷联手时,情况已大为改观。此时既已能够提供百谷、稻米供民食用,说明农业生产已经得到了有效地组织。《益稷》当然不会成篇于唐虞时代,但后人编纂此类文献,往往会有更早的文献或传说作依据,其中自不乏零星但却相当可信的上古史事遗存,因而很值得重视。以上种种材料,都可证明禹在早期农业发展领域曾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成就并不亚于被视为谷物之神的后稷。按远古农业的发展,后稷教民播种百谷当然是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成就,但却只能是之一,并不是全部。从组织农业生产的诸多环节看,土地才是发展农业的基础性条件。与此同时,为农业劳动提供更高效能的动力来源和农用工具,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农业经济的阶段性飞跃,往往会表现为劳动工具及动力来源的改进和突破。令人惊奇的是,上引《海内经》的记载,从后稷的播百谷,到叔均的作牛耕,再到禹、鲧的布土,正好把事关农业生产的这三个最重要因素——农作物、劳动工具和动力来源、以及土地等——全部赅括。这不应只是一种巧合,它表明古人对于农业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全面,具备了一定的系统化特征。作为一项足以与稷播百谷以及叔均作牛耕等相提并论的农业科技突破,布土是禹对上古华夏文明发展做出的另一项重大贡献,因此它才能够始终与治水并列,在后世得到广泛传颂。以往研究者仅仅将它视作一种治水的手段,实际是湮没了中华上古文明在农业科技领域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由于史料的缺乏,布土这项远古农业领域的重要技术突破,今已很难详考其具体内容。它可能与禹为恢复农业生产,需要改造经洪水长期浸泡已不适合耕作的沼泽湿地有关。前述《海外北经》《大荒北经》除了讲沼泽之地因多水而不可居住外,还都一致提到了所谓沼泽之神相繇或相柳氏“其血腥臭”或“其血腥”,因而“不可树(五)谷种”“不可生谷”的问题。其实,所谓“其血腥臭”“其血腥”等等,不过是用神话语言描述了沼泽湿地由于植物残体堆积过于丰厚以致腐气浓郁不得消散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而“不可树(五)谷种”“不可生谷”等,实际表述的则是沼泽湿地因为含水过高,透气性很差,因而无法进行农业耕作的土地特点。《山海经》的记载,可以说正是对洪水退后禹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及土壤特征的写实性描述。保证土壤的透气性,是华夏先民很早就总结出来的一项重要农业科技。据《国语·周语上》的记载,西周时期定于每年的立春之日,都要举行籍田礼,即翻垦土地的耕作仪式。按照虢文公的说法,是因为从立春到夏历二月,随着天气的转暖,“阳气俱蒸,土膏其动”,韦昭注:“膏,润也。其动,润泽欲行也。”此时如果“弗震弗渝”,就會导致“脉其满眚,谷乃不殖”。1可知籍礼中翻垦土地,目的就是减少土壤中富余的水分,以增加其透气性。显然,洪水过后要恢复农业生产,必须先行解决土地方面存在的这个问题。而所谓的布土,讲的应该就是禹通过改造沼泽湿地,为迅速恢复农业经济提供优质良性土壤的事迹。沼泽湿地的改造,首先要排涝。《论语·泰伯》记载孔子称颂禹“卑宫室,尽力乎沟洫”。何晏集解引包曰:“方里为井,井间有沟。沟广深四尺,十里为成。成间有洫,洫广深八尺。”2可见禹之所为沟洫,主要用于日常性的田间排涝、灌溉及管理,与洪水之后改造沼泽湿地有关,而不应仍是在治理洪水。排涝之后就是翻垦土地,挖沟培垄。垄用于种植作物,垄沟则用于排除积水。深挖的垄沟不仅可以增强垄土的透气性,以利作物根系生长,挖出来的土壤还可用于培高垄土。《国语·周语下》:“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韦昭注:“下曰畎,高曰亩。亩,垄也。”3可见文献中常常提到的畎(甽)亩,就是挖沟培垄整修出来的可耕良田。这种翻垦土地培高垄土的农田整修手段,以“布土”称之,可以说非常地写实。前述《大荒北经》《海外北经》记述禹改造沼泽湿地,除“三仞三沮”外,还提到了“厥之”和“湮之”等手段。厥即撅,通掘,即掘开沼泽湿地。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排涝,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日晒的方式降低土壤中的水分,增强土壤的透气性。《国语·周语上》记西周时期行籍礼,最核心的礼仪部分是“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4一墢,即一耜之墢。5耜正是用于翻土的农具。无论是夏禹之厥还是周人之墢,其用意是一致的。湮,《说文》:“没也。”6治理沼泽,显然不可能还会引水淹没之,只能是堆土覆盖之,其目的也是调和、改善土壤中的干湿比例。远古时期,在人们还没有大型运输工具的条件下,所谓湮之,也不大可能是从远方取土来堆埋,而应是即用新掘出来的土壤直接覆盖在上面,最终形成的正是垄、沟相间的畎亩式耕地。是以禹所实施的土壤改造,既可如《海外北经》那样称厥之,也可如《大荒北经》那样称湮之。先厥之,后湮之,正是同一种土地改造工程的前后两个步骤,合称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布土或敷土。畎亩整修技术是华夏先民在农业科技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吕氏春秋·辨土》对这项农业科技曾做总结:“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7后世根据地形高低以及旱涝的差异,又进一步发明了低涝之地植于亩上,高旱之地则植于畎中的技术,《吕氏春秋·任地》称之为“上田弃亩,下田弃甽”,8从而使不同条件的土壤都能开发成有经济价值的耕地。而据《海内经》所谓“禹、鲧是始布土”这一记载看,禹的父亲鲧实际也是布土的发明者之一。又《孟子·告子下》还称“舜发于畎亩之中”,9可见整修畎亩的布土技术应该在禹之前就已经出现。因此,禹可能只是在洪灾之后大力推广了这项土地改造技术,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遂将这一农业科技领域的重要发明归在了禹的名下,使之成为禹除治理洪水之外被人们广泛传诵的另一项伟大功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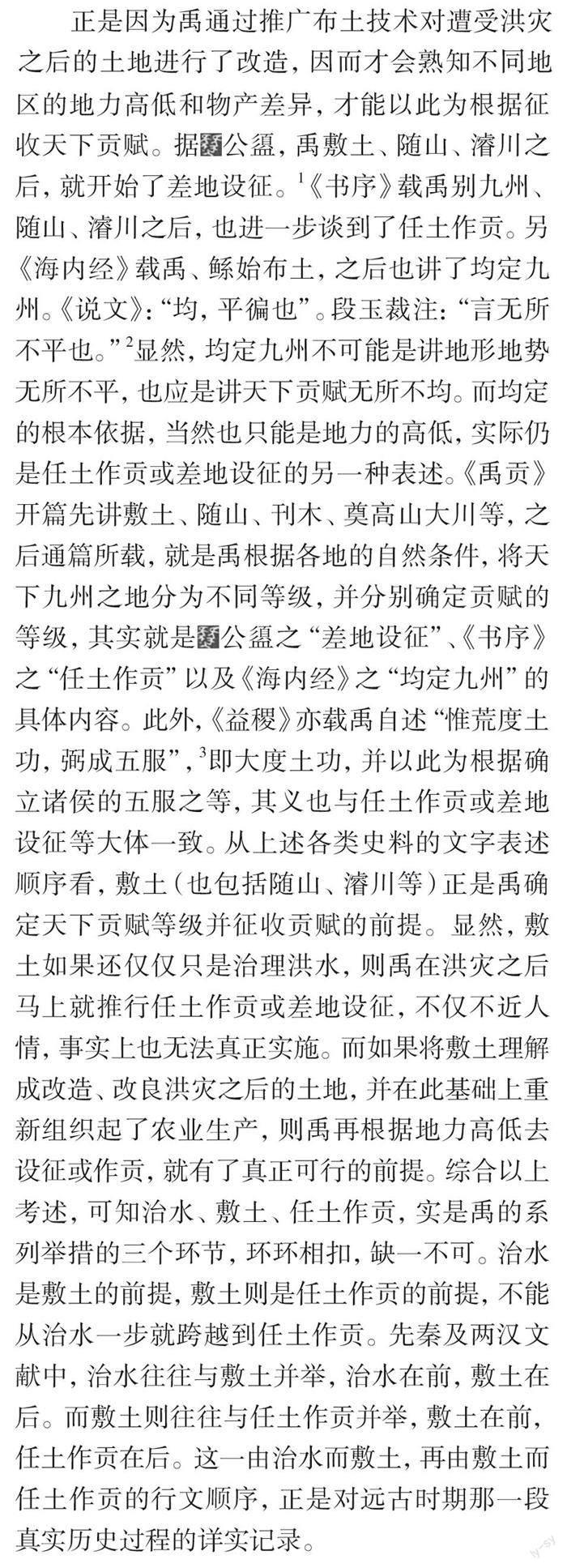
三、随山、刊木、濬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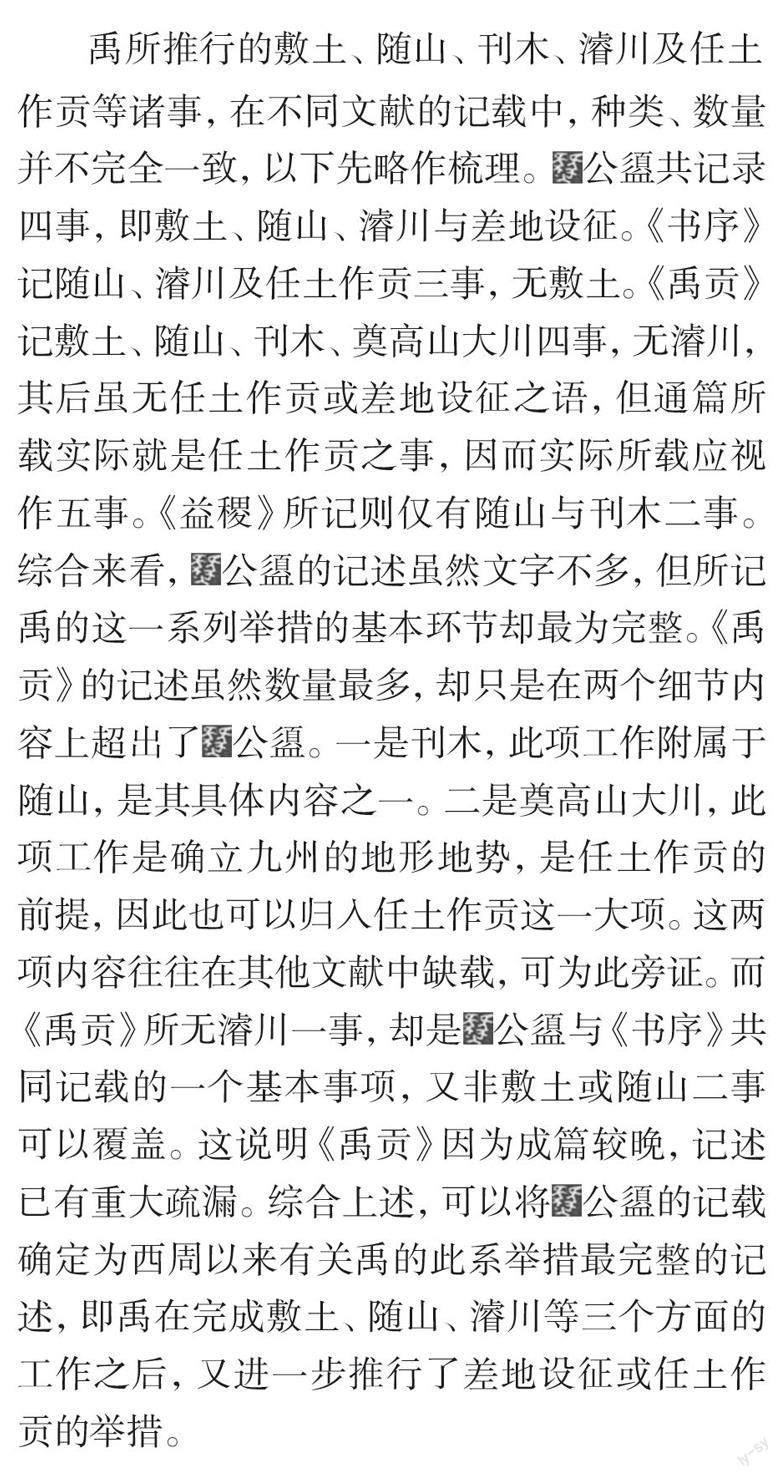

前文已证敷土是禹在农业科技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且敷土与任土作贡正为前后相关事项——先安排、组织农业生产,然后根据地力高低征收贡赋。显然,夹述于敷土与任土作贡之间的随山、刊木、濬川等,自也应置于同一语境中以求其事实真相。随,《说文》:“从也,从辵,墮省声。”5故自两汉以来,学者多从行字着意。按随字本义为从,太史公直释为行,两义显然还有一定的差距。故郑玄改释为“随州中之山而登之”,将字义落实到登上,但显属增一登字释经。伪孔传以后则多以“随行”为释,既保留了随义,又在事实上将字义落在行上。这一点颇似前文所述的释敷,如果仅释为布,于义难晓,故增一字释为布治,则既保留了敷的布义,又事实上将字义落在治上。这些增字释义、避实就虚的做法,都表明古人在做这些训释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是有意识的,但又无法避免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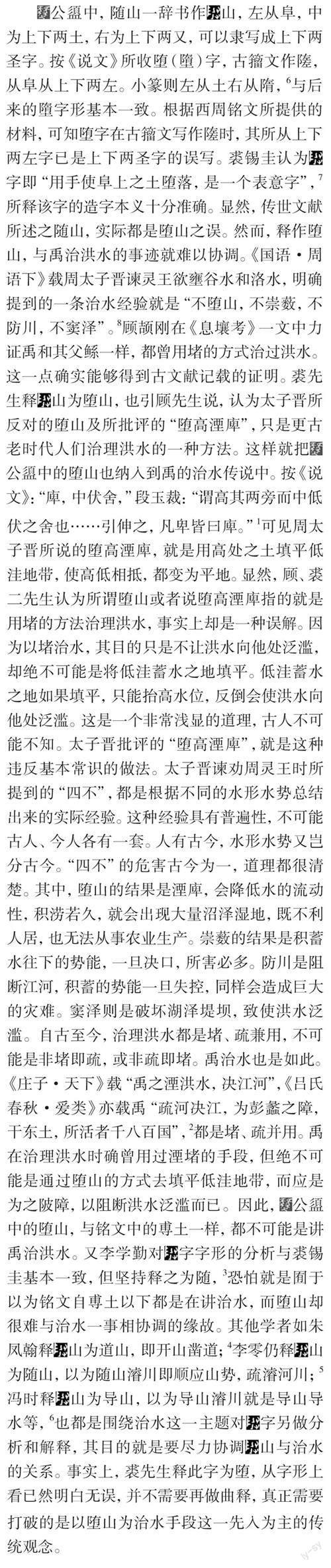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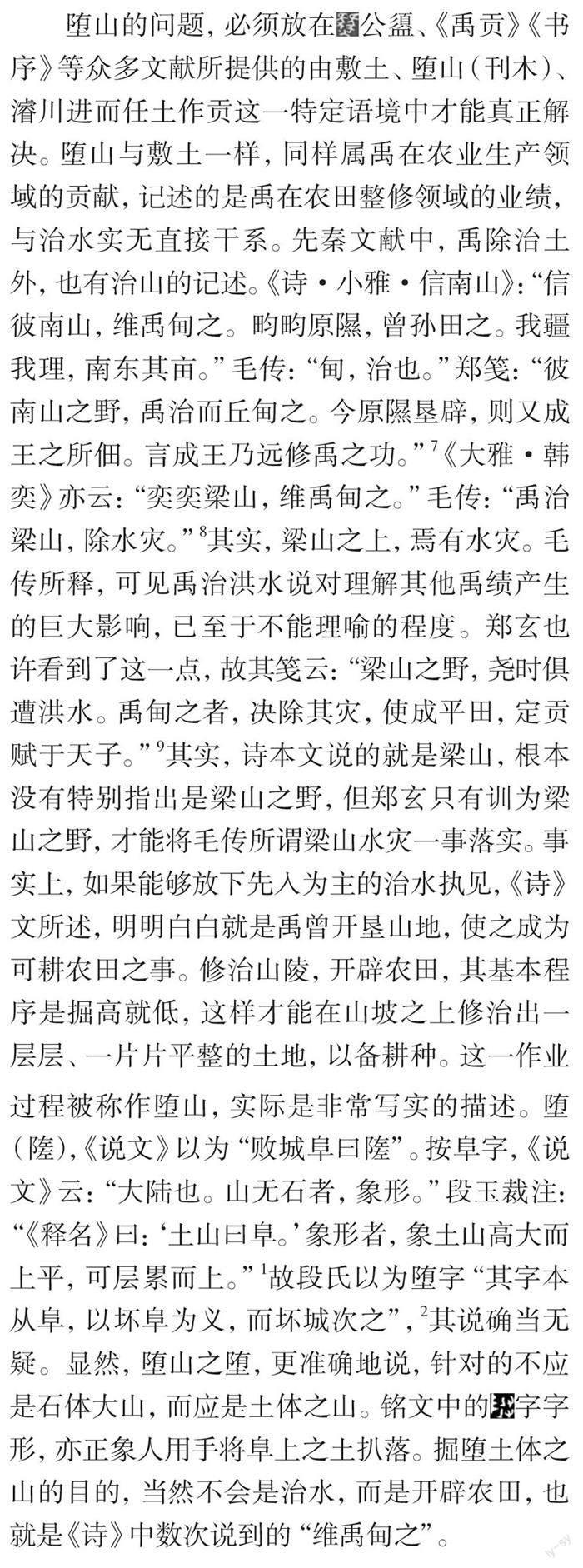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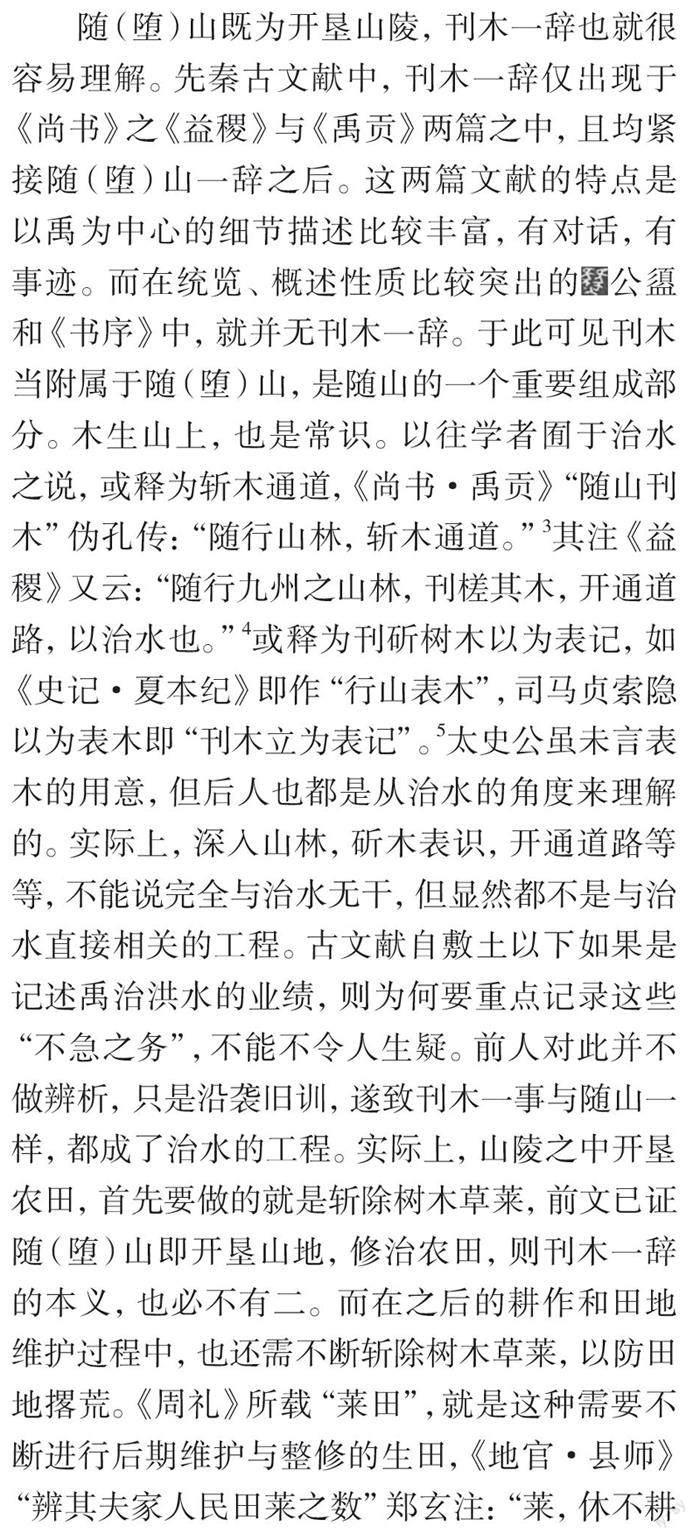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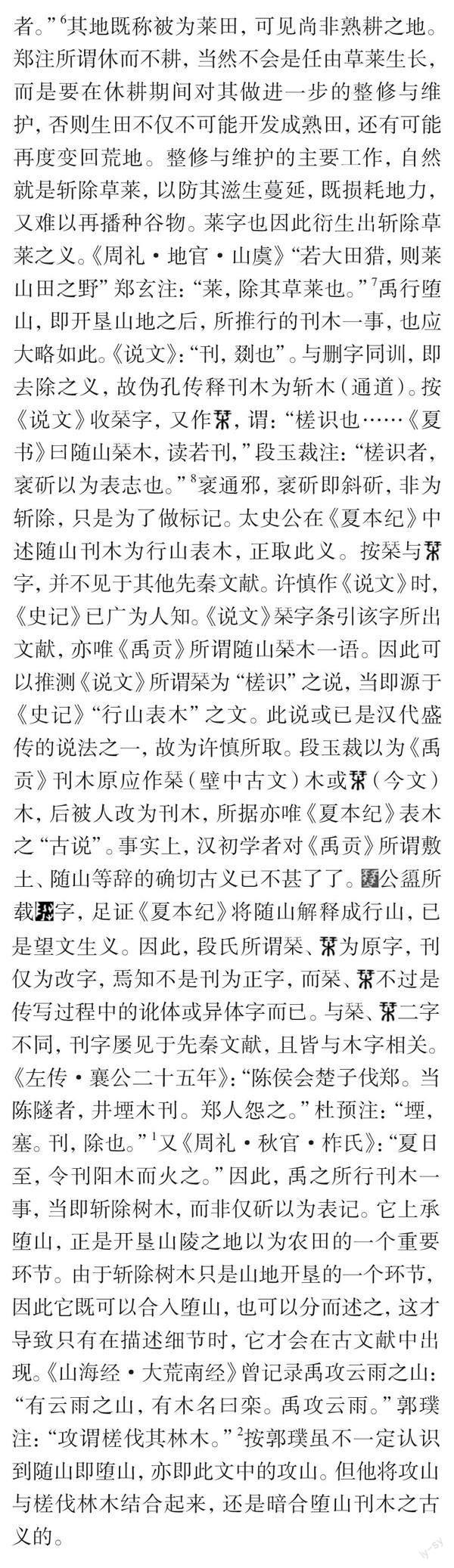
按《周礼·柞氏》所述,正是古人刊木垦辟山陵之法:“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阴木而水之。”郑玄注:“刊、剥互言耳,皆谓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为阳木,生山北为阴木。火之水之,则使其肄不生。”贾公彦疏:“此柞氏与薙氏治地,皆拟后年乃种田。”3柞氏与薙氏同为掌管垦辟土地之职,柞氏攻山陵之地,薙氏攻下隰之地。前者需要斩除的包括林木草莱,种类比较复杂。后者的工作主要就是芟除草莱。远古时期,在仅有木石工具的条件下,斩断树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要在山陵地带开垦大面积的耕地,就需要加快斩除树木的速度。郑玄言柞氏刊木与剥木都不过是斫去树皮,这显然更符合使用木石工具的实际情况。树剥皮则死,但只要树根尚在,底部仍能发出新孽。因此要永久地开辟出空地,就需要进一步“火之”,即放火烧之。郑玄注:“火之水之,则使其肄不生。”贾公彦疏:“斩而复生曰肄。”4火之水之,使其不再复生,这才最终完成了山陵之地的辟垦。阳木用火,阴木用水,即阳燥之地用火,阴湿之地用水,这大概是古人根据山陵不同区域土壤的差异分别发明的断根之法。而刊木之后继之以火烧,正是对广泛存在的早期农业的重要形态之一——刀耕火种的写实性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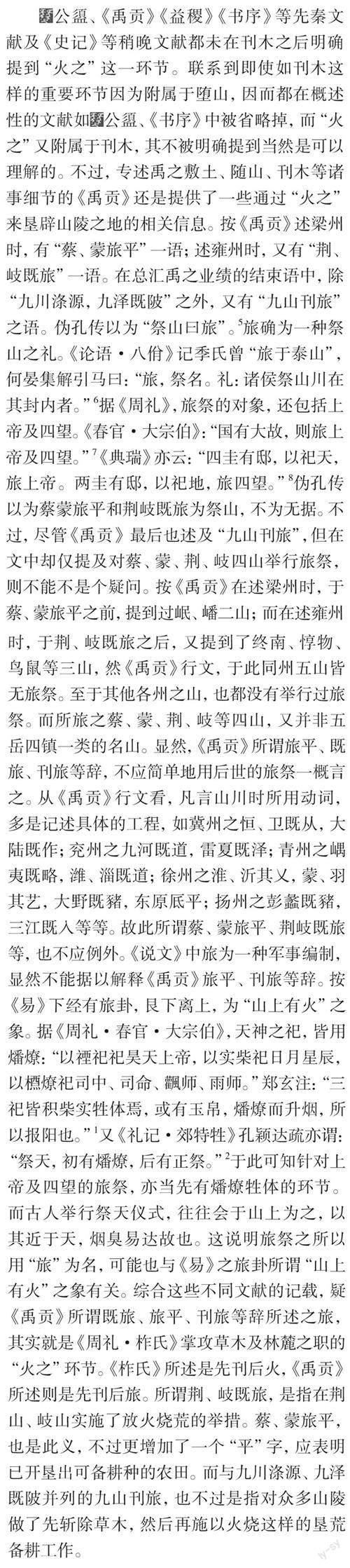

不过,濬川一事,确易与治水混淆。因为治水一事,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治理洪水,一种则是河流沟洫的日常管理。前人对此并没有做细致的辨析,导致讨论往往并不在同一个层面进行。严格意义上讲的大禹治水,就是指治理洪水。而在洪水泛滥之时,治水者或者是采取湮堵的手段来御灾,或者是采取疏导的手段来泄洪。在这一特殊时期,所谓“深其流”实在是无从做起。但是,针对洪水退后所形成的沼泽滩涂之地,确实可以通过深其流即疏浚小型河道的手段迅速清除积水和淤泥,使农田恢复耕作条件。在日后的田间管理环节,这一手段仍然既可用于排涝,又可用于灌溉,当然也会成为经常性的工作。禹的濬川,虽然广义上讲也是治水,但只能看作是敷土以下农田垦辟的环节之一,不能与治理洪水视为一事。除濬川外,《禹贡》还记载了禹“奠高山大川”一事,也涉及到河川。伪孔传以为是“定其差秩祀礼所视”。孔颖达疏则称“今始定之,以见水土平,复旧制也”。1传、疏所云,并不完全一致,可见所谓定其祭祀差秩之说,只是臆测,并无实据。按古文献中多有禹“主名山川”的记载。《尚书·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伪孔传:“禹治洪水,山川无名者,主名之。”《墨子·尚贤中》亦曾引述此语。又《大戴礼记·五帝德》云:“(舜)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王聘珍解诂先引《禹贡》之“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复引《吕刑》之“禹平水土,主名山川”,2可见王氏视奠高山大川即主名山川。据《禹贡》之本文,奠高山大川紧接敷土、随山、刊木等一系列恢复与发展农业经济的举措之后,而其后就是禹任土作贡的各项具体内容。显然,从语义的发展看,奠高山大川或者说主名山川,当是禹对九州形势及各州地理做了一次整体性的规划,是一項为推行任土作贡所做的重要的准备工作。
综上,禹绩中的敷土系列,发生在农业经济领域。它与治水前后相接,是禹在完成治水后所推行的发展农业经济的系列重要举措。禹在农业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其进一步推行任土作贡创造了前提条件。而贡赋制度的创设与推广,无疑又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要证明这么多的远古文明成就都是由禹一个人在短时期内创造的。禹只是这些伟大成就的众多创造者的杰出代表,由禹的事迹所折射出来的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成就及历程,才是本文所要揭示的历史真相。
[作者许兆昌(1968年—),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吉林,长春,130012;王一仲(1993年—),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23年3月15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