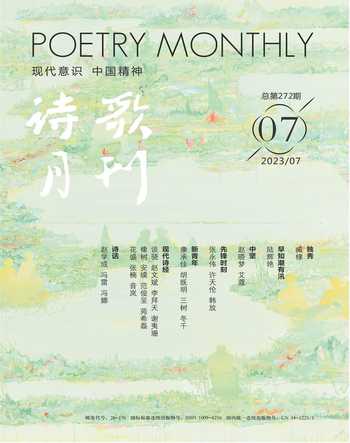梦境(外一首)
2023-07-26 02:37:06呼松涛
诗歌月刊 2023年7期
呼松涛
真是黄金的日子。鸥鸟预言般
立于桅杆。船长在船头
呼唤着他的大副
谁告别了九月的农场,谁就会
在航海日志上写下:
x月x日,朗姆酒甘甜,海风潮腥
夜色漫过船舷时,你正于一杯
成功的酒里,寻找橡木桶的气味
之后慢慢不清醒。你怀疑每块甲板
都有松动的可能性。正如你懷疑
那泥沙中的锚
正不断磨亮它体内,乐器的部分
“德瑞姆,德瑞姆
我遗失了我的六分仪。”
猫眼
猫眼再没有绽放过任何一只眼睛
他蜷缩在六月的房间,像
冰屋里的因纽特人
昨夜的肥皂沫,在洗漱池
完成一次英勇的坍塌
排水口,她的长发如海藻,使水流黏稠
像阳光拒绝晾衣架一样,她
仍旧拒绝了他的湿漉
于是,樟脑丸在衣柜兀自洁白
白鸽用扑簌回报吃食
风刮过楼下的红色大众
此类无意义,真是最中性的药剂
他从梦中醒来,左手撑着甲板
把身躯伏入海水里,眼睛
透过那狭窄的缝隙
在床底,他找到了他的拖鞋
猜你喜欢
内江科技(2022年11期)2022-12-19 14:59:20
孩子(2020年4期)2020-06-08 10:44:48
中国水运(2019年7期)2019-09-27 14:52:05
作文评点报·低幼版(2018年17期)2018-07-12 04:44:34
发明与创新·小学生(2017年8期)2017-08-04 06:44:10
少年文艺(1953)(2017年3期)2017-04-25 23:10:35
广东第二课堂·小学(2016年5期)2016-05-14 14:56:50
现代营销·经营版(2016年1期)2016-05-14 14:55:20
电子设计工程(2014年17期)2014-02-27 12:00:07
现代营销·经营版(2013年10期)2013-05-14 14: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