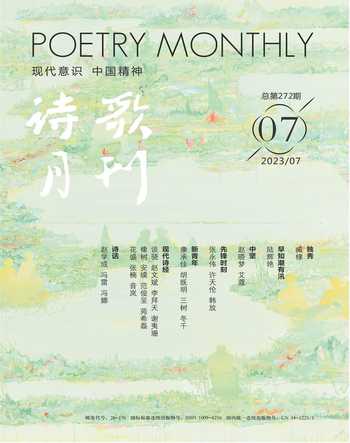植物现代性、主题性写作及其他
冯雷 冯娜
冯雷:冯娜好,春回大地,万物葳蕤,咱们就借机来聊聊“植物”的话题吧,当然这个想法不光是因为时令季节,还因为“植物”“风景”这样的话题近来似乎也引起了小小的关注和讨论。咱们还是先从你的创作谈起吧,你的诗歌中也多次写到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松果》《杏树》《宫粉紫荆》《苔藓》《风吹银杏》《橙子》,简直不可胜数,而且你对植物的书写也非常引人关注,有的研究者曾用“精神性植物视域”来加以概括,认为植物是跟你“整个的生命态度连在一起”的。你为何会注意到植物,植物和你的个人经历之间有什么特殊關系吗?你对植物是否抱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和寄托?有没有什么特别衷情的植物?请先说说自己的情况吧。
杏树
每一株杏树体内都点着一盏灯
故人们,在春天饮酒
他们说起前年的太阳
实木打制出另一把躺椅,我睡着了——
杏花开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还拥有一把火柴
每擦亮一根,他们就忘记我的年纪
酒酣耳热,有人念出属于我的一句诗
杏树也曾年轻,热爱蜜汁和刀锋
故人,我的袜子都走湿了
我怎么能甄别,哪一些枝丫可以砍下、烤火
我跟随杏树,学习扦插的技艺
慢慢在胸腔里点火
我的故人呐,请代我饮下多余的雨水吧
只要杏树还在风中发芽,我
一个被岁月恩宠的诗人就不会放弃抒情
冯娜:冯雷兄好,在我所生活的岭南,此刻已是初夏的风光,这也让我感到古人以“物候”观测的方法来认识时间和季节转变,是非常智慧的。植物,可以说是人类的“近亲”,是大自然的信使,我想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位诗人不喜欢植物吧(植物过敏症者除外),在众多诗歌书写中植物的身影比比皆是。你提到的我所写的植物,其实也涉及一个地域性的问题,譬如我写到的松果、龙胆草、山茶花等植物明显带有高原的物候特征;而宫粉紫荆、橙子、勒杜鹃等植物是岭南常见植物;银杏、苹果树、桃李等在北方广泛生长。所以,人们认识植物首先是认识一种地理特质,当然这些植物就像我们生命旅程中的过客,或与我们有故事的人。自《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中植物就不仅是简单的物象,而是寄寓了人类情感、情操的对象;我们今天看到桃花会想到“宜室宜家”、会想到“桃花依旧笑春风”,都是植物文化的积淀在起作用。人类与植物的故事是说也说不完,这也给我们创造了无数空间。在今天,我们认识植物的方式更多了,我们可以像博物学家一样,通过互联网技术迅速了解一种植物的生物特征,也会看到很多博物学著作翻译到中国,比如《玫瑰圣经》《花神的女儿》《被遗忘的植物》《森林之花》等等,它们完全是以植物为主体的写作,也为我们打开了很多认识植物的新视界。
冯雷:诗歌中的植物书写古已有之。在我看来,植物进入诗歌,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或者干脆概括为“植物现代性”。刚才你也谈到了《诗经》,据我所知,你对《诗经》尤其是《诗经》中的植物也很有研究。你觉得,古人的书写对今人有何影响?今人对古人有何超越?可否谈谈你的心得?
冯娜:你提到“植物现代性”,我注意到有一些批评家提出“植物诗学”(譬如王凌云),将诗歌中的植物书写作为研究主体。植物进入诗歌古已有之,从《诗经》时代“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到今天的“植物现代性”,其实包含的是人如何看待物的问题。作为“客体”的植物,很多都是这颗星球上的“活化石”,它们的生命比人类历史久远得多,从人类开始书写它们开始,历经几千年,除了少数灭绝的种类,很多植物依旧还在地球上生机勃勃。当然,它们的名字随着时代而更迭;比如,在《诗经》中的“舜华”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媚的木槿花、“芣苢”是常见的车前子、“蝱”则指贝母……在这些植物名字的变迁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语言的变革,还可以体会到古人今人在用什么样的心情和认知方式观照这些植物。我对古代典籍中的植物也谈不上研究,就是一种兴趣式的“按图索骥”。我出版过两本随笔小书——《颜如舜华——〈诗经〉植物记》《唯有梅花似故人——宋词植物记》,是以植物视角进入《诗经》和宋词的世界,去领略古人如何在天地山川植物中行走,又将怎样的情思寄寓于植物。在很多研究者那里,比如你提到的“植物现代性”,更多的是通过现代视野把植物作为一种文学方法和参照;而在诗人和作家笔下,植物是与人类“共生”的一种生命载体,是人类与自然交互的一种“灵媒”。由此,我也想到生物学博士、华大基因CEO尹烨曾说过,生命具有“亲生命性”,就是我们看到活的东西就会高兴,因为看到活物,意味着我们也活着;生命也具有“亲自然性”,我们说喜欢自然,其实说的是我们喜欢的是生机盎然、活泼泼的自然界。某种程度上,文学也是人类感知生命、通过与鲜活世界的链接、通过外界生命气息确认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田园牧歌式的、作为风景和背景存在的自然比比皆是;带着“人类中心主义”滤镜的生态观察不胜枚举。但是,人类身处的真实环境并不完全是生机盎然、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状况;特别是在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洗礼过的现代社会,要看到我们所处时代的自然和生态是复杂的、多维的,充满了不确定性。
如果要比较今人和古人对植物的凝视和书写有何不同,我想最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植物与人类生活的交互方式极大地改变了。譬如,今天城市中的人要观察植物,需要走进植物园或者到郊外、旷野中去,这和农耕时代“于以采■,南涧之滨”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了天壤之别。植物在古人那里是粮食、蔬菜、药物,是良木莠草;更是重要的物候,用以判断时令和节气。而在现代人这里,植物的功用性得到极大的拓展,我们对植物的认知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植物学、博物学的兴起也让我们可以从微观的科学角度来理解植物。但事实上,现代社会人与植物之间的关联已经不那么密切了,很多人已经不再可能生活在植物的环抱中。由于人工技术的介入,植物的“应季性”也不再明显,我们在冬天也能吃到大棚种植的“反季节”蔬菜水果,过去生长在深山老林的菌类或珍稀植物,我们现在都能在都市中见到。这种“物”的迁徙和变化不可能不影响人们对这些“物”的感知和情感链接,今天的人看到桃花都是种植在公园或作为行道树,很难体会“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人与自然、与植物的故事又该如何在城市中续写?最近几年开始提倡的“生态文学”“自然诗歌”等,我想也是一种回应。而植物这种物象,它所凝聚的诗人的意象,向来都是我们努力寻找的心灵的“对等物”。
冯雷:你所提到的“植物诗学”,其实在植物书写方面有特色的诗人不少,张二棍、宋晓杰、李元胜等等,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很长。去年,臧棣的《诗歌植物学》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无疑使得诗歌中的植物更加显眼了,同时或许也为当代诗歌在题材和方法方面提供了启示。你怎么看?
冯娜: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写作中,我知道很多诗人对植物很感兴趣,并有很多诗人对植物有深入的研究;比如诗人李元胜同时是一位生态摄影家,诗人沈苇写过很多西域植物,诗人路也也写过古代诗人与植物等。植物是诗人最容易攫取的自然界中最生动、活泼的意象,也是人格、情志的上佳载体。格物致知,中国诗歌传统中就是如此,当代诗人的植物书写更具现代意味和现代风格。说到植物作为一种题材进入诗歌,诗歌主题的整饬对于诗人而言,是创作整体结构性的统筹。很多诗人在实践中也表現出来这种独特的诗学追求和美学建构。臧棣的文本确实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样本,他的写作很早就呈现出一种题材遴选的自觉与筹谋;他的植物诗、动物诗,诗题“入门”“丛书”系列都体现了他对于自我诗学的整体性建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宏大叙事式微、日常生活与私人写作凸显的当代写作中,“写什么”这一命题又再次成为诗人关切的问题。写植物,是一种探索,传统诗歌中的植物书写和植物意象已经有着悠久的积淀,如何超越和突破其实是对当代诗人的挑战。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碎片式、零散的单篇写作,不足以支撑一个优秀诗人对世界、时代和自我的心灵世界做出整体性的观察和描述,寻找主题依然是作家或诗人的核心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她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融入西方文化的框架,每一首诗并非是单独排布的独立诗篇,而是一个有内在关联和延伸性的整体,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诗人对于世界的观察和理解所具备的那种稳定性和系统意识。对了,格丽克也写过很多植物,野鸢尾、延龄草、宝盖草等;所以植物题材不是哪位诗人的“发明”或“独创”;而是植物在每个诗人那里都有不同的精神投射和心灵映照。不论是选择植物还是选择某个主题,能够对自我创作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审视我认为这是当下创作者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怎么写”“为何而写”都将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
冯雷:植物等自然意象在诗歌当中烘托了抒情氛围,但显然又不只是作为抒情的背景那么简单。这个道理我觉得可以从小说中来借鉴。比如奥尔罕·帕慕克曾经说过:“景观的布局是为了反映画中人物的思想、情绪和感知的”,“小说里的景观是小说主人公内心状态的延伸和组成部分”,中国小说家很多也深谙此道。我注意到王干曾写过一篇文章《为何现在的小说难见风景描写》,王干的看法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共鸣,王春林、颜水生等做了跟进讨论。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王干是汪曾祺研究的专家,而汪曾祺曾在《说短》中明确认为“描写过多”是小说的一大弊病,他认为“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巴尔扎克的刻画人物均不足取”。我知道你其实也写过小说,对此你怎么看?
冯娜:我知道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讲风景、风物,包括植物等自然意象的书写是环境描写的一部分,用以烘托故事背景和范围等。但是难道我们没有在描写风物景致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单纯体验到自然之美吗?沈从文的湘西、阿来的藏地、汪曾祺的人间草木、李娟的阿勒泰……我想如果当代小说中风景描写的“消失”恰好对应的是人们故事发生的现场离自然风景已经遥远,发生在“格子间”、高楼大厦、工地路桥的故事必然是现代景观的描写。当然,单纯从小说的技术而言,风景描写肯定不能大量铺排以至于淹没故事主体;任何一种题材都需要“恰到好处”的魅力;我想您所说的是一个写作中“度”的把握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张九龄的《感遇(其一)》,“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通篇都在写植物、风景,但无一句不在讲人心和情志。又比如阿来在小说《蘑菇圈》里写了很多山地长蘑菇的景致,实际上也在写人和山林之间的情愫。我想,现代城市生活与自然风景之间的关系无需赘言,但人们的写作主题似乎更“精细”了;我们会看到大量分门别类的知识型书籍、类型化文艺作品涌现。说到这个,我联想到另一个话题。就是近年来由于互联网使文学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剧变,我们见证了“类型文学”的蓬勃兴起。白烨等学者认为类型文学是从网络到市场逐渐流行起来的,类型文学一般而言题材相近、受众群体相对固定。毋庸置疑,“类型文学”产生的基础是互联网带来的大众传播革命,受众需求直接影响到创作者的创作,从而细分市场。小说这一题材首当其冲地置身于这样的场域中,我们熟悉的科幻小说、穿越小说、悬疑小说、职场小说等门类越分越细,“越来越泛化、多样化”(白烨语)。你提到的关于植物、动物等书写的话题和研究我认为是跟这种题材的细分趋势是密不可分的。但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这种来自受众和市场冲击而形成的文学泛化和多样化,并未过多地影响到诗歌写作。一是因为诗歌本身属于小众艺术,不具备大众通俗阅读和传播的要素(譬如缺乏故事和情节、影视化的空间较小等);二是诗歌直接介入市场和商业运作的可能性远低于小说这种题材,使得诗歌一直处于大众传播的“低音区”。另一角度而言,也正是这种外部的喧嚣和推力往往并不切身“摩擦”诗歌,使得诗歌的发展遵循着自身内在的节律。就像我书写植物,在诗歌中我还没有像诗人臧棣那样把“植物”作为一种类型或系列的题材,可能就是自幼喜爱植物、经常与植物互动的性情使然。
冯雷:确实,或许是得益于科幻小说的强势崛起,这些年“类型文学”讨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就像你提到的一些研究者指出小说创作“越来越泛化、多样化”,相比较于小说创作中“分化”出了科幻、穿越、悬疑、职场、校园小说,有的人认为诗歌创作中没有出现类似的变化,乍看来也有一定道理。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植物书写,尤其是臧棣的《诗歌植物学》获得鲁迅文学奖给人以非常鲜明的印象,那你觉得类似于“植物书写”可不可以算是某种类型化的诗歌写作呢?
冯娜:“植物书写”只是“主题性”书写,还不能称之为“类型化”的诗歌写作吧?从类型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或可看出主题的选择与创作、阅读、传播接受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个有意思的情形是,类型文学似乎率先让创作者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他们对主题的选择是明确的,他们早早厘清了某类写作主题的创作理念和基本模式。至于“怎么写”“写得怎么样”,类型文学的评价标准也几乎脱离了传统文学的审美范式,直接面对受众的选择和市场的反馈。但就当代诗歌创作而言,创作者不可能认同同一套主题方法、基本模式以及相似的题材和艺术手段。学者吴承学曾在《论古诗制题制序史》中对中国古诗制题这一问题做了全面而精要的论述。他从“中国古代诗歌题目制作史”这个角度探讨了“创作意识的进化以及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中国古代诗歌经过从无题到有题,诗题从简单到复杂,由质朴到讲求艺术性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中国古体诗歌题目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对诗歌制题之“类”的考察,其实也是一种对诗歌内容的关切,如吴承学先生所说,诗题“积淀着审美历史感的艺术形态,从中既可以考察诗人创作观念的进化,也可以考察中国古代诗歌艺术风貌的历史演变”。近百年来,在现代诗歌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们创作观念、艺术风貌、主题选择的新变。某种程度上,诗人们创作主题的选择更加宽泛了;但就艺术创造性而言,新颖而纷繁复杂的主题涌现未必对应着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表达;而且对于前人已经涉足过的主题,要进行再创作的难度是上升的。
我们之前所说的主题先行的引导式写作固然有建构一个整体大视野的意义,但主题性创作往往僭越了诗意的偶发性和诗人的经验世界。就创作者个体而言,创作主题的选择首先来源于对题材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再结合自身的创作兴趣、学识积累和创作理念和雄心。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外部因素对创作者主题选择所施加的影响。比如,在《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我们看到卞之琳、冯至、燕卜荪、穆旦、王佐良、杜运燮、郑敏等诗人的诗篇,不仅是个人生命体验和诗学意识的求索,也是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民族危难之际,知识分子们历经屈辱的南渡、西迁中一种公共经验的集体呈现。历史将时代的主题袒呈于诗人眼前,时代的语境如战火的烈焰灼烧着诗人们的内心,写还是不写,这已然不是问题。另外一种对创作者主题选择的外部影响则来自于文学制度的倾向性和引导,在现当代诗歌中这样的例子很常见。最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题性的写作,比如脱贫攻坚主题的诗集《花鹿坪手记》(王单单)、《春天的路线图》(赵之逵),当代军旅主题诗集《岁月青铜》(刘笑伟),展现改革开放成就的相关诗集如《蓝光》(王学芯)、《新工业叙事》(龙小龙)等。雷兄对中国现代诗歌一直持续阅读,我想你目之所及,应该有更多的发现。
冯雷:确实,“主题”“题材”不失为是观察这些年诗歌创作的一个角度,远的比如说世纪初的“底层经验”写作,近的比如说近几年的“脱贫攻坚”诗歌。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来说,其中也不乏可圈可点之作。另外还有一些“行业诗”,比如“快递诗”“高铁诗”“石油勘探诗”“新工业诗”等等,这些实际上拓展了“主流”诗歌的题材范围。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些作品可能很难说是“主题先行”的,就像你所说的,是“对题材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再结合自身的创作兴趣、学识积累和创作理念和雄心”。所以这倒或许启示我们,大可不必挖空心思地去找题材、找主题,其实有诗意的题材、主题就像不知名的草木植物一样散落在日常生活里。
冯娜:说到底,写作还是一个人的孤旅,至于怎样认知世界、怎么发掘题材、建构自己的诗学空间,还是需要一个诗人在实践中去探索和创造。
冯雷,现就职于北方工业大学。
冯娜,现就职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