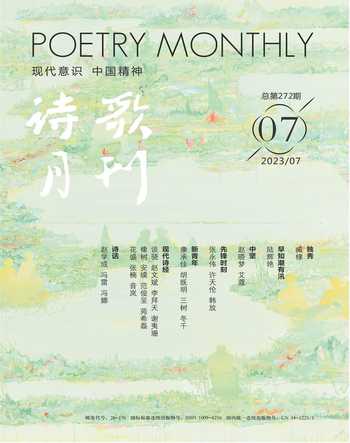巫山来信(组诗)
冬千
火山石
历史是多么有限的空间,而一次爆发
握紧双拳的巨石将膨胀,出口变得狭隘
作为一种孤独的存在,绝对地成为
倒影的面具,火塘假装是镜光,使牛羊
和牧歌的方言由此清亮,偶尔我也
坐在石上,不停更换坐姿,找到最痛的
那种,像鹳鸟啄住了一只木笼,两块
虫蛀的拼图,裂纹在吻合的须臾
就造成了我们和余光仍有一道背影的
距离,为此我总往这座火山的一小
部分灌水,熄灭无意中复燃的旧情
甚至植入水藻,放进鱼缸
我越来越讨厌做一个旧派的人
除了自己的所有事物,仿佛都在趋于
那个隐遁的极端,我早已习惯像潜浪
暗礁,独立而内敛着生命的激情
“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珍物”
夏霁书
云朵撒下那些珠子,如此清澄又易碎
拥向土壤,以维持水的完整
牛肝菌从湿透的木桩隙间
撑开了身体
像折叠的纸张起翅膀
“让它自由,变成蝴蝶”
虫类世界的箴言,不止一次
被我们用来安慰。菌群在低处
那些伞篷覆盖的,又是一个微茫
的世界,野蘑菇护佑着
蚂蚁,它们身怀知足的心情
迁徙繁衍,凭雨止渴
手持电筒的少年,出没在凌晨
谨慎地刨出菌菇,再把土填回去
并不是葬下什么,我们感恩
所有失去的殖土,转晴之后
山地松软,是净土放下了戒备
少年游
骑行途经这段路,每次我都小心翼翼。
道旁侧柏长着蜂巢,和雏鸟
在疾驰的货车盲区里
啄食面包糠,一旦有羽毛凋零了,
我就仿佛看到满地刺透我的箭镞。
受过多年时间的蜂蜇,骑行的
我,穿过这棵行道树时,仍
不自觉地减速,仿佛不远处
梦中的孔雀,在朝我开屏,
每根羽毛,都有感泣和自尊的形态。
巫山来信
掠过他头顶的,几对飞燕,还有火烧云
“它们一直燃烧,就好了。烧到天边
至少要,你所及之处。”如果一直这样
浮云比樱花永恒。从中他得到
爱的启示。他跑进涧底,读写给她的信
向瀑布后的听众。仿佛如此,回信
才足够及时。流水反复地念
幻听成雨声乱作一群细蚁,排好队搬家
在土地沾湿之前,他梦见它们的秩序
竟然情话般完整。生活将在新的穴道开启
雾起山中,空蒙如柠檬水
块垒凹陷,僵涸的心事被澆释
相爱的过程,一个灯谜的小暧昧
认出会更艰难。水汽怀疑我们
是否仅是露水的关系。退去的时候
我们呆在原地。云的余烬被吹散
是花神降临,他的手心被误认为雄蕊
“我知道如何爱了,就这样,一瓣一瓣的
没有放弃,那意味着枯萎。”
分水岭
爬上绝顶,面前是阳宗海
身后是松茂水库,曾经
欺负我的那些乌云也经过这里
雨滴在两条歧途上无法三思
曾经我们的郊游队伍也经过这里
我们分头去拾柴禾,我们一直
沿着泥流,边哭边奔跑,边犹疑
在距离不明的两片水域之间
架火取暖,柴焰像沉默中
挣扎的信号,直到今天
也没有灭,毕业后每当我登上
一座分水岭,似乎就听到
有人呼救,我躺在岭中的空地
想象大雾里一朵芳华不再的花
随风吹熄了淡水湖上的烟火
几缕烟乘风而起,在岭头见面
动物园
后来我越来越讨厌,用嗜好和审美
去成立一种规矩,尤其在栅栏里
那些铁笼钳制了犄角和根须
蔓延整个森林内部,就像那些年
要讲的每句情话,都要悄悄地说,以致于
你每个富于观赏性的动作
都被我看作手语,一句口齿不清的话
在长颈鹿的胃中反刍着
我赶了夜路来这里,把月光烙在
我的镜框、臂章以及一切反光
的事物上,劣迹斑斑
最忧虑的是禽类
我都在靠近,逼它们扑腾起来
而另一个受惊者,时而
是如虎添翼的我,时而
是插翅难飞的我
不出意外的话,我一直以
后者的身份,混在人群里,一声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