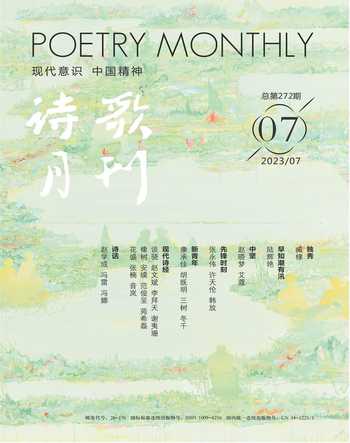一个叫白鹤尾的地方(组诗)
陆辉艳
岛上
几只猴子嬉戏着
从树洞里觅食
风吹过南湾岛和人群
被它饲养的下午过于磅礴
渔船停靠在浅滩,有人正拿着铲刀
敲打船身的锈迹
不远处,一个女人蹲在礁石上
细心地挖着牡蛎,手中的工具——
一把缩小了的镐头在挖着现实
牡蛎壳与岩壁融为一体
看起来,就像从石头里
不断取出鲜美的肉
大海一遍遍将它的泡沫传递过来
我弯腰,取出这饱含盐分的
天空的回音
(发表于《诗刊》2022年第10期)
强迫症
那个手提两袋垃圾的人
步子飞快
她把它们扔进垃圾桶
“钥匙……”她喊了一声
转身走回垃圾桶旁
两个垃圾袋被逐一打开
露出里面的内容:水果皮、旧牙刷、纸巾
碎瓷片,几个空的易拉罐
她重新扎上它们
这次她走远了
如果她再次转身回来
跟我预想的那样
重复打开那些生活的废弃品
寻找一把旧钥匙
我写下的,将会是这样:
她徒手拆毁了时间
最后将自己缝合
(发表于《十月》2017年第3期)
一顶帽子
小时候,有一年冬天
和玩伴互换帽子。我的蓝帽子递给她
她的红帽子递给我。半旧
却新鲜的帽子,不属于自己
我们各自戴在头顶,好像额外多出了
贫瘠生活里的一件礼物
不久,我们起了争执
她把我的帽子,狠狠踩在泥地里
紧接着,又迅速夺过我头上的帽子
——那是她的
她的动作如此连贯,毫不犹豫
至今我尚未反应过来
而我始终没能走到自己的对面
去看看那时的自己
我只是默默弯腰,捡起弄脏的帽子
抬头的瞬间,看见屋檐下
一排整齐的冰凌
它们尖利的锋芒刺痛着我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迟到的痛楚
曾是我写下它们的缘由
一个叫白鹤尾的地方
那块写着“白鹤尾”的标牌,应该早就在那里
因为不起眼,很少被来往的人注意
偶然的一天当我停在岔口处
发现它时,还是有点惊讶——
不远处一定有一片湖
栖息着一群白鹤
这强烈的念头促使我往岔路深处走
经过寂静的芦苇丛
一只蝴蝶翩跹在前方
像在给我引路
每到转弯处,我都让自己
保持着很轻的呼吸,担心惊吓
那随时出现的白鹤。但直到
走到路的尽头——没有湖
没有期待中的白鹤
原路返回时,我感到脚下的路
比来时更为悠长,它显现出
有如鸟类脖颈般的曲折
当我停下来往回望
白鹤已全部飞入激荡的想象中
缓冲
一排挖掘机,停在一个新的楼盘前
黄色铲斗垂下来,像在集体给大地鞠躬
它们埋着头,改变了这个世界
而我埋着头,却难以改变微小的部分
这多么悲伤,并不因事物生发类比
时间强大到可以改变万物的旅程
以至于古老情绪的触角,仅能触及有限的
认知:如此狭隘,通往光芒的入口
在热闹的尘世之外
因而我一次次俯身,为写下的某个句子
制造自动回归的合页,以缓冲身体里
日益密集的狂风和记忆
悬崖
阳光下,电线杆在路中央
投下一道阴影
一群黑山羊翻过坡地
来到大路上
面对这道厚重的阴影——
眼看就可以过去了
领头的那一只却凭空跃起
羊群跟随它,像一群影子
奋力跃过另一道影子
眼看最后那只瘦小的羊
也要跟着跃过去
可是它没有。它悠闲地甩着短蹄
踩着那道虚无的悬崖
慢慢踱到大路对面
眼看太阳就要隐入群山
路上已无阴影
眼看夜色就会覆盖一切
赶路的人放下他在尘世的悬崖
将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
在定安古县衙
天空要回避什么?
站在定安古县衙门前
对面的中南街开始下雨
雨不徇私,不舞弊
它下在屋顶、古墙和墙缝长出的青草上
一双拖鞋蹬着的三轮车
在湿漉漉的街道,留下模糊的车辙
时间要回避什么?
禁止喧哗,但雨水和鸟儿除外
它们鸣响之外的事物,如此肃静
雨停了,地砖上的脚印
凌乱且生动,轻如树叶投在大地之影
重如惊堂木之声响
似在审判,似在沉思
光
对光敏感,但对光亮的事物充满喜悦
天黑了,木质乐器在空气的摩擦中
发出颤音,那音色中的闪光
让我想起骑行途中,次第亮起的灯盏
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按下开关——
而光线真的存在吗?
——它来自于对光的想象
万物得以被看见
光的产物:影子,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内心的想法一再被投射
而我们用厚重的织物控制它,遮挡它
当木窗开启,光涌进来
鼔满风的窗帘,像两张被掀起的帆
带动我们居住的方形屋子,在激荡的
善于遗忘的生活中保持平衡
去南城
多年前的月亮,一直高悬在城市上空
有一张永不过期的火车票
它印上我的名字
为了不可更改的光阴
在新开发区的腹地,有一个
大型客运站,但并不通向我想去的某地
它待在越来越深的秋天。像一座
银色城池。这么多趟夜行客车
等着人去搭乘,旅途漫长
是凌晨三點的梦魇、小叶桉
立交桥一晃而过,熟悉的面孔
镜头似的一再浮现在夜幕中
集装箱房子
码头的装卸工纷纷走下船舱
在河边拍打身上的灰尘
有一个头上沾满草籽
远离了同伴
他停下来看了看江面,点燃一支烟
路灯下他的影子
像一件揉皱的衣服
摊在大地上
他抽着那支香烟,经过水位观测站
小卖部、家庭旅馆、路边炒粉摊
经过春天的木棉,有些落在地上
沉重而美好,像许多人的一生
再经过一个施工工地,最后
他走进一个白色集装箱房子
里面亮起了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