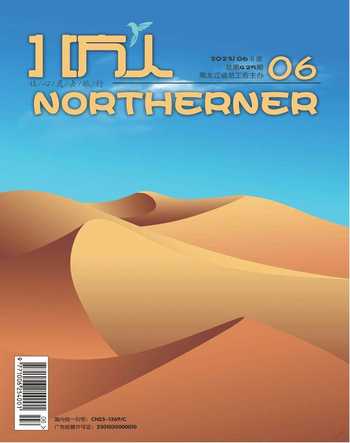没有电的夜晚,星星特别耀眼
杜佳冰

北京第N轮沙尘过境后的夜晚,我终于看到了一颗星星。
它在天幕中清晰地闪烁着,小而亮。我不是天文爱好者,也不懂星体的方位、名称或寓意,只是因为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夜空而开心——仅此而已。对现代人而言,连续一个月看不到星星,并不是一件会阻碍生产生活的事。
放在几千年前,阿拉伯半岛的农作物或许会因为看不到星星而枯死。为了减少蒸发,阿曼人习惯在凉爽的夜晚灌溉,他们用星星计时。有人按星星从地平线升起的时间计算,有人则对比人造标记的方位,以此判断何时供水和停水。失去星星,就失去了一部分时间。
只有在电力照明系统供应之前,一颗星的光才显得十分明亮。为了还原那片古老的夜空,人类学家南希·贡琳、阿普里尔·诺埃尔在新书《古人之夜——古代世界的夜间生活考》中编集了18篇论文,探索一个问题:“在电力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度过夜晚的?夜晚是如何同时做到解放人和束缚人的?”
当古代世界的最后一丝暮光消失,温度会随之下降,味道和湿度也发生变化。有些花朵是响应月光生长的,随月亮的出现散发出香味。
视觉受限开始让人感到不安。玛雅人会将最白的土壤铺在道路表面,或是嵌上闪闪发光的白色石头,使其最大程度反射月光,照亮脚下的路。
即便如此,黑暗笼罩下,一切都是模糊和危险的。因此,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夜晚常被用来比喻死亡、邪恶、孤独和苦难。
之后,火光亮了起来。古人围坐火堆前,开始享受夜间最受欢迎的一种娱乐方式——讲故事。“在黑暗中和火光下,社会关系、叙事风格和互动形式都会不同。”学者帕莉·维斯那对比了西非的朱·霍安西人白天与夜间的对话,发现他们白天的谈话围绕着批评、抱怨和冲突,而夜间对话中八成以上都在讲故事。“晚餐后,天黑了下来,白天恶劣的情绪变得柔和,兴致勃勃的人们聚拢在炉火旁交谈……”
这是夜晚的情绪。在夜色的天然掩护下,巴哈马种植园的非裔奴隶会自由地舞蹈。他们戴上面具,穿上戏服,跟随羊皮鼓和牛铃的节奏舞动游行,直到太阳升起。这是属于他们的狂欢节,是本土文化认同和自我掌控的时刻,也是“自由而非奴役的象征”。
火光第一次改变了人类的昼夜节律,增加了社会互动,也延长了生产时间。纳诺梅阿岛的原住民会点燃用椰子树枝做成的火炬,跟随月亮与潮汐的指引出海。船上的火光使哈维鱼跳起来,渔民便将它们网住。这种鱼是他们日常的主要食物之一。
历史学家罗杰·埃克奇认为,相比白天,古代的夜间劳动和社会交往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工作会和娱乐混在一起,“其特点是欢聚一堂和结伴而行”。
夏威夷群岛的渔民认为,黑暗中的太平洋并不是“一望无际的危险地带”,因为星星是“夜海中的岛屿”,能为他们指引方位。星空的富足还与大海的富足浪漫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会说:“今晚有鱼,因为星星在闪烁。”
《古人之夜》提到,“无论是战争、耕种,还是其他象征性的活动,人们当时都必须密切注意月相……以至于它们被神化了。”
夜空提供了一块画布,古人以此记录和延伸他们的宇宙观、神话、宗教和占星术。公元前1800年前后,安第斯山脉的一些地方为了观察夜空,还专门设计了下沉式庭院。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族女酋长习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她说:“如果午夜梦醒时分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
古人失去星星的无助感,或许我们只有在停电时才能体会。
街边小店的老板到了停业时间才会关灯,拉下卷闸门。那扇铁皮老闸门干脆爽利,哗啦一声,宣告他的夜晚降临。之后他回到家,洗漱后关上卧室的灯,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步:黑暗中仍荧荧亮着一小块手机屏幕的光,是现代都市人睡前最后看到的星星。
《古人之夜》形象地记录了变化到来的那一天:“现代城市文化与夜空的联系于1880年12月21日当天下午5点25分正式断开,托马斯·爱迪生按下了一个开关,将曼哈顿百老汇大街上的一长串白炽灯连接到了他附近的直流发电机上,一瞬间,电灯泡就把黑夜变成了白天。从那以后,城市中的人几乎从未真正把自己置身于黑暗当中。”
人类仅用100年时间就点亮了地球。在那之后,“夜晚不再被看作是神秘和不可思議的,而被认为是光线暂时消失或被中止,并且应尽快悄无声息度过的一段时间”。
人们失去了与夜空的亲密关系,赢得了白天。
但美国作家简·布罗克斯提醒人们:“回想过去,问问自己,光明对我们的阻碍是否比黑暗对我们祖先的阻碍更严重?”
(摘自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