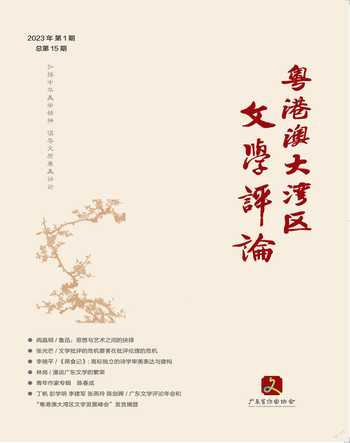鲁迅:思想与艺术之间的抉择
阎晶明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鲁迅一生思想与创作,以及参与社会革命的特点,分析了三者之间构成的复杂关系。回应了关于鲁迅文学成就究竟何在,參与社会革命的方法策略,以及在思想上体现出的深邃性等问题。试图打开认识鲁迅的思考维度,为树立鲁迅的当代形象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鲁迅;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选择了不止十种开头,都很痛苦地放弃了。谈论鲁迅是如此困难,哪怕要说出一丝半点琢磨好的“新意”,也得罗列出一大堆例证,讲清楚与以往各种评说的不同,才能小心翼翼地推出自己的看法。没有这样的逻辑过程,谈鲁迅是浅薄、单薄而没有说服力的;有了这样的繁复过程,那自以为是的一丝半点新意,又常常淹没在漫长的论证过程和引言当中,很少能得到别人的认知。或者,自己的看法本来就没有什么新意可言,只是阅读鲁迅原著时常有所感,阅读研究论文过程中又想与之讨论造成的某种心理冲动而已。但的确,在庞大的鲁迅研究背景之上,在鲁迅形象不停地被翻转的情形下,关于鲁迅,仍然有很多基本的问题有待不断地评说。
今天,我就想谈谈这样一个话题:鲁迅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说他是文学家,也有人说,不是连长篇小说都没有么;说他是革命家,也有人质疑,鲁迅为什么不骂蒋介石;说他是思想家,更有人会问,他的思想是什么,表达其哲学观的哲学论文是哪几篇。是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学术讲座的互动环节,在论文电子版的留言当中,在很多正式的文章,非正式的自媒体上,关于鲁迅的讨论并不会随着数量的增加,人数的增多而深入,反而越来越走向平面化、表面化。但并非不值得、不需要研究者去面对。经常有学者会面对读者、听众类似的提问,直接的、简单的回答也许可以是“理那些瞎说干什么”。但这终究无法有助于解释任何疑惑。
这种众说纷纭本身也体现着鲁迅的复杂性。而同时,所有这些又都因为对鲁迅复杂性认识不足造成的。我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终结性的答案,但也想就如何理解鲁迅形象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几十年来,这几乎是对鲁迅形象定位的定论,而且普遍认为,比起其他同时代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鲁迅多出来的身份与荣誉。三种组合,的确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而且明显有别于其他的作家。但这三个称号不能完全等同于叠加。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系有必要加以强调。鲁迅对文学的艺术的追求,与他在现实中遇到的社会斗争及短兵相接的战斗,与他个人的深邃、复杂的思想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纠缠、相互纠结、此起彼伏、波动不居的关系。理解鲁迅生命历程和鲁迅思想,阅读和阐释鲁迅作品,这三者之间构成的复杂关系,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角度。
我想就此漫谈一点自己的认识。我的谈论肯定是不周全、不系统,甚至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的。但愿意就此继续探讨下去。因为回答好这些问题,不但对认识鲁迅,而且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不追求“纯文学”的文学家
与其重复式地通过评价鲁迅作品的成就来强调鲁迅是第一等的文学家,不如看看鲁迅本人的文学观。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他的文学观其实十分复杂。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构成其文学的重要支点,或是我们理解鲁迅文学观的主要根据。
对文学的功用和价值,从弃医从文那天起,鲁迅就已经认定而且从未放弃。青年时期向往并相信“摩罗诗力”,真正走上文学道路后,依然相信“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鲁迅终其一生的事业就是写作,无论他的文学观发生怎样的变化,从未放弃过读书写作本身。有时我们也看到他似乎是不得以为之,但说到底还是文学信念所致。
在鲁迅心目中,没有离开现实社会的纯文学。文学的功用有时并不在其自身的高雅、风雅,而是其对社会、人生具有精神引领的作用。哪怕是写作者只为一己之利而写,那也是他参与社会的明证。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通过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评价,证明了作家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可能离开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这既是作家主观上表现出来的,也是文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2反对“贵族”式的风雅是鲁迅一贯的文艺观。“文艺家自惊醒了所谓‘象牙之塔 的梦以后,都应该跟着时代环境奔走;离开时代而创造文艺,便是独善主义或贵族主义的文艺了。”3事实是,文艺不可能脱离时代而独善其身,贵族主义不过是一种梦幻和自以为是而已。鲁迅对陶渊明多有评价,而评价最集中的一个观点就是,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并非真正的超脱,一样是在其温饱前提下的抒怀。“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4
那么,是不是鲁迅就视文学只是为社会革命的工具而不讲文学性呢?正相反,成天把革命文学的口号挂在嘴上,创作却乏善可陈只求革命的文学是非文学。尤其是到了二十年代末,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诸人因革命与文学问题产生论争,让他进一步深入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客观上也让他的文艺观更加全面、丰富。他说:“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他反对只把文学当作革命的工具而不讲艺术规律,不讲艺术本身的要求。“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这是说,文艺之流,从最初的什么主义到现在的什么主义,所写着的内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练的才技,造成一篇优美无媲的文艺作品,终是一样。” 对于创作者而言,“他们有表现或刻划的才技,他们便要如实地写了出来,便无意地成为这时代的社会的呼声了。然而他们还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1。他强调“精刻熟练的才技”对于艺术的重要,甚至认为,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有时会艺术地在无意中触及到了社会时代,即使是在意识上不自觉的,在表现上也不激烈和引人注意的(如陶渊明),一样也在其中流露出于时代生活及政治的态度。在强调文艺自身规律的同时,又反证了文艺与时代的关系。
鲁迅对于文艺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自有其深刻的思考,在总体一致的同时,也有随时代与文艺的发展而变化的多样复杂。鲁迅对自己创作多有自我评价。这些评价里一样透露着他的文学观。这种现身说法,更可直接见出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
总体上说,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视作“纯文学”(借用一下当代文学的概念)。我们都知道鲁迅有“遵命文学”说。说清楚鲁迅的文学观是个复杂的话题,我在这里首先想要说明的是,的确,鲁迅从开始就没有打算做一个优雅的、纯粹的文学家,没有打算在象牙塔里优哉游哉的想法。这一点,从他对自己作品在体裁上的定位即可见出。
鲁迅从来不把自己的作品视作某种纯而又纯的文学,因为创作目的和读者目标的不同,他对自己的作品在文学理论里叫什么,属于不属于其中的一部分并不关心,甚至自己的作品属于哪种体裁都无关紧要。比如对自己的小说,他说:“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2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3不难看出,“小说模样的文章”“蒙着小说的名”“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都是在“小说”之前加以并不确认的限定,这种表述决非偶然,也并不完全是谦虚,实是透视鲁迅创作观的一个侧面。
不独是小说,对自己其他方面的创作,也一样采取这种略带“解构”意味的表述。《朝花夕拾》是公认的记事散文合集,鲁迅自己却认为其中的作品“文体大概很杂乱”。1
对于自己的无论新旧体诗歌,更是要推动诗人头衔。“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凑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2关于散文诗集《野草》:“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3
总之就是,鲁迅每每总要为自己的创作在体裁面前加上一个略具消解意味的限定。我过去评说这些概念时,总认为这是鲁迅的一种谦虚。这当然是的确的,但除此之外也是鲁迅的文学观、创作观决定了的。鲁迅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鲁迅对杂文文体始终持辩护态度。他的辩护里,含着对杂文匕首投枪作用的坚持,并不打算得到文人学者赞许的笃定。“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4
鲁迅的作品,即使是从体裁意义上讲,都是极具开创性和“标准”价值的。但我们必须说,这些认定是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确认的,鲁迅自己更多地称自己的各类作品为“文章”,并没有特别强调在艺术上的优先地位。这不仅仅是一种谦词,而是鲁迅文学观及写作目的在创作上的体现。鲁迅说:“所以我的一点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这“悲哀”如何读解?正是鲁迅认定的,只要自己文章中所批判的积弊得以消灭,自己的文章也应当随之速朽。之所以还被留下来甚至入史,那实在也是所指问题依然存在的旁证。这才是最让人悲哀的一件事。
一切论说都指向一个论点:鲁迅是一位并不追求“纯文学”的文学家。
二、不主张无谓牺牲的革命家
鲁迅是革命家。这是后来者给他的命名,也是随着鲁迅声誉的不断增长而被确定下来的。如何理解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其实历来存在着分歧。鲁迅在世时,文学革命家们却经常会以失望的、不满的态度批评鲁迅不够革命。鲁迅的论辩并不全是同现代评论派展开,而且也要同革命文学家们争论。从青年时期起,鲁迅就是革命的向往者和践行者。这一点可以说终生都未动摇和改变。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鲁迅对自己的恩师章太炎的评价事实上就是坚持现实的革命观所得出的。“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5。为国家民族而投身于革命,在唤醒民众精神上做出最大努力,这是鲁迅矢志不移的立场和志向。
但我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鲁迅在为革命呐喊的过程中,始终有一条充满复杂思考和人间亲情友情关怀的认知,即他反对在革命的进程中做无谓的牺牲,更反对打着的旗号诱惑他人尤其是青年去付出无谓的牺牲。鲁迅当然是支持并爱护青年投入革命当中的。“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1但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则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2這里的“浪费”,尤以单纯的青年受人鼓惑而无谓地牺牲生命。那些自己躲在享福的地方,鼓惑别人去革命的大有人在。“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3他反对这样做,也警醒青年要有自觉的意识。“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4“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5鲁迅在杂文《牺牲谟》里活画了一副专门鼓动别人牺牲,自己却在享福中夸夸其谈的虚伪者的嘴脸。“我最佩服的就是什么都牺牲,为同胞,为国家。我向来一心要做的也就是这件事。你不要看得我外观阔绰,我为的是要到各处去宣传。社会还太势利,如果像你似的只剩一条破裤,谁肯来相信你呢?所以我只得打扮起来,宁可人们说闲话,我自己总是问心无愧。”6
鲁迅自己,则信守这样的原则:“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7“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但鲁迅对此是有自己解释的。“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8这里的发展,就应当包含着现实的革命,为此而战斗甚至牺牲。同时还应看到,随着对社会现实的认识,鲁迅的革命观也有变化、发展和深邃的过程。其中一点就是,从青年时期的崇尚“摩罗诗力”,到后来的强调韧性的战斗。因为现实太难心迹,单纯的热血很容易冷却,信念也会发生动摇。认识到革命的艰难,才能做出正确的革命行动的抉择。所以他强调现实的中国“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9。
鲁迅的革命和战斗不是盲动,却也不是因怯懦而退却,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所能做的和应该做的,也知道斗争必须同时也要讲究策略和方法。冯雪峰回忆说,1930年左右,“我们曾经希望他写些宣传当时政治口号的文章”,鲁迅则表示:“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些杂文,我比较顺手。”1通过写作投身和参与革命,鲁迅也一样有自己的判断。“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2
这里还想部分回应一下鲁迅为什么不骂蒋介石的问题。陈漱渝先生新近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鲁迅与蒋介石》一文正面回应了这一问题。如果从鲁迅的斗争策略角度讲,还可以进一步以史料来证明鲁迅的初衷。冯雪峰曾说:“一九三〇年夏天,李立三同志约他(鲁迅——本文注)见面谈话,他们两人讨论过关于鲁迅先生自己的战斗任务和方法问题。”3这次发生在5月7日的会面内容,后来者的回忆也各有所说,我以为鲁迅三弟周建人的说法基本符合鲁迅的本意。“鲁迅同我讲过他见了见过一次李立三。他说:‘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阵地,同国民党进行韧性战斗,要讲究策略,……”4我们从《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中可以知道,鲁迅对待革命,尤其是青年的战斗,是十分强调方法和策略,而非一味鼓惑人去做无谓的牺牲。但到自己该挺身而出时,他却从不退避。杨杏佛被国民党暗杀后,鲁迅不顾通缉的风险,毅然前去送别即是一例。
如何理解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仍然是一个深广的课题。而我在这里只取一端,试图说明其中的复杂面向。
三、没有哲学体系的思想家
我时常会跟朋友谈到这样的话题:究竟能不能说鲁迅是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人们总是说从鲁迅作品中获得思想,感受到鲁迅的深邃。但鲁迅的思想精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是一位现代中国的哲学家的话,他的哲学著作是哪一部,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什么地方?回答这样的问题的确很难。鲁迅自己说过:“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完美的文章,既没有主意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5哲学体系的建构,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6这就说得更透彻了。不但不想,而且厌恶。
那怎么还能说鲁迅是思想家呢?或者至少说,他对中国现实、历史、文化以及国民性的揭示入木三分,但要上升上普遍的哲学的思想,未免太牵强了吧。这是一个涉及一系列庞大问题的话题,需要讨论的侧面太多。在我看来,鲁迅是思想家,他的思想同时也闪现着哲学的光芒。虽然并没有体系建立,却明显可以感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后人的总结也许永远达不到他自身的丰富和深刻,但基本认知应该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从哲学上讲,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也是典型的具有成熟的存在主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無论在思考社会人生的层面上,还是在表达的方法上,都与存在主义哲学家具有最大程度的相似与吻合。
首先,鲁迅是介绍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克尔凯郭尔的第一人。1907年所作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中指出:“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即克尔凯郭尔——本文注)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1同时介绍了尼采、叔本华等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哲学家。鲁迅对这些人物的思想和文章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认同。俄罗斯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认为是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鲁迅则对陀氏的文学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其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2。
存在主义是最具文学性的哲学。《存在主义》一书的编者考夫曼曾在其前言中指出:“存在主义不是思想上的一个学派,也不可以归属于任何一种主义。”“将传统哲学视为表面的、经院的和远离生活的东西,而对它显然不满——这就是它的核心。”3这种反传统哲学的姿态,同时也体现在文体上。因为它极度强调个人,每一个思想者都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谈论个人、世界和宇宙。存在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著作有时是寓言,有时是散文,深奥的论述中,充满了个性化的感悟和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加谬,以及波特莱尔、王尔德,等等,首先或最主要是文学家。他们之间的差异比共性还要大。人们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具有共鸣性的思想。
鲁迅1919年写下的《自言自语》里有一篇《古城》,故事的基本元素是鲁迅的构思,但主题的揭示中让人想到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寓言《末日的欢呼》。一个小丑的真话被自以为是的观众当成笑话,并在这笑话中毁灭。到了创作的高潮期,鲁迅发表和出版了散文诗集《野草》。可以说,《野草》是集中表达鲁迅哲学观及其复杂思想的系列作品。《野草》里的好多篇什,都可以看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们的思想在其中的投影,更准确地说是鲁迅与他们之间在思想上的相近与共振。分析《野草》一系列作品与屠格涅夫、波特莱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尔德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作家之间思想上的内在联系,文体上兼抒情、叙事、哲思于一体的共同性,以及鲁迅作品的独创性,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事实上,这早已是鲁迅研究里的一个课题。但即使在存在主义的范畴内,鲁迅所做的也不是从哲学的角度去吸纳、认同和传播,而是在思想方法和表达上的共同性让人产生归类的想法。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就曾谈道:“试图以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去认识鲁迅,恐怕只会遭到鲁迅本人的强烈拒绝。”“鲁迅没有从一个经过欧洲哲学家理论化的现实存在哲学立志出发,而是独自展开了存在主义方式的思考。”4这正好说明一个共同的观点,鲁迅是思想家但并不建构思想体系,其独立的思想与存在主义处于不谋而合的关系。而这种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在思想上体现出某种共同性,本身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特点。山田敬三使用了“无意识的存在主义”这一定义来说明,鲁迅的思想与其相近却并非师承。我以为,“无意识”一词的限定既能说明一些问题,却也容易引起误解。如前所述,存在主义哲学本身并非体系,都是思想家们人生体验的独特表达。不但是鲁迅,其他的思想家也同样如此。比如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处不同国家,年龄相差近百年,却在思想上达到某种一致。但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早期的“无意识的存在主义”。不谋而合正是存在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与存在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区别,是鲁迅始终秉持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他思想上的个人性,与他对中国民族、历史、现实,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思考密切相关、相互交织,并以改造国民性为根本追求。这一点即使是在其最具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作品也仍然可以感受得到。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性和国家、民族意识,让一些研究认为,既然“鲁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依据现实情况,主动地选择自己的立场”,所以可以断言“鲁迅绝不是思想家”。1这就涉及我们对思想家、哲学家这一身份的定位了。鲁迅的中国观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他对中国历史、现实以及中国人的庞大的、复杂的论述,既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也是其参与现实斗争的一部分,同时还是其文学主题的一部分。瞿秋白说,鲁迅杂文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反对自由主义”。这里的反对自由主义,就是指鲁迅痛恨并反对中庸,反对调和,反对以留情面的方式留后路,搞变通,进而以“精神胜利法”而自我安慰。这些关于现实问题的探讨里,分明具有很深的哲学思考。
鲁迅就是一位并没建立思想体系和系统哲学的思想家。其丰富、复杂、深邃的思想蕴含在鲁迅的各类文学作品和著述当中。我们可以感悟、体会,并不断地将其进行自己的阐释。以我轻浅的阅读,不成熟的思考,不到位的表述,想要说清楚鲁迅是不是思想家,如何进行革命的革命家,以及怎样的文学家,是不可能完成好的任务。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值得长久言说下去。以上的文字只是各取其中的某一个侧面,初步表达我对相关问题的一点看法。冯雪峰认为:“可以说鲁迅是革命家,因为他的思想是革命的。也可以说他是思想家,因为他的革命思想,除了共产党之外,在中国可说是空前的。”“从创作活动方面来说,鲁迅是个作家,虽然他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在数量上并不很多,但把他的这不多的作品拿到世界上去,没有人能够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2这些通俗的论说很精确地证明了鲁迅终生所追求的事业和应该得到的声誉。
鲁迅的思想与艺术之间,乃至于同他参与现实的革命斗争之间,他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所做出的抉择,以及他一生中所经历的种种变化、发展,过程中的经历、思想、情感的矛盾、冲突和复杂纠缠,都具有评说的无限性。这正是一位伟大的经典作家给我们提供的无尽的话题,也是他始终吸引我们的根本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