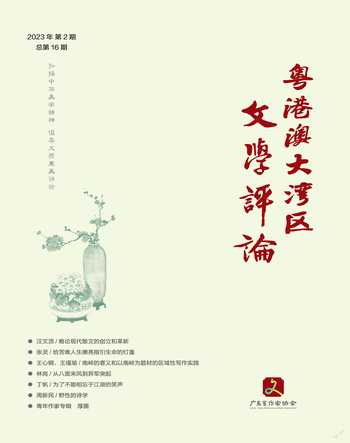个体、文化与重构
管兴平
摘要:文章从小说中个体(人物形象)的分析,再清理各种互相对立和渗透的文化,最后落脚在分析王安忆的“重构”,也就是说,不论是全球视角体认出的确定性,还是中国人的退隐的情感内涵,都带有王安忆本人的思考和对她的以往的都市小说的超越。
关键词:个体;文化;重构;王安忆
经过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及理论论争的影响,王安忆逐渐接受,理论已化为她小说作品中的血脉。王安忆受到过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欲望化书写及都市(城市)文学创作潮流的多方面影响,这些在她的作品中都有一一对应的表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追逐潮流,善于总结和化用。这于她个人而言是一种提升。尤其是自从1996年《长恨歌》发表以来,王安忆的都市文学创作(很多人说她继承了张爱玲),经过她本人的不断耕耘,已经形成了关于以上海为创作中心的城市人和城市形象的多样面目。她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中关于都市的书写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值得让人关注。
一、个体
在小说中,两代人(母亲、父亲杨帆与女儿鸽子、儿子兔子)的成长路径完全不相同,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又说明了后一代人的成长与前一代的连续性。小说写到的城市有扬州、哈尔滨、上海、纽约,乡村有高邮、宝应、黑龙江国有农场,而从中国到美国的鸽子和陈诚(兔子)则完成了都市人的身份转换。在这之中,小说所表达出的丰满的个体直接指向对“自我”生存的追问。
母亲的成长经历中有贵族的成分。她出身于基督教家庭(西方的影响),父母亲是自由恋爱结合的(有五四浪漫因素),教她的老师是旧俄(沙俄贵族元素)的“洛娃”老师,虽然她“对老师有不喜欢的地方”,但也接受了她的深刻影响(腔调、做派,夹杂法语单词而特别的发音)。在新社会到来之时,她又受到新的影响,进入工业大学学习(这是受到了新俄的影响),在大学里崇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艺加上接受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熏染。在新中国的时代氛围下,她在反右派运动中表现出的反激进言论的一面,侥幸与社会主流同轨而逃过一劫,后又因中苏交恶,由于她和苏联方面的联系而遭遇难题。在“文革”初期,她的个人思考是两不靠(既不保皇,也不造反),而是追问“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人类大同”1。在此之前,她就表现出了独立性:她的人性之中有美丽、独立、不顾非议的一面,一些男性对她的争风吃醋也没让她性格收敛,在反右中她独自一人面对同学的诘问时,辩论的从容与自如,虽落于下风也毫不慌乱。所以她是一个“异质的人”,当然,正如王安忆所说,小说创作中“有机会在现实常态中表现异质人物,也就是这些异质性才使得小说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生活。”2在生活之上的理想因此有了存储地。这也是她在“文革”初期飞蛾扑火的线索来源,她的心性之中早就存在献身于理想的情怀和品性。因此,她是异于常人的英雄。
父亲杨帆是扬州人,早年经邻家哥哥(共产党员)引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上了工业大学,和母亲同学。他出身于旧式大家庭,带有了褪不掉的印记,尽管他早已不习惯这样的家庭生活。在反右派运动中他不站边,没有受到冲击,在“文革”中被迫与妻子离婚,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在妻子获得平反后,他的境遇获得改善,在一双儿女到美国定居后赴美,他在赴美探亲时在同乡面前大谈革命和儿女,葆有革命人的本色。女儿指责他说:“伪君子!你和妈妈离婚,背叛革命,背叛儿女!”在酒醒一半时,他也说:“没有革命就没有我——胡师母拍拍父亲肩膀:没有谁历史都在进步!”3但最终父亲还是定居纽约。他虽有坚定的信念,但他是现实生活的妥协者,虽然也怀念革命年代,即使他在革命年代的表现既不扎眼,也不亮眼,他葆有的革命情怀给予了他生命的支撑。但最后他回归于家庭,或许是为了弥补家庭破裂的缺憾。
女儿鸽子外表像父亲,但性格、心理、身体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母亲。高傲、犀利、爱出风头,拥有运动员体质。上小学时就表现出了革命劲头(随着风潮),此時的她幼稚、爱幻想、追寻虚幻的革命理想。母亲遭难后,与母亲划清界限,但她最后还是成为“母亲的孩子”,母亲平反之后受到优待,她上了母亲的大学。后经推荐到美国留学,留在了美国工作与生活。但是她的复杂心思在父亲说要抱孙子时显露出来,“姐姐将筷子拍到桌面:我最讨厌杂种!”4革命烈士后代的光环并没有让她走向正面,而她的生命转轨了。不能说她背离了革命理想,因为她的言谈举止依然葆有这样的成分。她只是无法接受一个自己反对的东西,或者,她和美国男友在一起,也正是为了逃避自己的糟乱的过往,而选择让自己是一张白纸,让人作画的同时也隐藏了真实的自己,她的暴露心灵也是情非得已。她的性格具有双面性和二重性。
儿子陈诚(兔子)外表像母亲,但性格上像东北的“鼹鼠”。关于这个“鼹鼠”说法的来历,小说中写到陈诚消失了多天,师师去找姐姐问询,“临分手,姐姐说:我们东北,有一种鼹鼠,专在土里掘洞,一有风吹草动,就钻进去。危险消失,再从另一处钻出来,地下的通道长达几里几十里,男人就像鼹鼠!”5陈诚从小被寄养在孃孃处,后学厨,拜大师,没上过学(靠自学)。因此他与父亲杨帆是生分的,他也没做成“母亲的孩子”。因为得不到父母之爱,而有了心理创伤,这对一个成年男人来讲更要命,将是他一生的心理疾患。但他一直在实实在在的生活。王安忆在他身上寄予了的是民间的、带有隐逸气的一面。而且他表现上是低调的、不显山露水的,他的言行与他的性格心理也是契合的。作家这样写主要是为了表达后消费主义时代的价值取向和行走路径。对此,王安忆是带有情绪化和倾向性的。
三个人都遭受了创伤,又在家庭生活中心灵创伤弥合,但是部分程度上,因为父亲还在怀念革命,女儿和美国青年结婚,儿子返回上海时的失态,他们的这些行为均和母亲、政治、革命相关联。但是,“每一件在我们记住过去时发生的事,都发生在过去已不存在的当下,而不是过去本身当中,或发生在两者之间的临界状态。”1社会变革带来了机遇和改变的时刻,创伤已成为隐性态,不时发作。王安忆对个人的书写传达了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乐观主义的气息,而是怅惘和哀叹。
二、文化
小说写到了中国内陆南北文化的对比与交融,以及中美(西)文化的差距,主要传达了政治观念的不同造成的理解的不一致,以及现实的遭难给予社会、个人的印痕。
小说的第二部分主要写母亲的经历及对家庭的影响,因而无产阶级文化与旧文化的对比是书写的中心。母亲一代人所接受的苏俄革命的影响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是对传统生活中美(西)方因素(基督教文化)、沙俄贵族、封建大家庭文化具有压倒性的,这一新的改变来源于新生活的召唤,在现实的意义上则是革命理想的获胜,当然其中也有翻新,是一种新的文化自信。此期的无产阶级文化与以往的左翼文学也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苏俄来源是一致的。它在新中国的胜出也有区别于旧俄的地方(但是奇异的是,旧俄中的文化、文学也给予了这一代很大的影响,是远远超出了政治化方向影响的,是意料之外的。)这就是翻新,当然还有现实性,尽管存在片面的深刻,但无疑是在以新代旧之后的自信。因此,此期的无产阶级文化所要反对的旧的文化也就带有选择性,就像我们今天的文化也要面对的,如何选择此期的文化一样。
而小说中革命的一代人与他们的后代则表现出不同。母亲为理想而献身,死去的固然拥有价值,而活着的更多是苟活,因为在后革命年代,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出现使得后一代去拥抱西方,像鸽子一样,或者退隐民间,像兔子一样,其实后来也去往了西方生活。所以,以一种后置性的视角来观察,理想时代的价值观因为带有确定性,也就成了当前生活的重要启示:当前生活需要确定性(这是后现代解构时代的过度而造成的反弹),如果将理想时代的宏大叙事加以剥离、转轨、变道,会成为焕然一新的确定性。
小说也将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表现得泾渭分明。官方文化是宏大叙事,包括对反右、“文革”的认识和重新评价以及对母亲作为一名烈士的认定。比如陈诚尽管在舅公处学厨艺,也感受到了政治的关联,面对陈诚在家里留下,而增加了一张吃饭的嘴,大伯在和伯妈吵架时说的“等尼克松走过!”,话语之中所传达出的人情世故和政治气息,等等。但陈诚更多的走向了民间,他的追寻厨艺(吃)更多的带有竹林的一面(隐逸气),小说题记为清代袁枚的诗句:“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将江南旧影加以呈现,显示出文化深意。其中高邮、宝应、黑龙江农场的书写更是突出了他的没有个人身份(黑户口),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在一种苦难的底色上也隐隐约约透露出了一丝自足的快乐。尽管陈诚是自我独立的,但也是自我封闭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在纽约与师师结婚之后他还会返回去寻求自我的宁静的生活,道理是同样的。
小说中的美(西)方与中国也是不同的。虽然母亲是革命者,她的理想却并没有得到继承。父亲杨帆是她的同代人,同样受革命召唤,但他苟活下来了,虽然他心中的理想仍然是对革命年代的追怀与信服。一双儿女更是不同了。父母一代的生活更多的是帶有中国革命的印记,虽然鸽子也有这种记忆,但她选择留在美国生活,却也放不下中国美食,和拥有拒绝与美国男友生一个“杂种”的烦恼。而陈诚刚到美国时也是黑身份,他在异国也处于藏与隐之间。一开始他并不能融入美国社会,小说暗示他是因为政治原因才获得了绿卡,虽然身份转正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可是吊诡的是,他依然还会在回到中国看见大型工厂车间模型时落泪,他对以前的中国印记虽然没有母亲内里的革命化的内容,但工厂车间的热烘烘气氛还是带给了他磨灭不了的温暖记忆。面对孃孃让爷叔带他洗澡后的变化而产生的疑惑,他自己也是惊异的。因为,那一日在工厂的印象是如此深刻,“这简直是声色犬马的一日,惊艳之余,还有些微犯罪感。”1这样所显现出的中国和西方的杂糅,无论是身份、政治,还是情感记忆,正是后消费主义时代的特别征象。
小说也特别写出了儒学和佛理的成分。虽然在革命化时代里,这些都是糟粕,但作为中国人却是骨子里无法舍弃的生活方式和行事原则。这也传达出了革命年代的现代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在激进现代性的革命表现时,民间所存有的不变的田园隐逸与出世的转化。一方面是投身革命,一方面是远离主流。抗争与苟且,现实与竹林就这样在变乱时代互生共存,相互转化,其中有承接的线索可以追寻。理想化时代的革命信念根本上就带有民间的成分,即使无产阶级文化的初盛时期,民间都在。但现时代的回望视角更多在于处理民间与政治的关联,可以看出王安忆是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角(不仅是用社会主义文学内部眼光来看问题,也不仅是从中国本位立场来看问题),而是纳入到了新文化构成下的全球视野,具体而言,是在美(西)方与中国的互动与竞争当中的改变。而儒学与佛理既可以显现中国性,也可以表达超越性,两条道路并行不悖。
三、重构
小说开篇写美国的中国社会:唐人街和法拉盛,连接起了从乡村到都市的脉络,它们彼此沟通和融合。从哈尔滨到扬州,到上海,到高邮,再到天津,而落脚处是纽约。小说将王安忆以往以上海为中心的书写更往前推进了一步,将中国内陆的南与北,中国外部的中与美(西)连接起来,不仅让小说更多的增加了看点,而且把这些捏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广大的、丰富的中国社会,扩展了以前题材的狭窄与地方主义倾向,更以一种外部视角来看待中国内部变革,从而确证出一种中国改革信号,但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固然中国很多方面变化了,然而中国人的人心、理念、人情、风俗与习性依然有过往年代的存留,这也说明了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变与不变的常理,它也会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这也就进一步突显了社会所需要的中国性,通过王安忆的集中展示,可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优劣。
更主要的是,小说写出了后现代下的市井气,社会所出现的日益的世俗化。这固然是一种世界潮流,无论是西方对宗教的越来越多的淡漠,比如基督教的日益世俗化的趋向,还是中国对政治(信仰)的淡化,人们更关注个人财富与日常生活,还有民以食为天的世界本身的张扬都在说明世界在变化。但是,鸽子与美国男友生活在一起却留恋中国人圈子,陈诚的手艺与寻求宁静的融合,以及父亲的定居西方却是为了与儿女团聚等等方面,无一不是在展示中国人的生存哲理与法则。中国人的世俗生活原则甚至扩展到了美(西)方,王安忆好像是在写中国人的自我扩张之路,其实更多的是写中国人的自我救赎,而这是要通过日常生活化来达到的。根本的问题当然是,中国人大多融入不了西方,也不能够拯救自己,只是以一种千年不变之理来应对世事的变幻无常。
小说也借鉴了金宇澄《繁花》中的一面,比如对亭子间爷叔(还有一个乡下爷叔)、阿毛、蓓蒂等人名的借用,以及书写的“上海虹口的弄堂”,栾志超所住的市中心的“一条杂弄”,延续了王安忆本人写《长恨歌》的路子。同时又与其他以往的都市小说表现出不同。首先是小说直面革命,特别是“文革”时代的描述,将都市与政治、革命、历史相连接,传达出了宏大叙事内容,更进一步的,在后革命年代将政治、革命、历史的影响书写出来,提炼出创伤记忆,从而引人反思。其次是前面说过的,由中国南北、乡村与都市、中美(西)的地理范围的扩展,既增加了看点,又丰富了容量,而落脚点却是中国人的人情心性。其实是“混杂的中国”。比如说:“法拉盛的新草莽,其实是个劫后残留。追溯到共和开初,民国政府定都金陵,守北望南,家乡菜打底,发扬光大,养成一脉食风。经改朝换代,时间流淌,再添上感时伤怀,离愁别绪,天地人所至,淮扬一系格外受青睐。”1(还是中国样,尽管在美国)。第三,小说由乐观主义(激情)到悲观主义(冷静),可以说,王安忆以往小说中的乐观是虚幻的,一旦面对创伤性记忆的书写,她就会改变,因为暴力和血腥让她精神收缩而冷静、理性而客观。
还有,是小说写出了一些上海人,有为上海人正名的意味。写孃孃的威仪,更写她作为上海女人的一面:“头发的焦煳和着洗发膏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漫开来,说不出香还是臭,却有一股热乎。”2有张爱玲笔下的市井气。再譬如写新时代的工人,“爷叔是钢铁厂的铸模工,一个人住在祖父母留给他的房子里,平时上下楼点个头就过去了。”3孃孃托爷叔带陈诚上澡堂去洗澡,爷叔带他到了车间,等下班了再去,洗澡时陈诚看见了:“爷叔裆里坦然地垂着一大嘟噜,带了一种爱惜地擦干了,套上衬裤。”4而和爷叔一个车间的招娣:“这只手暖和,柔软,而且调皮,大拇指弯过来,一个一个按他的手指头,仿佛在点名。”1“余光里的背影,套在粗硬工作服里,却是轻盈的,一闪,不见了。”2又在扬州瘦西湖见到招娣,给他买了包子,他吃着哭了。在革命年代,作为工人的爷叔和招娣也是普通人,并非不可亲近的高大上的英雄,而是充满了人情味的。还有小毛,“小毛家原是看弄堂人,每晚摇着铃喊‘小心火烛的,最先是他的祖父,接着是他的父亲”3,小毛是街上的小混混,后来也改正了。一个街道混子和痞子也可能在时代变迁和年岁增长之后获得转变,赢得社会新的认同。还有单先生,胡老师夫妇,师蓓蒂,超哥(栾志超)等虽然都是有一些小缺点的个人,但无不是聪明、乐于助人和善良的化身。和王安忆其他小说中的上海人形象有了區别。比如王琦瑶给人印象是精明的、算计的和世故的,虽让人同情,但形象较为负面。也和社会上关于上海人的流言显示出差别。
总之,首先是《一把刀,千个字》中叙述的主观、武断(肯定性的),代表了一种确定性,是对革命变乱、虚幻、后现代(消费社会)之后的重构,因带有王安忆的个人观点而显突出。王安忆曾说:“我以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宝贵的特质是生活经验,这是不可多得,不可复制,也不可传授的写作。它源自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每个人置身其中,共同经历着起伏跌宕,这就决定了新时期文学的写作者多是有着丰富的阅历,跟随度过共和国的各个阶段,以特殊的禀赋,在普遍性的命运中,建立起个人的经验,再以自身的个别的经验出发,映射旷世的人生。”4建立在所生存环境之上的个人经验具有认识的确定性,王安忆一面传达出中国社会的变化气息,另一方面又将一种个人体认加以强化。但是很明显的,小说在怅惘、哀叹之后还是寄托在了西方(别处)。这也是王安忆视角调整之后(全球化视角?)出现的新的确认。
其次是,小说以一种回溯性的叙述展开,笔调是怀旧的,向后看的,“回忆的重构活动是在环境中进行的,而环境会比记忆试图恢复的短暂瞬间要更长久,并且其中会散落着此前留下的印记和提示物。”5小说试图通过人物(个体)的回忆重构一种回到(也是认同、承认)母亲的理想(但这已不可能),因而缺乏怀疑、质疑和批判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着”“活下去”取得了中庸的同一取向,这一东方化的立场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小说结尾中叙述的西化(到西方生活)下尤其显示出了局促和无法达成的目标。显然“回到中国”只是成了凭吊,人物内心已然丧失了心灵家园而不自知。这一丧失恰恰是几十年来的世事变迁带来的连根拔起,而这是在新的文化出现之初就已经显示出了端倪和苗头的,只不过政治化后的经济化更进一步地鞭打了陈腐的血肉。因此,人物(个体)的回忆的重构带来的是碎片化的情绪与心灵的弥合,一种带有情感滋润的退隐的力量,人们用这种中国化的方式来对抗世事的反复无常。而这一点,也正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