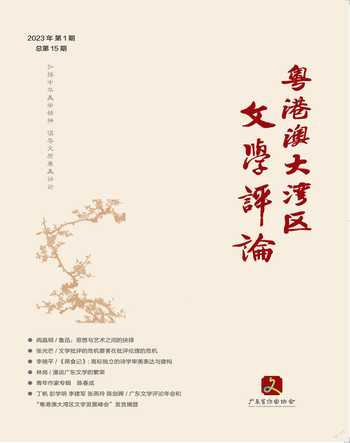文艺青年的阅读谱系与虚构的限度
何瑛
摘要:本文试图分析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经典的投影”,从浪漫主义遗产的角度读解,并探究当代读者对“理想文学”的期待,以及反思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小说中“虚构”的可能性和限度的问题。
关键词: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浪漫主义;虚构
2020年9月,著名出版品牌“理想国”在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了陈春成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瑰丽的幻想,清新典雅的文风吸引了众多读者。两年来,作品斩获了众多奖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学界的关注。赞扬者从中读出了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王小波、汪曾祺的痕迹,也有人在其中感受到《红楼梦》与《庄子》的意境;批评者称之“碰瓷”大家,是对杰作的模仿,并未能表达新的经验云云。考察网络上对小说集的不同声音,或许可以探究一代文艺青年的阅读谱系,探究当代读者对“理想文学”的期待,以及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小说中“虚构”与现实关系的问题。
一、时空的诡计及文艺青年的阅读谱系
在豆瓣的书评中,很多讀者称陈春成的小说“有博尔赫斯的感觉”。博尔赫斯的小说和散文中经常探讨的时间迷宫,在陈春成的小说中也经常出现。作者也并未隐藏自己的阅读谱系,开端便抛出了博尔赫斯“硬币”的故事:1966年一个寒夜,博尔赫斯站在轮船甲板上,往海里丢了一枚硬币。博尔赫斯曾在诗中写道:“寒光一闪,在浊水中淹没,时间和黑暗卷走了一件不可挽回的事,在地球的历史上增添了两串,不断的、平行的、几乎无限的东西……”1博尔赫斯沉迷于关于时间的书写,其小说中时间并不是单一向前的,而是立体循环,周而复始的。《夜晚的潜水艇》中的硬币代表了冥冥之中神秘的关联:1966年的博尔赫斯在轮船甲板上抛下硬币;1985年澳洲富商买下阿莱夫号潜艇寻找硬币,队长是一名中国籍姓陈的海洋物理学家;1998年一艘蓝色潜艇帮助阿莱夫号逃生于珊瑚礁迷宫;2166年有个孩子在海滩上捡起一枚硬币。一枚硬币缀连起不同时空的命运,让一切偶然性有了宿命的意义。“阿莱夫号”这一命名本身就是在向博尔赫斯的小说《阿莱夫》致敬。博尔赫斯的“幽灵”在小说集其他篇目中也有闪现。《裁云记》中“我”去拜访老师的朋友,在一栋如同迷宫的筒子楼里,听他讲一本如流转不息、无穷无尽填字游戏的古书,让人想起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的余准拜访花园迷宫听阿贝尔讲何为无限小说的场景。《尺波》中层层叠叠的梦境讲述的其实不是铸剑本身,而是物质之间不可思议的流转,那梦境中守着火焰的铸剑师,让人想起博尔赫斯《环形废墟》那个梦出少年的人,最后发现自己也无法被火焰吞没,亦是别人造出的幻影。《音乐家》中古廖夫晚年钟表匠身份的设定,亦是在向偶像致敬。钟表匠在精密的零件之间是不是能实现对时间的掌控权?时间这种现代性的产物是不是有其虚假的一面?小说集中异质的时间观开启了逃逸到另一空间的可能性,倒映着博尔赫斯时间观的影子。
考察小说集的名字,本身就是时空和空间的缀合,“夜晚”提供的是做梦的时间,“潜水艇”则是做梦的空间。在陈春成的小说中,音乐、技艺、典籍提供了造梦的素材,它们引导着人物进入诗意的乌托邦。在空间的选择上,作者则偏好海洋、湖泊、山林、园林、寺庙等场景,古典、诗意、浪漫的图景造就了清新典雅的文风,也成为小说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
小说《夜晚的潜水艇》中,海洋是造梦之所;《音乐家》中,深潭则是噩梦之渊。音乐审核员古廖夫的朋友穆辛在同伴的霸凌中沉于潭底,站在岸边目睹这一切的古廖夫难道可以摆脱道德的审判吗?他目睹着朋友那倔强的头颅消失在潭面而无动于衷,童年时的罪恶需要用一生来救赎。如同无法逃避的宿命,在漫长又如同幻觉的人生中,童年的那一幕只是一场排演和预兆,在古廖夫承担音乐审查工作的日子里,他也一次次扮演着刽子手,摧毁着那些同类的心血,把那些承载着幻梦与希望的乐谱沉入绝望的深潭。终于,在开篇写到的那个雨夜,他等到了一生中唯一救赎的机会,他用单簧管挽救了几个大胆的年轻人,同时也拯救了一直被自我阉割的作为音乐家的自我。想象中的“穆辛”帮他唤起那些被深藏的灵感,在幻想中完成了一场关于空间逃逸的演奏会。
有读者从陈春成的小说中读出了王小波的意味,在文字风格上他们当然完全不同,但是在对“自由空间”的想象层面却有相似之处,这种对自由的想象和对专制的抨击或许来源于米兰·昆德拉和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精神遗产。《音乐家》中,古廖夫童年好友的穆辛沉入深潭;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中,叙事者“我”少年时的好友妖妖沉入大海。这两篇小说的背景都是文艺遭受政治严苛审查的时代,结局都是叙事者“我”的朋友消失在水底。但是水底不仅仅意味着厄运:《绿毛水怪》中的水怪们在海底感受着不被限制的自由,《音乐家》中沉入深潭的穆辛作为古廖夫的另一重人格帮他发现“被压抑的自我”。海洋和深潭以物理空间的广阔暗示了另一重世界的可能性,毕竟,在本就如此虚幻不甚理想的现实中,谁有资格说另一重世界是一场虚幻呢?
除了海洋外,山林也经常现于小说中。山林这一空间既源自作者本人的童年经验,也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意境。在《竹峰寺》中,芍药花、蛱蝶碑、《金刚经》和隐士文化、老庄之道混合在一起,渲染了小说古典美学的色彩。小说中寻幽僻之处藏老屋钥匙,是对一个人精神原乡的“藏”;寻找蛱蝶碑,是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找”。小说书写的是在世界剧烈变化的当下,个人如何平复内心的不安,找到心灵的归依之所,当“我”面对如蜃楼般升起的楼盘,沈从文和汪曾祺在小说中书写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学恋旧,在《竹峰寺》这里找到了痕迹。除了上文提及的作家外,很多作家的影子也在陈春成的小说中闪现,这证明了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的判断:小说的精神是持续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前面的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1文学是具有可持续性可传承性的,这种传承往往不是靠直接阅读,在文学的“环形废墟”中,经典的火焰照亮了新作的骨骼,文学精神得以一代代传递。
二、“耽匿”的书写或浪漫主义遗产
《夜晚的潜水艇》中出现了“果壳”这个喻体:“仿佛鸟栖树,鱼潜渊,一切稳妥又安宁,夜晚这才真正地降临。门关好了,家闭合起来,像个坚实的果壳。”2“这个灵感或许来自博尔赫斯的《阿莱夫》,那篇小说引用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台词:“啊,上帝,即便我困在果壳里,我仍以为我是无限空间的国王。”3果壳和潜水艇的形态都暗含了对闭合空间的追求,和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探讨的鸟巢、贝壳的意象相似,都表达了“退隐到自己角落”的原初愿望。
耽园、匿园出现在《李茵的湖》中,指涉了耽溺和隐匿。耽匿的母题出现在每一篇小说中,包括《裁云记》这样的政治讽喻小说。在一个乔治·奥威尔风格反乌托邦故事的外壳下,主人公“我”对洞穴的迷恋仍然成为小说最核心的欲望。“我”在山居研究《海洋生物学》,研究建文帝的去向,制造永动机,那些无用的兴趣是“我”的洞穴和陷阱,让我用一生的时间沉迷游荡。文中写到一栋筒子楼,楼中住户是一些着了“魔障”的人,他们原来都是些教授学者,后来放弃了世俗的荣誉和温暖,在世界的某个点上钻了牛角尖,无暇他顾,从而抛掷了一生。每一位住户,都拥有自己的洞穴可以沉迷于迥异于尘世的一生。小说中提到声部追逐的复调音乐“赋格”“像长蛇吞食自己尾巴”的文字游戏,让人想起博尔赫斯笔下那本无穷无尽的“沙之书”,暗示着时空绵延且无限,在现实的日常规训空间之外也存在其他的神秘空间。小说中“云朵修剪局”的工作是荒谬而机械的,但是又是“不需要理由的事情,是文明世界的基石,不容动摇”4。于是耽溺于文学和艺术的洞穴成为了逃离庸碌日常的方式,以审美逃逸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消极反抗。研究者认为,陈春成的小说“为心灵打造一个坚实而紧闭的空间,此种心法暗合了当代千万小资的自我疗愈之道”5,在《夜晚的潜水艇》的豆瓣评论中,不难发现小说在幻想世界中开辟的自由体验,被处于同样境遇的读者们深深共情。王德威认为,陈春成梦幻、诗化的写作和台湾的“内向世代”有共通之处,“内向世代”和社会历史的关系仍以想象为屏幕,其主体是脆弱的6。但是与袁哲生、邱妙津、赖香吟等作家困于自我的内在书写不一样的是,小说家典籍、音乐、风景共同构建的美学中实现了情绪的疏导,将被困的自我从狭窄的空间中引向开放自在的想象空间,从而抵消日常从事无聊工作的精神内耗,这种温和的疗愈方式被现代都市“搬砖人”深以为然。
陈春成的小说提供了一种应对现实不满时平和且低成本的对抗方式——退回自我。如果我们考察陈春成小说的读者,或许可以窥见一代年轻人的困惑。在物质条件相对优渥的独生子女时代出生,迈入社会后又发现面临着板结化社会带来的压力,顺应时势在“内卷”的焦虑中升学就业,却未必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我的期望。新冠疫情时代加剧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感和生活的不安全感,小说提供的想象空间给读者情绪的纾解提供了通道。豆瓣评论中不乏溢美之词:
在外界风波不息,动荡局势裹挟下的今日,遇见陈春成的文字是幸运的,他在现实的边缘精雕细琢,在细微处为你描摹出内心小宇宙的形态,给你留出短暂逃离此刻的喘息空间。1(作者:台北夜没有车)
读陈春成的小说,要打开身体里隐藏的触角,和被高楼大厦所麻痹了的视觉,潜入那些神境,我也好想像一片被遗忘的书签一样长睡在古旧的书页里啊。2(作者:幽草)
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认为“一部小说必须纯粹是诗”3,小说、诗歌、哲学本质上是相似的,它们都在寻找一种和谐的心境,唤醒人们对世界的感觉。他秉持着在梦和诗中重建理想国的浪漫主义,试图以诗意“心灵”的力量重返黄金时代。在诺瓦利斯的诗中,远与近、高与低、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一切界限皆消失殆尽。无论是辽阔的空间,还是无垠的时间,都可以汇聚于想象的内心世界。自然与音乐在诺瓦利斯的诗中成为外界和自我精神沟通的媒介,将自然万物融入诗歌之中,以音乐般的诗超验性地呈现世界的本质,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陈春成践行着这种理想,自然和音乐在作者的笔下成为逃逸的通道,人物以美学逃离了外在的压迫,建构起一个桃花源的世界。
《竹峰寺》中的“我”藏在瓮中听山峰生长的声音,《音乐家》中一张张乐谱在古廖夫眼前升腾起幻景,在陈春成的小说中,人物内心幽闭蜷缩的空间藉由自然与音乐得以向广阔的世界延伸。作者对想象力无比珍视,试图在其辉煌宫殿寻找到“内在的自我”,“自我”或藏在深海的潜水艇中(《夜晚的潜水艇》),或藏在竹峰寺山涧的瓮中,或藏在能将人化为无形的酒中(《酿酒师》),歸根结底藏在似曾相识真假难辨的记忆中(《李茵的湖》)。除了“寻找自我”之外,陈春成的小说中还有一种执念:想象并非一个人的蜃楼,在神秘不可知的时间长河中,它会对他人的命运产生意义,甚至可以拯救他人于危难之中。譬如《夜晚的潜水艇》中1998年的陈透纳在幻想的海底之旅中拯救祖父于危机时刻,《音乐家》中古廖夫在想象的音乐会中遁于无形逃避了现实的追捕。
三、虚构的瓶颈及“成熟小说”的理想
如果说陈春成小说中的梦幻空间吸引了众多读者的话,对梦幻的耽溺也遭到了很多批评——譬如有豆瓣评论认为作者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孤芳自赏,小说“飘着落不实”,读起来像《萌芽》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作品。考察豆瓣评价两极分化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是因为过度营销带来的高期待和消费者逆反心理。小说出版后获《亚洲周刊》2020年度十大小说、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豆瓣“2020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总评第一名,作家余华、阿乙、史航、贾行家等人力荐……陈春成的名字在各种媒体上频频曝光,读者和评论家将他和博尔赫斯、希区柯克比对,京东网站直接在书名后加上推荐语“游荡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间,汉语的一种风度与可能性”……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会被广告安利下单,也会在下单后感受到过度营销影响了自己的购买自由而产生逆反心理,还会因期待值过高而“由粉转黑”。这种复杂的消费心理机制召唤出一个个苛刻的评论者。第二个原因或许和读者对文学的期待相关,“萌芽”“新概念”被作为一种“青春文学”的标识,体现了读者对一种假想中“成熟文学”的期待。“成熟文学”是告别了青春期过多自恋情绪的,放眼更广阔世界的“理性”的文学。李静认为对《夜晚的潜水艇》的差评,“很多虽颇有洞见,但也不乏一种高高在上的‘审判感,其背后仍带有对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虚构的某种轻视。”1豆瓣评论中的确有很多高高在上的恶意差评,但或许不仅仅是“对虚构的轻视”那么简单。读者会在小说瑰丽自在的想象中滑向抒情的港湾,感受到暂时的自由,却也会在沉浸后感受到厌弃,陷入关于“深度”的诘问。文学可以沉浸于想象之中,让抒情抚平个体内心被隐藏的褶皱,但也可以在想象之中寻找到和现实的联系。针对其作品“缺乏对生活的关注、对困境的回应”的批评,陈春成在访谈回应道,“应对现实世界的法子并不这么单一,除了如实描摹它,我们还应当有能力另行构建一个世界。将米酿成酒,不如米饭管饱,给人生活的气力,但于生活之外,提供一种醉意和超然,也挺好。而且留心的话,即使是最离奇的几篇故事里,也有对现实的鲜明映照。”2其实在陈春成的写作中,现实是存在的,比如《音乐家》中苏联文化专制的阴影,《竹峰寺》中“文化大革命”的故事背景,但是为什么会被读者认为是缺乏对现实的观照呢?
纵览全书,小说中的现实世界都是作为模糊的背景存在的,是虚空的镜花水月,是想象的亭台楼阁。历史背景出现在小说中,却缺乏和人物有效的细节联系,最终沦为可以随意替换的道具。现实感的丧失或许是很多青年作家共同的缺陷,也是一代人面临的共同处境。网络时代开启了足不出户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也改变了一代人和社会沟通的方式,但是在精密算法和流量包装下的认识一定是真实可信的吗?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有可能产生像《平凡的世界》这样诞生于真实生活经验的作品吗?
另外,《夜晚的潜水艇》对细节和修辞的耽溺也会让读者产生“空中楼阁”的印象,或许可以从“颓废”的角度来思考浪漫主义风格的缺陷。尼扎尔在雨果的《黄昏颂》中发现了颓废的所有标志——过度描写,突出细节,以及一般地抬高想象力而损毁理性。3哲学家尼采将他曾迷恋的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音乐定义为“颓废”,勃拉姆斯抵制当时的音乐变革,期望重新回到18世纪的音乐传统,呈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怀乡病,在尼采看来是生命力孱弱的表现,但瓦格纳是尼采《悲剧的诞生》的灵感缪斯,他为什么也会被认为是“颓废”的典型呢?在尼采看来,瓦格纳的音乐以浪漫主义的内在匮乏导致了虚伪的激情和做作;其浪漫悲观主义艺术不是对生命的肯定,因為对现实的不满而关注过去和彼岸,其中充满了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迎合了现代人寻求麻醉和解脱的需要;瓦格纳音乐追求音色的华丽和强烈、音调的象征和暗示意义,成了仅仅满足和主宰官能感受的艺术。1尼扎尔和尼采对浪漫主义的批判都导向了对艺术沉迷于形式、沦为表演和游戏可能会丧失超越性和革命性的担忧。对修辞和风格的批评本身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我也愿意将对《夜晚的潜水艇》的批评理解为读者对文学介入现实的一种呼唤。在繁复的修辞瑰丽的想象编织的蜃景中,读者被诗意的力量打动,而当作者自身徜徉在梦幻的海洋中始终不肯靠岸时,读者反而会豁然清醒,产生审美的倦意。
毕竟,虚构照进现实的那一刻是极其动人的,在前辈作家的幻想世界中,现实其实无处不在。米兰·昆德拉说卡夫卡实现了一个古老的小说美学的雄心:梦与真实的混合。2卡夫卡的小说释放了想象的自由,完成了一篇篇梦一般的小说,但是无论在《城堡》中,还是《审判》中,现实总是悬浮于虚构的上方,梦和现实因为荒诞的本质被天衣无缝地缝合在一起;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亦是如此,小说以飘散着迷雾的英国传说探讨民族记忆和遗忘的命题;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柯希莫栖居于树上,却始终未拒绝现实;王小波的《万寿寺》中,离奇荒诞的长安城也一直在映照和批判现实。相比起来,《夜晚的潜水艇》中的现实被模糊化,搁置在一旁。小说中处理的现实危机的方法,或是直接遁形(《裁云记》),或化作无形(《酿酒师》《音乐家》),在另外一重空间中实现个体自由。这种处理危机的方法看上去颇有诗意,但是却显得消极孱弱。《“面孔”或“格套” ——关于当下青年写作的一次讨论》一文对包括青年作家笔下“逃逸式”主人公有这样的评价:这类写作所建构的纯粹、孤立的个体形象也喻示着与外界社会的隔绝,同时包含着屈从、躲避现实的消极意味,也可能消解着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改造现实的意愿和动力。3这种评价其实暗含了读者对虚构小说的现实观照的诉求。略萨对小说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有着发人深省的洞见:“在编造和讲述的故事中,如果小说不对读者生活的这个世界发表看法的话,那么读者就会觉得小说是个太遥远的东西,是个很难交流的东西,是个与自身经验格格不入的东西;那小说就会永远没有说服力,永远不会迷惑读者,不会吸引读者,不会说服读者接受书中的道理,使读者体验到讲述的内容,仿佛感到亲身经历一般。”4虚构当然意味着对现实的拒绝和批评,用虚幻的世界来代替现实的世界,小说中幻影的存在其实暗含着对现实的反抗和日常生活中难以餍足的心理缺陷的弥补;同时虚构小说的艺术魅力又来源于与现实联系的那条纽带,如果缺乏与现实的对话和批评,那小说的艺术魅力也会大大削减。
我们身处于一个信息自由又闭塞的时代,消费社会景观纷杂却呈现出单一同质的话语,网络上无数的信息从我们眼前涌过,而我们却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小说的复杂性似乎在“单向度社会”坍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一个经典“洞穴”理论:生来被囚禁在洞穴中的人,看到光的影子,觉得那是真实。洞穴固然可以给他提供安稳的栖息之地,但是当他走出洞穴后,用刺伤的双眼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才会恍然觉悟之前的一切光影都是虚幻。那个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又冒险返回洞穴中试图改变众人的世界观,这个勇敢的引领者,如果可能是一个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的话,为什么不能是作家呢?我们享受着洞穴中家宅一般的庇护,也期待着新的视角来戳破生活的真相。虚构小说永远需要进击现实的勇气,我们期待着,为虚构文学照进现实那一刻的光芒而激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