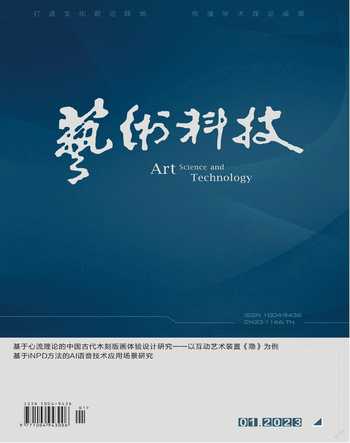西汉复合造型玉器设计方法与风格探究
王芷晴 崔华春
摘要:西汉玉器中存在大量将不同形体融于一器的复合造型,通过同质形象的对称相连、异质形象的重新组合、多种形象的交错拼接,呈现出天地神人、万物生灵之间互相渗透,超越自身属性的多样化艺术造型。文章结合案例梳理分析其形制类别,深入探究其使用的设计方法,剖析和解读纹饰组合的内在规律,从线条运用、造型艺术、表现形式三个方面总结其蕴含的艺术风格。西汉复合造型玉器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多样的艺术风格为更好地解读西汉玉器审美文化精神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也为当代视觉设计提供了可参考和借鉴的设计形式。
关键词:复合造型;西汉玉器;设计方法;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J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1-00-04
0 引言
西汉的雕刻艺术继承和发扬了楚器物中常用的复合造型方法,复合造型是综合两个及以上的不同自然物象,形成新艺术造型的设计方法[1]。镇墓兽、虎座飞鸟、漆木羽人,这些造型都表现出楚人对复合造型方法的深刻理解和精湛运用。在浪漫奇诡的楚风浸润下,这种复合造型方法也被广泛运用于西汉的玉器设计中,表现形式多样,既有同类物象之间的复合,又有不同物象之间的复合,还有物象与器皿之间的复合。如龙凤合体玉佩、多螭纹玉剑饰、双龙首玉璜,这些玉器作品中的动物形象以突破常理和自然法则的姿态,相互浸透、错综相连、多样拼接,以诸多组合形式赋予玉器神秘而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西汉复合造型玉器具有深刻而丰富的设计美学价值,因此,深入分析西汉复合造型玉器纹饰的艺术设计正是探究西汉设计理念、审美意趣和文化内涵的有效途径。
1 西汉复合造型玉器的形制类型
西汉玉器中的复合造型纹饰有两种类型,一是玉龙、玉螭、玉凤、玉兽面等单体纹饰造型,这些神兽本身就融合了多种动物的局部特征,是以多种动物形象组合而成的复合造型。二是这些单体形象构成的组合玉器,既有同类神兽之间的复合,如双龙连体玉佩、双凤纹玉韘等组合形式,又有不同神獸之间的复合,如龙凤纹透雕玉璧、龙螭并体玉带钩、四灵纹玉铺首等。根据纹饰形象的组合形式归纳其形制,其构成方式可以分为四类。
1.1 整体复合型
整体复合型是将相同或不同属性的单体神兽取其整体加以复合的造型方式,形式内容多样。既有在玉器外缘增添相同属性的对称式双兽结构,如一系列透雕出廓的双兽玉璧,华美而精致,又有在整体轮廓对称的基础上局部纹饰不完全对等的非对称双兽造型,如西汉玉韘两侧多透雕不对称凤纹,创造出均衡的视觉效果。还有以龙、凤为主体纹饰搭配猴纹、熊纹、虎纹、鸟纹等辅助纹饰的多种形象组合造型,运用在玉璧、玉佩、玉韘等器形中。不同类型的动物组合展现了汉代玉工愈发成熟的多形象复合造型设计手法。
1.2 局部共形型
玉器纹饰形象的组合常出现局部结构共享的形式,有的共用身躯,有的共享尾翼,有的双身共用一首,有的双首共用一身。最典型的当数各种各样的双龙首玉璜,在璜的两端只取龙首,龙身共享并与玉璜结构相合,表现的是古人心目中的虹霓之形[2]。此类造型更强调玉器的抽象和神秘感,以众多超自然且充满幻想的巧妙构形创造出一系列独属于西汉的复合形象。
1.3 附加形象型
附加形象型玉器是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加饰其他出廓纹样的造型方式,此类造型主要在出廓透雕的玉璜与玉觿中出现,如在双龙首玉璜上加饰螭兽的镂雕双螭出廓玉璜,在龙纹玉觿上加饰螭龙、凤鸟与异兽装饰的龙纹玉觿。这种造型多继承了战国时期的风格,纹饰繁复细致,轮廓突破边界,是西汉复合造型玉器中十分特殊的一类。
1.4 派生复制型
派生复制型玉器将来自现实或非现实的同种自然形体取其整体或部分,再以某些特定方式进行组合,通常一个器形中出现三个或以上相同形体,以此构成新的形体。如玉璧中的透雕三凤玉璧、玉韘中的双龙双凤组合、玉剑珌中的多螭虎组合等。这种造型源于原始艺术中怪异的合体动物,如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复合造型神怪,以同类自然形体的派生和复制扩张其原有特点,增加兽的神性和超能,从而使形成的复合造型的自身力量超越原有形体的特质,增强艺术效果和感染力。
2 西汉复合造型玉器的设计方法
西汉复合造型玉器无论是构图、造型还是纹饰都极具形式感和艺术美。设计形式精炼巧妙而变化万千,达到了外在造型表现与内在寓意传递的和谐统一。汉代玉工为了在玉器中营造运动、力量、张力的艺术效果,创造出多种设计方法:随玉赋形、动势布局、多维取象、跨维构成、纹样模块,这些设计理念在西汉复合造型玉器中的运用,成就了西汉无与伦比的玉器艺术。
2.1 随玉而琢的构形布局
西汉玉器中的纹样常表现出随玉而琢、适形于器的特征,即根据玉器外形的限制设计和安排相应纹样的造型和布局。这种处理通过对主体纹样的扭曲变形或添加相关辅助纹样来填充适应器型,组成形式秩序井然而变化万千,主题鲜明而题材丰富。
在圆形的璧器、环器和剑首中,通常采用几只神兽首尾互衔环绕成圆,搭配其他小兽纹饰的方式来满足器形需要。如徐州楚王后墓出土的龙凤纹透雕玉环,主体框架是由三条虺龙盘绕成一个圆环,在龙身空隙处透雕有熊、凤鸟和卷云纹进一步充实构图,构成饱满和谐的圆环造型。
在璜形器中也常常运用适合的纹样布局来营造丰富多变的造型和流畅的动态感。湖南省长沙市杨家山131号墓出土的一件龙形璜式玉佩整体璜形由两只向背而出的对称蟠龙组成,龙首雕琢精细,龙口大张作吐云状,龙身蜷曲呈“S”形,为进一步充实璜形,周身幻化为缥缈云气,周身透雕的云气纹不仅使璜形器更加稳固充实,更增添了神兽踏云而出的神仙气息,富有装饰性与浪漫诗意。
由此可以发现,这种随玉而琢的构形布局体现出玉工对玉料的极致运用,在有限、特定的形状范围内,物尽其用、因材施艺、随石赋形,创造出丰富多变、饱满流动的造型,是西汉复合造型玉器中运用最广泛的设计形式。
2.2 适形于器的动势分布
在西汉复合造型玉器中,强烈的视觉张力不仅来源于纹饰形象本身的扭转交叠,还来源于器型外形所产生的视觉张力。从造型轮廓来看,空间的趋向性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动势走向,从而在观者心中产生了不同的方向感和动态感。简单来说,横向的矩形容易产生向左右方向的张力,竖向的矩形容易产生向上的张力,而圆形则容易产生向中心旋转的张力。对西汉玉工来说,玉器形状位置的一些微小变化都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倾向张力,这也成为复合造型玉器设计的关键,依据玉器的不同造型设置多种方向动势的构图,塑造出充满气势与生命力量的结构与形象。
圆形构图虽在视觉上常给人一种重心稳定的造型感受,但在西汉玉器中,圆形构图并没有被本身的造型特点所束缚,而是利用空间的倾向性,创造出向心与旋转的运动感和动态张力。如在圆形玉璧中,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镂雕龙纹环E133-2通过双龙双螭首尾相连、互相追逐的结构来创造向中心旋转的张力;龙与螭之间的对峙又产生了互相冲突的对抗力,两种力量的互相牵制使造型极富动感。
心形构图以玉韘为主,通常以左右两侧不对称的附属纹饰变化来表现反向或偏移的倾向张力。玉韘的结构为上窄下宽的长椭圆形,中心圆孔位置偏上,顶点向上收尖。这种结构本身便使观者产生了向上的视觉判读。因此为了避免玉韘显得头重脚轻,玉工们设法将重心下移,在两侧出廓的动物纹饰上采用向下的姿态来平衡视觉中心。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妻窦绾墓出土的2:4154心形玉佩,器物上无论是左侧的凤首朝向还是右侧的花蕊卷曲方向都为倒置状态。这种巧妙的形式将向上的玉韘结构和向下的装饰纹饰相结合,使观者在视觉上不断进行两个方向的判读。
在横长方形的玉器中,其本身的外形会给观者带来向左右或上下的倾向张力,而向左右扩张的力量倾向尤为明显。如徐州狮子山出土的一件双龙透雕玉佩,其向左右扩散的张力一方面追寻着流转回旋的云气向上弥漫,另一方面依循着相互回望的龙首向中轴线回压,在力量的交织与循环中形成强有力的动态视觉之美。
2.3 多维取象的造型方法
西汉复合造型玉器中的多维取象是一种在同一件器物上雕刻多种视角呈现的不同造型的造型手法。玉工们根据不同的动物纹饰和器形需要,选取合适的视角来塑型,在平面的形态下采取分段式的多维视角取象,以正视、侧视、俯视等角度展现神兽的头、颈、胸、脊柱、尾巴等部位,从不同视角表现单个动物形象或将不同视角展现的形象组合在单个玉器中,营造出强烈的立体感和动态感。一般来说,玉饰上的形象种类越丰富,运用的视角便越多,雕刻技法多采用圆雕、浮雕等立体化的表现手段。如陕西汉武帝茂陵园出土的兽面形四神玉铺首,整体为横向的长方形,表面纹饰布局巧妙地将兽面纹与四灵纹组合在一起,兽面纹以正视视角表现,四灵形象以侧视、俯视视角表现,玉铺首整体构思精巧,四灵神兽和兽面纹的组合展现了浪漫神秘、和谐统一的汉代风格。
进一步分析这些复合造型玉器中动物形象的多视角组合取象方式会发现,神兽的头颈部通常为正视视角的完整形态,单独来看,整体非常协调。但当身体与头部相配合时,由于前胸的造型视角转向了俯视,此时呈现的图像与正常的生理结构相冲突,神兽的尾部和爪子的配合关系也与正常的生理结构不同。此类扭转视角的呈现方式虽违背了正常的生理结构,但不同视角平面造型的交叠扭转实际上是将三维立体的形体投射在二维空间的变形,因此在视觉上会给人以强烈的扭转张力和立体效果[3]。多维取象的造型方法是西汉玉工在平面中营造立体化效果的极致创造,通过浮雕、镂雕、圆雕等多种工艺的精湛运用展现出登峰造极的艺术效果。
2.4 突破平面的立体构成
在部分复合造型玉器的构图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样式,表现为神兽的身躯穿过器物边框延伸至另一面,环绕器物的周围并盘踞于两面的形式,有着穿越边界的自由灵动之感。如广州南越王汉墓出土的D89-3玉剑珌在两面雕有两只螭虎,其中一只为过墙螭兽与另一面的螭兽相互呼应,生动传神。可以发现此件玉剑珌中的穿墙螭兽通体以圆雕工艺雕琢而成,而另一件螭纹玉剑首上的穿墙神兽则结合了圆雕与浅浮雕的技法。在外周的壁面上雕琢一对龙,龙的头及前爪盘踞剑首表面,脖子以下的身躯仍悬于壁上。圆形是極具形式感的形状,玉工为了不破坏圆形剑首的整体轮廓,将侧边壁面上的躯干部分作浅浮雕处理,器物转折处没有堆砌多余的纹饰,而在顶面的龙首则以圆雕精雕细琢,巧妙而精致。
由以上分析可知,玉工通过穿墙螭兽的巧妙构思将器物的阳面与阴面相连接,器物的两面不再是单独的表现画面,而是融为一体,突破平面,达到了和谐统一又富有变化的艺术效果。
2.5 灵活运用的模块单元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西汉复合造型玉器中各类神兽的身躯和羽翼往往呈现云纹化的构成方式。这些螺旋状的云纹在西汉发展成了模块化的纹饰单元[4],并与神兽形象互相交织,形成了具有汉代风貌的艺术形式。单元式的卷云纹以多样的组合形式构成形象。而造型简洁、容易制作的特性也使这种纹样单元适用于多种玉料形状。因此,汉代玉器的纹饰题材往往营造出众多神兽腾绕隐没云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仙境场景。例如,河北省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透雕双龙谷纹璧,其上端出廓部分透雕出一对大小和纹饰完全相同、背向而立的双龙,身躯曲线表现出优美的“S”形,龙尾向上延伸与云气纹形态融合共构,呈现出多对“S”形相背排列和组合的巧妙构图,龙身后足透雕的云气纹单元衔接协调了主纹饰与璧体,更丰富了图式内容。此器中“S”形龙纹与云气纹单元的巧妙配合不仅体现了玉工在规整中寻求变化、在静态中寻求动感的美学观念,更营造出汉代人寄托在玉器中的氤氲弥漫、云气升腾的仙家胜境。
3 西汉复合造型玉器的艺术风格
从西汉复合玉器体现的独特设计理念可以发现,西汉的玉器设计者擅长将各种不同的自然要素组合再造、相融一器,在技法上更多地运用浮雕、镂空、透雕的立体化技艺来强调造型,在纹饰上将各类自然形象加以神化,形成了气韵生动、写意抽象、古拙灵动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
3.1 气韵生动的线条之美
西汉玉器纹样的风格特征与线条艺术的构成息息相关,从视觉感受来看,曲线比直线更容易在观者心中产生弹性与张力,不同曲度的造型表现出不同的运动倾向。与战国时期相比,西汉玉工更擅长运用自由畅快的曲线来营造富于律动和节奏的动态美感。具体来看,战国早期龙形玉佩与西汉中期螭纹玉剑璏的造型虽都为形似“S”的曲线造型,但能明显感受到西汉螭纹的曲度更大,表现出充满气韵与生动的线条勾形。如果说这里的“气韵”是指线条展示出的生命力,那么“生动”就是这些线条组合而成的运动之美,“气韵”与“生动”不可分割,浑然一体。在立体的玉饰中进一步凸显了线条的这种特性,快速流动的线条充满了动势,表现出鲜明的轮廓与细节。
除了线条的曲度变得更大,器物整体形制由扁平转向曲面,玉工们灵活使用各种雕刻技艺使玉饰向着更加立体的造型艺术发展。在塑造动物形象时,轮廓线所构成的面不再是呆板的平面,而是强调曲面造型来产生强烈的立体感,并随着场景和时空变幻而形成不同的光影效果。玉工们精湛的雕琢工艺,使平面的线条产生层叠分明的立体效果,体现了时空交织的动态美感。表现“气韵”与“生动”的线条正是西汉继承楚美术风格的重要表现。化静为动、虽静犹动的简洁线条表现出动物生命的神与气,快速流动的线条使画面产生了无限的生机和运动感。
3.2 写意抽象的造型之美
西汉玉器的审美继承了楚人的美学风格,在楚人的观念中,事物有着表象以外的精神体系,更注重感性想象的真实性而不是理性认知的真实性,在雕塑造型上不那么理性、规范、合乎结构比例,而以突破逻辑形式限制的形象思维方式,表现出写意抽象、自由浪漫的审美特点。因此,在具体的纹样造型表现中,以多维取象的造型方法将神兽身体的不同部位进行平面视角的交叠扭转,以突破平面的造型布局,展现出神兽环身穿越于器物两面的巧妙构图,塑造出不符合实际比例结构的饱满身躯和强烈扭转的夸张姿态。这种特点体现于玉剑饰中的各类螭虎造型,过长的脖颈、弯曲到极致的脊背、卷曲飘逸的长尾、矫健而有力的四肢,神采奕奕,昂扬向上。不重视细节的修饰雕琢和主观的传情达意,最为突出的是过分弯曲的身躯、强健有力的四肢和飘逸灵动的姿态,如此简单纯粹且具有野性的形象,表现出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和力量[5]。
3.3 古拙灵动的气势之美
西汉复合造型玉器中神兽造型明显注重对象的姿态动作,而不是具体的面貌特点。这些神兽形象以夸张扭曲的姿态组成各种图示。虽然大小不符合比例、身形姿态不符合常理、过于方的折角也缺乏柔美,但这些不符合现实结构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带来丝毫怪异之感,还通过笨拙而又直白的艺术表现,增添了器物的运动力量和气势之美。这种力量和气势在玉器构图中常常通过弯曲的线条来表现出一种或几种动势,产生打破器物限制的视觉感受,营造出充满气势与生命力的形象。而在西汉复合造型玉器的视觉表现中,动物不是以其精神个性或内心状态,而是以它们的实际活动和动作姿态来展现与世界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的。正因如此,复合造型玉器的表现题材中常出现激烈紧张的神兽对峙和戏剧性的争斗场景。活泼灵动、翻腾奔跑的各类神兽在快速的运动和力量比拼中展现出古拙灵动的气势之美。
4 结语
西汉复合造型玉器通过各种设计形式的视觉表现将不同动物的自然屬性融于方寸之玉间,体现出独属于汉代的纵观天地人神的浪漫宇宙图景。在此番图景下,复合造型玉器中动物与动物之间相通,动物与植物之间相通,动物与人之间也相通,展现出“联通万物”“适形于器”的时代审美特征。文章从艺术设计学视角出发深入探究西汉复合造型玉器设计方法,梳理玉器复合造型的组合逻辑和艺术特征,从这些复合造型中感受西汉玉器艺术的表现形式,探讨传统纹样的创新组合形式,以提供更多的设计思路与途径。
参考文献:
[1] 王祖龙.楚美术观念与形态[M].成都:巴蜀书社,2008:88.
[2] 李竞恒.先秦两汉时期的双首龙玉器源流及其文化含义[J].中华文化论坛,2019(3):37-45,154-155.
[3] 蔡庆良.玉器鉴赏之六汉代玉器(上)[J].紫禁城,2010
(8):38-47.
[4] 马颖.汉代玉器审美形式与风格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8:79.
[5] 李泽厚.美的历程[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136.
作者简介:王芷晴(1998—),女,湖南郴州人,硕士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视觉传达与信息设计。
崔华春(1974—),女,山西太原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与理论、视觉传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