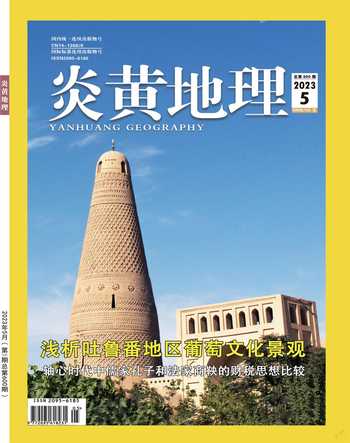大运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逻辑、内在特征与传承路径
王辉?张丰?李平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载体,以身體为符号,须借助“人”的行为活动体现。现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文本分析法、实地调研的研究方法,以“人的行为”为逻辑起点,探究大运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境及传承路径。探究结果显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逻辑是移居者“求健”的外在表现和定居者“求适”的内在需求。新时代大运河体育非遗主要面临着管理者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度不够、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信心不足、受众传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性不强等问题。现依据大运河体育非遗的内在特征,针对面临的现实阻碍提出建议。通过“上”“下”合力,提高管理者的重视程度;通过“内”“外”同步,提升传承人的文化自信;通过“多方”协同,加强受众自觉传承的意识,从而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勇气,也蕴含了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开启了大运河文化传承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八年来,国家层面陆续推出了《大运河文化传承保护规划纲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北京、江苏、浙江等沿线城市分别制定了规划方案,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推向了新的高潮。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大运河丰富的文化遗产,大运河在入选名录中以静态的遗产点和遗产段为主,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其重要的“活态遗产”[1],这些“活态遗产”集中反映了大运河沿线居民的实践活动、生活方式、生产技艺、行业组织以及传承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社会需求的“文化互惠”,与地理环境、人口、经济、群体、行为、政治、心理、文化等内生性社会学要素紧密相连[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呈现人类历史文化的载体,是现代人追根求源的产物,是体育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见证[3]。因此,探究大运河沿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逻辑,挖掘大运河体育非遗的内在特征,分析新时代大运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现实阻碍,不仅有利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传承,还有利于大运河文化带的高品质建设。
大运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逻辑
大运河作为人工开凿的水运河流,有明确的目的和作用,无论是其最初被用于军资配送,还是后来的漕运输送,都是国家政治意识的体现。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运河沿线主要有两类人群,一类是“移居者”,该类人群以船为家,长期在河上漂泊,以运送物资为生;一类是“定居者”,也就是依河的常住人群。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环境中潜移默化的精神积淀和穷年累世的感情酝润[4]。大运河特殊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孕育了独特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本体、以人为主题,是通向身体哲学的身体遗产[5]。体育非遗以人为载体,以身体为符号,须借助“人”的行为活动得以体现[6]。本文从大运河居住人群的视角来探讨大运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逻辑。
移居者“求健”的外在表现
“健”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因。“求健”是人类最早产生的生存意识,伴随着人们对“健”的追求,产生了武术、气功等传统体育项目[7]。移居者作为大运河沿岸的一类特殊群体,其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与定居者有着很大的差别,主要的生活环境往往局限于船舱的一隅之地,所以他们采用了特殊的健身方式,例如江南船拳、渔舟剑浆等传统体育项目。
定居者“求适”的内在需求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我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生成与延续必定离不开自然条件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制度保障。历代聚居人群的繁衍生息和适应性选择,塑造了风格迥异的身体运动类型[8]。依据城镇的形成条件,可以将大运河沿线城镇分为三类:一类是早期的古城聚落逐渐扩展而成的城市(现运河沿线的大型城市),他们构成了大运河最初的据点;二类是因运河开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商贸聚集地(现运河沿线的古商业街);三类是靠河而居的村庄,受自然因素影响,部分大运河形成的滩涂,吸引了流动人群在此建房落户,形成了运河沿线的村庄(现运河沿线的村庄)。沿线居民为了适应大运河开运带来的一系列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得不主动适应新的环境,进而形成了如沛县武术、邳州狮舞、孙氏太极拳等传统体育项目。
大运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特征
大运河沿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典型的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动地反映了沿线居民的生活智慧。大运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体育非遗的传承性、活态性、身体性、地域性、流变性、脆弱性等基本特征”[9],还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包容性
大运河的通航,不仅给沿线居民带来了新的商机,还带来了新的文化冲击。随着大运河流动的不仅是船运物资,还有移居者的文化行为。定居者的文化行为也会受到移居者文化习俗的影响,久而久之,促使了大运河沿线传统体育兼容并包。例如,沛县武术是江苏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包含了少林拳、大洪拳等十二种拳种。
多样性
民俗体育是一种地域民众体育活动的选择,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大运河纵向贯连了中国东部的8个省市,56个核心区域,沿线居民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风土习俗差异很大,因此产生了多样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据统计,大运河沿线城市国家级体育类非遗项目有90项,省级项目达到了480余项。舞龙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在全国各地分布广泛,截至2015年12月31日,收录于国家级和省(直辖市/区)级的舞龙类非遗项目就达到了187项[10],大运河沿线城市中舞龙类非遗项目达到了20余项。
独特性
体育非遗起源并根植于特定地方与特定人群的地域文化,是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化。大运河文化遗产包含27个河道遗段,58个遗产点,每个遗产点对地方经济、人文的影响各不相同,随之形成的体育非物质文化也各具特色。例如,睢宁市的龙虎斗突出的是龙和虎的互动;无锡的凤羽龙采用不同材质来制作龙具,从而突出地方特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直溪巨龙通过龙的长度和造型突出巨龙村民的智慧;邳州狮舞中公狮和母狮共同表演,通过狮子把门、狮子下山等故事情节的表演,突出邳州狮舞的特色;浙江草塔抖狮子由1个狮笼、1个彩球、5只狮子和若干纤绳组成,通过演出人员牵线控制彩狮,从而呈现出彩狮在狮笼中或跳、或抖、或扭、或举趾搔耳等动作;浙江境内的九狮图是由提线木偶和地面舞狮结合产生的,又称“拉线狮子”“颠狮子”。它由狮笼(狮子架)、9只狮子和1个彩球组成。狮子和彩球连有38根纤绳,由狮笼后的11名演员操纵表演,展示狮子在空中挪腾跳跃等动作。
大运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的现实阻碍
管理者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重视度不够
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国家级及省(市)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到了570项,再加上市级、县级的体育类非遗项目,数量超过1000项,但在各地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或是规划中,却很少有针对体育类非遗保护的策略和方式。在大运河文化带、文化公园的建设规划中,也鲜有关于体育类非遗的内容。体育非遗作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在全民健身、体育公园建设、体育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在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公园、大运河旅游等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但由于管理者或组织者对体育类非遗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大运河体育非遗的传承、产业化发展仍举步维艰。
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对体育非物质文化的自信心不足
目前,体育非遗的传承主要由特定的传承人或是传承群体进行传承和推广。受体育非遗本身的特征和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等因素影响,体育非遗的传承一直是处于“输血”状态,自身的“造血”能力差,传承人或传承群体的传承依靠政府扶持才能勉强维持。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体育非遗实地调研后,发现很多体育非遗项目的传承仅仅停留在申请认定的层面,只是为了完成考核,每年参与一两次表演或上级部门来参观或检查时进行表演,其他时间基本上没有活动。
受众传承体育非物质文化的自觉性不强
受众的参与度决定着体育非遗的传播广度以及传承人才的储备量。体育非遗文化传承的后备人才不足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体育非遗的社会化传承已成为各个项目的传承方式之一,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受众对所参与体育非遗项目的认识不足,自觉传承意识不强[11]。例如,在邳州狮舞项目所在地进行考察时,对于为什么没有参与舞龙舞狮表演的问题,当地居民大多表示传承舞龙舞狮是传承人的事情,跟他们无关。
大运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路径
“上”“下”合力,提高管理者的重视程度
体育非遗归属于当地的非遗保护中心管理,“上”受上级主管部门政策规划的指导,“下”受项目传承群体和受众推广項目的影响。上级主管部门的政策和要求,直接决定了体育非遗管理者的行动方向,因此,要提高组织者和管理者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提升他们对其的重视程度,就要从顶层设计层面提高对体育非遗的重视。例如,在各地的大运河文化带规划纲要、大运河体育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各地非遗保护政策等文件中应充分体现体育非遗的价值以及提出相应的推广方式。“有为才有位”体育非遗项目的传承效果,直接影响了组织者和管理者对体育非遗的印象和重视程度。在调研中发现,无论何种级别的体育非遗项目,凡是传承人积极推广的项目都能得到管理者的大力支持。例如,邳州跑竹马传承人一生致力于跑竹马项目的传承,在他的努力下,地方很重视体育非遗文化的挖掘,所以从江苏省各市县体育类非遗项目的数量来看,徐州市的体育非遗项目是最多的。
“内”“外”同步,提升传承人的文化自信
运动行为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外部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传承人传承决心的大小。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外部面临着资金、场地、器材不足,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条件制约。内部则受传承人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体育非遗项目的技术水平、管理组织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把体育非遗项目的传承当成“事业”的传承人,其传承的决心和效果都有明显提升。因此,要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信,不仅要注重改善外部环境,还要注重传承人提升的内部主动意识的增强和专业水准。
“多方”协同,培养受众自觉传承意识
在不断变迁的历史现实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传统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必须在现实“场域”即社会现实生活需求、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和城市化的社会变革中重新加以认知、评估、选择、发展和创新[1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曾是大运河沿岸当地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但随着大运河功能的改变,大运河沿线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民众参与传统体育的自觉性下降。要提高受众参与体育非遗的自觉性,需要体育部门、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旅游部门、教育部门等多方协作,共同宣传、推广大运河体育非遗项目的开展,提高人们对体育非遗项目的好感度及好评度。
参考文献
[1]彭兆荣.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纲要[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04):83-87.
[2]李阳,赵刚.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性发展的思考[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37(03):324-330.
[3]李平,王辉,赵功群,等.基于传承人视角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7(04):70-75.
[4][8]薛浩.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成机制与路径选择[J].体育文化导刊,2019(05):41-46+52.
[5]向云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M].中华书局,2013.
[6][9]陈小蓉.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特征、功能、分类[J].体育科学,2022,42(04):14-21.
[7]刘一民,宋红霞,刘翔.健:中华传统体育的文化基因——基于健文化生成演进的历史逻辑[J].体育学刊,2021,28(04):8-15.
[10]王亚敏,陈小蓉.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舞龙项目分类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7(01):83-87.
[11]王辉,李平.“特色小镇”建设进程中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路径研究[J].体育科技,2019,40(04):94-96+99.
[12]王继帅.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文化资本生成逻辑[J].丽水学院学报,2021,43(02):51-56.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