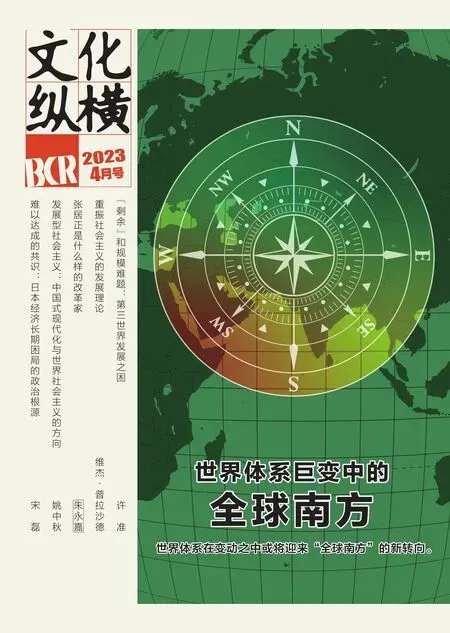美国还能打“互联网自由”这张牌吗?

人工智能(AI)作为科技前沿的热门话题,其发展一直为人瞩目;而在大国竞争中,谁能更好地开发和利用AI,就将在未来占得先机。1月27日,美国和欧盟首次在该领域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预测极端天气和应对气候变化、应急响应、医保事业、电网运行,以及农业发展等五大重点领域就AI的应用展开合作。协议中的一段话耐人寻味:“今天的声明也建立在《互联网未来宣言》中提出的愿景之上,即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开放、自由、可靠和安全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我们期待着通过这一倡议深化我们与欧盟的合作。”
《宣言》系去年年中由美国总统拜登牵头签署,该宣言一共两页半,没有什么深文奥义,仅罗列了几大价值,可重点还是重申“互联网自由”这一老套口号。虽说如此,《宣言》背后所蕴含的战略布局,无疑值得我们结合科技治理的内外新形势,来重新思考应对之策。
命运多舛的《互联网未来宣言》
其实,这份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彼得·哈勒尔和白宫技术政策特别助理、哥大法学院教授吴修铭牵头制定的《宣言》谋划已久,但无奈庙堂朝野阻力颇大。一方面,由于早期媒体披露的草案要求签署国只能使用“值得信赖的”网络设备,外界视其为夹带私货打击中国制造,没有主义,只有生意。更让互联网自由分子忧心忡忡的是,这类联盟目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另起炉灶将稀释掉其他联盟的努力,特朗普的“清洁网络计划”就是前车之鉴。
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最终比原计划晚了半年多,拜登领衔大笔一挥,《宣言》凑齐了61个国家。可仔细考察签署国名单,全球网民数前十的国家中,竟有四国缺席——前两名中国和印度、第五名巴西、第八名俄罗斯。中俄本是《宣言》斗争对象,没上榜天经地义。印度和巴西也由于此前国内互联网管制,被排除在外。可是,就算是这61个国家,又有哪个国家未曾违背《宣言》宗旨呢?哥伦比亚军方刚被声讨针对记者和政客的监控,尼日尔才经历十天之久的全境封网,匈牙利和以色列还在为间谍软件Pegasus挑起的事端背锅。就连美国“自己人”英国,前脚刚签署《宣言》,后脚就在议院继续推动强化内容管制的《在线安全法案》。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宣言》的影响力,也因此《宣言》不大可能对互联网国际治理格局带来实质性影响。总的来说,拜登政府的这步棋,并不是什么高瞻远瞩,充其量只是以“互联网未来”之名,为“互联网自由”招魂。
什么是“互联网自由”?
“互联网自由”口号由来已久,发端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兴盛至特朗普上台前。其间,“互联网自由”发展出两层内涵:市场自由和信息自由。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首先,互联网自由中的市场自由,是新自由主义在互联网产业的体现。美国通信产业的扩张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时,美国经济内外交困,内陷经济滞胀,外临日欧大敌;于是,以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出去管制(de-regulation)药方,一步步颠覆了从进步运动、新政时代以来的经济政策。互联网产业兴起后,无论是民主党当政,还是共和党上台,延续此前去管制政策基调,给孵化期的互联网企业开了多盏绿灯,由此成就硅谷繁荣。[1]
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讨论最初聚焦的是市场自由,可是市场自由固然重要,但其影响局限在经济领域,对国际政治、国际社会的影响有限。很快,美国便发掘出互联网自由的另一副面孔——信息自由,它将带来更持续的国际影响力。一开始,克林顿政府并不强调信息自由。基于当时对互联网的理解,信息自由不言自明,无须争取。的确,互联网技术刚出现时,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互联网技术将彻底颠覆传统主权国家对舆论的管控。经典表述出自克林顿政府首席技术政策专家迈格辛纳,“互联网技术短期内使主权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并且长远看来,信息终将摆脱主权国家的干预”。克林顿本人也开玩笑道:政府控制互联网信息,就如同“把果冻钉上墙”一样困难。不曾想,没过几年,“果冻”真就上了“墙”:各国政府不但利用掌握的技术搞信息审查,甚至可以指挥更懂技术的互联网平台搞信息审查。这么一来,反而把信息自由这一层面的“互联网自由”意识形态威力给衬托出来:信息自由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恰恰是反对国家干预信息的自由传播,这一点与美国冷战以来的外交姿态一拍即合。因此,小布什政府除了继承和推进克林顿政府市场自由这份政治遗产之外,也在信息自由层面做足了文章。为此,小布什还专门成立“全球互联网自由工作组”(GIFT)督办此事,其使命就如其英文简称,到处送礼撒钱,资助各类促进互联网自由的公民组织和技术项目。
接下来数年间,白宫的类似论调不绝于耳,其高光时刻无疑是2010年1月21日,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发表题为“互联网自由”演讲。希拉里一方面谈理念,强调互联网自由之于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谈现实,她巧妙地将互联网自由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主张当前互联网自由现状已“威胁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2]在“互联网自由”这面大旗下,倘若一国政府过度审查和干预互联网内容,就会被扣上互联网不自由、侵犯人权的帽子。通过将互联网自由对接上民主和人权话语体系,希拉里为美国政府直接干预他国政治做了强力背书。
就在这一通洋溢着振奋之情的演讲一个半月后,奥马巴政府以GIFT为班底,改头换面成立新的“网络自由工作组”,落实互联网自由事业,其资金支持比小布什政府更大,也更具针对性——超过1亿美元被用于资助加密、反内容审查技术工具和相关民间组织。正是在希拉里演讲后,互联网自由开始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崭露锋芒。表面上,它关心的是信息的自由与否,但实际上,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与平民化,它逐渐成为一种足以影响他国政权稳定的话语输出。并且,美国经过多年经营,已手握两大保障:其一,互联网自由的直接受益者是微软、谷歌、脸书、推特等美国互联网平台,它们具备技术和市场的全球统治地位,借助这种统治地位,也为了延续这种统治地位,它们不遗余力地将互联网自由的逻辑和话语,推广到其国际商业版图的每一寸领地。其二,互联网领域颇有影响力的自治组织,长期以来多由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互联网域名管理就是其中典型,直到2016年,美国政府才极不情愿地移交控制权。
美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控制权上的绝对优势,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当然,它们也没有坐以待毙,在信息控制、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方面与美国推行的互联网自由开辟战场,致使这些美国互联网巨头和自治组织也无法置身事外,轻则被罚没,重则被拉黑。即便在外略有阻力,“互联网自由”在希拉里演讲之后一时间成了国际外交的关键词之一。尽管很难把当年年底兴起的“阿拉伯之春”完全归功于希拉里演讲,但后续史料披露也表明,这次在苏东剧变之后全球最大的区域政治格局变动,也与美国有直接关联。[3]互联网自由给美国帝国主义开了一扇便门,不战而屈人之兵。
“互联网自由”消亡史
“互联网自由”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成为动员群众星火燎原的社交网络热词。然而在随后几年内,这一理念却屡遭挫败,跌下神坛。可以说,本世纪最初二十年,前十年是火山爆发,顶峰是希拉里演讲;后十年是熔岩冷却,冷水是一盆接一盆。
第一盆冷水,便是美国在互联网自由问题上的屡次心口不一、自相矛盾。比如,在希拉里演讲后不久,维基解密爆料,希拉里亲自向美国外交官下令网络监听他国外交情报,甚至还监控联合国秘书长。一国情报机关的这类监控,在外交领域本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希拉里高调演讲在先,再出手就是打脸。这类自相矛盾并不止这一起。内有“9·11”后大规模国内监控、阿兰·斯沃茨自杀悲剧,外有推动阿拉伯之春、网络攻击伊朗核设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互联网自由战略的最大挫折,还是来自斯诺登事件,该事件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全球电话和互联网进行监控的情况,各大美国互联网公司都参与其中,监控对象不仅包括其战略敌手,也包括本国公民和西方盟友。可以说,斯诺登彻底打破了美国政府原有的互联网自由战略路线图。直到奥巴马政府后期,奄奄一息的互联网自由理念,已不再具备希拉里演讲时的号召力。正如哈佛法学院古德史密斯教授所言,美国从未毫无保留地坚守互联网自由,也不是两手干净到未曾插手控制本国和他国互联网,因此美国大可不必,也没资格以“互联网自由”王国自居。[4]
历史有时很吊诡。新自由主义浪潮虽然给互联网自由的第一副面孔市场自由注入源动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催生的右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后者中断了美国一贯的互联网自由立场,不再强调国际自由市场和基本人权这套普世价值,甚至在某些领域彻底甩掉偶像包袱,筑起贸易壁垒,直呼“美国优先”。在特朗普任期内,媒体真假新闻之辩、“黑命贵”运动中的言论封控、国会山后特朗普被推特和脸书封号等事件,加速了互联网自由的消亡。这些事件单看可能无关宏旨,但串联起来,毁掉了美式互联网自由的公信力。
第二个挫败来自互联网自由内涵自身的演变:原本一体两面的市场自由和信息自由,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互联网自由的两个层面通常被认为不可分割:市场自由是信息自由的保障,而信息自由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自由。互联网“端对端”架构,流淌着自由基因,越自由越发展,越自闭越萎靡,这似乎已成铁律。难怪希拉里演讲时信誓旦旦,“那些限制信息自由或者侵犯网民基本权利的国家,将自绝于新千年(互联网产业)发展机遇之外”。然而,近年历史表明,二者关系并不是双向奔赴这般简单。
首先,市场自由并不必然促进信息自由。市场自由意味着去管制,二者互为表里。可现实是,随着平台的扩张甚至垄断,平台对互联网的控制程度越来越高,其为自身利益而利用技术设下种种言论控制,手法之隐蔽,范围之精准,政府有时也望尘莫及。因此,脱离管制的平台可能成为信息自由的新敌人,马斯克接手推特后的一系列闹剧就是例证。信息控制也未必导致市场萎靡,中国就是典型。中国不但孵化出世界第二大互联网产业,而且在数字支付、电子商务、新一代网络设施、人工智能等领域大有赶超美国之势。这就让带着傲慢与偏见的“互联网自由”拥趸们难以理解。
其次,即便在信息自由的制度建设方面,对比2010年希拉里演讲时,美国也不断“开历史倒车”。必须承认,美国作为“互联网自由”倡议者,在信息自由方面,向来是全球表率。其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是1996年《传播风化法》第230条款。该条款规定,除知识产权等极少数领域,对于网民在平台上发布的信息,平台无须承担任何责任。230条款背后是宪法第一修正案,230条款是面子,第一修正案是里子,这种信息自由,全球独此一家。
然而,面对越发强势的互联网平台及其背后超越主权国家的全球资本,美国政府也开始担心:信息太过自由,会不会遭遇反噬?例如,正是由于法律责任的豁免,违法成本下降,使得美国社交平台成为谣言、假新闻、仇恨言论、恐怖主义的“欢乐谷”。于是,近些年风向转变,美国也开始限制信息自由,强化内容治理,其中最成功的改革是2017年限制网络卖淫信息自由流通的《禁止网络性交易法案》。仅在2021~2022年间,美国参众两院就酝酿了20多个法案,都致力于改革230条款,它们大致分四类:完全推翻230条款;限制230条款适用范围;增加网络平台义务;限制网络平台主动审查用户言论。可以预见,230条款未来即便不被完全推翻,也必将进一步受限,而在它庇护之下的信息自由理念也将随之受挫。
或许因为互联网自由自身的无力,近些年,美国互联网自由战略在国际上也面临重重阻力。以其战略伙伴欧盟为例,就不是一味顺从美国,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数字服务法案》等立法举措,限制美式互联网自由理念。就像欧洲老板德夫纳写给美国老板施密特的那封公开信说的,“从我们欧洲人自身角度出发,我们害怕谷歌,因为它威胁到我们的价值,威胁到我们的人性,威胁到全球社会秩序,以及欧洲的未来”。
而且,不管美国愿不愿意,互联网自由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地让步于互联网秩序。各国政府正在拆分互联网,铸造物理的或虚拟的数据和信息壁垒,目的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划出一片更可控的网络空间。在数字时代,国内数据和信息的控制,成为各国内部治理的关键;而能不能最大程度地把握数据和信息的国际流动,构建一个对本国有利的国际互联网秩序,成为其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拆分,还是控制,这都与早期互联网自由的愿景背道而驰。无怪乎从希拉里演讲后,民间机构统计全球互联网自由度一路下跌,这表明一个大趋势:尽管程度不一、手法各异,但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将曾经开放自由的互联网,分割成一块块越发可控的自留地。或许在美国人眼里,这些自留地下面就埋葬了其苦心经营的互联网自由理念。
希拉里在那次演讲中提到:“现如今,美国和中国在互联网自由议题上有分歧,我们坦率而一致地解决这些分歧。毕竟,这不仅是关乎互联网自由,而且关乎我们未来整个世界。”十三年后,回味这句话,让人不禁感慨:随着互联网秩序不断遭遇挑战,中美在互联网自由这个议题上的分歧在缩小,反而是双方“积极、合作和密切关系”随着新冷战的升温,迎来比以往更大的考验。能不能在新国际格局下,打好和应对好“互联网自由”这张老牌,成为两个互联网大国共同需要面对的考验。
拜登此番借《宣言》为“互联网自由”招魂,并在后续科技治理政策中一再强调,自然是与其对外(尤其对华)战略部署有关。平心而论,尽管消亡征兆不断涌现、矛盾之处暴露无遗,但其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野心未必完全没有市场。这是因为其背后依然有一整套多年积累下来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支持,它对于绝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甚至西方普通民众仍有一定吸引力。况且,哪怕“互联网自由”就此消亡,还可能出现其他新提法。对于技术人员和网络用户规模都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而言,互联网本身永远是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能否审时度势,争取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中更大的话语权,并针对《宣言》和相关政策提出稳健而又睿智的交锋之策,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注释:
[1] Jeff Kosseff,The Twenty-Six Words That Created the Interne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Anupam Chander,“How Law Made Silicon Valley,”Emory Law Journal, Vol.69,2014, pp. 639.
[2]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Archived Content,January 21, 2010.
[3] Evgeny Morozov,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Public Affairs, 2011.
[4] Jack Goldsmith,“The Failure of Internet Freedom,”in David E. Pozen ed.,The Perilous Public Squa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