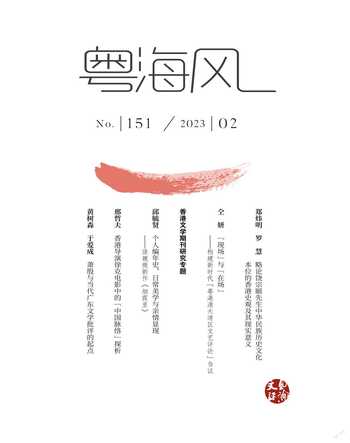略论饶宗颐先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本位的香港史观及其现实意义
郑炜明 罗慧
小引
饶宗颐先生乃一代通人,世人称之为大师。的确,饶先生是于古今中外文史哲艺之学无所不窥的,他曾经耕耘过的领域很多,如上古史、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悉昙学、宗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历史学、方志学、古典文学、艺术史、目录学等,皆有著述传世[1]。至于本文所要论及的饶先生的香港史研究,其实只占他全部学术的极小部分而已。但是,我们相信透过探索饶先生香港史研究的历史学思想、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点,仍然可以从小中见大,一窥饶先生的学术的深奥内涵。
曾有人指称香港是一部大书,深奥而且难以读懂。这话说得没错。我们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准确地认识香港历史和文化的渊源,跌入了西方论述香港历史时预设的话语陷阱,犯了人云亦云的毛病,故此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每有底气不足、畏首畏尾的表现,这是很可惜的。
一、饶宗颐先生开始研究香港史的背景
饶宗颐先生研究香港历史,始于1958年冬天。他在其香港史研究的核心专著《九龙与宋季史料》一書的引言中曾经这样自述:
百粤史事,余曩者稍曾究心……于宋帝海上播迁史迹,妄有著论,十载以来,此调久已不弹……去冬以硇洲问题,与简君往覆商榷,文字累万言。[2]
此书刊行于1959年末,文中“去冬”所指应即1958年冬天。至于“简君”,乃简又文先生;饶先生的《九龙与宋季史料》一书,开卷有简氏序文。
据简又文先生序中所述,饶先生曾向简氏自言“余本无心研究九龙史迹,自前岁拜读尊著,始措意及之”[3] 云云。可见饶先生本来无意去开拓自己旁涉香港史研究这一领域的。
原来在20世纪五十年代时,香港学术界一时南下的文人、学者云集,其中包括罗香林先生、简又文先生、饶宗颐先生、王世昭先生等,他们都对香港九龙半岛与宋末二帝相关的史料和史实极感兴趣,于是好朋友之间会就这个范畴的学术问题,展开深入的口头上的探讨,其中又以简又文和饶宗颐二位先生用力最深,最终二位先生在1960年前后,都正式发表了相关的著作[4]。简氏乃饶先生早在抗日战争避寇广西时已结识的好友;罗氏则曾于抗战胜利后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乃饶先生的老上司,而当时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又成了同事。总之,简、罗和饶三位先生一直关系友好而密切,当时是经常切磋琢磨学问的,这一点在简氏序言和饶先生自己的引言中都有述及,于兹不赘。他们在1957年至1960年年中这三年多里,对南宋末与九龙的历史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其贡献在香港史研究这一领域的学术史上,是磨灭不掉的。
还有一个背景是必须一提的,那就是饶先生的家学。饶先生的父亲饶锷先生,也是一位学者,尤其擅长于方志学和地方文献之学,著有《潮州西湖山志》和《潮州艺文志》等[5]。饶先生幼承家学,父亲便是他的启蒙老师,因此他从小就打下了很好的方志学和研究地方史的基础;少年丧父后,不久便续成了饶锷先生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自己又主编了民国版的《潮州志》(其中就曾撰写过南宋末二帝播迁海上的史事),并著有《潮州丛著初编》等。此外,饶先生20岁左右又曾在国立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任纂修;抗战胜利后,被民国政府委任为广东文献委员会的九位委员之一。可以说,饶先生对地方史,尤其是广东省的各地地方史,有着极为厚实的基础。据饶先生接受香港中文大学何文汇教授访问时所讲,他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开始关注香港的历史。饶先生从20世纪五十年代末起,走进香港史研究这个领域,固然是因为受到朋辈诱发的兴趣,但亦可见其学术方面自有根基、渊源和缘命。
二、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为本位的香港史观
过去许多研究香港史的专家学者,喜欢以鸦片战争后清廷向英国割让香港作为香港历史的起点,而前于此的会被称为所谓的香港史前史,俨然有明文记载的香港历史应该由英国管治时期说起。此外,他们又会积极地宣扬传播香港在英人管治前乃一条小小的渔村,又或者是几乎等同于一块荒芜的石地等。这种处理方式的历史书写,其实是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史学最典型的表述,而目的只有一个,他们是想透过这种论述,坐实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观点:他们想要预设地证明殖民地政策,在政治上和历史上都是正确无误的,因此这些被殖民的荒凉或弹丸之地,才得以发展起来和有所成就,而这一切又都是殖民主的功劳。这一类观点,至今在香港史学术界和现实的香港社会生活中,还是很有市场的。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饶先生一如许多他那一辈的学者一样,都是很坚定地恪守中国历史学家传统的。他们大多不爱空谈什么历史和文化的理论,反而会穷究史料、考证史实,以委婉的文笔隐晦地、若不经意地写成传统的史地考据文章,以他们所揭发的更全面的历史事实,来反驳一些失实偏颇的观点。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1. 饶先生在《九龙与宋季史料》卷三《行朝所经九龙半岛附近地理考证》和卷四《论官富场原属海南盐栅兼论其宋以前之地理沿革》,这两章写的就是要告诉大家,经过他的考证,香港的九龙半岛的官富场即后来的九龙城寨;古墐即后来的马头角村、马头围;浅湾即后来的荃湾;城门即后来的城门村、在城门河之上游;等等。而官富场在宋代乃东莞四大盐场之一,且在南宋孝宗以前已有,说明了此处已有盐官治署,属已有行政管辖的地方。饶先生又考论大奚山(即大屿山)在宋淳熙时私盐大盛,朝廷屡命广东官员查禁。[6]
2. 饶先生尝于《李郑屋村古墓砖文考释》一文中指出,该古墓乃汉墓,其中砖文上有“大吉番禺”“番禺大治历”等吉祥语的文字,可结合《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汉时番禺亦设有盐官,加上明代方志文献所记,故饶先生论证“自番禺盐官论之,九龙一带,汉时可属番禺”“晋以前,其地实属番禺所辖”。[7]
3. 后来饶先生晚年在笔者的协助下,又撰写了《由砖文谈东汉三国的“番禺”》,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论证了东汉晚期至三国时代,“番禺作为南海治所……当时港九深圳同属番禺辖境,为士赐、士燮父子势力膨胀的时期,或当燮弟武为南海太守时候……是番禺的全盛时期”[8];明确指出其时李郑屋村等九龙一带属士氏家族势力范围。
4. 他又引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之最末第二条,指出其中的“东官郡,汉顺帝时属南海……西邻大海。有长洲,多桃枝竹,缘岸而生”的“长洲”,“或即今日香港之长洲,亦未可确知”[9]。
5. 他在《港、九前代考古杂录》一文的“八、香港与元明以来之香市”这一节里,又引《永乐大典》广字号的资料,论证了榄香,即白木香的种植可追溯至元代;又引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之中相关记载,指出明代在粤东在东莞的寥步有药市、花市、珠市和香市等四市。他为此进一步做出了经济史角度的说明:
东莞以香市为输出大宗,人称为莞香,每年贸易额值银锭数万两以上。香港之得名,由于其村为运香贩香之港口。白木香或名香仔树,属于乔木之双子叶植物,新界大埔、林村、粉岭各地,旧尚有野生香木遗存。[10]
6. 到了1997年5月香港回归祖国在即,因为庆祝回归,饶先生应约为《中国文物报》写了篇《香港考古话由来》,很多话他就畅所欲言了:
香港在前代是香市贸易的港口,万历时郭棐著的《粤大记》书上海图出现“香港”的名字。元代东莞的白木香价值和银相等……有人说香港原来只是一个渔村,是不符合事实的。[11]
他还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了在香港南丫岛大湾考古出土的牙璋和越南的牙璋应有关系,认为可代表上古中原的礼制文化已传播远及中国南海边裔地区,意义非常重大,论断“具见汉文化在周秦以前与南海、交阯已有密切之交往为不可否认的事实”[12] [13]。
根据上引几条,已可清楚看到饶先生的香港史观。说来说去他只想忠于史实地指出香港这个地方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英国管治之前,早已纳入中国历代政府这样或那样的行政编制内,并且有着相当显著的经济生产,更是受到历代中国政府有效管治的。他曾有这样的一段言简意赅的结论:
香港是古代百越地区滨海一港口,英国人未来之前自有经济价值,盐业、采珠、香市、陶瓷业都有重要地位。[14]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上述这一小段正好代表了饶宗颐先生那种反殖民主义史观的、微言大义的中华民族的香港史观。纵观他的香港史研究,他竟对“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史,连一小段文章都没有,笔者认为这相当能说明饶先生内心的以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为本位的立场。
三、饶先生香港史书写的内容和研究方法
饶先生在香港史研究方面,内容从所涉及的时代言,起自上古夏殷,以迄英人管治之前。综合地看他相关的论著,笔者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一部“香港史纲——从上古至鸦片战争前”。
他的香港史研究,或详或简地包括了如下内容:
1. 史前岩画。
2. 殷商时期的南丫岛大湾出土的牙璋及所象征着的中原礼制文化已传播至中国南海滨海边裔地区的重大历史意义。
3. 从李郑屋村古墓的砖文考释,论及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香港属番禺辖下,再据《三国志·吴书》的相关史料,证明其时正是士氏家族势力在岭南最盛之时,今天的香港、深圳一带,皆受士氏管治。
4. 唐代灵渡山的灵渡寺和南汉时期屯门山的杯渡禅师石像等与杯渡禅师的关系,指出港九佛教史迹,应以此二处为最古。
5. 引北宋《元丰九域志》及《宋会要辑稿》等力证东莞乃古盐场,而大鹏城附近叠福场及九龙的官富场皆属东莞的盐场;又据考古发现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甲戌,有官富场盐官严益彰于香港北佛堂门为倡建天妃大庙之摩崖石刻,从而论定香港宋以来已是盐场,颇有经济价值。
6. 考证唐宋以来中国古籍和海图中与香港相关的许多地名。饶先生早于抗战前,已受到顾颉刚先生的赏识,曾受顾先生委托,编成了《古史辨》第八册(又名《古地辨》)[15]。又曾撰有《楚辞地理考》[16]。他是我国现代学术界历史地理学的先行者之一。他对香港地名的考释,除一如其上古地理的考证之外,更有一个特点便是努力从行政编制和制度史的角度,考证并说明了香港在不同朝代和不同时期行政归属的沿革,乃至该地公營的经贸生产等,这一点又不脱方志学者的本色了。他根据古图籍方志和其他文献,考证过的香港地名很多,如杯渡山、屯门山、大奚山、大姨山、大嵛山、大鱼山、大步海、官富寨等数十个,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7. 对南汉、宋、元以来香港历史上的经济生产和贸易等,如九龙大埔墟自南汉以来的采珠业及在元代时其与张弘范之子张珪的关系、宋以来的盐业、元以来莞香贸易和明以来的陶瓷业,皆有所着墨,可谓非常用心良苦。
8. 对南宋末二帝海上行朝曾经过九龙的史料、史事和史迹,有详细而深入的考究。其中发掘并公布了不少前人未知见的史料,如陈仲微《二王本末》的几种元代版本及邓邦述所藏旧钞本、邓光荐《填海录》佚书、元人黄溍《番禺客语》、宋人徐度《却扫篇》、黄安涛《高州志》等许多宋元以来文人笔记和方志著作中的相关史料等(恕不尽录);又考证澄清了一些前人如阮元、戴肇辰、陈伯陶等错误,并提出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实在皆有功于学术研究的向前发展。
饶宗颐先生的香港史研究,在方法上显而易见的是以传世文献史料的钩沉、汇辑和排比爬梳,以考证为主要的研究手段。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掌握是极其丰富的,已达到可谓惊人的程度,大家要知道他活跃的年代还没有以关键词检索文献的“e考据”法。而他对文献理解和诠释也是功力极其深厚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考证的时候,又会用上传统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文字声韵的训诂等传统国学的方法,尤其留心于各史书同一内容记载中的异文,从中他得出了不少心得和新的见解。例如:饶先生曾在著作中引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中的“司谏都尉”,指出“司谏”应为“司监”之音误,而“监”字又为“盐”字之形讹,实则段氏记载或已在说汉顺帝时东官郡(案:即后来东莞)已有“司盐都尉”这个行政制度中的盐官,在管治着包括“东有芜地(案:据《太平环宇记》引《郡国志》,应作‘芜城),西邻大海,有长洲(案:或即香港的长洲)”等在内的各个地方的盐政。因此,饶先生认为段氏此一记载“和早期香港不无关系”[17];若据唐代段成式此说加以推论,则香港有可能早在公元125年至144年间,已是附属于东莞,并归当时的东官郡司盐都尉管治的地区。此外,饶先生同样很重视考古出土的材料,这正是古史研究中二重证据法的传统;再加上历史遗迹的踏勘寻访(此属历史人类学范畴的田野调查),则已是三重证据法了。饶先生唯一没有使用的方法就是西方的历史文化研究理论。
余论
要公允地评价一位前辈学者,首先应该把他放在学术史上来讨论。
饶宗颐先生在香港史这一研究领域里(一如他在许多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从来不占主流或主导的地位,原因或与饶先生恪守中华民族文化本位、忠于考證所得、力主凡事皆须先求真有关。但今天回头再看,我们会发现饶先生连在香港史研究这个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打游击经过的小领域”,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性格和风格。当我们看见他信心十足地、充满乐趣地以传统的文献学和史学的方法来完成研究的时候,我们已忘了什么才算是主流。
老实讲,我们所认识的饶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对古巴比伦和印度的文化都很有研究,并且在学术上是主张兼收并蓄的、态度相当开放的纯学者。他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物质生活领域是非常不甚了了的,但我们清楚的知道,饶先生的心中永远横着一把秤,这把秤的一端是自古至今皆相对开放的、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而另一端则是经过公允地研究和书写的、符合史实的证据。
从饶先生的香港史研究,我们同样可以窥见并且深切地领会了他所常常强调的做学问的人必须义无反顾地拥抱寂寞是什么意思了。
而饶先生香港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今天大家都在关心所谓香港要“爱国者治港”和“人心回归”的时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人心回归,首先是要大部分国民尤其是香港的居民,对香港的历史有一个正确和准确的认知,从而知其正统所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这是饶先生治史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关注点),必如此,人心方能循序渐进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人心,不是只靠一些口号就能安全着陆的;而在充满后现代不确定性的时代里,安全乃最为不可或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注释:
[1] 详参郑炜明、胡孝忠编:《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三编》,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
[2] 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59年版,第2页。
[3] 同[2],第1页。
[4] 简氏的相关论著,参考简又文主编:《宋皇台纪念集》,香港赵族宗亲总会刊行,1960年;简又文:《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猛进书屋丛书(不著出版年月。应亦在1960年3月前后。案:猛进书屋乃简氏的书斋名号,故此册乃其自印本)。
[5] 参考郑炜明、陈玉莹:《饶锷先生的潮州方志学初探》,见郑炜明主编:《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十周年馆庆同人论文集——饶学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8—68页。
[6] 同[2],第24-50页。
[7] 饶宗颐:《选堂集林·史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67-1073页。
[8] 饶宗颐著,郑炜明整理:《由砖文谈东汉三国的“番禺”》,见《李郑屋古墓》,香港历史博物馆编,2005年,第8—15页。
[9] 同[8],第9页。
[10] 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314页。
[11] [17] 同[10],第1277页。
[12] 同[10],第1278—1279页。
[13] 同时请参考饶先生有关牙璋与南海这方面的两篇论文:《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开幕演讲》,见[10],第310-314页;《由牙璋略论汉土传入越南的遗物》,见[10],第315-321页。
[14] 饶宗颐:《香港考古话由来》,见[10],第1279页。
[15] 未刊。当时已交付出版社,因抗战时出版社大火而告终。近年郑炜明、胡孝忠据该书原已刊的目录,逐篇钩沉,重编成书,将于中华书局出版。
[16] 饶宗颐:《楚辞地理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