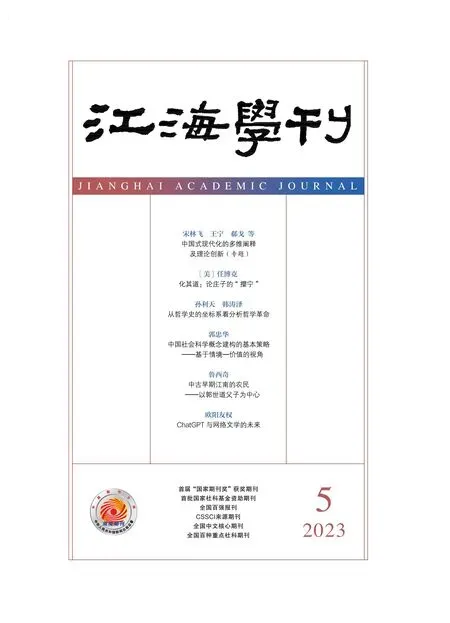中国古代生命美感话语的文字实践
——以“点”字为例
王 耘
新时代以来,“中国学派”风起云涌,以昂扬之姿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学派”不应只是“在中国”的学术团体,而理当创造出“属于中国”的学术特质。回到文明最渺小、最原始,也最基本、最真实的“质素”——“文字”上来,应是立足本土,扎根现实,建构和发展“中国学派”的主要途径之一。“文字”既是文明的表皮细胞,又是文明借以生根发芽的“土壤”和“本怀”。与西方的“表音文字”相比,中国的“象形文字”表意,尤擅表中华文明原始之意。文字渗透、贯穿于哲思、文学、艺术、社会活动、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文字不仅是一个有待取样的“对象”和标本,更是一种曾经构造中国古代文化之肌理,至今仍焕发着蓬勃生机的现场。因此,回到中国,还原历史,建立基础可靠的“中国学派”,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和标语,而应具体地落实下来,尤其是落实到中国古代文字这一场域中来。
就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表象而言,文字的价值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在“言意之辩”面前,任运逍遥的中国古代文人不信任、不依赖,甚至主动拒绝类似“语言即言说”的符号学表达,刻意缄默,收敛自身的叙述欲望,也就自然划定了其与文字之间的距离感,着力规避文字作为符号规训世界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书同文字”又曾是秦始皇昭告天下设立皇权的手段,统一“意识形态”,营造庙堂朝歌的渠道和方法。由文字铺垫而兴起的“文章”——是“文章”不是“文学”——并非单纯的如同“文学”的艺术文本,其所展现出的是一种立于天地上下之间仰观俯察洞彻古今的完善君主熠熠生辉的政治理想。这意味着,文字之于文人与帝王存在矛盾。
然而,我们更应当看到文字的深层内涵,文字本身是活的,它有生命,它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生活,并且热爱生活。文人欲把文字心灵化而不得,帝王欲把文字工具化而不获——现实帝王毕竟有别于理想君主,无法阻挡文字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化石”、见证者。在中国,是文字,而不是理性,成为塑造文明的“单元”组织;一部文字萌芽、发生、发展的历史——而并非个人才情、利欲、意志的左闪右躲、含糊其词——才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传统文明曲折变迁的全息“写照”。因此,“中国学派”的崛起,离不开文字这一“富矿”。
本文从中国文字与古代生命美学的关联这一角度出发,以“点”为例,探寻“文字”所包孕的“哲思”。在中国古人的生活世界里,美感话语实践的基本模式是一种文化“一体化”的活动。作家、作品、读者、社会乃至时代、流派、风潮相互映射,难分彼此。这是因为,所谓作家、作品、读者、社会,乃至时代、流派、风潮皆与生活世界“共生”,共同在生活世界中呈现。有鉴于此,本文以“点”为例指出,“文字”是中国古代生命美感话语实践中重要的“场域”,是这一“场域”凝聚了附着在文字身上的认知性、情绪价值、想象力和道德归属感——一如“点”表征了中国古人审美生活世界中的整体生命美感。对这样一种极具张力的美学现场的还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美学的重构以及当代中国新文明的建设提供积极而有益的思考。
“点”的语词含义:双向复调
“点”的词义既立体又丰富——“点”同时具有动词和名词双重词性;更重要的是,“点”的动词词义、名词词义的语义内部,“相生相克”又“相反相成”。
“点”是一个动词。作为动词,“点”兼具对同一行为或肯定或否定的所指。一方面,“点”可以是某一肯定性的动作,另一方面,“点”又可以是对同一行为的否定。例如“点火”,点燃是点,熄灭也是点。点燃是带有肯定性、建构性的动作;熄灭,义同于抹去、消磨,是带有否定性、解构性的行为。因此,“点”具有“正反”两面,双重“特效”——肯定性的例证不胜枚举,至于熄灭,《尔雅》里便把“灭”解释为“点”,“灭谓之点”。(1)《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所以,“点”不是单向性的,它具备“往返”于“成住坏空”的循势能力和可顺可逆的互文价值。
首先要注意“点”的错误和过失“用法”。“点”很有可能带来“污”效、“染”性——不可控、不确定、不经意的点,不被人接受、欢迎,无关乎艺术,而就是一种破坏、“染污”。《颜氏家训·治家》提到借还他人之书时,便提到“祸”自“污点”:“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2)颜之推撰:《颜氏家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44页。“童幼婢妾”在书籍上留下污点,和“风雨虫鼠”毁伤书籍一样,必须严令禁止。
与此相近,“点”的正面“形象”往往带有意外之喜。仍以《颜氏家训》为例,《杂艺》篇中的“点”便全然不再是污点,而焕发着艺术创作的蓬勃生趣。其曰:“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3)颜之推撰:《颜氏家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第987页。“随宜点染”四个字,给人们留下了“非”蓄意为之的深刻印象。“非”蓄意为之,不等于有意为之,亦不等于无意为之,而“为”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如何为之?“点”。艺术创作实践活动的共识是,“非”蓄意为之才是自然的;这种“非”蓄意为之之所以成立,缘于“点”具有有序与无序、有意为之与无意为之的对冲印象——举重若轻,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随宜点染”不是“随意点染”,更不是“肆意点染”,“意”是被遮蔽、隐藏起来的“内化”的状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而已。因此,“点”实则中和、含摄、收纳了有序与无序、有意为之与无意为之等各种可能性,它不是单纯的动作,而是复杂的行为。
除动词外,“点”又是一个名词。作为名词,“点”的语义更加充盈。一方面,何谓“点”?梁启超《墨经校释·经上》:“端者,几何学所谓点也。”(4)梁启超撰:《墨经校释》,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48页。端就是点,点就是端。点是切分至于不可切分的最终结果——“‘点者无分’,盖点者不可分者也,不可分则无间也”。(5)梁启超撰:《墨经校释》,第49页。“线”可以有“间”,“面”能够切分,“体”更是如此,但“点”无“间”,不可再分,是分的单位和结论。世界的整体被称作“兼”,世界的部分被称作“体”。在此基础上,“尺者端之兼,端者尺之体也”。(6)梁启超撰:《墨经校释》,第4页。尺是端点的集合,端点是尺的部分。这是一种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的解释,关于端点的分析更易走向原子论——原子无穷,但原子必然以物质实体单位的方式最终存在。
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点又不只是空间中无差别的众相之一,点还有“初”的含义。正如“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无厚、无间,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端是最前者。所以,“点无长短广狭厚薄,故云无厚。凡形皆起于点,故云最前。《说文》云:‘耑,物初生之题也。’耑,端之原字。与此文最前义同”。(7)梁启超撰:《墨经校释》,第48页。点是肇端,是初始,是最“前面”的那一个——“凡形皆起于点”。换句话说,点是起点,是积沙成丘的沙,是意识起心动念最初的触发者。这个“点”,不再是基于科学,分析至于无穷而最终得到的抽象数据和名词,而预示着生命成长特殊的历史经验,蕴含着个体生老病死、此在在世的时间性。“引端(点)为尺(线),则尺(线)函端(点)无数。”(8)梁启超撰:《墨经校释》,第53页。因此,“点”有生命,“点”是生命的原初形态,是生命之初那个孕育着未来的“导引”“逗号”,是饱藏着生命和生命感的“萌芽”“胚胎”“原型”。
值得强调的是,“点”本身可以成为“时间”的“标志”,它在句读中的作用便是如此。众所周知,古人句读为断句,易于理解;更为吟咏,易于诵读。“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咏,谓之读。今秘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中间。”(9)《康熙字典》,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13页。一句话说完了,称之为句;一句话没说完,语气稍有停顿,称之为读。重点在于,无论句读,皆以“点”来标志,或在字旁,或于字与字之间。因此,“点”是句读的“标志”,也是时间的“标志”——它是对文章气韵之韵律的点化和揭示,它引领读者深入文本内部的生命节奏,是为审美。
“点”的文化特质:全面范畴
“点”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一个全面的范畴,一个互涵、互摄、互融、互通的范畴。溯源可知,“点”是与中国远古巫术密切关联的巫术动作,《楚辞·七谏》之东方朔《怨世》篇中就有“点灼”的讲法。所谓“点灼”,一般指的是“污蔑毁伤”,但“点”与“灼”连用,却透显出卜筮乃至燔祭传统的历史印迹——“点灼”的原型,实为“点火”。唐朝诗人罗隐《长明灯》写道:“不知初点人何在,只见当年火至今。”(10)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六六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622页。强调长明灯之今火,缘于当初之曾“点”,长留于世,持存的时间性,其中带有初始意味的“点”,影射着巫术信仰的内涵。
“点”这一动作,首先是一种社会行为,彰显着政治权力的味道。《后汉书·酷吏列传》描写“斗筲小人”,言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11)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99页。在这里,“笔不点牍,辞不辩心”的反面表述,恰恰是文笔点牍,而辞辩以心。所谓“文笔”,点画于案牍,服务于文官,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一层面的极致表达,乃“御笔钦点”。《梁元帝启东宫荐石门侯启》曰:“切以凤鸣朝阳,必资蓝田之宝,龙门点额,亦俟棠溪之珍,是以紫玉见称,黄金为贵,文传梦鸟,学重灵蛇。”(12)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五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其中,“点额”是高频语汇。何处“钦点”?“额”。当然,在不同语境里,“点额”也有不同含义。《康熙字典》在解释“的”时就提到,“《史记·五宗世家程姬注》:‘的’,以丹注面,妇人有月事,妨于进御,难于自言,故点的以见”。(13)《康熙字典》,第714页。此处的“点额”,便不是钦点,而是自点。重点是,“点的以见”虽然也是某种权力隐喻,但更多涉及性的层面。
在围棋中,“点”为落子。梁武帝《围棋赋》曰:“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或取结角,或营边鄙,或先点而亡,或先撇而死,故君子以之游神,先达以之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秘。”点子即为落子。(14)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七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8册,第549页。
“点”在中医里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点药”是制作丹药的关键。《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中有“取腊日猪脂熔,以槐枝绵里头四五枚,点药烙之”的做法。(15)张仲景撰:《金匮要略》卷下,《四部备要》第65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3页。点烙,与“点灼”类似,都是通过局部“点”化的加热和灼烧炙烤来处理药材。此外,“点穴”也是寻常做法,类似于针灸。《魏书二十九·华佗传》注中《佗别传》曰:“有人病两脚躄不能行,舆诣佗,佗望见云:‘已饱针灸服药矣,不复须看脉。’便使解衣,点背数十处,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纵邪不相当。言灸此各十壮,灸创愈即行。后灸处夹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调,如引绳也。”(16)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2页。
点化金银,是冶炼金银的基本步骤。《康熙字典》对“银”的解释中包含着对“假银”的提醒,“丹阳银、铜银、铁银、白锡银,皆以药点化者,皆假银也”。(17)《康熙字典》,第1231—1232页。真假另当别论,由此起码可知,金银本可药用,而“点化”即丹药冶炼的实际过程。所以,所谓“点铁成金”的“神迹”,并不是一种夸张到不可思议的“变态”情境,而有其文化语境中的经验事实。
《全唐诗》收录了吕岩的两首诗作,《寄白龙洞刘道人》与《敲爻歌》。前者写道:“竞向山中寻草药,伏铅制汞点丹阳。点丹阳,事迥别,须向坎中求赤血。取来离位制阴精,配合调和有时节。”(18)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八五九,第9707页。后者写道:“声闻缘觉冰消散,外道修罗缩项惊。点枯骨,立成形,信道天梯似掌平。九祖先灵得超脱,谁羡繁华贵与荣。”(19)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八五九,第9715页。在几乎雷同的叙述逻辑中反复提及“点”——不仅揭橥了“点”是制作丹药的程序之一,并且表明“点”之前后,“枯骨”与“成形”构成了鲜明对比。如何化死者之腐朽为生命之传奇?“点”。为什么?枯骨者,鬼也,魂也,营魄也,而起死回生、死而复生这一经过,由“点”这一动作来完成。换句话说,“点”是“神化”得以践履的根本性转捩。
审美艺术创作正是基于如斯启发,将创作过程比喻为“点”。何谓创作?“点铁成金”。如何点铁成金是另一个问题,但既然有点铁成金,也就有通过“点”而实现从铁到金之转化的预设——一次质变,通过点而化成。凡言“点铁成金”,莫不提及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20)黄庭坚撰:《答洪驹父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与道教方术如出一辙。点铁成金之外,吕岩《七言》“晨昏点尽黄金粉,顷刻修成玉石脂”,(21)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八五六,第9679页。便不是点铁成金,而是点黄金粉,成玉石脂。贯休《拟君子有所思二首》“安得龙猛笔,点石为黄金”,(22)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八二七,第9321页。更是点石成金。刘得仁《赠王尊师》“符札灵砂字,弦弹古素琴。囊中曾有药,点土亦成金”,(23)彭定求编:《全唐诗》卷五四四,第6294页。则说的是点土成金。
“点”的审美意蕴:直抵人心
“点”是一种人的外在行为,这种外在行为如何内化,积淀起人心中原初尚未定型的,却郁郁葱葱真实存在的审美意蕴?关键在于建立“点”与审美“意念”之间的联动机制。
中国古代审美活动中的“意念”,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复杂的范畴。这种“意念”不是一种持续性的一贯的专注于某一既定对象的主体心理驱动力——客体本身不确定,主体本身不确定,孰主孰客亦不确定。所谓“意念”不是“我”的专属——构成自我、超我、本我的意识流或潜意识流,而是“天地”的共享——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我在天地中”是第一要义。所以,“我”的意念要把“我”放归自然,把“我”还原为“无我”,并享有“我”成为“无我”的过程和愿景。“意念”即“无我之我”在自然大化流行中拥抱世界、礼赞生命的审美体验,创造美更类似于感受美。这样一种审美话语模型,可以用一个动词来概括,乃“点染”。何谓“点染”?“点染”即以有限的笔触,减省的、经济的,甚至吝啬的笔墨,于“满纸生水”的“画面”中略施一毫半墨,便如同蜻蜓“点”水一般,置盐在水,无痕有味。“点染”非但不是“渲染”的前奏和准备,“渲染”反而是“点染”的“反义词”。“渲染”是浓墨重彩、繁缛绮靡、争奇斗艳的堆叠之辞——“渲染”追求的是“形”的丰腴,“点染”表现的则是“神”的雅好。显然,“点染”更符合文人趣味。只有“点染”,才是对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嗅、不可触知的生命意蕴的心灵把捉,而如此把捉,又是只有在审美之文人亲身“临现”,见之、闻之、嗅之、触知之之后,有所领悟的当下境界。
从普遍的语义学上来分析,“点”与“灵魂”之间是有“兑换券”的。“点”是一个行为,一个可知的动作;“灵魂”是一个假设,一个不可知的“神我”,二者本无关联。然而,在“意念”的感召下,“点”需要有“灵魂”,“灵魂”也需要通过某一特殊意象来表现——唯其如此,有了“灵魂”的“点”才能够表现“意念”。具体而言,“点”不只是人的形体动作,如点头,如顿首,作为更加“形而上学”的举止,它还具备活跃于“灵魂”层面的可能性,如《报任安书》“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24)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5页。其中,“自点”或可谓自取其辱,亦可谓自我反省;重点在于,“点”指向了自我,一个抽象的我,我的“灵魂”。
进一步而言,究竟怎样表现人的“意念”抑或“灵魂”?画“眼睛”,造“阿堵”。如何塑造人之“阿堵”?“点”——“点漆”!
这其中隐藏着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线索。所点者,漆也。为什么一定是“点漆”,不是点灯点烛点火?中国古代的建筑俗称“大木作”,中国古代的家具俗称“小木作”,木作无论大小,都与一事有关,那便是漆艺。中国的木作擅用斧凿,强调榫卯的咬合衔接能力,而缺乏对木料平整抛光的表面处理能力,所以,漆艺是配合木作出现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技术。这项技术的水平在东汉末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当时的漆艺惯用黑色底漆,上设赤色图案纹样,几案、棺椁、日常器皿,包括用来指明经络走向的人体模型,无不如斯,极为流行。换句话说,所谓“点漆”不是文学艺术家们信马由缰的突发奇想,它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经验。只不过,在文学作品中,所点之漆无双色。
“点漆”一词并不专供于画“眼睛”,该词亦有其他所指。《金楼子·说蕃》中有言:“遥光美风姿,眉目如画,发鬓若点漆,隆准,口如含丹而足蹇,体殊肥壮,脚如三岁小儿。”(25)萧绎撰:《金楼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35页。在这里,“点漆”被用来形容“发鬓”乌黑油亮,无关“眼睛”。从这一侧面可知,所谓“点漆”的“漆”,是黑色的。白居易有诗《送毛仙翁》:“绀发丝并致,龆容花共妍。方瞳点玄漆,高步凌非烟。”(26)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四五九,第5224页。白居易在这首诗里明确指明了“漆”的颜色——“玄漆”不是朱漆、红色之漆,是黑漆、玄黑之漆。在“点漆”一词中,“漆”指的便是黑漆。与“玄漆”相对应的,是“方瞳”,方瞳、玄漆,乃仙翁“标配”。
事实上,“点漆”的深意,主要用于表现黑亮有光——仅仅亮是不够的,还要放光,有“光点”。“光点”常用于描写隐士,潜藏着修行的含义。《神仙传·东郭延》即提到“延遂还家,合服灵飞散,能夜书,在寝室中,身生光点”。(27)葛洪撰:《神仙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
照此“点漆”逻辑发展下去,是不是只有“点睛”,通过既定的动作和程式,“点”出黑亮透光的“阿堵”,才能够呈现乃至放大人的灵魂和意念?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更为复杂。《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28)刘义庆撰:《世说新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此典亦可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四之《巧艺部·画》。据《排调》可知,荆州刺史殷仲堪曾一目失明,如果他没有失明,也就无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典故,所以,殷仲堪说“我形恶”,不是怨气,是事实,但顾恺之却偏偏要以殷仲堪为模特,为其点睛,绘制一个盲人形象,难度可想而知。无论如何,顾恺之不打算回避现实中的困境,反而用两个动作来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这两个动作,一个是“点”,一个是“拂”——无拂有“点”,有拂亦“点”。即便有“拂”,轻云蔽日,亦难掩眼眸流露出的华彩。顾恺之表现出充分自信,证明自己足以在“拂”“蔽”的不利条件下,彰显“点”高超绝伦的技艺。由此,“点”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动作,而是一种价值和意义的彰显。
除绘画、雕塑等视觉造型艺术外,王羲之对杜弘治的口头评价,“面如凝脂,眼如点漆”,亦在具体的文学经验上,以另一种方式——文字的方式,把“点”送上了文学舞台,送上了人物之文学形象塑造的崇高“圣殿”。“凝”是不动的,却又不至于“僵持”和板结;“点”是涌现的,却又不至于“漫漶”和流淌。至此,无论笔墨还是文笔,皆有“点睛之笔”。有漆一“点”,恰恰说明“点”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中,能够直抵人心。
“点”的思维模式:涟漪
“点”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实践活动中的重要范畴,最终酝酿出了一种类似“涟漪”般的,能够不断吐纳的,既向四周扩散又朝中心收拢的行为模式与审美图式。
在各种古代文明形态当中,生命感是中国古人特殊的精神遗产。不同于古希腊人之于真理不懈追求的理念、古希伯来人漂泊无依而终于还乡的欲念和古印度人渴望从生死中解脱的观念,中国古人更趋向于参赞天地,肯定此岸当下的现世伦理,而尤愿主动拥抱与时俱变、消息有常的真实生活。生命不等于生命感,生命感是能够体验和感知生命的主体体验、感知生命的过程和结果。中国古人的生命感中涌动着生命的道理,自在故乡,而规避、化解了死亡,与此同时,又构成了其特殊的体验、感知模式——“涟漪”。
围绕“涟漪”的是两种动作的契合,不强制连贯,而主客合一。一方面,吸纳、含摄、该取外在于己的世界,另一方面,吐露、分享、弥散内在于己的自我。自我与世界是交互、回环、圆融的,“涟漪”既可以是水滴,又可以是漩涡。上善若水,不仅因为水者善下,还因为水有涟漪。水可以凝结,可以蒸发——上下自如的气化景观,才是中国特有的自由意境。如斯自由意境是审美话语的实践,是天地中人葱茏而丰盈的生命记忆。
书法中的“点”是最典型的例证。点是书法基石。《蔡中郎集》中的《隶势》篇中言及“佐隶”,便有“纤波浓点”而“错落其间”的讲法。“波”或纤细或绵长,“点”或凝重或灵动,重要的是,“点”是波,乃至浪,乃至幅的肇端、起始、归宿和终结。字形本身是一种符号,符号的本质是“点”。
首先,“点”是动态的平衡。“点”不是静止的而是有收放的。它既有所内趋,又有所外拓。一方面,从内趋的角度来说,“点”有所针对。《战国策·秦策》之“顷襄王二十年”记录了秦白起拔楚,楚人黄歇前来游说昭王的说辞:“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点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29)刘向撰:《战国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5页。在这里,“点斗”即战争双方点对点有针对性地较量和缠斗,但这不是艺术。另一方面,从外拓的角度来说,“点”又存在“过度”使用的风险,尤其在书法创作中。《颜氏家训·杂艺》:“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30)《颜氏家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第986页。所谓“至为一字,唯见数点”,“蓄意”放大了“点”的审美效果,而适得其反了。所以,“点”是一种在内趋和外拓之间的动态平衡。
其次,“点”是有为与无为的对位与综合。“点”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但正因为它的艺术表现力强,往往指称不确。在某种意义上,“点”是含糊的、多义的。在“点”的身上,可辨识度与可创造性始终是同时存在的矛盾力量。点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自然表达的累赘?《文心雕龙·隐秀》即把“妆点”列为“天成”的反义词——“妆点”不仅反映出人为痕迹,且表明这是一种过度人为的负面做法。不过,从客观角度上来说,过度不过度并无客观标准,往往是基于主观判断得来的。《艺文类聚》卷四的“七月七日”收录过一首梁沈约《织女赠牵牛诗》,其曰“红妆与明镜,二物本相亲,用持施点画,不照离居人,往秋虽一照,一照还复尘”,(31)欧阳询撰:《艺文类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7册,第215页。并无过度之嫌。所以,“妆点”“施画”适当与否,由具体语境决定。
最终,“点”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实践的行动与图式,其最高形态是“自然”。“自然”的基本形态是“意”的隐显——经由“点”的介入,进入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吴书·赵达传》引吴录曰:“曹不兴善画,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32)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5—1426页。曹不兴的笔误,为什么不是童幼婢妾意外点污的污点,而反转为“蝇”,反转为形象逼真、催人举手弹之的“生蝇”?此典亦可见于《艺文类聚》卷六九之《服饰部上·屏风》。事实上,这段话可以结合《论衡·累害》来看,其曰:“论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贤洁也,以涂傅泥,以黑点缯,孰有知之?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33)王充撰:《论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结合“以涂搏泥,以黑点缯”与“青蝇所污,常在练素”两句可知,用青蝇来象征污点,其来有自,类似表述还可见于《后汉书·杨震列传》。所谓艺术全在似与不似之间,是不是一种对于艺术创作中错误的纵容和庇护?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因就以作蝇”的“因就”——曹不兴的画法乃顺势而为。势源于场域,源于艺术创作的现场经验,带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就势而言,创作的重点不是对错,而是创作者的感知力、应变力和处理特殊突发状况的能力。换句话说,“点”的生命感是一种“自然”的表达,这为曹不兴无剧本、无蓝图的即兴创作提供了充分前提。
《世说新语·言语》篇言:“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34)刘义庆撰:《世说新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第59页。在这里,重点不在于天月明净与微云点缀孰优孰劣,而在于“微云”是“点缀”的主体——“微云”与“纤翳”相对,是在朗阔的月夜图画中凸显出的远近浓淡的运笔。何谓“点缀”?“点缀”不只是一个点,还可以是一条线、一片云。此典亦可见于《艺文类聚》卷二五之《人部九·嘲戏》。绘画中的“苔点”在现实世界里寻常可见,《水经注·济水》在描写济水东北“华不注山”的时候,就说它“青崖翠发,望同点黛。”(35)郦道元撰:《水经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点黛”,几乎是描写山之“崖”青葱苍翠的专属词,《浍水》中也曾用到。所以,“苔点”既出于匠心,也是一种对自然造化的“摹拟”。白居易《三谣:素屏谣》:“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璪之松石?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36)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四六一,第5247—5248页。点无论多么具有不确定性,也终究是可知的、可见的可为之举——超越于点画而进入“无”的世界,是中国古代文人更乐于标榜的精神世界,因为那样一个世界,不可知、不可见、不可为,是为空虚。
无论如何,中国古人的审美世界是通贯的整体,点化的对象不仅包含艺术,也包含金属,更包含人生和生命的修行。中国古人的生命感如同“涟漪”,是要有所得的,服从于实用主义的现世原则而不是空洞的教条,与此同时,也是要有所吐露和有所绽放的,如树要开花,花要结果。
结 语
建构当代中国的新文明形态离不开现代文明的洗礼,但更应当在中国古人的生命感中寻找带有民族印迹的审美“原型”。现代文明的内在逻辑是以离析、分析、辨析为基础的,所谓综合,实为离析、分析、辨析之后的结果——对立统一的关系不是对立与统一并存,而是从对立走向统一。在大多数语境中,综合、统一只是一种理论虚设,无法实现。依据这一逻辑,书法就是书法,绘画就是绘画,文学就是文学。然而,中国古人的生命美感话语系统却并非如此,书法、绘画、文学等皆是某一生命特殊形式的创作体验、表达系统,以一“点”,即可说尽一切。
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实践中出现过许多与主体论相关的范畴,“点”是最特殊的一个,而种种特殊的属性使“点”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实践活动的代表。“点”的多义性、复杂性、矛盾性不仅消弭了它的词性“障碍”,而且该摄和圆融了有为与无为的双重世界。“点”并不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元范畴,中国古代美学的元范畴是“道”,但“点”却是“道”直接而充分的体现。“道”具有原发性、双重词性,语义复杂、全面、无所不在,恰与“点”相通。所以,研究“点”,便于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集群做整体的关联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