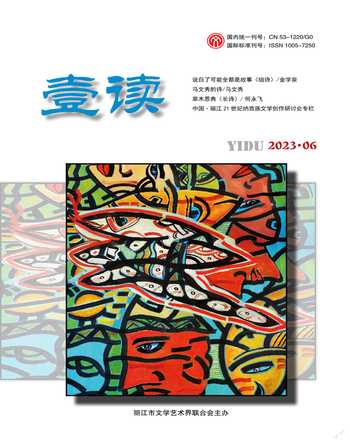根性蓝焰,纳人文学之火的可能性
在喧嚣现实的钢铁之上,对根的凝视是一种内视力,纳人文学的诸多血液、片片光域,由此继续涌动,并连接崭新与古老。
纳人生命观意识与文学之灵
20世纪纳西族文学创作谈论会于1994年召开时,在丽江古城尚能低饮传统生活的最后一抹余韵。27年来,全球化的飓风已将多数人推向物质至上的围栏,处处改天换地,日新月异,纳人区域和其他地方一样发生着剧烈变迁,这一变迁背后,是一张以经济为主轴的世界图纸。一直以来,我每年都会像候鸟飞回丽江短暂地栖于旧巢,从而亲历两个世纪之交故乡所发生的变迁,但回去得越多,就越是因纳人根块的减损沉入一种忧伤的挫败。顾彼得于1941年前往丽江前,获知“那个地方太遥远了。可以说那个地方在中国之外,是‘边远蒙昧之地,去那儿是沉没在甚至不通汉语的蛮族之中”,而今天,丽江早就是滚滚旅游红尘的冠冕之城,蓦然回首,满目非故乡之人,满耳皆异乡之语。
提及这些,实际上我是想说,在时代之场的文学棋局上,对于被日益汉化的纳人文学来说,作品深境中的文体、观念、声音、意象、精光、气韵,是否可能重新从泥土中崛起?如同濒临熄灭的火塘再次燃起腾腾蓝焰。记得多年前,纳人作家拉木·嘎土萨曾提醒我说,“要用纳人的本性去覆盖已经接受的那部分汉文化”,这句话值得深思。
站在纳人文学的主位上,许多纳人作家的文学作品,已深陷一种悖论的矩阵,作品一方面以纳人文化为主题,同时又以汉文化破碎混乱的现代性为统领文本的思想主线,能否以自身的心轮、飞翼或利刃冲出这一悖论,是纳人作家今天面临的一道难题。我认为,解决这一难题需得在根本处下力,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回返到纳人生命观意识,使之成为映照文本的精神镜像。
风雷激荡的崭新中,隐匿着恒常不变的常识,与创世之初一样,大自然神秘地驮着天地人——人、社会、自然的同源性,这一纳人传统文化的观念母题,穿过时间的渊面直抵眉额。纳西是祭天法祖之族,大地强有力的意识,让纳西人醒悟到自己的本来家世——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有生灵都保持着神秘关联,这种关联既是物理的,也是灵能上的,人的一切拜大自然所赐,因而生活的奥义之门秘藏在对大自然无尽的感恩中,一年四季须得举行无数感恩仪式、忏悔仪式、除秽仪式、驱邪仪式,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还债式的谢恩。
多元夹层是纳人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质,在新与旧的撞击中,不断开新花结新果,但一直坚韧地持有自己的根系和脉动,这是这种自成一体的山野文化的重要魔法,里面挟带着大自然丰沛的天启和馈赠。
文章是一股气,化词为语,化词为锋。若我们剔除腐质直奔中心,可说文学是纸上的声音样态,文学的民族性不是词藻的堆砌,而是积存在声音的魔力中,文学之灵隐伏于其间。诸多妙音在时光中流转,吸附着雪山之音、大江之音、祖先之音、心脉之音,想来纳人文学的肺腑之音,亦是如此。
重返超时间的纳人母题
“纳人文学”,不仅仅指书写者有纳人血统这一标签,分析其界限与内在性,主要包括三种样态:纳人民间文学、纳人作家文学、其他纳人文学作家作品。就其本质,纳人文学的主轴指以纳人范畴内的主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白庚胜主持的丛书《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2016年光明出本社出版),从纳人作家文学的角度,汇集了1949年以来纳人作家群体的主要作品。和钟华、杨世光主编的《纳西族文学史》(199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从整体性的角度,对纳人文学史的脉络进行了多视角的评述。
从文化地缘的角度,纳人文化是形成“丽江之魅”的根本,是丽江面对世界时的“唯一性”优势人文资源,而在浩瀚的文学版图中,那些具有异质魅力的纳人文学作品,更能异峰突起。文化是一个活体,祖先的根气必然以新的方式在现实中升腾,在全球化旅游化浪潮移山倒海的年代,纳人人文元气逐渐支离破碎,当此之际,纳人文学该如何重返超时间的纳人母题?
参加1994年20世纪纳西族文学创作谈论会前后,我撰写了《对20世纪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几点思考》一文,提出纳人作家文学应该朝着“神奇的现实”靠拢:
“关于‘神奇的现实,很难给它下一个具有完整内涵的定义,但它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自然力量,民族现实的文化,以及历史。纳西族地区的神奇自然力量,神奇的混合的文化现象,及神奇的纳西文化本身,构成了我所谓的纳西族地区的‘神奇的现实……纳西族作家们需要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深处,不断向‘神奇的现实靠拢,找到各自恰当的创作方式(包括语言、语感、结构、描写手法,具有某种高度的感觉或智慧),写出优秀的纳西文学作品。”
边缘大野,涌动着不灭的浪漫主义,溃退的山水仍激荡着山之脊水之华。李霖燦曾说:“麽些(注:纳西)象形文字的经典给人的印象只有一个字——美!一种满纸鸟兽虫鱼洪荒太古之美。”许多流传至今的古东巴经,有着超时间的文学性,并贯穿着纳人山野生活的民间调性。在将这些民间经典译为汉文时,深谙乐府诗的李霖灿在字里行间留心保留了纳人歌谣、颂腔的口语特点,读之如聆“纳人乐府”。近几十年来,纳人学者翻译了众多古东巴经典的汉文译本,代表性作品如《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一百卷),纳人作家也翻译整理、创作了不少以东巴文学为题的作品,代表性作品如戈阿干的《祭天古歌》《格拉茨姆》《查班图》。倍感从文学当代性、文体水准、文体诗境的角度,在东巴经典的汉文译本及以此为题的创作领域,尚大有文章可作,新阳转故阴,金声连玉振,期待能出现闪耀着卓异灵光的崭新佳作。
自古以来,作为在生活同大自然相交的每一点上追寻深情的审美民族,纳人既朴素又庞杂的文化体系蕴含着爱与美之结晶,其生活美学的灵芬,来自天空土地的阳面和阴面,对这一自然母题的书写,是纳人文学的一个优质集成,成果斐然,希望以后能够出现《塞尔彭自然史》(吉尔伯特·怀特著)那样的纳人自然文学写本。
抢救记忆,记录即使命
探讨纳人文学的民族性,不得不直面时间性,当民族记忆被遗忘,或被夺走,文学的民族性将成为一堆空壳,种种丰饶的真实存在将消散如烟霜。历史的洗牌方式与现实的洗牌方式并不相同,随着时光的突进,历史在加速断裂、加速消失,全球化和狂飙式的发展,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优越的物质生活,但若控制不好均势,世代积沉下来的人文生态一旦被毁坏,被拆除,“今天”将全方位成为时间深处的废墟之场。对于当代纳人文学来说,在剧烈变迁的现实中,以文字悉心雕刻时光抢救民族记忆,无疑是一项使命。
值得庆幸的是,有为数可观的纳人非虚构文学作品面世,许多沦丧的往昔已被记述下来,在这一领域,赵银棠、杨世光、戈阿干、和国才、拉木·嘎土萨、杨福泉、李承翰、夫巴等等纳人作家建树颇丰。站在时光的纵线上,无疑,1940年至1980年这40年的民族记忆仓廪,是需要记录的重点,一个1940年出生的纳人如今已81岁,如果不乘着很多长辈尚健在的光景,从各个视角作生活史、口述史、回忆录、亲历记、田野追踪、微观主题的深度记录,则记忆的沟壑将会大到无法弥补。客观来说,对1950年到1980年的深度记录,显然较为单薄,不少领域至今还是一片空白。从方法论的角度,关注人是记述性文本的首要目标,时间的现场印记和质地、叙事的第一手精确细节由此衍生。
以文学样态储存民族记忆的路径,是茕茕苦行之举,这一寂者的淬炼,如同坚守祖先绵绵不绝的火塘,哭之笑之,而衷肠不改。记得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引用过的一句话:“火对我们的记忆具有强大威力,以致沉睡在最古老的回忆之外的种种生活由于火焰的照耀在我们身上复苏,并向我们揭示隐秘心灵最深处的家园。”
斜阳下的绿雪新天地
美国诗歌巨匠埃兹拉·庞德,系20世纪欧美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代表作是创作时间长达五十多年的《诗章》。他在这部陡然穿越东西方文化的意象派诗歌巨著中,贯穿了中国主题,越到后期这一主题就越突出,值得注意的是,从《诗章》第98章开始,中国大西南边陲纳人的自然与人文元素不断出现在各章之中,成为继儒家文化以外第二个鲜明的中国元素,近年来,钱明德、赵毅衡、王卓等学者就这一主题发表了研究文章。
“丽江”有三次直接出现在《诗章》,分别是第101章、第112章和第113章。在庞德的神秘主义自然观中,纳人的文化和自然形成天人与共的一个整体,交织着真实、记忆、传说、风景、生死观,纳人仪式被“浓缩进风景之中”,而“风景又在仪式中复活”。 在第112章中他写道:
如果我们不祭天,
没有什么是实在的。
如果不祭天,
就没有现实。
纳人的殉情观念和祭风仪式显然深深触动了庞德,他试图冥想那生与死共同居留的“无限”,在第101章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情死少女的诗行:
太阳和月亮嵌在她的后背上,
星星圆盘缝在她的衣服上,
在丽江,雪山绵延,
草场广袤,
驱魔人的脸
亲切祥和……
在后期《诗章》中,庞德的漩涡主义写作风格臻于精纯,其中诸多对纳人文化的描述和咏叹,令人想起他说过的“黎明带来乐园的希望,给那些善于继承文明传统的人。”庞德从未到过丽江,据钱明德的研究,他的纳人文化资料主要出自顾彼得的著作《被遗忘的王国》、洛克的著作《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孟本》,这几本书是当年留学美国的丽江纳人方宝贤借给庞德的,并经方宝贤衔接,庞德认识了顾彼得。据女儿拉齐维尔兹(Mary de Rachewiltz) 2012 年 10月 11日发给钱明德的电子邮件,1960、1961 和 1962年,顾彼得(Peter Goullart)三次到庞德位于意大利北部布伦堡的家园一起度假,俩人一起常常畅谈丽江及纳人文化。在一声无法挽留的遥叹中,庞德于未曾发表的《詩章》断章中写道:“洛克的土地和顾彼得的/天堂;/被风儿吹成/词语的形状。”
过去、今天、未来,俱归于存在,埃兹拉·庞德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梦魇,一生命运多舛,他辽阔而微妙的笔触戳开“存在”,试图把暴烈时代收入到一束强有力的光柱,在他遍浮意象的视域中,纳人是离大自然最近的种族。庞德诗篇中有关纳人文化的意象和隐喻,呈示了他对生命神秘归途的探寻,在许多方面愈加悖离自然的今天,世界更加趋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的危机是自然危机的另一面,站在良性的后现代立场上,纳人传承久远的文化体系中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丰厚元素、那些循环流动着异质之美的亲自然活态根脉,值得纳人文学深深思索,并以有着显著纳人特质的各种文体写出佳作。
(白郎,1968年生,云南丽江人,纳西族,随笔作家,《读城》杂志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李惠文 和丽琼
——纳西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