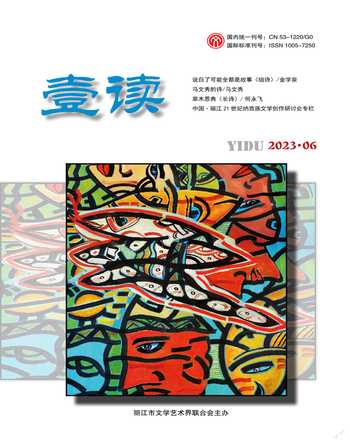厨房(外一篇)
李方
有只猫,全身通体纯黑,只在尾巴尖上,长着一撮白色的毛,像是调皮捣蛋的小姑娘,把蝴蝶结扎在了发辫梢。我原以为它是不小心将尾巴尖蘸到了白粉桶,但仔细观察,确实是那儿的毛色出了问题,是自然变异的结果。它时常翻过村部的围墙,在厨房的门前徘徊。偶尔,它会轻轻地抬起前爪,重重地落下去,抓挠厨房的铝合金门扇。
这是令人担忧的。起码我是忧虑的。
厨房里有我和队员每周一从城里带来的伙食,包括蛋、肉、油、米、面和蔬菜。除了面粉和大米怕受潮搁在凳子上,其他都在冰箱里。
一只猫,哪怕它是尾巴尖上长着一撮白毛的黑猫,既无力打开铝合金的门窗,也没有智慧开启紧闭的冰箱。我内心所担忧的是,这间厨房,是公共场所。凡属于大众的,从来就没有专人操心某件事情,比如:厨房的门窗未必一定会关闭,三开门的冰箱也并非铁板一块。
这间厨房,夹在村委会的办公房屋和村医务室中间。砖混墙体,彩钢瓦覆顶,明显比其他房屋矮半截。原本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并不清楚。驻村工作队调整之后,我们到来之时,这间房就是名义上的厨房,只是没有任何灶具。“原本有呢,调整之后,原来的工作队走时全都拿走了,本身就是人家购买的。”村支书是这样解释的。
帮扶村处在大山深沟里,距离市区至少一百公里。我们是做好了长期住在村里开展工作的打算的。不在村上开灶,显然是不行的。
“如果你们要开灶,就要自己购买灶具。村上没有这笔支出。”
驻村工作队一般由三人组成。但是我们单位人手紧缺,只能派出我担任第一书记,配备一名队员。脱贫攻坚时期是这样,现在实施乡村振兴,依然如此。只是帮扶村作了调整,工作性质有了变化。我驻村四年,对村党支部、村委会这两个中国最基层的党、政组织机构,还是比较了解的。大概问了一下,倒出乎我的意料:村两委五个班子成员中,竟然有四位家住县城,只有兼任村会计的党支部丁委员家在本村。原因是,帮扶村在实施生态移民时,四名村干部都在移民范围内,被集体安置到县城的易地搬迁小区里。每天从县城开车来村上,晚上下班再开车回县城。显然,中午饭,也是要在村上吃的。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厨房所需灶具,我们开了一个清单,单位照单全买,外带一台冰箱。地处偏远,买菜不易,一次采购,便于储存。关键是谁来做饭,由谁掌勺,谁是主厨,谁是那个难求的“一将”?专门雇佣一个厨师吗?根据我对当地劳务市场的了解和掌握,雇一个厨师,每月的报酬最低也得3000元。这笔费用谁出?派出单位不可能出。因为驻村的人每天都有生活补助,单位不能、也不可以违规支付这个钱;驻村的人支付吗?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事实是,食材已经由驻村的人负担了,再承担雇佣厨师的报酬,而吃饭的却是包括村两委班子成员在内的所有人,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驻村工作队的人负责购买食材,厨师的工资由五名村干部承担行吗?这个纯粹不用商量,村干部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他们工资本身就低,早上起来吃早餐,在家里就可以吃饱喝足,午饭不吃完全可以坚持到下午回城。让他们平摊厨师的报酬,就为中午吃一顿饭,说出来就是个笑话。
最终,想到了一个勉强可以行得通的办法。全村共有七个村民小组,每个组有一名村民小组长,俗称队长。队长每月的工资是1750元,负责村民小组的日常事务。事情并不很多,只是比较琐碎,需要经常性入户了解、登记发生变化的情况。但凡常年住在村子里的队长,对本组十几户村民每家的锅大碗小,基本上都是了如指掌的。七个队长当中,有一位刘队长,原来独自在新疆开过饭馆,专做“新疆沙窝大盘鸡”,实施生态移民时,全家搬迁到了县城。他就把新疆的餐館易手,从新疆回来,在县城开起了餐馆。新疆天宽地阔,独门生意,还可勉强维持。回到县城,餐馆密集,竞争自然激烈,时间不长,就关门歇业,在县城打零工了。老家原来所在的组,还有十来户常住户,选举的时候,就把他推选为组长。他偶尔从县城来到村上,处理一些组里的事情。
村干部就决定由他来担当厨师,他就是那个难得一求的“将”。他在组上的工作,则由大家帮着干,其他人进村入户摸排的时候,谁家有了新的动态,就顺手记录上,用不着他亲自跑一趟,也就是变相地雇他当这个厨师,工资就是队长的工资,少是少了点,但也只是中午做一顿家常饭。傍晚其他村干部回县城,只剩下我们两名驻村的人,做不做,吃不吃,由我们。
他都没怎么考虑,就说:“行。”
万事大吉,厨房点火启用,土鸡两只,就做大盘鸡,以示庆贺,也显示刘大厨的手艺。
刘大厨将切菜板搁在案板上,手执菜刀,砰啪有声,肢解鸡体。村妇联主席蹲在门口,削着土豆块。我瞅着那一堆剁得鸡零狗碎的肉块,向刘大厨讨教:“这些鸡肉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刘大厨一边弹着烟灰,一边往锅里倒水,一边说:“这不倒水嘛,用开水淖一下就行了,洗了就没个鸡肉味儿了。”
我心里嘀咕:那还淖个什么劲儿,直接下锅炒,原汁原味岂不更好。但人家在新疆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大盘鸡吃过,众口难调,说好说歹,评论一番,一哄而散,刘大厨也潇洒地骑着电动车回了县城,说是锅碗瓢盆放着等他明天早上来了再做处理。我望着杯盘狼藉,看着厨房犄角旮旯里的尘土和蛛网,地上的鸡骨头蒜皮,感觉吃到胃里去的那些鸡肉和土豆块,都生长出鸡毛和茎芽,戳得难受。刘队长虽然成了厨师,但万事也不能全靠他。女人心细,我请了妇联主席,烧了几壶开水,对这间重新启用、灰尘遍地、挂满蛛网的厨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彻底打扫,虽然没有做到窗明几净,起码看起来整洁有序多了。
我发现,刘大厨是个烟鬼。即便是锅里正炒着菜,或者正在下面条,他嘴角的香烟总是叼着的。想来,他在新疆做大盘鸡,或者在县城开餐馆,他的食客当中,估计有很多人都吃过他的免费香烟灰吧。我让他做饭的时候戴上口罩,别再吸烟。他嘻嘻一笑,说:“习惯了。”随手将烟蒂扔在地上,用脚底板狠狠地碾压一圈,继续手里的活计。
我还发现,相较于抽烟的爱好,刘大厨更钟情于下象棋。环境卫生整治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保洁员是主体,护林员、公益性岗位人员全部参与。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的人,没有紧急的工作和会议,全部上阵。从早上开始,整顿到中午回村部吃饭。只要我们回来,刘大厨总要逮住一个会下象棋的人,不管时间迟早,先要下盘棋才肯进厨房下面或者炒菜。有时候是羊羔肉煮在了锅里,他也要抽空和人下一盘。每次,都大喊大叫,把棋子拍得啪啪直响。我在旁边观战,说:“你用手指轻轻推到那个位置上,效果也是一样的,干嘛非得摔绊棋子呢?”他弹着烟灰,摔着棋子,说:“下棋就是为了过瘾嘛。不拍响,不吓住对方,哪还下什么棋啊。”
啪——“将军着呢,看清楚,将军着呢,缴枪不杀。”
心里惦记着下棋,难免要影响到他做饭的质量。村子里的产业,主要是养殖业,羊是很多的。大家打平伙,动不动就宰只羊羔子吃,也算是帮助养殖户增收吧。但是刘大厨心思在棋盘上,羊羔子要么火候不到没煮烂就出了锅,要么就是盐淡调料重,很难吃到正宗的羊羔肉的香味。
夏日天长。六点,村干部们陆续走了,村部安静了下来,但是太阳才落到树梢里。这个时候,是一天中最安闲的时刻。有时候,我也想自己在厨房里,细心静心精心地为我们两个人做顿饭。但是一推开厨房的门,看到刘大厨中午饭之后又没洗锅收拾,地上到处都是菜叶、蒜皮,饭桌上也到处都是汤汁、饭片,锅里歪倒着饭碗和筷子,一副兵荒马乱的景象。我清楚要做一顿饭,首先必须收拾这个烂摊子。等到我洗涤出眉目,那个想细心静心精心的“心”,肯定会被荒草所掩埋。也慢慢悟出来刘大厨在县城开餐馆,很快关门歇业的某些原因了。
扭头转身拉上门,作罢。
如果自己不在厨房动手,晚饭的吃法,只剩两途。要么泡面,这个最简单,也最省事;要么开车到十多公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找家餐馆,随便打发。队员虽然比我年轻很多,但既不会做饭,也不愿动身,通常是泡面就着浓咖啡当晚饭,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吃法。我自己,也想了一些办法,就是每周来村上的时候,多带八宝粥,或者芝麻糊。烧壶开水,把八宝粥整罐坐到开水中,温热,喝粥;或者就冲芝麻糊,凑合。
早饭吃得像皇帝,午饭吃得像财主,晚饭吃得像乞丐,这是饮食保健的经典说辞。都说驻村工作艰苦,也无非就是农村工作难搞,跟农民难打交道,办公条件不比机关罢了。其实驻村工作最艰难的地方,恰恰是一日三餐不好解决。现在每天中午起码有一顿热乎饭,至于早餐和晚餐,全在于自己的意愿和谋划,简便也好,不吃也罢,只关乎你自己,别人,是无法替代,也不会操心费神的。
等到了冬季,那只黑猫出现了。
就像柜子里藏着细软的老财主担心蟊贼和劫匪一样,我开始担心那只猫。每天晚上,我都要去检查一下厨房的铝合金门窗。果然,有好几次,门是开着的,并没有关上。我里里外外,大喊加跺脚,确认黑猫没有进到屋内,才关门闭窗走人。
有天早晨,刘大厨人还未到。村主任进了厨房,四处翻捡,想找点吃的。无意中,他在敞开的饭锅里,看到一只老鼠从锅底爬到锅半壁,又滑下去,滑下去,又快速地倒换着四条细细的腿和爪子往上爬。村主任打开手机录了十几秒的视频,发到了村干部群里,引起大家的哄笑,他才动手处理老鼠。
只有一个人没笑。
我们的队员。
从这天起,队员开始不吃厨房饭锅里做的饭了。
大家都劝他。又不是死老鼠,是活的,可能是从房顶上掉下去的。而且,活的老鼠,只是在空锅里做徒劳的想要逃离饭锅的努力,又不是被做在了饭里。锅么,用开水烫过了,用清水加洗洁精反复洗过了,怎么能因为锅里跑过了老鼠就不再吃饭了呢?广东人不是专门吃老鼠的吗?可见也是一道美食啊。
“我又不是广东人,我是宁夏固原人。”怎么劝,队员就是不吃饭。他不吃饭,难为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大厨。他为什么洗了锅不盖锅盖呢?锅里跑进去老鼠,导致队员感觉不干净,不吃饭,责任在他。另一个人就是我。我是第一书记,队员不吃饭,我也有责任。队员又不会开车,来来往往,都乘我的車。为了保证让他每天至少能够吃上一顿饭,我也只好放弃厨房里的饭,开车拉着他,到乡上找餐馆吃,甚至开车到县城里去吃。
这让大家的心里都有了一个小小的疙瘩。我心里更增加了一层疑虑:或许,我是冤枉了那只猫吧?如果不是我关防太严,那只跑进饭锅里的老鼠,恐怕早就被这只黑猫逮住当作了点心也说不准。
疫情防控最紧要的时候,刘大厨被封控在小区出不来,村干部和我们被封控在村部出不去。乡政府派人到村,送来了几十箱方便面和矿泉水。但是每天泡面也不行啊。厨房里洋芋有的是,是村集体的土地里种的,秋天挖出来装在袋子里,都堆放在厨房里,米面油也有。每天至少总要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洋芋面吧。
我私下里跟另一个队长李文成商议,让他妻子每天中午来村部,做一顿午饭。报酬是一个月1000元。钱由我个人出,从微信上转给他。这个钱,当然是少了点。但是疫情封控,谁也出不了村,也打不了工,况且天寒地冻,也没什么活计可以做。李队长同意,他妻子也乐意。之所以选择李队长的妻子,是因为我在他们家吃过饭,知道他妻子做饭是把好手,而且人干净麻利。
李队长的妻子姓喜。喜萍萍。她来的第一天,专门抱来了他们家的电饭锅。村部厨房里跑过老鼠的那只电饭锅,她放到了案板底下。然后,她烧了开水,开始认真仔细地清洗厨房里的所有用具,连冰箱里的抽屉,都端出来擦洗了一番。每件东西,开始固定地方。比如,大碗,在碗柜的下层,小碗和碟子,在上层。筷子、笊篱、锅铲,在不同的塑料小筐里。盐碟、醋壶、油泼辣子瓶,每顿饭之后,都会收拾进冰箱。她把案板洗得发红发亮,吃过饭后,从一卷地膜中截出一块,覆盖到案板上。
队员开始愉快地吃饭。
就这一顿午饭,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洋芋面。也吃大盘鸡。每次我都是帮厨的。她用女人镊眉毛的那种小镊子,细心地拔掉还匿藏在鸡肉中的粗根,再用加了食盐的水,浸泡、洗涤鸡块,然后才下锅。干拌面、臊子面、米饭炒菜,也就厨房冰箱里储存的那几样菜,她总能变着花样做出来。
大家全都吃得很舒服。
相处半个月,彼此熟悉。有时候她来做饭,我如果闲着,就去帮厨。有天做清炖鸡,我帮着清洗鸡块。她不无遗憾地轻轻叹口气,说:“唉,老人常说,千里路上做官,为的就是吃穿。看着你是个公家人,每月领着工资,可是都快退休的人了,还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天寒地冻的,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好衣服也不敢穿,到处是土,真是可怜啊。”我无言以对,自找台阶:“哪里都是工作嘛,权当是退休前的热身吧。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退休了也还是要回到农村去的。”她一边切着葱姜蒜,一边说:“那不一样啊,在我们山里,像你这么大年龄,都成老太爷了。你们一天,责任大的,心里也不宽展啊。”我无语,内心里,觉得她在某些问题上,比我看得更深更远。
腊月十三,是我的生日。那天喜师傅做的是牛肉臊子长面。吃饭时队员说是我的生日,她坚持要给我打一个荷包蛋。我嫌麻烦,硬拦着没让她做。我说:“这就是长寿面啊。”吃过饭,她洗洗涮涮,拉开冰箱一看,说:“还有些牛肉,也有萝卜,今天下午我不回去了,晚上给书记包顿牛肉饺子吃吧,庆贺你的生日。”
这真让我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在帮扶村里过生日。以前过生日,无论如何,我都会回到市里,要么和家人一起过,要么和亲朋好友在餐厅里大吃大喝。在这深山大沟的朴素村落里,在疫情封控的村部里,在这间很小的厨房里,喜厨师和妇联主席,精心地包了满桌的饺子。
我从疫情防控点回到村部,进入厨房,手里拎着一瓶酒。我说:“今天必须喝酒。庆祝我的生日,也要感谢在场的各位。”但是两位女性坚决不喝酒,但可以以茶代酒。队员原本是不喝酒的,他对酒精过敏,却坚决要喝酒。“我只喝半杯,舍命陪君子,祝书记生日快乐!”这个杯,不是什么高脚杯,也不是什么玻璃酒杯,是一次性饮水杯。他半杯,我满一杯,都一饮而尽。
李文成队长等着接妻子回家,看到队员喝了半杯,就说:“书记,给我也倒半杯,你倒满杯,祝生日快乐!”再次一饮而尽。
村主任的爷爷刚过世,本来说的是不喝酒,看到李队长和我喝完,激情被点燃,也拿了一个杯子,说:“我和文成一样,也是半杯,书记满杯,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三满杯53度的白酒,我直接醉倒。
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是喜厨师在做饭。我负担了一个月的报酬后,是队员接着支付的。队员之后,是村干部们……
刘大厨偶尔来村部,遇到饭点,也在厨房吃饭,继续抽烟,然后,逮住一个人,把棋子拍得啪啪响,大喊大叫:“将军着呢,看清楚,将军着呢……”
厨房夹在其他房屋和医务室的中间,干净而安详。那只黑猫,腰身一拱,尾巴尖上的白毛一闪,从村部的围墙上翻过去,不见了。
半夏
到了七月半,马沟就完全地覆在绿色下了。既像铺了一张绿毡,又像盖了一床绿被。连那曲里拐弯的硬白村道,都被嚴严实实地遮蔽在绿荫下了。
绿色来自树木、庄稼和野草。
马沟有很多树,但品种少。最多的是柳树。村道边、山梁上、屋宇前、山沟底。很多树活得都没有了年龄,却一直枝繁叶茂地长着。老树就是大树,树大了就招风。夏风一起,柳树就跳舞,枝枝叶叶,披头散发,左摇右摆,柳树的叶子,又密又细,搅和在一起,成一团墨绿,甚至是黑,在风中,黑球团那样在半空滚动。东山坡顶上有几株古树,不聚在一块儿,高一棵,低一棵,孤零零地挺在山的拐弯处,山的断崖边,黑塔般矗立着。这很让人费解,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跑到那样一个地方去栽植了一棵树。在山里,一棵树,就是一块界碑,也是一个路标。“看到那棵树了吗?过了那棵树,就到了赵垴的地界了。”或者:“你就顺着这条路走,走到那棵大柳树跟前,就到了野狐子崾岘。”望山跑死马,就这样用手遥遥地一指,你就朝着那棵树走吧。有时候你正大步流星地走着,突然出现了一道沟,路断了,张眼一看,满沟的柳树,像汪着满沟的绿水,会吓你一跳。其次是榆,马沟人把榆树叫“茹树”。我想那仅仅是因为发音的关系吧,“茹树”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榆树更多地集中在房前屋后,是一种和人比较“亲”的树。春来它先绿,绿的却不是它的叶,嫩绿,淡黄,枯白,飘落,那是它的花和果,也是它的“籽”,榆钱。七月半,榆树让风带着它的“籽”,散播到了各处,叶子才正盛,墨绿。马沟还残存着未被“天牛”遭害死的一些白杨,扎堆,挺拔,风姿绰约的样子。叶子宽大,随风翻飞,叶面是绿,叶背却是银子一样的白。风来,散一树碎白银在树梢,哗哗作响。还有为数不多的杏树,品种已经老掉了牙,导致结的果实都无人去食,大风一过,落杏满地,金灿灿一片,也只有老人看着可惜,不想白白糟蹋东西,蹲下来拣拾,然后嘀嘀咕咕,想着陈年旧事,孩童的时候为了吃上一颗酸涩的杏,得费多少心机,嘟囔现在的孩子口味刁钻。一边慢慢地去掉果肉,挤出杏核,砸破硬壳,得到褐色外衣包裹的杏仁,再褪皮,露出心形如玉的洁白果仁,拌凉菜,偶尔泡茶。过去,杏核可以卖钱,也可以捣成糊,女人用来抹脸。“如今,把他家的,都是撇的货了。别说是杏仁,就是女人,也老得没人要了,也是个撇的货。”
乡村振兴,绿化美化环境,给村道两边栽植树木,都是松树,有着很美的造型,根部用草绳五花大绑带着很大的土块,挖掘机挖出坑,栽上树,水罐车浇过水,不用管,保活。但是松树长得慢啊,也就是个景致,不指望它长大成材。
说到绿荫覆盖山峦沟峁,地埂路畔,那还必须说到山毛桃。山毛桃绝大多数是野生的,在我的认知里,它们并不是树,它们同那些柠条、刺蓬、冰草、灰条相似,茂密葳蕤,繁多遍地,到处生长,无需栽培、浇水、松土,谁都不会去特别关注,任它们随心随意地绿,顺时应景地长,然后默然无声地枯。这就是乔木与灌木的最大区别。作为使用者的人,注重的是“材”,所以杨柳榆杏,才被称为树,栽植到视线所及、用时方便的地方,而山毛桃,尽管漫山遍野,是构成七月半山川绿荫遮地的最重要成分,但受到的轻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况且,山毛桃的果实,要到八九月间才可采摘加工,换取几两碎银。现在,它尽可以像以前那样不动声色、不被人知地生长。春秋两季植树,每次都是几千棵的栽植量,也大都寻找田埂地头,荒坡沟底,栽植下去,也是不用管护,却都长得很好。贱,也有贱的好处,那就是生命力顽强,在不断的自然进化中,已经练就出一种见缝插针、有土就活的本领。
树大不但招风,也招鸟。鹁鸽是成群结伙地在山沟梁峁间盘旋,麻雀是在白杨树的枝叶里唧喳,乌鸦是在柳树上孤鸣,野鸡是在草棵下散步,啄木鸟是在树干上巡诊,沙鸡是在电线上弹琴,燕子是在屋檐下成亲,“姑姑等”这种传说中的飞鸟还在一边飞过断崖一边哭诉着“姑姑等,姑姑等”……这是马沟盛夏里的另一道风景。
其实,七月半,真正绿荫铺地的是各色庄稼。
马沟人的来钱路无非三途:种地、养殖、务工。
全村有将近800的劳动力人口,除过16岁以上在校就读的学生,也还有690人。但马沟在外务工的人并不多,这缘于马沟村的经济支柱是种养收入。要想发展养殖业,家里就得有至少一个壮劳力。盖圈舍,垫牛圈,出牛粪,使用铡草机,从青贮池里掏饲草,准时准点添草拌料,生牛犊时不分昼夜的守候,这不是身单力薄、家务缠身的女人所能胜任的。养上七八头牛,一个大男人都累得够呛。而要把牛羊喂好,个个膘肥体壮、毛色顺滑光亮,饲草保障是首要问题,也是重大任务。大面积种植青贮玉米成为必然,青壮年首选不是外出务工赚钱,而是留在厚重无言的土地上“立地生金”,这是马沟村最大的实际。所以,与其他空心村、老人村不同,马沟村是年轻人的村庄,也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村庄,更是烟火旺盛热气腾腾的村庄。
西吉县的马铃薯全国驰名,也是西吉县的支柱产业,但马铃薯在马沟的种植,仅限于够吃的水准。像张脑组李军那样种植40亩,将收获的马铃薯运往淀粉厂出售的,比较少见。每家每户,种植二三亩,也都在边埂地角,施肥很少,管护上跟那些覆盖山坡的山毛桃差不多。盛夏正半,墨绿色的叶子间,白色的花铃夜晚的繁星一样,在风中闪烁。花叶的底部,土地已经开裂了许多土缝,说明马铃薯的茎块正在积蓄养分和增大它的体量。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青贮玉米。正午时分,我进入到村部对面高家的青贮地里,玉米的茎秆,已经超过我一米七五的身高,宽大的叶子,必须小心地分开,以免锋利的边缘划到我的脸上。我蹲下来,顺着潮润的行子看出去,土地不规则,行子也不直,望不到头。
种植的玉米,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做饲草为目的的青贮,追求的并不是结在茎秆上的棒子和它的产量,而是玉米茎秆的粗细高低,这决定着每亩将产生多少饲草。第二类是籽粒玉米,也就是结棒子的玉米,是以玉米的产量高低看收成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覆膜种植,土地酥软,地膜保墒。前半年干旱,但苗是保住了,前段时间几场透雨,旱情完全解除,每株玉米都生机勃勃,茁壮成长。但是也有少量倒伏的玉米,或者风,或者雨,或者溜进庄稼地的狗,都有可能使原本扎根不牢的玉米倾斜倒伏,但这样的玉米,只要根不断,茎还连,就不能对它失去信心,它依然可以汲取土壤中的养分,不断地生长。但也有极个别直接折断的玉米,这是不幸的玉米,就像是人群中遭遇重大残疾的人一样。它们的命运是悲惨的,别的玉米都在健康茁壮地生长,而它,却因为外来的力量,遭遇如此的不幸,这样的玉米,要么干枯,过早地痛苦地结束一生,要么艰难地活着,却注定结不出棒子了。在干净而无杂草的玉米行子里,我发现了半被掩埋的除草剂的药瓶。农药,主要是除草剂,用于杀死野草的幼苗,将空气、阳光和土壤中的养分,更多地让庄稼享用。除虫的药使用的并不多,除非出现了大面积的病虫害。我在身旁的玉米叶子上,发现了一只爬行的小飞虫。不认识它,也不知道它的名和姓,但看起来,它对玉米的危害是不大的。也许它是一只喜欢独自旅行的虫子吧,偶尔出现在这片叶子上,就像我偶然出现在这片玉米地里一样。当然在一切事物中,都会有例外。我就在一株玉米的叶子上,发现了黄斑。农作物中有黄锈病,也称黄疸,主要危害树和小麦,呈孢状,是锈孢子器,破裂后散发褐黄色粉末,会传染,造成大面积黄锈病。但这株玉米叶子上肯定不是黄锈病,这只是这片叶子被虫子咬过后发生的枯黄。
细致认真地观察玉米和其他庄稼的生长过程,也是审视自己的人生。当然并不是想成为农业专家,但是对于驻村第一书记来说,对于一个以写作谋生的人来讲,观察任何事物都是有用的。
和往年的种植不同,2022年马沟村的种植出现了两件新鲜事,在马沟村可称之为开了先河。其一是玉米大豆复合式种植,也就是套种。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不让一分地撂荒,这是硬指标,硬任务。还是在寒冬腊月,村两委成员和我们驻村工作队就进村入户,家家动员,要在开春时,进行玉米大豆复合式种植。一块地,不能全种玉米,而是要种两行玉米,间种一行大豆。一说种大豆,村民们都误以为是炒着吃的蚕豆。我们说大豆就是黄豆,就是毛豆。村民们意见更大了:全种玉米都不见得能收多少,这是谁想出来的“馊主意”,专门折腾老百姓?我们讲粮食安全,讲科学种田,讲投入与产出。越讲,村民们越糊涂。老丁年轻时在陕西渭南当过兵,还干过一段时间的村会计,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不反对推广玉米大豆复合式种植,但是他却提出了所有村民都存在心底的疑虑:“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你就说复合种植,也就是套种。两行玉米,一行大豆。行与行之间是不是要留出空隙?地就那么大,留的空隙多了,是不是种的株数就少了?你们说是要确保粮食安全,要给老百姓增加收入。就那么一亩地,越种越少,反而能增产?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只好请农业技术员给大伙儿做解释,现场进行科普: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是利用玉米、大豆的“身高差”,解决两者“争地”的问题,既能充分发挥高位作物玉米的边行优势,又能扩大低位作物大豆的受光空间,还能充分利用大豆中的根瘤菌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有机氮的特点,补充玉米生长所需要的养分,能够提高土壤的肥力,从而提高玉米的产量。老丁垂头嘀咕:“话是这么个话,听着也有道理,科学上的事,咱老百姓不是太懂。但是实际上怎么个情况,又没种过,谁知道。”支书的父亲老刘常年走南闯北收破烂,见识和老丁差不多。但是他想着总要支持儿子的工作,就对老丁说:“老丁,远路上的话咱不说。你和我,带个头,开春了全都套种,秋后了看,出水才见两脚泥嘛。不种,咋知道好不好?不能光等着别人出头的椽子先烂,当出头鸟。”老丁不干,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年的庄稼两年种呢,我不能把宝全都押在这个新玩意儿上。”最后勉强答应,一半地套种,另一半还按老传统。有这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农带头,别的人才开始报亩数。乡政府下达给马沟村玉米大豆复合种植的任务是400亩,开春了,播种了,技术员来到村上,和我们一道,每天奔波在山梁坡地里,指导村民开垄、覆膜、点种。最后,完成的面积是460亩。
现在,七月半,天宇干净,风清气爽。我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刘建飞,特意去查看套种的玉米大豆的生长情况。夏雨过后,土地潮湿酥润,玉米、大豆都特别茂盛。通常情况,是两行玉米,套种大豆一行。我们先查看玉米的长势。套种的玉米,都是籽粒玉米。我们发现,套种确实是减少了玉米的株数,但是因为通风更畅,日照更强,再加上大豆根系输送的营养,很多玉米都“生了双胞胎”,结了两个棒子而不是原来的一个!这恐怕就是农业技术员所说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了。穿过两行玉米,套种大豆的地块,马上就显出开阔来,蹲在地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山上那棵孤独的柳树。玉米常种,大豆初见。茎高四到五十公分,豆荚二三十个。不过顶部还在开花,豆荚还在增加。这种作物,跟蔬菜豆角类似,简直就是从根部开始结荚,有些都长到土里去了。长势实在喜人。仔细观察,大豆的茎秆上,有细密的头发丝般的绒毛,想来,那就是大豆茎秆上的呼吸器官吧。大豆的叶面上有少许虫洞,前段时间旱情严重,也滋生了不少虫子,经过两场大雨,虫子被冲刷掉了不少,但依然还有留存。好多种植戶其实已经购买了杀虫剂,担心再下雨,药未打。
从套种的地里出来,到了村道边的大柳树下,恰好遇到了在柳树下乘凉聊天的老刘和老丁。老刘的自行车停在路边,后座上架着一捆刚挖的“地骨皮”(一种中药材)。老丁笑嘻嘻对我说:“书记,你到地里看套种去了?真个长得好,真是没想到,现在有点后悔。”老刘挖苦打击他:“现在后悔也晚了。当初让你带个头,你还说不能把宝全部押到这上面呢。”老丁依然笑着:“庄稼年年种啊,今年后悔了,明年就全种么。我不像你,你八头子来钱着呢,你看,这一早上,挖了这么一捆地骨皮,少说也弄了一百元了。”老刘也笑了,说:“你享福著呢么,我是个贱骨头,就是个土里刨食的命么。”我和建飞笑着离开了。
第二件,就是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370亩,与山东一家在西吉县注册的蔬菜公司签订种、管、销合同,种辣椒和小南瓜。辣椒苗和南瓜种子由公司提供,种植技术由公司指导,收获的辣椒和南瓜由公司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全部收购。在半山坡的旱地里栽辣椒、种南瓜,那就是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但承包经营的年轻人有想法。东西两山之间不是夹着一条滥泥河吗?滥泥河上不是有座水坝吗?水坝里不是常年都有一泓清澈的碧水吗?就在山上挖了两个巨大的蓄水池,用管子将坝里的水“泵”到蓄水池,将池子里的水压到每行辣椒、南瓜地里,而且是最为省水的“滴灌”。这样,村民的一块地,可以收三份钱。先收土地的“租金”,再到蔬菜地里去务工,收“薪金”,辣椒、南瓜卖了钱,到年底村集体经济壮大了,作为“股民”的村民还可以“分红”。许多人搞不明白,土地还是那些土地,不会增加一寸,人还是那样的人,汗水摔八瓣还是那样在干,怎么会“从土里刨出金钱来”?这就是办法。
辣椒、南瓜试种成功。尽管前半年雨水少,有旱情,但因为“引水上山”,精准滴灌,干旱并未影响辣椒和小南瓜的生长。这时节,260亩辣椒,已经整整齐齐,白花开遍,辣椒那小小的尖角,小铃铛一样缀满茎秆;110亩小南瓜,扯蔓坐瓜。我和合作社的负责人喜占川大致估算了一下,差不多是这样的收获:每亩产辣椒约1500公斤,按照合同,每公斤2元,每亩的收入是3000元,270亩辣椒总收入将近80万元;小南瓜保守估计每亩产1000斤,每斤1元,110亩的总收入也能达到10万元。刨除地租、苗子、地膜、农药、人工工资、滴灌设备等投入,利润差不多是50万。辣椒、小南瓜的长势和未来预期的收成,也让乡政府、村委会信心大增。乡政府、村委会专门请了县资源局的领导来村上,对马沟村整个东山坡进行航拍绘图,做土地开发规划,村干部开始挨家挨户去做思想动员工作,让老百姓流转自己的土地,交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来经营。明年,东山的1587亩山地,都将得到彻底的改造,全部采用滴灌,种植辣椒、小南瓜、西红柿等各类蔬菜。那么,马沟村所有的妇女都可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既不耽误送孩子上学,也不影响照顾老人,还能增加务工收入。
从2020年整村脱贫,步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如今乡村振兴已有两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许多工作要做。但首要的是在脱贫基础上,根据村情,确定产业,扩大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村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重中之重。
马沟村正处于半夏。整个村庄,就是一株正在蓬勃生长的庄稼,不断地汲取大地的营养,沐浴和风丽日。环境整治,就像是去除庄稼上的锈斑和害虫,将村庄涤荡一新;细雨微露,那就是移风易俗,给村庄的内里,滋生一种清新向上的力量。每一天,庄稼都会生长一寸,玉米在饱满,豆荚在膨胀,土豆在增大,牛羊在肥壮,这是一股暗暗生长的力量,使马沟村逐渐地成长,逐渐地健壮,逐渐地爽朗,逐渐变得美丽吉祥。
等到金风起,万山红遍,那时的马沟,必然是一幅丰收的景象。
责任编辑:尹晓燕 包成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