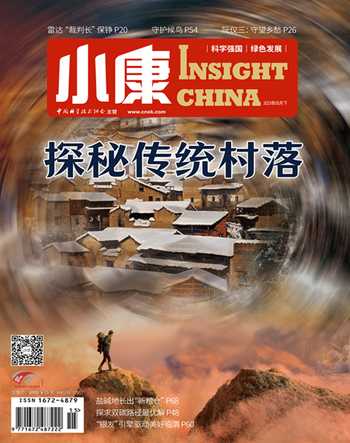世界候鸟日水:维持鸟类生命
袁帅
2023年世界候鸟日的主题是“水:维持鸟类生命”。世界各地很多水体和水生生态系统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依赖它们的候鸟也是如此。

世界候鸟日旨在提高人们对候鸟及其保护相关问题的認识。该纪念日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鼓励国家和地方采取行动保护候鸟。不同于其他关于生态保护的纪念日,世界候鸟日每年有两次,即5月和10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这样的安排反映了鸟类迁徙的周期性,也反映了南北半球不同的迁徙高峰时期。2023年世界候鸟日的主题是“水:维持鸟类生命”,以此强调水对候鸟的重要性。
由尼加拉瓜艺术家奥古斯托·席尔瓦制作的2023年世界候鸟日全球宣传海报以水的蓝色为主色调,展示了12种迁徙水鸟:非洲硬尾鸭和卷羽鹈鹕提醒人们,许多物种需要湿地和开放水域进行迁徙、越冬和繁殖;有些鸟类需要特定类型的水域栖息地,比如勺嘴鹬在迁徙和冬季时依赖的滩涂、蓝翡翠钟爱的红树林和其他沿海地区,以及赤颈鹤筑巢时通常会选择的季节性洪水泛滥区;家燕的食物——昆虫、棕煌蜂鸟经常光顾的蜜源植物、美洲雀栖息的草原和欧斑鸠栖息的河流森林也都离不开水;北极海鹦和漂泊信天翁代表着海洋,它们正日益受到化学物质和塑料垃圾的污染;鹗寓意着当人类共同努力保护地球时,鸟类数量的下降趋势是可以逆转的。
湿地、河流、湖泊、溪流、沼泽和池塘都是候鸟觅食、饮水或筑巢的重要场所,也是它们在长途旅行中休息和补充能量的地方。不幸的是,由于人类对水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人为造成的污染和气候变化,世界各地许多这样的水体和水生生态系统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依赖它们的候鸟也是如此。
鄱阳湖建闸引争议
鄱阳湖建闸争议再掀热潮。今年1月,该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送至生态环境部报批,这是该建设项目动工建设前的最后一关。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地点位于鄱阳湖入长江口约27公里处,正好扼鄱阳湖与长江干流水体交换之咽喉。正因如此,该项目自2000年左右动议以来,一直备受全国乃至全球关注,被国内环保界冠以“争议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其争议的最核心问题是“工程该不该建”,而不是“工程该怎么建”。
对此,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文简称绿会)研究室主任杨晓红表示,鄱阳湖是目前长江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长江最为重要的大型通江湖泊之一,其生态地理位置高度敏感。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每年4至8月的丰水期江湖连通,9月至翌年3月枯水期调控,全年有7个月属于控闸状态,其工程无疑肢解了长江和鄱阳湖水域完整的生态系统。其工程方案将对鄱阳湖水质、水温、流速以及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众多越冬水鸟、植物与植被等产生不可逆或不确定影响,江湖连通性被阻隔。同时,由工程建设而引起的生态变量也是复杂的,目前工程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所涉及的水生环境、主要的珍稀物种以及江湖关系改变的综合效应研究等都还非常薄弱,不足以得出“工程建设生态影响小”“生态影响风险总体可控”的结论。
以闸坝上行、下行的鱼道论证为例。环评报告论证,多依据数据模型和物理模型进行推演,国内尚不存在针对四大家鱼幼鱼上溯而建设鱼道的成功先例;鱼道通过闸坝的进出口高程分别为3~6米不等,其诱使鱼类过闸的概率偏小且过闸后成体空中跌落、与水体碰撞易受伤。形体比常规鱼类大数十倍不止的江豚,要想通过鱼道就更不容易了,建闸后将直接影响闸址前后几十公里范围内的100余头江豚种群生存。更何况鄱阳湖与长江干流自由水体交流的时间受限,交流的生物量,也远不止现环评影响报告书所罗列的江湖洄游类的四大家鱼、河海洄游的刀鲚、鲥鱼等少数鱼类。
此外,以清华大学教授周建军为代表的科学家通过专业论证认为,近些年鄱阳湖陆续出现的长时间秋旱现象,并没有导致鄱阳湖水情变化的基本规律发生改变,鄱阳湖作为长江具有过水性、吞吐性、季节性特征的湖泊水文属性,并未因秋旱产生实质性变化,不应该建设鄱阳湖水利工程,而建闸则将彻底改变鄱阳湖自然属性和独特的湿地环境。“该建设项目存在发展需求与解决方案不匹配、解题思路错误的问题,针对江西省提出的鄱阳湖‘长期秋旱‘水资源不足以支撑长期发展的问题,应该在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整体发展战略以及长江全流域‘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总体定位上创新性寻求解决方案,尽可能小地干扰自然栖息地,而不是通过简单筑坝制造更多的问题和极大的生态风险。”杨晓红告诉《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
据杨晓红介绍,鄱阳湖建设枢纽工程涉及鄱阳湖湖区及长江中下游众多生态敏感区,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目前的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对该工程所带来的生态影响估计与补救防范措施设计不足。该工程共涉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各种类型的国家自然级保护区19个,其中涉及长江重点鱼类保护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3个;各种类型的省级自然保护区16个;县级自然保护区6个。其中仅湖区对候鸟迁徙产生直接影响的碟形湖达到102个、占到湖区总面积的22%。“几乎没有哪一项建设工程,能对我国自然生态保护如此大范围、如此多生境与物种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在短期内基本很难系统理清其生态影响的方方面面,更不要说能准确地提出系统、全面针对工程建设所带来的扰动或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对措施。在论证不充分的前提下动工,容易得不偿失。”
此外,杨晓红表示,考虑到2021年施行的《长江保护法》要求将长江干流、重要支流、重要湖泊等控制断面的生态流量纳入日常调度,鄱阳湖上游五水及长江干流的水量水情,均在此要求落实范围之内。此项工作落实后,必将对鄱阳湖的水文变化乃至长江中下游、长江全流域的保护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鄱阳湖建闸的必要性将大大降低。
“长江是水源丰富、水系众多、承纳众多流域来水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和人文文化。如果长江最大的淡水湖泊的江湖连通被切断,其他中下游仅存的洞庭湖、太湖、巢湖等少数大型湖泊也按此思路来囤水、截水,解决发展之需,让长江哪怕只是其中下游成为一条直溜溜的排污沟,丧失其水源供应、生物资源供给、纳污等生态功能,也无疑是一大悲剧。”杨晓红如是说。
《海洋环境保护法》有待完善
生命起源于海洋,全球约有670余种以海洋为生存环境、以海洋生物为全部食物或主要食物的海洋鸟类,在我国就记录有183种海鸟,如红喉潜鸟、黑脚信天翁、白鹭、海鸥等。早在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曾奔赴多个省份开展《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工作,同时委托上海、江苏、广西的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报告显示,“当前,我国近岸局部海域污染较为严重,海洋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全国约十分之一的海湾受到严重污染,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足40%,约42%的海岸带区域资源环境超载,部分地区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破坏退化问题较为严重,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多发频发,溢油、危化品泄漏等环境风险持续加大”。
对此,绿会政研室杨洪兰分析称,这一问题的出现,虽然有相关行政部门执法监管粗宽松软的原因,但海洋污染及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缺少来自社会力量的监督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架构却无法满足保护海洋环境的实际需要。
杨洪兰表示,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条款明确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权利赋予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实施《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3号),这一规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涉及海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仅由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作为主体开展,社会组织无缘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但是,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编第七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中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和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均明确规定了社会组织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拥有赔偿请求权。而《海洋环境保护法》却将赔偿请求权只限定在拥有海洋环境监督权的部门,这显然与民法典、民诉法、环保法的规定相背离。
“既然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均授权社会组织可以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那么海洋环境保护也应当在此范围之内。但现实中却出现多起由社会组织提起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規定被裁定不予受理。法院认为,具有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只能是‘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而不能是社会组织。因此,环境保护组织被完全排除在了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之外。”杨洪兰这样告诉《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
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也为了国家法律规定的统一性,杨洪兰建议,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设置前置程序,即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发现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反映,违法行为在60日内没有得到处理或解决,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也没有提出损害赔偿的,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增加上述规定,一方面可以维持目前现有的诉讼秩序不被打乱,另一方面增加补位的公益诉讼,可以防止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救济出现真空地带,更有效地保护我国海洋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