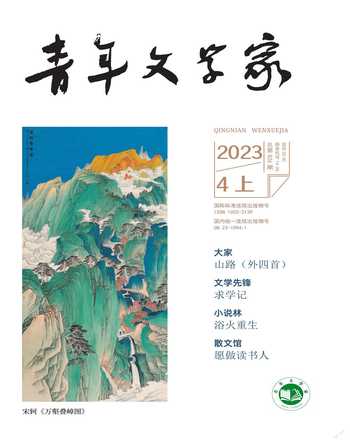由虚构建造的时间迷宫
缪文培
一、虚构的存在与表达
虚构作为一个动词,指的就是凭空捏造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不真实的世界在面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的时候往往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因为真实的世界不能成系统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真实即存在的事物,以及原物曾经存在的事物这些常识性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而博尔赫斯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用时间去使他的作品自解。实际上博尔赫斯的风格是很好模仿的,其关键就是对排列方式不厌其烦地组合,俄罗斯套娃一样的层叠故事结构,以及用准确的数据或者真实的人物姓名来插入在虚构的故事之中。但模仿他的难点在于,其他作者很难达到那种在极其有限的篇幅之中却浓缩着饱含意义的智慧。其实能够被模仿或者不能够被模仿都不会损伤到博尔赫斯的写作才能。
我们能感觉到虚构,我们常说这部电影是虚构的,这部小说是虚构的,这是形而下的虚构,是我们能感觉到的某些是虚构的。形而上的虚构却是我们不能感觉到的,只能去思考,用自己面对现象世界时的思维能力去思考此种虚构。而博尔赫斯的虚构显然属于后者,其实无论是形而下的虚构还是形而上的虚构,其何以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世界?我们认为想象便是虚构的存在方式,是想象让虚构得以存在。
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中提出:“虚构将已知世界编码,把未知世界变成想象之物,而由想象与现实这两者重新组合的世界,即是呈现给读者的一片新天地。”他指出,虚构是带有意指向的,而想象却是没有任何意指向的,虛构也就是在无任何想象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论是能够感觉到的虚构还是必须去思考的虚构,其所有的来源都是想象,都是由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中无论是人还是任何其他形而上的想象所构建的。而如果要把这一切都归功给博尔赫斯的“才能”这种有些形而上的东西,那么我们对于文本的探讨是难以继续下去的,因为这样会把他的创作导向推向不可知的境地。但假若事实不是这样,甚至不是博尔赫斯所说的对于虚构和永恒的探索只是来源“爱好”,而是来自他强烈的寻找本能,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存在的困惑以及制造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永恒。由此我们可知《小径分岔的花园》不是因为他的爱好,也不是因为在某种神秘力量的推动下写成的。它应该是博尔赫斯无数次的追问和思考之后的产物。如前所述,是想象让博尔赫斯乃至文学的虚构得以存在,但仅有想象,创作是难以进行下去的。任何事物总要表达出来才能彰显其本体的意义和价值。《小径分岔的花园》因想象而存在,表达着博尔赫斯的内在需求和价值追求,但虚构也有其特殊的表达方式,其表达方式首先是选择,因为想象是无意指向的,通俗的说是漫无目的的,而虚构的内在要求是必须由一定意指向的,这也就决定了博尔赫斯选择想象的材料的时候必然会有选择的去除符合审美世界的情感价值的相关材料相互融合,因此小说的核心部分是被融合在五个盒子之中,第一是余淮博士的证词,第二是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三是汉学家艾伯特,第四是崔鹏,第五是崔鹏建造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些都是博尔赫斯想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但是它们需要构成一个整体。所以选择之后就要融合,这个融合一方面是把博尔赫斯提取出的相关材料之间进行相互融合,另一方面是把这些材料和现实世界相融合,以期达到现实世界和审美世界的相互观照和相互接近。所以文本中有余淮坐火车,下车之后又与一帮孩子交谈的情景,这就是在与真实融合,这种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画面让作品的可信度增强,之后却又写道余淮要找的汉学家是如此神秘,但镇子上没有人不知道,而且拥有一座中国古代花园这些略显离奇的事,又使文本变得神秘起来。既然选择之后,便是自解,是自我消解,也就是提取的相关材料全部消解在审美世界之中。在文中,博尔赫斯把时间想象成一个圆形的物品,时间可以从过去流向未来,也可以从未来去向过去,某个物品也可以像存在于平行时空那样在现在、过去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之中同时存在,这显然不是博尔赫斯的无所谓的想象,在借汉学家艾伯特对崔鹏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的解读,博尔赫斯完成了对自己审美世界的建构。最终,他用虚构虚拟出一个他对永恒时间的观念形象世界。但这个形象世界是不能完全界定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审美的世界。
二、博尔赫斯虚构创作手法的意义
在探讨了博尔赫斯的叙述过程之后,我们应该看到,虚构这一手法在这一篇作品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这种创作取向究竟对成就《小径分岔的花园》有什么用处?我们常常去观照某一个事物或者是现象时总是想先问问它是什么,它为什么而存在之类的问题,我们对文学也是如此,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很难得到满意的回答,也许乔纳森·卡勒指出的“文学就像是杂草一样的”对文学的说明反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而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也指出:“‘文学一词如果限指文学艺术,即想象性的文学,似乎是最恰当的。”如上所言,虚构在自身的自在存在与表达之后,通过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构成了文学的自在与存在,因而,虚构便是文学的存在方式。而博尔赫斯更是在此基础上,在不断地探索形而上和文学的可能性的过程之中,靠着他那独特的想象美学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思想迷宫。
博尔赫斯历经了现代主义的高峰和后现代主义的萌芽,却始终以一种古典主义的情怀对待自己的写作。他创作的时间跨度超过七十年,虽然当时的他常被同行们误解,甚至连马尔克斯也说过:“博尔赫斯对于我们这代作家的意义只在于他的精确。”他们认为博尔赫斯的传作,与拉美的苦难现实无关,更与整个人类的现实处境无关。然而,对一个在眼盲的幽暗中逐渐老去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探讨生命和宇宙的实存本身更现实和迫切的呢?在博尔赫斯看来,虚幻,或许正是他要面对的惨淡人生。
博尔赫斯并不是不关注现实世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有一句很精辟的话语:“诗比历史更真实。”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历史首先是真实的,而为什么说文学比历史更真实呢?历史的真实往往是一种事实的真实,而文学的真实是一种价值的真实。事实的真实往往必须客观地存在着,就像新闻的真实性一样,它要求我们必须还原事件的本来面貌,不容许我们在评判其事实的时候带有任何一点自己的主观价值情感立场在里面。而这往往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人生而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情感价值区域,我们又常常歪曲事实的本来面目。有一句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表达的正是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去相信的历史的真实往往被歪曲不可信,难道我们要去相信虚构着的,以一种弄虚作假的环境中构建的文学吗?其实,真正意义上说,我们无所谓相信不相信,而是我们要不要去承认虚构的文学。博尔赫斯说过,是哲学和宗教启发了他的文学活动,“我想尝试一下哲学和宗教的可能性”(《博尔赫斯全集》)。但当我们认真阅读他的作品后会发现,对于这两个方面,博尔赫斯目光的重点其实是放在哲学之上的,而他想借助哲学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却是时间的问题。博尔赫斯认为,时间问题是哲学问题的根本核心。博尔赫斯在他的大量作品之中都写到过那句他一直相信的柏格森的话:“时间问题是一切形而上问题的关键,解决了时间问题,别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博尔赫斯也承认过,他一直迫切地想知道时间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他认为,要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他就无法继续生活。换句话说,博尔赫斯的文学活动是由于对时间问题的探索而激发的。
博尔赫斯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探索和尝试,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吗?我认为,不是。在一个虚构的环境中建构的写实作品,常常能够引起轰动。比如,我们常这样评价一篇作品:很真实,催人泪下,可是,催人泪下的只是事实的真实吗?当然不是,而是这故事所传达出来的人性之真,以及作家所表现出来的情怀。博尔赫斯试图对时间问题的解释,指向对永恒的渴望。因此,博尔赫斯的作品是虚构的,他虚构出一个审美世界,这个审美世界不是我们所认识的现实世界,这个审美世界所表达的正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人在其特有的情感价值立场上所评判的这个审美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正如格林菲斯在《论文解读:指南与范例中》中一直强调的那种观点一样:文学表达普遍真实的人,并且文学表达现实世界中应该可能的行为和行动,这个可能的行为也就是说如上所言的文学在虚构中表达人类普遍的情感和价值的真实。而博尔赫斯所作的对与永恒和时间的追问可能正是在表达着此种真实。
博尔赫斯虚构了一个梦幻的世界,他虚构的深层理由在于人的内在祈向,与普遍的人的情感理想追求有关,博尔赫斯不关心事实如何,他只关心文学应该怎样。
换句话说,博尔赫斯借助虚构出的审美世界所要传达的是情感的真实和价值的真实,这个审美世界让人类荒诞孤独的情感得以安放,让人类对于人生稍纵即逝,一切都是短暂的,这些本能的恐惧得以消解。这才是博尔赫斯成为博尔赫斯的真正理由。
在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中,我们都比较倾向于为人真诚而摒弃虚伪,对人对己真诚才会获得社会的认可。可也有人说,其实现代社会中人大多是虚伪的,是为了某种利益诉求。对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常常以虚伪示人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是一个不真诚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把自己最美好最精彩的一面展示给别人,恰恰是对别人最大的尊重,也是彰显自己最大诚意。那么,以此联系博尔赫斯的虚构,作家创造出虚构的文本,难道说就是作家在说假话,是虚假小人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柏拉图反对修辞,主张驱逐诗人,是因为柏拉图认为诗人、演说家运用修辞没有表达出任何接近理式的真理,认为他们只是在迷惑大众。诚然,诗或者文学以虚构的形式在表述着某种真实,到那时创作者为了说明这种真实只能用虚构的方式去表现创作者的诚意。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语言。文学也可以说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也是由语言所组建的。但是从古至今,人类其实已经意识到语言在表达人类的情感和价值的时候往往是非常无力的。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说,语言要真正说清某种真实是根本做不到的,后来庄子也明白了这一点,其《庄子》篇目几乎都是用寓言述说的,可语言不也是虚构的吗?庄子费尽心思用非常生动且引人深思的寓言故事表述着某种真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庄子的诚意吗?再回到博尔赫斯身上,博尔赫斯也有率性表达自身情感价值的强烈需求,其率性表達便客观不自觉地通过内在的诚意而显现,再由此而指向想象的虚构,利用虚构的方式,最后才构成其文学。
“正如米夏埃尔·兰德曼所指出,人‘离心地生存着,文学的虚构性赋予人以超越性,让人走出自我,远离自我,然而,又让人真正找到人本身,真正回归自己。”(马大康《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这里的走出和回归,并不是博尔赫斯或者读者单方面的状态,而是在通过这个虚构的文本,创建和阅读的过程所达到的双方的精神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