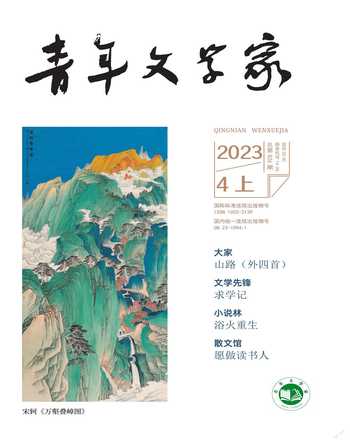匆匆又一年
黄和根
小时候,我对过年总是怀着一种特别的期待。
细细的竹根上绑着一个炮仗,“啾—”的一声,冲天而去,“叭—”的一声,在半空炸响了,这是冲天炮的声音。“摔炮”的最高境界,是砸在池塘的水面上也能炸开,当然这是力气大的孩子的独享,一般孩童只能摔在硬邦邦的地面上,方能作响。“地雷炮”的威力在于点燃导火索,然后扔进池塘,炸得水花四溅,或者埋入一片空旷而松软的土壤里,炸出一个碗口大的小坑来—每当这时节,孩子们必欢呼雀跃。再有就是大人们放过的鞭炮,其中必定有飞散的单颗。孩子们一一拾掇了起来,又从大人那里偷得一两支烟,点燃了炮仗,远远地丢出去,“嘣”的一声脆响,于是,孩子们又一番欢呼雀跃了。
玩气枪的忌讳在于瞄准人,滚雪球的余悸在于全身湿透,打雪仗的恐惧在于伤及伙伴,踩高跷的顾虑在于掉落水坑,收压岁钱的绝望在于被父母拿去保管,说话的纠结在于语焉不详,除夕和大年初一的恼恨在于天未亮便要起床……这桩桩件件,无一不令人耿耿于怀,却也无一不令人欢呼雀跃。
过年的好处在于,只要你不捅破天,就算当着“虎妈狼爸”的面儿也可明目张胆地犯错。倘若你的寒假作业能够侥幸熬到过年还未做完,则过年期间,你完全不必提笔作业,更不必秉烛夜读,苦背那一篇篇嚼碎了舌根仍旧背不出来的“之乎者也”。倘若你足够聪明,趁父母兴味正浓,便可提一些要求,哪怕稍微过分,也总能够得到允诺。正是这样一份喜悦,让人欢呼雀跃。
然而,好景不长。
一心盼着长大,一心盼着踏入社会,一心盼着闯荡江湖,那时节的度日,用了“煎熬”二字,恐怕也是丝毫不过的。誰知盼着盼着,眼看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我们居然确乎长大了,踏入社会了,闯荡江湖了。
那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江湖梦。那梦境,不是呼风唤雨,便是指点江山。总之,必须是救世主。总以为目前不可得者,在若干年以后的将来,一律只如探囊取物而已;而那些不想见的,于行将呼风唤雨之际,瞬间便可烟消云散。
事实上并非如此。不但不如此,反倒遂了洪流的席卷,受了生活的压迫,挨了事业的鞭笞,使得原本豪情万丈的自己,竟越发举步维艰了起来。正当此时,双亲也两鬓斑白,小孩亦到了年年盼着过年的年岁,至于祖父祖母,或者老态龙钟,又或者入土为安……
每当这个时候,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年,不觉有了无数的感慨,万分的唏嘘。办不完的年货,给不尽的压岁钱,走不完的亲戚,送不完的礼品,无止境的应酬……这时,你恰如那热锅里的蚂蚁,真正是心急如焚的。身处拮据之境,而又偏有担当者之于过年,好比拿着一个烫手的山芋,不吃饿得慌,吃又烫得紧,真是束手无策。
一个人总要经历一些苦难,方能在他品味幸福的时候有所领悟。倘若一个人的幸福与生俱来,那么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就会变得束手无策,甚而自甘堕落。
当一个人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其实就能体会当年父母面对过年是一种怎样的心境了。每当我听见人们的嘴里念叨着过年的许多情形,心里莫名就会泛起无数的滋味,仿佛装的是五味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