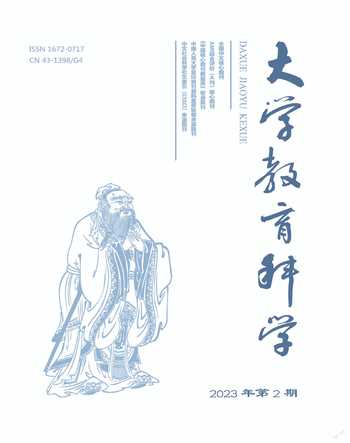重审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式、趋势与争议

摘要: 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兴起源于社会各界的问责,这是招生规模扩张、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和新管理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全球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主要存在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基于产品质量观、注重知识创新、秉持学徒制培养的德国模式;另一种是基于过程质量观、注重能力训练、秉持结构化培养的美国模式,其他国家则介于两大模式之间。近年来,随着德国模式的知识创新原创性标准逐渐遭受质疑,美国模式的人才培养高效率优势开始受到青睐,由此各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普遍朝着过程质量观转向。然而,我国博士生教育起步较晚、学术积淀不够且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贸然模仿强调实利功用、面向多元需求的美国模式,可能会导致质量的进一步滑坡。为此,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未来进路应是:在重塑学术导向的基础上,再去强调满足与适应社会需求,依此摸索与构建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模式。
关键词: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规模扩张;知识创新;能力训练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2-0061-10
博士生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塔尖,承担着创新知识产出和拔尖人才供给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学界的普遍共识是:“在本科、硕士、博士这三类教学项目中,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最大的是博士教育水平。”[1]但从跨国比较来看,不同国家对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关注重点存在明显差异。欧美国家由于博士生培养已逐渐规范化、结构化,因此在问责制和新管理主义的驱动下,他们一方面关注博士生修业年限过长、流失率过高等问题[2],另一方面则探讨博士生教育如何适应知识模式转型、社会需求多元的趋势,即落脚在如何提振就读兴趣、发展可迁移能力之上[3]。而在我国,由于博士生教育起步较晚且扩张速度过快,2011年和2021年开展的两次大规模调查,都表明博士生最基本的学术能力尚有待提升[4,5]。那么,人们谈及的中外博士生教育质量差距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知识创新的差异,还是职业能力的差异,抑或是全面的落后?可以说,不同维度的差距呈现,表面上与各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阶段与水平密切相关,但深层折射出质量评价重点的差异。本研究将通过梳理全球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兴起缘由、典型模式与普遍趋势,重新审视我国学界倡导模仿美国模式这一趋向究竟是“正途”还是“歧途”,进而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发展路径与评价进路。
一、社会问责与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兴起
目前,质量提升成为全球博士生教育改革的主流趋向,而评价作为保障博士生教育質量的核心环节也受到广泛关注。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政府和学界甚少直接聚焦博士生教育及其质量评价,多是笼统地把“研究生教育”作为统一整体来关注[6,7]。究其原因,其时各国博士生教育规模普遍较小,主要任务是培养从事原创知识生产的学者,与社会的直接关联并不密切。直到近3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博士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并逐渐嵌入到各国知识经济的发展议程中。由此,博士生教育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8,9],相关政策与研究日益增多且主要聚焦在质量问题上[10,11]。恰恰在这一时期,关于博士生教育质量的质疑与问责也逐渐显露出来,进而引发评价热潮的兴起。
社会问责直接源于近年来博士生规模的迅速扩张。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发达国家普遍加速扩张博士生规模,如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的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增长率均超过100%,美国、英国等博士教育大国的增速也在50%以上[12](P143)。其背后驱动力在于:博士生规模既是衡量创新国家发展、高层次人才供给的重要指标,也是大学赖以获取经费投入、提升研究产出与学术声誉的关键驱动力。不过,博士生的规模扩张也带来一些非预期的影响。首先,扩张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饱和,世界主要国家超过50%的博士毕业生主动或被动地流向政府、工商业等非学术领域[13]。这种就业多元化态势,使市场雇主成为政府与高校审视博士生教育质量问题的驱动力量。雇主们发现博士毕业生往往不能有效适应岗位需求,进而对质量提出质疑:博士生培养太过注重学位论文、培养模式过于专深狭窄、未能回应就业市场需求等等[14]。其次,扩招加速了博士生教育内部结构的分化进程,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具有密切关联。如芭芭拉·科姆(Barbara M.Kehm)发现,欧洲除传统学术型博士学位外,其余多种类型的博士学位也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15]。这种多元学位类型在使博士生教育更具社会适应性的同时,亦导致原本统一的质量标准变得有些模糊与混乱。再次,扩招带来的最显著问题是博士生流失率过高、修业年限拉长,这是培养模式未充分适应新变化与学生就读动机日趋多元化共同引致的。以美国为例,近四十年博士生的自然流失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16];博士生延期毕业率也持续居高不下,人文类和社科类七年的延期毕业博士生比例分别达到70%和60%[17]。这两方面数据,在我国学界多被解释为是美国质量把关严格的体现,并被作为分流-淘汰机制改革的重要依据[18]。但在美国政府和学界看来,博士生教育的高流失率、修业年限过长是“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体现,其严重浪费了优质培养资源,可谓是“当代博士生教育的核心问题”以及“美国的丑闻”[19]。
综上,博士生规模快速扩招使教育质量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学者均在呼吁对博士生教育进行“重新思考”[20]与“重新展望”[21]。从表面来看,社会问责源于博士生规模扩张的自然结果;但从深层来看,它也嵌入到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新管理主义问责的时代趋势中。基于知识生产转型的角度,“学术资本主义”“三螺旋”“知识生产模式Ⅱ”等理论和概念的提出,对作为未来知识工作者的博士生提出了诸多要求,包括从事跨学科研究、面向社会应用需求等,而传统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及相关制度安排由于阻碍这一目标而亟待变革[22]。而从新管理主义角度来说,博士生教育因日益嵌入到知识社会发展议程中,逐渐被剥去“学术卡里斯玛”的色彩,在规训社会中被纳入“理性化”的轨道,并成为“审计”的对象[23]。无论出于何种解释,博士生教育都不再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事务或培养活动,更需要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问责、评价与监督。这亦是全球博士生质量评价兴起的根源。
二、知识创新抑或能力训练:博士生 教育质量评价的两种模式
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方法问题,更涉及对教育本质与目标的理解问题,也即坚持什么样的质量观。从世界范围来看,人们对这一问题存在分歧,并呈现出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基于产品质量观,认为博士生教育应强调知识创新,评价权交由学术同行;而另一种观点基于过程质量观,认为博士生教育主要是进行能力训练,教育质量高低由社会各界共同检验[24]。可以说,质量观在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中发挥着定向作用,直接决定着评价的目标、主体、方式、内容与阶段的差异。并且,由于质量评价引领与贯穿着培养全过程,两种质量观实际也反映着不同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差异。因此,论及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式,应立足于质量观主导取向与培养模式表现形态。基于此,我们可对世界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进行两种模式的划分:一种是基于产品质量观、遵循“学徒制”培养的德国模式;另一种则是基于过程质量观、遵循“结构化”培养的美国模式。两种模式的划分,可为各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主导取向提供分析框架。
(一)基于产品质量观的德国模式:注重知识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博士生教育肇始于19世纪初的德国柏林大学。在“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的洪堡理念影响下,德国博士生教育始终坚持的目标是“培养学术接班人”,培养结果的评判标准在于“博士生是否对所在学科领域做出了原创性知识贡献”[25]。与知识创新目标相匹配的是学徒制培养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导师作为“博士之父/博士之母”(Doktorvater/Doktormutter),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具有绝对权威性。在此模式下,博士生需将能推进学科发展的问题作为学位论文方向,并在学科共同体的质量把关之后才能获得学位资格。正如威廉·克拉克考察德国博士生教育后所归纳的那样:“现代哲学博士必须造就一个现代的学术身份、一种浪漫主义的著述者身份,其表现就是通过博士论文的杰出作品,在其中必须要有点卡里斯玛或天赋之光,无论多么微渺也必须要有一点。”[26]
此特征也鲜明体现在博士生学位论文的审阅与答辩过程中:一方面,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普遍未设置阶段性的考核要求,但在最后的论文审阅过程中,导师、全院教授以及外校学科专家会对学位论文进行集体把关,并对其是否具备原创性价值以及能否具备答辩资格进行综合判定[27];另一方面,由柏林大学开创的答辩制度,持续时间往往达到2~4小时,它既具有加持学术头衔光环的“神圣化仪式”色彩,同时也有公开接受学科共同体质疑的“公开学术辩论”意味[28]。
以上目标设定与制度安排借助博士生教育场域惯性,使德国知识创新导向的产品质量观至今仍占主导地位。产品质量观下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几乎等同于博士论文质量,衡量标准不在于博士生个人能力得到了怎样的发展,而关键在于他们拿出的学术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在此评价模式下,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基本属于学术共同体内部事务,以导师为代表的学术权威对质量把关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基于过程质量观的美国模式:注重能力训练
相比德国,美国社会的市场性和竞争性更强,其博士生教育从一开始就未完全遵循德国模式。如美国博士生教育发轫的19世纪后半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高校便开始摸索建立研究生院、将学科类型区分为“基础—应用”、强化服务社会职能,这使博士生教育诞生之初的目标就不局限于纯粹的知识贡献[29]。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为满足规模扩张、竞争压力以及多元群体需要,美国开始探索注重效率、程序标准化的博士生教育结构化改革:“将传统上没有系统组织、博士生身份模糊、缺乏制度性规约、重科研轻培养、交织在大学日常学术活动之中而非一个明确学业阶段的博士生教育,转变为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任务、系统性的、有组织并且有完备制度约束的培养模式。”[30](P265)
这种“结构化”培养模式使市场成为影响博士生教育的关键要素。美国政府与学界普遍认为博士生教育的重心不应仅仅落脚于生产出一篇“学位论文”(Ph.D. as a Product),而更应转向博士生的能力训练过程(Ph.D. as a Process)[31],也即令经过训练的博士生,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工人核心能力的要求。此导向也得到系列质量评价政策的贯彻,如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美国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开展的多个评价,其指标体系都甚少涉及知识创新方面的内容,反而将“可就业能力”和“职业胜任能力”作为衡量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标准[32]。
可见,基于过程质量观的美国模式,更强调博士生的能力训练,注重博士生对就业市场的适应性及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度,评价权也从单一学术共同体转移至社会各利益主体手中。
综上,两种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式,在评价的目标、主体、方式、内容与阶段上存在诸多差异(见表1),提供了各国政策出台与研究探讨的基本参照框架。并且,这种模式差异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国际比较光谱,德国与美国分属两端,偏向产品质量观的国家(如日本、俄罗斯、印度)更接近于德国模式,而偏向过程质量观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则更类似于美国模式。这也为后续探讨中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问题奠定了比较基础。
三、模仿美国模式:博士生教育质量 评价的全球趋势
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可划分为以德、美为两端的模式光谱,但21世纪以来,各国博士生教育出现了共同改革趋势:培养理念从培养学者到培养精英、规模结构从单一扩张到结构分化、招生选拔从评估学习到全面考察、培养机构从一方主导到多方协同、导师队伍从独立培养到团队指导、课程结构从专业主导到通专结合、国际化从经济主导到全面行动、质量保障从导师主导到多方参与[12](P142)。这八大新趋势表明,以往不同模式的截然分离已开始出现变化。并且,与其说这是全球趋势,毋宁说这是对美国模式的模仿趋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于德国模式的知识创新原创性标准飽受质疑,另一方面也与美国模式的人才培养高效率优势密切相关。
(一)德国模式的知识创新原创性标准饱受质疑
在产品质量观的德国模式下,博士生提交一篇具有原创性知识贡献的博士论文,是评价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不过,这种原创性标准正面临诸多质疑:第一,原创性的标准存在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它究竟是指理论原创、知识原创、方法原创抑或全面原创?尤其是,目前各学科领域已经高度专门化,究竟是否存在统一的原创性标准?退一步来说,假如承认原创性存在统一标准,但科学社会学的大量研究表明,许多研究尤其是一些具有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性研究往往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辨别与承认,此即著名的“科学睡美人”(Sleeping Beauties in Science)现象[33]。这些原因导致对博士论文的原创性判定成为突出难题。第二,目前学术创新的难度愈发增大,博士论文很难被当作“诺贝尔奖”来评审[34]。实际上,绝大多数学科都处于托马斯·S·库恩所言的“常规科学”阶段,并不具备范式转换的革命条件[35]。再加之庞大的博士生规模,对博士论文知识创新的原创性期待更像是一种理想追求而非现实可能。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博士论文的合理定位,应从“大师之作”(Masterpiece)转向“学徒习作”(Apprenticeship Piece),应降低对知识创新原创性的要求[36]。第三,随着博士学位类型的多元化,许多实践导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否已天然背离了原创性知识贡献的初衷?换言之,如何对这些实践导向的学位论文进行原创性评价?而另一方面,即便是偏重学术导向的学位论文,目前在许多偏自然科学的学科领域,博士论文越来越以多篇论文汇编的形式呈现。然而,这些学科往往以团队合作、多人署名的形式发表论文,如何评价博士生在这种论文集当中的个人贡献[37]?这些问题目前尚未有明确答案。
概言之,上述质疑揭示出产品质量观之所以适用,是由于德国之前具备了政府充分放权、市场尚未介入、追求纯粹知识、博士生规模小等特定条件。而从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问责趋势的兴起,德国模式所追求原创性标准的不适切性便逐渐凸显出来,人们开始寻求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重新定位以及转换传统的质量评价模式。
(二)美国模式的人才培养高效率优势日益凸显
基于过程质量观的美国模式,并未严格遵循追求高深学问的“洪堡精神”,而是通过結构化培养来对博士生进行能力训练,努力使博士生成为适应于各行业的精英人才。如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2012年发布的报告《从研究生院到职业生涯之路》指出:教师所开发的课程应当指向帮助博士生更好通往职业生涯,使博士学位的市场识别信号更加凸显[38]。这种模式内在要求着博士生教育的目的不再停留于结果层面的博士论文,而需置于多元主体、权责明晰、程序严谨、约束力更强的制度情境中,使博士生得到扎实、充分的训练。
毫无疑问,相比于德国模式追求原创性可能导致博士生培养的低效性与不确定性,美国模式的结构化特征使博士生培养更具高效性与确定性。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北美模式的吸引力在于,与通常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它似乎能够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上确保高效率的和对研究者的有效训练。”[30](P267-268)这种高效率显著体现在招生、课程、考核等各个环节。在招生环节,美国高校普遍设置了博士生招生的程序公开、标准测试、集体决策等机制,这为他们面向数量庞大、来源多元进行“高效率的多中选优”奠定了制度基础[39]。在课程环节,美国博士生教育高度重视课程学习,各高校课程体系普遍具有规范的课程设置、系统的课程结构安排、大量严格的课程修读要求、个性化的课程修读计划等特点。这种面向全体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为他们奠定了扎实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基础[40]。在考核环节,博士生经过课程学习以后,还要通过资格考核和最后的毕业答辩才能最终获得学位,而这个过程往往是在导师委员会集体把关下完成的,进而从制度约束层面保障了博士生的能力训练能达到培养要求[41]。在这个过程中,由严格考核引致的美国博士生高淘汰率,虽也被诟病造成了培养资源浪费,但毫无疑问也起到了科学鉴别、及时止损和分流淘汰的作用,进一步保障了人才培养高效率。
对于以上特征,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如此评价:“尽管19世纪美国大学借鉴了德国博士生教育的基本理念,并使其适应了美国国情,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并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太大的影响,相反,主要是美国在影响其他国家。”[42]可以说,正是人才培养的高效率优势,使美国博士生教育成为世界争相模仿的“金本位”。
(三)秉持过程质量观成为各国改革的共同趋势
目前各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改革的普遍趋势体现为秉持注重能力训练的过程质量观。倘若说这一趋势的出现,内因源于德国模式知识创新原创性标准受质疑与美国模式人才培养高效率优势凸显,那么外部环境的变化则起到了催化作用。正如希拉·斯劳特等人所言:“学术工作的结构正随着全球市场的出现而发生改变。由于国家对全球市场份额的竞争加剧了,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制定了国家高等教育与研发政策,这些政策最终重塑了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43]在此背景下,博士身份的“学术卡里斯玛”色彩也被逐渐祛魅:“博士, 作为曾经的少数学术精英, 在今天变成了一种波及广泛领域的高智力、专业和工作领域的职业资格。”[44]这种变迁趋势对过去注重知识创新的产品质量观形成挑战,全球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开始朝着美国模式转向。
21世纪以来,各国都在对博士生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譬如,欧洲各国在2003年发布《柏林公报》,决定将博士生的能力训练作为创建“欧洲高等教育区”和“欧洲研发区”两大目标的主要纽带。在随后几年的卑尔根会议、伦敦会议以及赫尔辛基会议上,这一战略方向得到不断强化[45](P70-72)。如英国明确提出以雇主需求为导向进行博士生教育改革:一是政府对以雇主需求为导向的博士生项目加大资助力度;二是与就业相关的可迁移性技能训练成为培养关键要素;三是建立研究生院、博士训练中心等组织机构;四是鼓励雇主以多种形式参与到博士生培养中来[46]。法国则于2016年4月颁布《关于确定博士学位和博士生院作用的裁定》的方案,将博士生教育视为一种“研究型的职业经历”,为社会各行业提供专业人才[47]。即便是最坚持产品质量观的德国,近年来也意识到过于追求原创知识贡献可能与社会相脱离,因此也在模仿美国推进结构化改革。所谓结构化改革,也即将博士生培养过程纳入培养项目、学术中心以及研究生院等组织框架当中,并在博士论文以外提供更系统的能力训练环节。据统计,德国目前就读于结构化培养项目的博士生已达到30%左右[48]。除了欧洲国家以外,譬如日本等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博士生教育改革计划,核心目的均在于通过能力训练,使博士毕业生能更好适应学术界以外的工作[49]。
上述趋势正如2015年《牛津宣言》所提出的那样:“作为新知识、新观点及新方法的创造者,博士学位获得者们卓有智慧、能力非凡且多才多艺,他们能够成功进入宽广的职业生涯,为技能型劳动力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关键,必须受到充分认识和广泛宣扬。”[50]目前各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整体趋势开始从“产品质量观”转向“过程质量观”,更加认识到博士生教育应当是“对未来研究者的训练”而非“一篇增进人类知识的著作”[51],而这恰恰是美国模式所引发的世界潮流。
四、再反思:我國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争议与进路
面对轰轰烈烈、席卷全球的博士生教育评价改革普遍趋势,我国相关政策与研究也将美国模式作为模仿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建立系列评价制度、强调知识应用目标、提倡培养可迁移能力、面向市场雇主需求等等[52]。这一战略趋向,看似遵循了模式光谱中各国转向过程质量观的共同路径。但实质上,我国博士生教育是否到了亟待改革的地步,此改革浪潮是否切中了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真实问题,相应的质量保障文化有无建立健全?这些问题事关我国博士生教育评价的未来走向,亟须进行深入理性的思考和解答。倘若答案为否,那么这种质量评价模式更像是对美国的简单模仿,而非出于博士生教育改革发展的真实诉求。正是基于此,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亟须摆脱片面模仿的路径窠臼,努力摸索出适合国情的新进路。
(一)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热潮具有外生性
如前文所述,世界范围内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运动的兴起,与外部问责环境有着密切关联。正因如此,国外有学者认为:博士生教育目标和实践层面的变化,更多是迫于外界的、非直接的压力[53]。然而不应忽视的是,美国之所以仍在持续推进改革,源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饱和、博士生流失率与延期率过高、各行各业对高层次人才具有迫切需求等等。而欧洲和日本除同样有这些需求外,也有应对博士生教育国际竞争力不足、传统模式不适应性日益凸显等问题的动机。这说明,这些国家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趋向过程质量观,固然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刺激影响,但根本上还是出于本国的内生需求。
那么,这种质量评价浪潮对我国是否存在适切性,我国质量评价改革是否具有内生需求的支撑?不难发现,我国推进博士生教育及其质量评价的改革,核心立论基础多是借鉴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改革经验,但甚少说明原有博士生教育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弊端以及国内呈现出怎样的新需求。举例而言,一方面,从博士生规模满足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我国20世纪末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博士生招生规模迅速从1999年的17 724人增至2020年的116 047人,增幅达到554.74%。但这种规模扩张的背后,动机更多为“建立世界博士生教育大国”“达到美国一样的每万人博士人数占比率”,呈现出一种追赶式发展与补偿式扩张的工具价值取向[54]。但需要考虑的是,我国究竟是否需要这么多博士生,现有的专科、本科和硕士规模是否适应市场需求,如此庞大的博士生规模是否会带来过度教育,与市场对博士的需求又是否匹配?如果这些问题无法得到确证,那么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转向过程质量观,就无法得到市场需求的证据支撑。另一方面,如果倡导过程质量观的评价模式,那么实质上是摒弃或者不主要坚持产品质量观的评价模式。但问题在于,我国博士生教育所承载的原创性知识贡献任务是否已经完成?进言之,目前博士生教育是否已不需要或较少需要进行知识创新?然而回溯国内现实,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仍未得到有力回应,一系列卡脖子创新困境也依然没能破解[55]。
因此,倡导博士生教育拥抱过程质量观、积极面向市场雇主需求,究竟是一种正路还是歧途?对于这一问题,目前仍存在争议,并无明确答案。基于此,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倡导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改革,并未证明是植根于国内内生需求,更像是模仿美国模式的外生路径。
(二)我国博士生教育尚未建立良好的质量保障文化
秉持过程质量观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意味着要接受更多问责,具有更多功利主义特征。显然,这会对博士生教育的学术本质造成一定冲击。而国内学界恰恰忽视的一个前提是:欧美国家之所以能顺利推进这一评价模式,是因为他们的博士生教育具有扎实的学术积淀。
以欧洲为例,一方面,由于长期坚持德国模式,各培养单位对博士生知识原创性的要求仍内嵌于培养模式之中;另一方面,在全球竞争压力和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影响下,博士生教育固然开始转向过程质量观,但这主要发生在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学和学科之中。而由于过往的学术传统,欧洲依然保障了博士生的学术训练水平以及学位论文质量[56]。而在美国,董事会、大学校长与行政部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中枢站”和“缓压器”的角色,承担了外界问责的压力,为底部沉重的院系与学科提供了学术活动的充分自主性。并且,全球人才的虹吸效应,有效保障了博士生培养的师资质量与生源质量,这为美国知识创新与能力训练之间的张力平衡奠定了扎实基础[57]。概言之,欧美国家的博士生教育经历过追求纯粹知识、由学术同行评议的阶段,更多是在学术积淀的基础上实施质量问责、提升人才适应性。
而我国博士生教育自诞生之初,质量评价便带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甚少面对学术共同体与市场的监督与评价压力[58]。虽然以往各种评价,从形式上比较看重博士论文的原创性,近似于德国模式。但由于学术共同体的自主性、自律性并未沉淀与培育起来,系列培养机制也尚未建立健全,人们发现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把关,往往要依靠“把发表若干篇高级别论文与学位授予挂钩”的制度来实现,但这会进一步弱化导师和院系的培养责任[59]。因此,即便是追求知识原创性的产品质量观,似乎也从未有效达成过。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在不具备扎实学术积淀与严格质量保障的前提下,贸然强调博士生教育对市场的适应性,可能会使本就根基不牢的博士生教育更加脆弱、质量更低。
(三)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未来进路
基于以上论述,如果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不加分辨地追随国外趋势,这并不是一个明智、审慎的合理进路。遵从注重能力训练的过程质量观,看似能让我国的博士生教育更具适应性、更具活力,但实则会模糊博士生教育原本清晰的学术边界、侵蚀本就不牢固的学术基础。换言之,当培养知识传播者、转化者和应用者成为博士生教育的主导目标时,从未实现过的知识生产者目标是否会被“弃之不顾”?当对市场雇主的需求满足度成为判断博士生教育价值的核心标尺之时,需长期深耕的学科和专业是否会逐渐萎缩甚至消亡?钻研探索前沿学术领域的博士生,是否会得不到足够重视与支持而消减学术热情、阻碍学术成长?
正是基于此,我们需追问与探讨: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未来进路究竟是什么?我们首先应建立的一个基本认知:产品质量观和过程质量观只存在评价侧重点的差异,两者分别反映了学术创新的本质要求和服务社会的适应需要,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原则上,一个理想的博士生教育评价,应兼具产品质量观和过程质量观,引领博士生既能做出学术创新成果,也能具备社会所需的各项能力。但由于不同国家博士生教育发展阶段与水平存在差异,以及同时强调两种质量观可能会导致培养环节混乱,因而世界各国仍主要秉持某种质量观导向并辅之以另一种质量观作为平衡。基于这个判断,何种质量观、何种模式更适用于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应当根据我国博士生教育实际来灵活调整。在模式选择上,我国不应盲目追随美国模式,简单进行过程质量观的转向。恰恰相反,我国应重新汲取德国模式的有益营养,重塑和强化博士生教育的学术导向,注重学术创新价值追求、学术质量观念引领、学术同行评价制度等,使博士生培养质量评价更具内部驱动力。而在博士生教育具备充分学术积淀之时,再逐渐开始强调市场评价的作用,这就需遵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政府在质量评价的作用需从直接的人财物控制转为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制定政策和发放拨款间接参与博士生教育,给予学术共同体充足的自主性;第二阶段,学术共同体对博士生教育质量的评价扮演主要角色,并以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培养核心抓手,并注重研究原创性的把握;第三阶段,在博士生教育的学术积淀达到一定程度时,开始注重市场雇主的需求,将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理论结合实际等适应市场需求的可迁移性能力作为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标准。这三大阶段属于方向性的要求。
为进一步提升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制度弹性与可行空间,还有必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其一,注重学位类型的差异。学术型博士生的质量评价,更应遵循知识创新的产品质量观;而更倾向于面向市场应用需求的专业型博士生,则相对侧重能力训练的过程质量观。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相关质量保障尚未建立健全,即便专业型博士生培养强调应用性,但不意味着不需要建立在扎实学术基础上,因此也不能忽视学位论文的抓手作用与训练功能。其二,关注学科类型的差异。由于不同学科的知识特征与文化传统各异,博士生规训方式与培养重点及其相应的质量评价也存在显著差异。譬如有国外研究指出,强调理论的学科更注重知识创新的产品质量观,而依赖技术的学科更倾向于能力训练的过程质量观[60]。我国也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理工农医科,人文学科更倾向于认为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关键指标[11](P23)。其三,要逐步建立健全质量保障机制,不仅限于“申请-考核”制、课程“准入-退出”制、“分流-退出”制、职业发展能力提升机制、多元化学术考核机制等等[61]。通过三大阶段与三大举措,最终摸索与构建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式。
五、结语
我国已成为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大国, 但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尤其是学术创新能力仍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62]。采取适当的评价方式以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是未来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然而,追赶不意味着追随,借鉴不代表模仿。全球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改革,均立足于当时、本地的紧迫问题,呈现出国别性和时间性的特点[9](P56)。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梳理全球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兴起、模式与趋势,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在尚未完成扎实的学术积淀时,不可贸然转向强调实用、面向多元需求的过程质量观,而应在坚持学术导向的前提下去满足与适应社会需求。
这一研究结论的得出,是对国家政策与学界倡导的一次重新审思,也呼应了科姆对德国博士生教育趋向美国模式的忧虑:“结构、质量、产出和绩效水准却被学科之外的部门严密地监控着,这些部门有着纯学术之外的动机、意图和目标。这是否会最终影响到研究训练本身,仍然有待观察。如果最终功利主义的观点如此强大,而忽视了关于质量和卓越的学术概念以及由好奇和兴趣所推动的科学研究,那么情况很可能还不如从前。”[45](P74)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国家的语境下,我国博士生教育如何在学术守正创新与满足市场需求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确抉择,科姆的预言颇值得警醒。对我国博士生教育来说,必须保持对学术导向的充分敬畏与坚守,才不至于在世界改革趋势与市场适应浪潮的影响下迷失自我。这也是本研究希冀引发学界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钱颖一.大学的改革(第一卷·学校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648.
[2] De Valero Y F.Depart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ime-to-degree and Completion Rates of Doctoral Students at one Land-grant Research Institution[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1(03):341-367.
[3] 樊成,李北群.“能力修補”还是“能力陷阱”?——欧美博士生可迁移能力培养的争议与逻辑要义[J].大学教育科学,2021(04):86-96.
[4] 陈洪捷,赵世奎,沈文钦,蔡磊砢.中国博士培养质量:成就、问题与对策[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06):40-45.
[5] 许丹东,沈文钦,翟月,陈洪捷.中国博士生的培养现状与问题——基于2021年全国博士毕业生离校反馈调查的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05):73-79.
[6] Malaney G D.Graduate Education as an Area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J].Higher Education: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1988(04):397-454.
[7] 沈文钦,王东芳.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欧美研究生教育研究——一个学术领域的起源与演变[J].教育学术月刊,2018(08):26-37.
[8] 朱宁洁.博士生教育研究中欧比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01):120-124.
[9] 沈文钦,赵世奎.西方博士生教育研究的主题[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12).
[10] Felbinger C L,Holzer M,White J D.The Doctorat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Some Unresolved Qu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9(05):459-464.
[11] 沈文钦,赵世奎.博士质量观及其差异性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所有博士培养单位的调查[J].教育学术月刊,2010(01).
[12] 王传毅,赵世奎.21世纪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八大趋势[J].教育研究,2017(02).
[13] Neumann R,Tan K K.From PhD to Initial Employment:The Doctorate in a Knowledge Economy[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11(05):601-614.
[14] Turner,P.The Generic Skills Debate in Research Higher Degrees[J].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2004(03):375-388.
[15] [德]芭芭拉·M·科姆.通向博士的路径:在精英选拔与规模扩张之间[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02):2-12.
[16] Cosgrove P B.The Nature of Success in Doctoral Education:The Roles of the Student[J].Self 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 in Adult Educational Contexts,2019:1-15.
[17] Sowell R,Bell N,Zhang T.PhD Completion Project:Analysis of Baseline Demographic Data[J].CGS Communicator,2008:1-8.
[18] 曾剑雄,张国栋.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的运行动力及推进策略[J].大学教育科学,2022(02):45-53.
[19] Smallwood S.Doctor Dropout[J].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4(19):A10.
[20] Armstrong J A.Rethinking the Ph.D[J].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4(04):19-22.
[21] Nyquist J D,Woodford B J.Re-envisioning the
Ph.D.:What Concerns to We Have?[M].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0:3.
[22] 陳洪捷.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与博士质量的危机[J].高等教育研究,2010(01):57-63.
[23] Kendall G.The Crisis in Doctoral Education:A Sociological Diagnosis[J].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2002(02):131-141.
[24] 陈洪捷,等.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9-31.
[25] Gerhardt A,Briede U,Mues C.Zur Situation der Doktoranden in Deutschland–Ergebnisse einer bundesweiten Doktorandenbefragung[J].Beitr?ge zur Hochschulforschung,2005(01):74-95.
[26] [美]威廉·克拉克.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M].徐震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44.
[27] Gymnich M,Stedman G.Doktorandenbetreuung:Betreuungsmodelle und Qualit?tskriterien[M].Handbuch Promotion:JB Metzler,Stuttgart,2007:78-91.
[28] Van der Heide A,Rufas A,Supper A.Doctoral Dissertation Defenses:Performing Ambiguity between Ceremony and Assessment[J].Science as Culture,2016(04):473-495.
[29] Berelson B.From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61(05):25-29.
[30] LaPidus J B.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J].In Defense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001.
[31] Kehm B M,Teichler U.Doctoral Education and Labor Market:Policy Questions and Data Needs[M].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bor Force.Springer,Cham,2016:11-29.
[32] 戚兴华.绩效与公平:美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价值取向探析[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9(04):29-34.
[33] Van Raan A F J.Sleeping Beauties in Science[J].Sci
-entometrics,2004(03):467-472.
[34] Mullins G,Kiley M.It's a PhD,Not a Nobel Prize:
How Experienced Examiners Assess Research Theses[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02(04):369-386.
[35]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5.
[36] Kehm B M.Developing Doctoral Degrees and Qualifications in Europe:Good Practice and Issues of Concern a Comparative Analysis[J].Studies on Higher Education,2004(06):10-33.
[37] 岳英.重识博士论文的价值危机:知识、技术与权力[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01):2-14,186.
[38]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Pathways through
Graduate School and into Careers[M].Princeton.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2012:31-33.
[39] 赵祥辉,王洪才.博士生“申请—考核”制的典型模式、特征与启示——以柏林洪堡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为考察中心[J].现代大学教育,2022(01):52-59.
[40] 包水梅.美国学术型博士生课程建设的特征与路径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16(01):116-124.
[41] 杨青.美国一流大学博士生分流淘汰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启示——以康奈尔大学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19(10):91-98.
[42] [美]阿特巴赫.美国博士教育的现状与问题[J].别敦荣,陈丽,译.教育研究,2004(06):34-41.
[43] Slaughter S,Leslie L L.Academic Capitalism:Politi-cs,Policies,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209.
[44] Boud D,Lee A.Changing Practices in Doctoral Education[M].London:Routledge,2009:3.
[45] [德]芭芭拉·M·科姆,朱知翔.博士生教育去向何方?——全球變化背景下欧洲的新举措[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04).
[46] 褚艾晶.以雇主需求为导向的英国博士生教育改革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05):69-73.
[47] 高迎爽,郑浩.法国博士生教育职业化改革:逻辑、措施与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12):67-72.
[48] 巫锐,秦琳.新世纪德国大学博士生教育改革的行动逻辑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20(03):106-112.
[49] 陈兴德,陈凤菊.卓越大学院计划:着眼“世界一流”的日本博士生教育改革[J].大学教育科学,2021(04):97-104.
[50] UK Council for Graduate Education.The Oxford Statement[EB/OL].[2022-06-25].http://www.ukcge.ac.uk/.
[51] Allen-Collinson J.Professionally Trained Resear
-chers?Expectations of Competence in Doctoral Research Training[J].Higher Education Review,1998(01):59-67.
[52] 秦琳.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逻辑、目标与路向——知识生产转型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9(10):81-90.
[53] Kehm B M.Doctoral Education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A Comparative Analysis[J].Wenner Gren International Series,2006:67-78.
[54] 赵祥辉,陈迎红.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变化、争论与进路[J].高教探索,2021(08):43-49.
[55] 马戎.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博士生培养体制应当如何改进[J].社会科学战线,2016(12):223-241.
[56] Bao Y,Kehm B M,Ma Y.From Product to Process:The Reform of Doctoral Education in Europe and
China[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18(03):524-541.
[57] Nerad M.Doctoral Education in the USA[J].The Doctorate Worldwide,2007:133-140.
[58] 刘泽文,罗英姿.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沿革与启示[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0(02):68-73.
[59] 赵祥辉.博士生发表制度的“内卷化”:表征、机理与矫治[J].高校教育管理,2021(03):104-113.
[60] Hockey J.Change and the Social Science PhD:SupervisorsResponses[J].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1995(02):195-206.
[61] 汪霞.高质量的博士生教育还需要完善哪些培养制度[J].中国高教研究,2020(06):9-12.
[62] 王传毅,杨佳乐,辜刘建.博士生培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的实证分析[J].宏观质量研究,2020(01):69-80.
Re-examination of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Doctoral Education: Patterns, Trends, and Controversies
ZHAO Xiang-hui
Abstract: The doctoral educ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stems from social accountability,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enrollment sca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and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of new management.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two typical models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global doctoral education: one was the German mode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oduct quality, focusing o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adhering to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While the other is the American mode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ocess quality, focusing on ability training, and adhering to structured training. Other countries remain distributed between the continuous spectrum of these two models. In recent years, as the German model's original standards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have been gradually questioned, the high-efficiency advantage of the American model in talent training has begun to be favored,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doctoral educ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has generally shifted towards the concept of process quality. However, China's doctoral education started late, academic accumulation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s not perfect, hardly imitating the American model that emphasizes practical utility, and its diversified needs may lead to a further decline in quality. To this end, the future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doctor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to emphasize meeting and adapting to social needs based on reshaping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exploring and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s: doctoral educ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scale expansion; knowledge innovation; ability training
(責任编辑 陈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