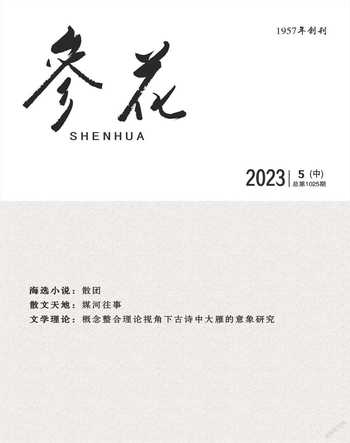地域文化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
迟子建是中国当代文坛上较有独异性的作家,素有“极地之女”称号的她,用笔描绘了那片生养她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事悲欢。自踏入文坛以来,迟子建就不厌其烦地书写记忆中的东北往事,在多部作品中展示了白雪、黑水、林海等自然风光,也为读者生动地讲述了东北多样化的民情风俗。似乎可以这样说,东北这片黑土地养育了迟子建,也在无形中成就了她的写作,使得她的作品总是弥漫着浓郁的东北乡土气息,读来素朴自然。文学地理学是近年来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一个前沿学科。一般来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作家所在地理位置及自然地理特征的关系。地域文化,简言之就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闪现在迟子建作品中的地域文化无疑是东北的黑土地文化。如果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迟子建的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等于是探讨东北黑土地文化与迟子建的关系及对其创作的影响,总结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东北大地的自然风光
东北文化也被称为“关东文化”或“黑土地文化”。东北文化是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共同积累下来的文化。这种黑土地文化放到迟子建的作品中谈,就是其中或隐或显的东北气息,弥散着迟子建独特的童年记忆和生活经验。迟子建出生在东北漠河,黑龙江畔的木刻楞房子养育她成长。她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北极村童话》即以她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借用儿童视角,为读者介绍北极村的生活,温暖又略带感伤。作为地地道道的东北人,迟子建热衷于描绘家乡的自然风光,小即一草一木,大则一江一山,无不尽收眼底,用唯美的文字呈现出来。无论是东北年年一见的白雪,还是北极村的极光,抑或是流淌不息的河流,都透露着东北味道。
(一)白雪
雪,是东北最有特点的意象。它既不同于南国的雪那么湿润,也不像北方其他省份的雪那么脆弱。像对家乡的眷恋一样,迟子建对雪也有数不尽的情怀。在《白雪的墓园》中,父亲去世,几个孩子埋葬父亲并隐瞒了母亲,没有说墓园的具体位置,结尾在漫天大雪中,母亲找到父亲的墓园进行祭奠后,卸掉一切重负似的为大家做了饭,白雪除了纯白柔美,也寄托了孩子对父亲的追思、母亲对丈夫的不舍与释然。似乎所有的不幸与痛苦都随着一场大雪被掩埋进了尘埃里,生者借白雪再次走回现实生活中。《朋友们来看雪吧》透过写胡达老人的光辉一生,进而邀请“我”的朋友到乌回镇看雪。那里的雪洁白无瑕,虽然美,但是实在是影响交通,又因为胡达老人已经不在了,如若被雪围在塔城,不会再有人接站了。散文《我的世界下雪了》中的雪轻柔可爱,如“落雪的天气通常是比较温暖的,好像雪花用它柔弱的身体抵挡了寒流”,寥寥几笔,回忆了“我”与爱人早年在雪中漫步的场景,并借此怀念已故的爱人。迟子建笔下的雪是可爱的,有着时间前后的差别,同时,也是温暖的,它有着北国独特的味道。久别家乡的游子常常把对家乡的思念寄托在漫天白雪中,让这北国的精灵带来故乡的记忆,在白雪中感受属于黑土地别样的温度。
(二)极光
迟子建素有“极地之女”的雅称,这个称号与其家乡漠河县有很深的渊源,因为家乡地处整个中国的最北边,距离北极圈很近,因此,极光对她来说也是熟悉的景致。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极光听起来有一种神秘感,白夜的到来也让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异常欣喜。《北极村童话》中,迟子建以儿童视角倾听奶奶讲白夜,“夏至时,在漠河,可以看到北极光。拿一小片玻璃碴,把它浸入水中,可以看到好多色彩”。最终,“我”在离开北极村之时,见到了五彩斑斓的极光。《假如鱼也生有翅膀》中也写道:“每逢夏至到来,白夜就降临了。天色在午夜时分仍很清朗,你甚至能辨别出落在花圃上的蝴蝶。白夜就像新嫁娘一样容光焕发,那洒满了阳光的路,宛若它拖曳下来的洁白的婚纱一样,令童年的我欢喜不已。”奇异的自然景象给这片黑土地蒙上一层神秘感,令读者愿闻其详,品味独属于迟子建的美妙记忆。
(三)河流
黑龙江省的河流也许并不算多,但都比较有名,比如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迟子建早年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就非常典型地写到了很多河流,借由河流,尤其是额尔古纳河,讲述了沿着河流生活的鄂温克族人的生死悲欢。《逝川》中在江边生活的人们都喜欢在“鱼汛期”捕泪鱼再放生,以求福,在江水的滋养下,他们热爱生活、生生不息。《烟火漫卷》写松花江的开江一般出现在清明前后。滚滚而来的江水冲破冰排,释放了积攒一个冬天的活力,那壮观的场景让人震撼。此外,迟子建还写了很多其他河流,河流不倦地奔涌前进,正如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体现向上的昂扬态度。北国风貌在迟子建的笔下熠熠生辉,那一城一地、一草一木仿佛早已融进迟子建的生命。读者跟随着生动的文字,领略独属于东北的自然风光。极光、白雪与河流,读者仿佛亲自在东北黑土地上游历了一番,更加敬畏黑土地上的一切自然风貌,对其充满礼赞。
二、古老东北的民情风俗
民情风俗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人的生活状态,迟子建的作品中出现的是东北大地的民情风俗。古老的东北黑土地不仅孕育了任劳任怨的一代农民,而且经由这些劳动人民,发展出了许多有关饮食、节日等方面的礼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民情风俗仍历久弥新,迟子建深恋故土,不厌其烦地用多种文学样式来为读者呈现别样的东北风情。
(一)饮食
迟子建的家乡及后来定居的哈尔滨多处临江,所以在她看来,吃鱼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白银那》中突然而至的鱼汛,给村子里的人民带来很大的惊喜,每个人都兴奋极了。《逝川》里的吉喜老人从小就爱吃鱼生,在逝川边居住的人们以打鱼为生,捕捉泪鱼是为了祈福,除此之外,捕鱼都是为填饱肚子。《树下》中的多米则更喜欢吃蒸鱼子。《烟火漫卷》中,刘建国每逢送人到黑河,必吃江畔小馆子的酱焖杂鱼,用白鱼、草根、花翅等鱼加大酱细火慢炖,极其美味。东北河流不多,但流域广,因此,东北人经常和鱼打交道,吃鱼也就再平常不过了。
此外,咸菜和干菜这两样最不起眼的小菜却是东北人青睐的对象。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东北的冬天寒冷干燥,很多食物、蔬菜不便于储藏,加上人需要盐分补充体内能量,聰明的东北人便早早在秋季就腌好咸菜、晾晒好一些蔬菜干等做提前准备。《北方的盐》就向读者讲述了东北人腌菜的一些情况:“家庭主妇们还把新鲜的豆角、辣椒、芹菜、黄瓜、萝卜、芥菜等等塞进形形色色的缸里,撒上一层又一层的盐,做成咸菜,以备冬季食用。”还有东北人赞不绝口的东北酸菜、糖蒜、蘑菇干、豆角干等。北风呼啸,一代又一代的东北人在黑土地上认真生活,孕育了独特的过冬菜品文化。
东北出产的蔬菜样式不算特别多,所以土豆往往成了人们倾心的对象。《亲亲土豆》更是直接以土豆作为题目,用一个夫妻间感人的小故事带出了礼镇家家户户都爱吃土豆的事实,甚至最后秦山去世也是用土豆作为坟安葬的,读来有一股浓浓的温馨感。迟子建曾这样写“吃土豆”:“吃土豆的名堂大得很,蒸、煮、烤、炸、炒、调汤等等,花样繁杂得像新娘子袖口上的流苏”。多种吃法浸润着东北人的劳动智慧,《雾月牛栏》中的宝坠最喜欢吃饼卷土豆丝,《逝川》中的老吉喜除了喜欢吃生鱼,还喜欢在炉子上烤土豆。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说土豆与粉丝是常见的配菜,因为价格便宜且吸收汤汁,口感柔韧。可见,土豆是东北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东北人最为赞叹的一味佳肴食材。
(二)住房
前文已经提到,迟子建从小生长在木刻楞的房子里,其实东北的居住房并非只有这一种,还有鄂温克族的希楞柱、汉族的板夹泥砖房以及一些俄式建筑,这些五花八门的建筑共同构成了迟子建创作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成为东北的活广告,在作品中大放异彩。首先就是迟子建的家乡——北极村中典型的俄式建筑木刻楞房子。北极村毗邻俄罗斯,因此,一些饮食服饰,甚至居住文化等都与俄罗斯极为相似,木刻楞原本是俄罗斯专用的住房,因地理原因,北极村的房子几乎都是木刻楞。其次,还有一种现在不多见的希楞柱出现在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据说是鄂温克族人居住的窝棚式房屋。“三十几根一端削尖头、一端平面的松杆,排列组合成一个圆圈,外面还要罩上能够挡风的动物皮围子,希楞柱就这样建造成功了。老一辈人之所以如此离不开希楞柱,是因为鄂伦春人民在建造的时候往往在顶端留有一个能够看见天空的小孔,白天阳光普照,夜晚星星眨眼。虽然从小孔里面看到的星星也没有几颗,但却显得异常明亮,有如夜晚中的明灯一般。”简单朴素的希楞柱融汇着鄂温克族人的智慧,虽然不比现代房屋避寒效果好,但是透露着和谐与温馨。最后一种几乎就是现代房屋了,板夹泥房屋,也即迟子建家乡永安镇房屋的原型。这种房屋很适合东北人居住,房屋较低,窗子也相对矮,屋内的标配是火炕、火墙、锅炉,取暖做饭非常方便。而且邻居之间距离很近,《原始风景》就描画了在板泥房中与邻居的互动关系,“我母亲在阳光下淘米的时候,另外两户的女主人也在淘米”,将东北人做饭的日常氛围渲染得轻松愉快。
(三)节日礼俗
东北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别具一格的民俗文化自然也是一道风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其中的人物相信山神、熊神等,并以敬畏之心为人处事。而汉族人逢年过节的礼俗更是繁多。在《秧歌》中,迟子建细致描绘了东北人正月十五看秧歌戏的习惯,大家争先恐后地看戏,抢不到前位的,还可以看各式各样的花灯。《清水洗尘》介绍了东北人过年“洗尘”的习俗,“礼镇的人把腊月二十七定为放水的日子”,即洗澡洗一切脏东西。寓意新的一年要干干净净,除去一切污秽。东北民间有“二十七,洗福禄”的说法,所以“洗尘”也带有祈求新年平安多福的意思。年在南方意味着春天到来,然而在北方,尤其是东北,等于还有至少两三个月才能窥见春天的脚步。如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说:“年在南方是春的代名词,而在寒流依然占领统治地位的哈尔滨却是雪骨冰心。无论是公园还是街市,冰灯雪雕随处可见。”为了庆祝新年,榆樱院的住户也早早起来造冰灯、制雪雕,借此祈求喜气。此外还有正月初七“人日子”吃面条,二月二吃猪头肉、剃龙头,七月十五放河灯,等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东北多民族、多人群的民情风俗,成就了迟子建的乡土系列文学,她心系家乡,念念不忘。家乡的种种风情透过她的妙语出现,增强了黑土地的特色与读者的体验感,深化了东北地域的文化内涵。
三、魅力无限的东北方言
东北方言无疑是进入东北文学和了解东北文化最便利的一把钥匙。说到东北方言,读者内心一定会涌现搞笑的词汇和口音。迟子建将这些外省读者看不懂、听来搞笑气十足的日常口语应用在了作品中,风趣幽默又显平易近人。实际上,迟子建极善用古典文學的“雅”来写作,又结合自身经历,融进了东北方言的“俗”,她的作品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作为东北作家,迟子建很喜欢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将东北生活完整地呈现出来,不仅包括大量的方言词汇,也有一些东北民谚俚语。如在《北极村童话》中,迎灯小时候在姥姥家“猫冬”,感觉冷的时候,喜欢躲在姥姥的“胳肢窝下”。他们把香皂叫作“香胰子”,小坑儿一般叫“小洼兜”,蒸的馒头是“暄腾腾”的;《白雪乌鸦》中指明“耗子”是东北人对“老鼠”的地方性叫法;还有《亲亲土豆》中的“土豆栽子”,等等。还有《北极村童话》中的“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八月十五。杀猪、宰羊,气得蛤蟆直哭”等民谚语或自创性歇后语。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在东北,形容一个人聪明,会用“奸”;形容人体格健壮,一般用“瓷实”或“结实”;程度深,多用“贼拉”“嘎嘎”这种生动的词汇。阅读迟子建的作品,会发现很多东北方言被纯熟地应用于其间,这样充满泥土气息的文字也传达出东北人生动的日常生活状态,不仅显示了东北本色,也成为迟子建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语言特色。
四、结语
迟子建作为东北作家的一员,非常了解东北的地域文化,如果说萧红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描绘东北小城的女作家,那么迟子建就是接续萧红,将东北文化用文学的形式发扬光大的典型作家。同时,相对于萧红、萧军这类东北作家群作家对古老中国东北大地上多灾多难的东北人民生活的描写,迟子建更多描绘了东北土地上安详和谐的草木人事。迟子建倾向于把家乡及东北整个地搬到文坛上展示,赞美家乡。地域文化在迟子建身上的浸染,读者无从得知,但是透过她温暖的文字,读者能在头脑中构造一个想象的、最接近现实的东北世界。在今天,很多人向往慢节奏的生活,迟子建恰好用东北文化建造了一个宁静的世外桃源,那里不仅有无穷无尽的东北文化传统,也有人们一直追求的自在独行的闲适感。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杜东妮.迟子建作品中的东北民俗文化探究[D].淮北师范大学,2020.
[3]宿博涵,刘淑梅.黑龙江地域文化对迟子建文学作品的渗透[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5(23):211-213.
[4]唐红新.论迟子建小说的地域文化书写及其意义[D].兰州大学,2010.
[5]刘潇.迟子建小说创作的文化视角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4.
[6]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7]迟子建.烟火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8]迟子建.炖马靴:短篇小说30年精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曲镜丹,女,本科在读,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王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