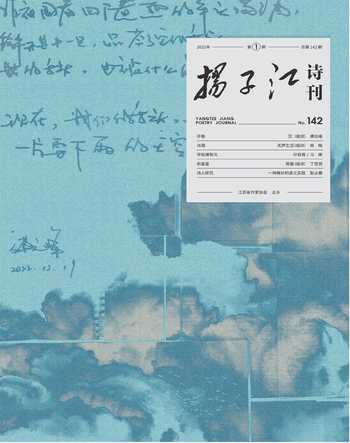诗和舞台
韦锦
一
有时候,一些自以为没必要回答的问题,会内化于写作中。有的以清醒的意识和你的写作方向、意趣、持守浑然一致,另一些则一直作为问题发挥潜在的作用,以非自觉的方式置你于被动。当然,这被动在好多情况下未必是坏事。对一些问题的不求确解可能恰好使人避开束缚。但这仍不能作为对许多问题避而不答的理由。一个诗人可以不按套路说话,但不该自认为有无视问题的权利。
比如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从事戏剧工作对诗歌创作有何影响?这样的问题原以为清楚,但实际未必。上世纪70年代末,中学阶段迷恋写诗。可那是我写诗的开端吗?那时写出的文字和对诗的痴迷有关,但不知距诗有多远。痴迷可让人走近痴迷的对象,有时也会悖反。细想之后,之所以还愿意视之为起点,因为那种痴情的程度属于诗。数十年来,这种痴迷不曾中断。幸运的是,诗神在大多情况下未对这痴迷表示厌弃和拒斥。尤其在迷恋戏剧并对之投入较多精力后,诗的容颜在我眼中反而更切近、更清晰。是诗让人在非诗的领域也和它频频相遇。
迷恋戏剧,是和迷恋写诗难分彼此的一回事。说是迷恋写诗的自然结果也行。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不短的时期,我热衷于把诗写长。《深肤色的女子》《趁耳朵还能听见雷声》《转向或阿兰之歌》《口吃的狐狸》,写了一首又一首。心里似乎有一团团抖不完的线球。直到写出《蜥蜴场的春天》,忽有所悟似的决定不写长诗了。觉得长诗结构是个难题。明面上的抒情很容易浮泛。不像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它们都有隐性的结构在支撑。那种宗教的、文化的东西给了作品足够的景深。所以尝试写诗剧。从《楼和兰》《田横》起,有意识避开现代、后现代戏剧的一些套路,尽量少玩理念,不玩理念,而特意讲究叙事风格的传统性。在情节线索结构、人物关系结构、情感矛盾结构的设置和推进中,构建戏剧的张力系统,让叙事、抒情有所附丽,避免空对空的惯性和随意。与此同时,未曾间断的抒情诗写作也有了突出自身特征的主动,开始着力于提取素材、题材中的戏剧性要素,以形成结构性张力和冲击力。这样写,打破抒情和叙事的界限,甚至也打破了诗和戏剧的界限,在我近年来陆续发表的《分行的散文》中有一定体现。
同时,对什么样的诗是好诗,好诗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思考时也越来越有意识地着眼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具体说就是,在我心目中,好诗在外表上不一定很像诗,但也不能让人觉得不是诗。诗的语言要有节奏、有韵律,但节奏、韵律是否都要通过格律等技法来实现,就不一定。如果不对仗、不押韵、不合规制还能有内在的音乐性,那在语言表达的层面上说就是好诗。就像无调性音乐,不按固定的调式体例来写,却还能充满音乐性,形成迷人的语音织体。新诗在形式上,劣势化为优势的可能,或就体现在这里。从内在的诗意、诗性的角度说,我欣赏的好诗可能不符合超现实或后现代等标准,也有别于其它传统意义上的界定。(布勒东和阿多诺,都是我视野里的灯火和星光,但从不是需要恪守的信条的制定者。)它不是简单的平面化、碎片化呈现,也不是严格的轻质叙事和零度写作。着眼于世界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又关注日益加重的破损和断裂。尽可能减少虚妄和过度浪漫。清醒又不摆看破一切的架子。冷热轻重都取决于生存情状和心灵情态在诗中生成的需求。反抒情是因为有假抒情,就像当年反崇高是由于有太多让受众厌恶的假崇高。总的来说,说得直白些,诗的语言不是不需要,而是太需要音乐性,那种内在流动的音乐性;在诗意诗性上,不是不需要,而是太需要感情和思想,那种有思想的感情和有感情的思想。那些和自己、和周围人的呼吸有关,和族群的存亡绝续有关,和人类前景的泥泞、艰难有关的东西,有时会像冰一样凉,有时又像烧红的铁一样热。在任何地域、任何时候,诗人都不该是冷血动物。即使在日常的繁琐和俗杂中,也不能以看似豁达的麻木和颓唐自得。那同样会给人假模假样的感觉。因此,不贫血的诗,我认作好诗。这既指外表上的不苍白,又指内在蕴涵的不稀薄。另外,不指望会有那样一种诗,从里到外是全新的,让人打眼一看有横空出世的感觉。作为一个置身传统又立足现代的创作者和欣赏者,我从个体的角度这样期待并指认那些不坏的诗、比较好的诗:它可能仅仅在靠近人性、揭示人性时比此前的文字更透彻一点;也可能仅仅在哭诉人类困境时更深切一点;或者在表达世界的美妙时,表达得更新鲜更神奇一点。有时候,仅那一点就让人兴奋。
二
基于上述一些认知,我对诗歌和舞台剧在当下是否属于边缘领域,以及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化环境时,便在紧迫之外少了些匆忙。老实说,因为了解得少、不全面,觉得诗歌现状还挺不错。网络诗坛很热闹,纸质诗刊很从容。常常有年轻朋友把我的诗编发到他们的个人平台上,也年年有一两家纸刊发我一两组诗。或者说,有热闹的地方去,有清静的地方呆。真的挺好。诗本来就这个样子,无所谓边缘不边缘。即使在发达的唐朝,写诗成了晋身的台阶,大多情况下,诗也主要是诗人间的事,和大众的娱乐及其精神世界关联不大。今天,信息时代,诗与大众的关系已切近得多。许多年轻人,生活在不同层面上,却能拥有各自的平台和较为自由的写作、展示空间,作品水准让我时感佩服。我相信,在那深水中,一定有一些大家伙在慢慢长成。我对新诗的未来少有悲观的理由。
舞台剧的发展受产业化等多种因素制约,现阶段面临着瓶颈。迎合出品者旨趣和口味,但无法满足多方面需求的剧目多,票房和艺术兼具、有针对性和较高精神质地的东西少。这种局面的突破,需具备好多因素。诗歌和舞台剧联手,彼此合作扩大影响力,获得更多关注和认可,也是很重要的方面。诗人朋友要对戏剧的价值和意义多些思量。伏尔泰说,一个有戏剧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刘楠祺的翻译是“有前途的”)。试想一群有各种差异的人,在同一时刻,同一屋檐下,为同一个故事里的人物命运忧喜焦急,或心潮起伏,或扼腕叹息,那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场,和各自呆在网格里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样的场和诗所形成的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同向和同质。所以建议诗人朋友们时不时也去剧场泡泡。从另一个角度说,要争取让从事戏剧的朋友不小看诗人,不把网络上乃至冠冕堂皇的纸刊上,一些闹着玩儿的东西当成诗的典范。这一点本来并不难,过去曾有不止一个时期,文学和戏剧彼此借重,互增優势。典型的例子如诗人霍夫曼斯塔尔与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互相促发,使《玫瑰骑士》《失去影子的女人》《埃及的海伦娜》等在世界歌剧舞台上常演不衰、光彩熠熠。而《俄狄浦斯王》《埃莱克特拉》《猫》《茶花女》《卡门》《佩里亚斯和梅丽桑德》《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布兰诗篇》《古雷之歌》《浮士德》等数不胜数的歌剧作品或康塔塔,大多是与诗、诗剧、小说结合的杰作。《猫》若不是韦伯改编成音乐剧,恐怕也没有今天的知名度,尽管它是获过诺奖的大诗人艾略特的大作。《布兰诗篇》《古雷之歌》这些组诗和长诗在世界范围内的重光和流传,都与音乐的加入极其相关。所以说,只要不把对方放在受鄙视的位置,写作者努力让作品充满诗意和戏剧性,作曲、导演又能敏锐发现这诗意和戏剧性,对文学和戏剧便都有好处。
现在写诗剧的朋友不少,据我有限的阅读,许多是非常好的案头剧,但少有着眼于舞台和受众的剧本。戏剧尤其歌剧是综合性艺术、受限的艺术。在舞台上,空间、时间,都是被限定的。诗人的文字在时空的双向和多向延展上,原有的自由度在此要有节制。如何正视限制、接受限制,须做一些专业知识上的了解。这些都不难,难的是如何发挥储藏已久的潜质,写出和一般“行活”不一样的东西。那会给人跨界的惊喜。元杂剧曾兴盛一时,有人说这和文人士子混迹梨园有关。随着科举的恢复,这类人撤出梨园重回仕途,戏剧制作(不含后来的话剧)在人才资源上开始衰竭,经由明清一步步向简易化、模板化、过度娱乐化蜕变。动作程式化和唱腔的固化,使形式板结,内容浅平,既成范式也成枷锁。设置噱头多靠花样翻新。艺术品位无底线下滑。编剧沦为打杂,作词沦为填词。板腔体的套路实用、好用,然难避简陋,难免僵滞。剧本创作本身的独立价值渐渐不存。说来说去,这未必是戏剧本身的问题。我宁愿把这种趋势称作非诗化和反诗化导致的必然塌陷。这就需要新的力量不断从外部冲入。近年来,中国舞台上“歌剧热”占尽风头,方兴未艾。这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艺术的要求在逐步提高,审美需求正从单一化、平面化向综合化、立体化转变。原有的剧作者队伍已不能满足需求。但愿有更多的诗人朋友感受到这种需求。诗人的想象力、情感的强度、对独特性的热衷和挑战极限的勇气,以及驾驭语言、营造意象、塑造个性的能力,都是打造舞台作品不可或缺的特质和要素,是诗人们独具的优势。自16世纪末诗人里努契尼编创第一部歌剧《达芙妮》至今,诗和诗人在歌剧史上发挥的作用一直举足轻重。我期望,诗和歌剧的融合能获得越来越宽敞的空间,诗人戏剧或戏剧诗人能拥有双引擎动力,给综合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大的可能,同时也让诗的园囿连接上更开阔的场域。
三
跨界曾让我深有感触。在参与创作歌剧《马可·波罗》的过程中,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存在于人类之间的共同、共通的诗性。歌剧《马可·波罗》从好多方面说是跨界融合的产物。故事原型、舞台形象,都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下诞生的。歌剧制作团队的构成也是如此。作曲家、导演、舞美、服饰、灯光,以及首演时主要角色的扮演者,都来自国外;指挥家汤沐海是德籍华裔,有长期跨境求学、演出的经历和阅历。在这样的团队中,只有我本人没有一点国际化背景。但本人的参与,也有一定程度的跨界意味。此前,尽管有几部诗剧作品,但自认还仅仅是一个诗歌界的写作者。当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筹划首部原创歌剧时,推广古典音乐及西洋歌剧艺术的乐评家,也是诗歌爱好者和关注者的刘雪枫先生,向当时的董事长张宇推荐了我。张宇先生和刘雪枫先生一样,对诗歌的了解也非常多。他有时会脱口而出,背诵当代诗人的作品。对诗和诗人的爱重可见一斑。因此说,在我这个业外生手和多个行家里手之间,选择我来创作一部带有实验性质的歌剧作品,和那种对诗歌持有期许的眼神有很大关联。而且,在后来反复打磨的过程中,唐晓渡、李琦、王自亮、沈苇、孙晓军等诗人朋友,以及剧作家罗怀臻、作曲家雷蕾、文化学者王洪波、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专家陈桂秋,给我提供的助力和加持,更印证了跨界合作的有益和有效。没有诗歌和来自多个领域的援手,《马可·波罗》会是另一番模样。
前后五年多的不断修改完善,给了我许多体验与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对文化融合必要性的认知不断深入。人类之间共同和共通的东西其实很多,少的是发现和珍视。尤其在今天,致力于此,中国诗人更是义不容辞。我在剧中借文天祥之口唱出的,也许代表了不止一人对人类文明愿景的祈颂,其中的诗意想必无分古今和中外:“终有一天,人有人的尊严。/自己的幸福不导致别人的厄运,/自家的宫殿不赶走别人的房檐。/年年岁岁,春归的脚步如期而至,/繁花像爆竹响遍枝头,/和平成为酒浆,丝绸,无边的桑田。/啊终有一天,终有一天,/羡慕不引发侵扰,拳头不怂恿贪婪。/爱自己的山河,也珍惜别人的江山。/让自己有未来,也让别人有明天。”这一段咏叹调,国内演出时赢得一次次掌声,意大利巡演时也被掌声一次次打断。在歌剧演出中,这样的“违规”是不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所谓南北,无所谓东西。
歌剧首先是诗剧。唱词是剧诗。词非诗之余。就像宋词不是唐诗的尾巴。宋词是诗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歌剧语言和诗的语言唯一的区别应该只在接受音乐性限制这一点上。而接受音乐性限制的结果,不是让它变轻、变白、变俗,而是更受控、更凝练、更具象。它要有诗性,那是语词和修辞与日常性的对应和对峙,是表达方式、呈现效果和现实之间距离的拉开及确认,是让语言本身具有审美价值。它作为戏剧的要素之一自然要有戏剧性,那是除了词语搭配的反常和超常,还有情景指涉、速度切换和跳跃幅度的出人意料。而它的音乐性則着眼于语音、语感和节奏,是声韵的色彩、明暗、清浊、强弱形成的语音织体。
其实,这未尝不是一个诗人在抒情诗写作上也该接受的限制和成全。甚至未必不是对口语化写作的另一种呼应。口语化是珍视声音而非放弃声音。我心中一个久未显形的意识日渐清晰:诗剧和歌剧不过是诗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马可·波罗》序幕部分有一节咏叹,是主人公对东方的回忆和遐想:“我想念的中国,在遥远的东方。/那绚丽的火把,饱满的粮仓。/辽阔的疆域,辽阔的富饶。/炊烟提着村庄上升,城市在星空下喧嚣。/笙歌缭绕,玉楼吹箫。/征人在征途回首,美人在月下远眺。/那是天堂的郊区,春风的驿站。/鸟鸣传递花香,云擦亮蓝天。”“提着”“传递”“擦亮”等动词,利用视听通感、主客错位等技艺,让炊烟和村庄、鸟鸣和花香、云和蓝天发生本不具备的关联,让戏剧性在逸出惯性的词语间次第呈现。而“绚丽”修饰“火把”、“饱满”修饰“粮仓”、“辽阔”修饰“富饶”,则用反常的词语搭配使语言更加具象。
歌剧写作让我把关注语言的难度系数,具体体现在对接受主体感知可能性的观照上。由此再反过来发力,自许由笔尖到口唇,由案头欣赏到诵读及吟唱,诗理应经得起眼睛和耳朵的双重打量。“街灯亮,西域夜未央。/霜华重,飞蛾敲窗。/唐时明月照影处,/汉家女子,且把他乡作故乡。/彩云在江南,/曼舞轻歌,自有莲荷香。/金波淡,玉绳转,/非鸿非燕,溢彩流光。/请君看,月迷中原,风吹钱塘。”这是马可·波罗与大宋女子传云初见,传云且歌且舞的咏唱。既想彰显宋词的典雅、优美,又想去除酸腐气息,故注重意象的自然和节奏的流畅,并在用韵上有所讲究。整段通押江阳辙,中间采用稍微随意的交韵法辅以言前辙,明亮和清远交替,幽怨和期许错落。汉语声韵在色彩丰富上具有的魅力,诗人在今天不能一概忽视。
四
诗人借由歌剧也许可以在体味先锋性和世界性时,既保持锐度和宽度,又尽力达到不偏狭和不空泛,从而让创作领域得以拓展。歌剧《马可·波罗》在大背景真实的前提下悬空写作,先是要塑造一个合乎文明演进向度的戏剧形象,让长期以来脸谱固化且符号化的旅行家、旁观者,成為见证者和参与者,让他置身不同文明形态的冲突中,与各种人物发生关系,在爱恨情仇中重获血肉和体温。他和传云的相识相爱,与文天祥的数度交锋,乃是文明的自省和互为镜鉴,体现着历史人物的恒久魅力和现代价值。对传云的塑造与之相应。有网友称,传云的光彩过分夺目,此剧应改名《传云传》。愚以为,传云和马可·波罗,二者形象的起伏上升是紧密的正相关。作为大宋派到西域试图阻止马可·波罗一行与蒙元合作的美女杀手,她身怀绝技,情义满腔,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她再三劝说马可·波罗改变行程到大宋,劝说未果,两人拔剑决斗,在把对方打翻在地剑指咽喉时,又无法下手,唱出了“我怎能得不到就把他杀掉”的咏叹。而那时以至今天,多少人心理恰好相反,只要自己得不到就千方百计毁掉。许多悲剧即根源于此。传云的抉择体现出我们的文明另有枢机,对生命、对美好事物的珍重,会适时触动心弦,促发颖悟。在传云眼中,马可·波罗单纯、英俊、热爱和平,是“闯进暗夜的灯火”,是光停住心灵的黑,是她生命嬗变的触媒和动力。这种东西,和种族、地域,和其归附的组织不相混淆,有单独的价值和意义。为此,在最后关头,在依命行事和遵从内心驱引的两难处境,她在唱出“能不能得到,都不能毁掉”后,宁可杀死自己,也不伤害对方。正是因此,在尾声中,参与海战被俘入狱的马可·波罗,才会怀着对传云的思念及对东方的眷恋完成行记。全剧在马可·波罗“遇见你时失去你/失去你时拥有你/你的手在我手中/你的心在我心上/我的心连着那东方/你就是我的东方”的咏唱中结束。剧场里的人们或许会由此看到,有一群东方人,他们不是只会记仇,或只会记着自己对别人的好;他们欣赏别人的好,并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好。他们以自身的良善,不断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向往。那样的良善,是文明激荡的浪花,也是文明不致断流的泉源。这是一个中国诗人抛却诸多纷扰敞开心怀,想尽量不自卑,也不自大;想尽量让置身其中的文化与人类的精神家园同构,在抱持愿景冲决壁垒的进程中同向同步。
而在声乐套曲《万里长沙》中,我则表达了与之相应的另一种期望,即通过揭示屈原、贾谊、谭嗣同、蔡和森、袁隆平等古往今来一系列仁人志士的内心诉求,祝颂脚下的土地和生息于此的民族在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的同时,还能美起来,还能让心胸和疆域一样辽阔起来,以经得风,经得雨,经得起五洲端详。
从诗歌写作的角度说,这样一些舞台形象,也许正好是一个诗人在寻求和打造心灵的客观对应物时,稍可自豪且至为宝贵的收获。
《马可·波罗》在意大利费利切歌剧院的演出售票率达到91%,欧洲观众购票比例超过90%。那个剧院按座席是意大利第一大、欧洲第二大。上世纪80年代,正是这个剧院包机载帕瓦罗蒂来华演出,开启了歌剧艺术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在这样的剧院有这样的票房,让付出艰辛努力的出品方和境外运营方深感欣慰。演出前后,有许多让人怀想的情景,其中的一刻相隔日久依然清晰。那是2019年秋,9月30日,在热那亚,在距离诞生《马可·波罗行记》的监狱旧址不过几十米的地方,演出前的见面会刚开始不久,那位把剧本译成意大利文的翻译家、院长助理走到我面前,微微俯身,他不无激动:“这些年,我们剧院很少上演原创剧目,你是我见到的少有的还在世的剧作家!”他一本正经的话语,让我心里有种异样的滋味,一时不知作何反应。“我要告诉你,我把唱词译得很美,很美的意大利文,尤其是传云的咏叹调。感谢你塑造了传云,这个女子,风情万种,温柔,美,玉石,又火一样。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方。”那一晚,我为自己不懂意大利文而深感遗憾。那一晚,他让我帮他确定由五个汉字对应的名字——帕亚卢斯克,他说他想有一个和中国诗人一样的名字,他和我先后拥抱了六次。那一晚,站在一旁的大使、文化参赞、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及费利切歌剧院院长,在耐心等我照相时目睹我们交谈与拥抱,脸上的笑意并无勉强。
(作者单位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