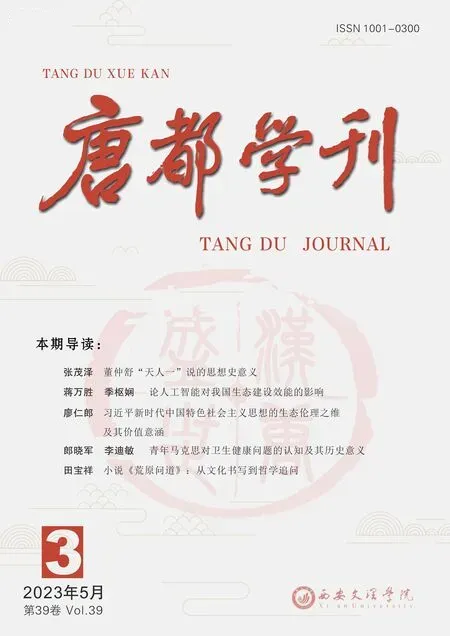郭熙画论观照下的苏轼山水诗刍议
张珈萌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中国的山水画发展到北宋渐臻佳境,与此同时,宋代的山水诗也在这一时期开辟出独特的面貌。诗与画作为艺术领域中的两大代表性文学艺术门类,都是传神写貌、抒情言志的重要艺术形式,二者相互影响的关系早为前人所关注。厘清二者在发展、形成过程中彼此的渗透与影响,对于我们认识特定时期或具体作家的艺术创作特点和作品风格确有重要作用。在诗与画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山水诗与山水画的关系尤为值得注意。北宋以诗画擅场的苏轼对于诗与画的关系有诸多论述,提出过影响甚大的“诗画一律”等观点。因此,于苏轼个人来说,其山水诗的创作与其绘画主张应该是彼此渗透、相互影响的。郭熙是北宋画坛上活跃的大家,在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成就卓著。郭熙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深刻影响了苏轼的山水诗创作,是我们深入分析诗画交融这一现象的绝佳例证。
一、郭熙画论对苏轼的影响
山水画在唐代已经形成了较为独立的风格流派,吕少卿在《唐代山水画风略论》一文中,将唐代山水画概括为三类,大致可以反映出唐代山水画的主流风格:“其一是李思训为代表的工细巧整、青绿重彩一格。其二为吴道子所代表的注重线描、不以设色绚烂为要求的‘疏体’。其三是以王维、张璪、王默等为代表的‘笔意清润’、重视墨法技巧甚至大泼墨的水墨画风。”[1]苏轼有《题王维画》一诗,从中可以略窥王维画作的特点。诗中有云:“青山长江岂君事?一挥水墨光淋漓。手中五尺小横卷,天末万里分毫厘。”[2]2420可见,王维的确擅长泼墨的水墨山水,并且作画的视角以远观为主,成平远之势,而这一创作取向一直影响到宋代。
苏轼曾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云:“唐人维摩诘、李思训之流,画山川峰麓,自成变态,虽萧然有出尘之姿,然颇以云雾间之。作浮云杳霭,与孤鸿落照,灭没于江天之外,举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尽矣。”[3]2216在苏轼看来,符合唐代典范的作品应是笔力雄健、浑厚端庄、气势壮阔的具有阳刚之美的作品,即后文提及的符合“古法”的作品。以青绿设色更能衬托此类作品的富丽恢宏之气。李思训虽在设色上采用金碧青绿,但笔法和画面意境趋向阴柔。苏轼《王晋卿所藏著色山二首》云:“缥缈营丘水墨仙,浮空出没有无间。迩来一变风流尽,谁见将军著色山。”[2]1532营丘指北宋画家李成,其画作为萧疏清旷的水墨山水。这里所说的“风流”则是唐代之“典刑”,即以著色为主、浑厚端庄的金碧山水,故而苏轼说现在像王晋卿这样的作品已经不多见了。虽然唐人作画不以烘托烟云为佳,可到了五代宋初画坛宗尚发生了变化,浮云雾霭散漫于山际,孤鸿落照灭没于江天的景象,逐渐成为北宋大家惯常在山水画中的表现方式,故而苏轼才有“举世宗之”之言,这一画作风格在五代宋初的领军人物是李成。《宋朝名画评》将李成的画列为神品,其突出的特点在于“咫尺之间,夺千里之趣”[4]。可见,李成画面的空间布局极为宽广,视角疏阔,上承唐代王维的作画视角,同时影响了后来学习他的郭熙。《图画见闻志》谈及郭熙云:“工画山水寒林,施为巧瞻,位置渊深,虽复学慕营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壮,今之世为独绝矣。”[5]《画鉴》亦云:“郭熙,河阳人。学李成善得烟云出没,峰峦隐显之态。”[6]郭熙一如李成喜作浮云杳霭,到了北宋中期,“烟云出没”的构景如苏轼所说已蔚成风气。
苏轼的师友中不乏优秀的画家,其中郭熙对他在山水艺术理论与创作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堪称苏轼重要的引路人。郭熙似比苏轼年长三十余岁,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云:“元祐以来,郭熙、泰和间张公佐皆年过八十而以山水擅名。”(1)参见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初编,第136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今人考证郭熙约生于1105年,卒于1094年[7],较苏轼年长约32岁,因其高寿,故有约数十年与苏轼在世时间重合。就二人在艺术领域是否有相互学习的经历,可以从苏轼的几首题画诗中看到些许踪迹。录原诗如下:
《郭熙画秋山平远》
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间。
离离短幅开平远,漠漠疏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时,中流回头望云。
伊川佚老鬓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阳。为君纸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
我从公游如一日,不觉青山映黄发。为画龙门八节滩,待向伊川买泉石。[2]1427
《郭熙秋山平远二首》其一
目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此间有句无人识,送与襄阳孟浩然。[2]1453
《郭熙秋山平远二首》其二
木落骚人已怨秋,不堪平远发诗愁。要看万壑争流处,他日终烦顾虎头。[2]1453
这三首作品是苏轼就郭熙的画作题诗,诗中明言“为画龙门八节滩”,即央求郭熙为他画龙门八节滩,此可以证明苏轼与郭熙相识并有交往。兹按郭熙深受神宗器重,熙宁间为翰林待诏直上,《画继》所谓“神宗好熙笔,一殿专皆熙作。”[8]嘉祐间即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苏轼,对郭熙这样一位声誉日隆的画坛大家有所仰慕并结交应该是很自然的事。《郭熙画秋山平远》一诗的前四句是对郭熙《春江晓景图》的描绘,蔡宽夫《诗话》云:“今玉堂中屏,乃待诏郭熙所作《春江晓景》。禁中官局,多熙笔迹,而此屏独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9]紧接着画卷铺开是郭熙所作的短幅《秋山平远图》。“平远”是郭熙擅长的画面空间布局,继承了李成“近视如千里之远”的笔法,特别是在短幅的画作中,如此布局视野极为开阔。画面集中表现“漠漠疏林”和“中流云”,“漠漠”之态恰好与“平远”的视角形成呼应,而烟云出没于山间同样是学习李成,以表现“峰峦隐显之态”。苏轼于此画之景唯提及此两点,而这恰是郭熙画作最为擅长之处,可见苏轼对郭熙画作的精髓了然于心。黄庭坚有《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一诗,对郭熙《秋山平远图》的描写更为详尽,“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脚明,归雁行边馀叠。”[10]11366《题郑防画夹五首》其二亦云:“能作山川远势,白头惟有郭熙。”[10]11366都是侧重表现郭熙画作的平远视角以及萧散缥缈的景致。好友之间得一佳作相互唱和,表现了苏、黄二人对郭熙画作由衷的赞赏。苏轼《郭熙秋山平远二首》其一首句的“尽”与“边”二字同样点题中之“平远”,营造出萧散冲淡的意境。《郭熙秋山平远二首》其二则是说郭熙之画能够引发观者的诗愁,观画触发了观者的画外之思,而引发画外之思的关键则是“平远”之境。
从上述诗句中可以看出苏轼对郭熙的画作心有戚戚,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郭熙画作在神宗时期的影响非常巨大,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二人在艺术上有相近的审美取向,故在有关绘画领域可能会有交流和切磋。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郭熙山水画的喜爱,不仅表现在他赏画、评画、题画与郭熙有相似的审美取向,同时他本人山水诗的创作似也受到郭熙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存郭熙的绘画理论著作是其子郭思编述的——汇聚了其父创作经验和艺术见解的《林泉高致》,其中《山水训》一篇,详细论述了郭熙绘画创作的理论主张。《林泉高致》虽然编纂成书于徽宗时期,但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苏轼应该是了解或者熟悉的。作为北宋在诗画领域擅场的大家,苏轼山水诗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郭熙之画及其画论的影响,并内化为他创作山水诗的技巧。苏轼山水诗的创作对郭熙绘画作品及画论的借鉴可以从上文对郭熙三幅画作的题诗中提炼得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远望取势,诗中有画,画外之意。
二、诗与画的视域架构:远望取势

苏轼曾言“诗画本一律”,因此在其山水诗的创作中以观画的眼光来描写眼前之景并将远观的视角纳入其中来表现山水之势似在情理之中,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即是典型的代表。此诗作于熙宁二年(1069),其中“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波平风软望不到”[2]257这几句与上文《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一诗所列举诗句在句式和内容上如出一辙。《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一诗作于元丰元年,晚于前诗,李思训画中的绝岛与苏诗在行旅过程中初见的淮山也定不是一物,由此可见,苏轼对山水实景的视域观照与他评画、赏画或题画时强调的空间布局关注点是一致的,这也很好地佐证了他所提出的诗画相通的艺术理念。苏轼在行旅过程中创作的山水诗,均是以远望的视角建构山水空间,这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主张,而且其诗在取景的视角和描写技法方面,与其论画如出一辙。
郭熙提出画山有“三远”,即高远、深远和平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至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13]0578c“三远”的构图视角在苏轼的山水诗中也有恰如其分的表现,《江上看山》将三种观山的视角均融入诗中,对郭熙绘画思想的学习和践行堪称惟妙惟肖。《江上看山》从不同的视角介入,“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写行舟之快,两岸的群山倏忽即逝,这是“平远”的视角。“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写观山从山前到岭后,则是采用了“深远”的视角,表现了群山重迭之意和山形的复杂多变之态。“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写仰望高山,山势愈显高耸,行人则高远隐约,难以辨清面目,采用的是“高远”视角。“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上承颔联,诗人想与山上行人打个招呼,无奈孤帆疾驶,不及与言,回扣首联。全诗围绕看山展开,通过不同的观山视角,使得群山的特点一览无余。
郭熙于“三远”中最为推赏的是“平远”。平远构图的妙处除了上文提及的“极人目之旷望”外,还能尽显山川之晦明变化,即“真山水之阴晴远望可尽”[13]0575d“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都是强调通过远望的视角表现山水的明晦之态。他说:“山无明晦则谓之无日影……今山日到处明,日不到处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明晦不分焉,故曰无日影。”[13]0577c-0577d在郭熙看来山水画中的光影要通过明晦来表现,而明晦之态又是通过远望而获得的,从现存郭熙的画作中可以看到他擅长通过平远的视角来表现山水的光影,而这一点同样受到了苏轼的关注。苏轼在《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其十八《溪光亭》中云:“决去湖波尚有情,却随初日动檐楹。溪光自古无人画,凭仗新诗与写成。”[2]642这首诗后两句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古代山水画对于光影的表现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只有像郭熙这等级别的画家及其他少数优秀画家才有这样的眼光和水准。
苏轼在山水诗的创作中同样借助“远望”的视角来表现光与影,原因可能正如他所说明晦难摹,只能“凭仗新诗”来完成。如“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2]334两句,月黑如何有光?这里诗人摒弃了惯常湖光映月的表现形式,而是通过借助远寺的微暗的灯光富有创新性地表现不同于常理的光影。“江寒晴不知,远见山上日。朦胧含高峰,晃荡射峭壁”[2]6,是通过日影来表现山的明晦。“光摇岩上寺,深到影中天”[2]193是借光影将潭水与远方的寺庙勾连起来,一方面表现潭水之深,正如苏轼此诗自注云:“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测。”[2]193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寺塔之高,“南寺有塔,望之可爱而终不能到。”[2]193“林缺湖光漏,窗明野意新”[2]198,写湖光穿过稀疏的树林映照在亭上,此景象唯有通过远望才能收纳于目力所及范围之内。“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2]288几句中,“山有无”是指山之或隐或现,能看到山的明晦之态应是远望视角,若是身处其中便难观变化,正是郭熙所言“近者拘狭不能得明晦隐见之迹”[13]0575d。综上可见,平远的视角在绘画中可以充分表现出山水的明晦之态,而将此种视角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之中则能通过光影的变化丰富山水的表现形态,这也是苏轼山水诗的绝胜之处。
三、诗与画的焦点:“云烟”与萧散缥缈的意境
苏轼诗画一体的艺术观贯穿其一生的创作实践中,他能从画中提炼出诗句。如《袁公济和刘景文登介亭诗,复次韵答之》一诗云:“登临得佳句,江白照湖渌。袖手独不言,默稿已在腹。……惜哉此清景,变灭不可逐。归来读君诗,耿耿犹在目。”[2]1617-1618登临观景画中有诗,归来读诗诗中有画。其《跋宋汉杰画》云:“仆曩与宋复古游,见其画潇湘晚景,为作三诗,其略云:‘径蟠趋后崦,水会赴前溪。’复古云:‘子亦善画也耶? ’”[3]2215在宋复古眼中,苏轼不仅是诗人,同样也是画家。郭熙主攻绘画,好的诗句便能在他眼中构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林泉高致·画意》云:“思因记先子尝所诵道古人清篇秀句,有发于佳思者,并思亦尝旁搜广引以献之先子,先子谓为可用者。”[13]0580a其后列举了一些诗人的写景名句,皆是极富画面感的佳句。可见,对于画家来说他们创作的灵感有时亦来自于清绝的诗句,融会于心,下笔成画。诗画相通,所通之处不外乎景物与意境,苏轼在对郭熙画论的借鉴与实践中,频频表现“烟云”一景,而以“烟云”构图、入诗则易于营造出冲融缥缈、萧散平淡的意境。
承上所言,北宋山水画以烘托烟云为佳,一变唐代之“典型”。关于烟云对于山水画表现的作用,郭熙曾言:“水,活物也。……欲挟烟云而秀媚”[13]0577d-0578a,山“以烟云为神彩……得烟云而秀媚”[13]0578a,“山无烟云如春无花草”[13]0578c,山水因烟霞更加秀媚可爱。烟云除了给山水增色增态外,于山之隐现、山之高矮的表现亦有巧妙的作用。“今山烟霭到处隐,烟霭不到处见,山因烟霭之常态也。”[13]0577d“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13]0578d山峦的隐显变化使得画面更具立体感,同时又使山具有明晦之态;画山高耸唯有出入云霄方能显其峻,最适于画家用短幅作画,即苏轼诗中提到的“离离短幅”“咫尺”,可以扬长避短,尽情展现画面中景物的特点而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苏轼对于烟云表现画面的妙处了然于心,在为他人题画时也往往借云烟来烘托景物,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王定国此画以“烟江叠嶂”为题,明确了画面的内容,观者可以从视觉上赏析此画,而苏轼将之转换为诗语。“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2]1526一句,云烟作为喻体承载着诗人的情感。作者将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运用得浑然自如,“云烟”的功能也更为多样化。《虔州八境图八首》其七:“烟云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2]765整首诗都是围绕“烟云”展开描述,首句以烟云烘托出郁孤台的高耸之势,与次句中的“浮空”相呼应。进而又从眼前烟雾缭绕的景象联想到在之罘山上观海市蜃楼,而远处蓬莱仙界中的仙宫又正是因这“烟云”造势而呈现出明灭有无之态。“烟云”在这首诗中不再仅仅是作为简单的物象而存在,而是在整首诗歌中起到了建构全诗结构的作用,整首诗的意境也全靠“烟云”来烘托。
苏轼在《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一文中说:“诗有奇语,云烟葱胧,珠玑的砾,识者以为画师之流。”[3]326故其山水诗中也常常借助“烟云”来构建诗歌内容,烘托诗歌意境。如《初入庐山三首》其二:“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2]1153诗人昔日未曾到庐山时曾于梦中在此一游,而今昔时梦中的场景就在眼前,心中自是畅然愉悦。诗中的“杳霭”连接了梦与现实,跨越了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不仅为从前之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还为现实中的庐山增添了一抹仙色,使得庐山在梦与现实之间并未有明显的不同,从而才使得后句的“真”落到了实处。山水诗写景摹物重在表现景物的特点,平铺直叙显得生硬呆板,借“烟云”衬托景物的特点要比平铺直叙生动得多,如《骊山》云:“复道凌云接金阙,楼观隐烟横翠空”[2]2356,以“烟云”表现楼观之隐现。《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云:“曳杖不知岩谷深,穿云但觉衣裘重”[2]2013。前句言岩谷之深,后句如再直说山高则平淡无味,“穿云”句与前句在内容的叙述上变化了角度,从侧面烘托了山高的特点,谷深与山高又暗自为对。《同王胜之游蒋山》云:“略彴横秋水,浮图插暮烟”[2]1200也是借“烟云”描写佛塔之高。《与客游道场何山,得鸟字》云:“洞庭在北户,云水天渺渺。”《九日黄楼作》云:“烟消日出见渔村,远水鳞鳞山齾齾。”[2]840“烟云”在这里犹如帷幕一般,当帷幕拉开,山水之景跃然眼前。凡此,皆系借助烟云来描绘山水。
对北宋山水画有重要影响的李成专攻水墨山水,独创萧疏清旷的“平远寒林”,后来学习他的郭熙等人在画面意境的营造上也专注于冲融缥缈、萧散平淡的意境。此种意境为宋代文人所钟爱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正如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14]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3]2124虽是评论书法,但同样适用于绘画和诗歌领域。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在共同的文艺思潮和审美倾向的作用下,文学、绘画、书法等不同领域出现近似审美取向的情况并不鲜见。从绘画艺术的角度来看,水墨本身具有古淡清幽的特点,下笔施墨时又有轻重之分,因此,以水墨作画有助于从色彩上烘托出冲融缥缈的意境。而且“平远”的视角也有助于此种意境的营造,如郭熙所云:“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缈”“傍边平远,峤岭重叠,钩连缥缈而去,不厌其远”。而“烟云”作为画家笔下常见的物象,在意境的营造上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手法显然对苏轼颇有启迪之功。纵观苏轼的山水诗,其中有不少冲融缥缈、萧散平淡风格的作品。如《凌虚台》云:“落日衔翠壁,暮云点烟鬟。”[2]199以烟云切淩虚之意,烘托出缥缈的意境。《僧清顺新作垂云亭》云:“路穷朱栏出,山破石壁狠。海门浸坤轴,湖尾抱云。葱葱城郭丽,淡淡烟村远。纷纷乌鹊去,一一渔樵返。雄观快新获,微景收昔遁。”[2]428诗人以垂云亭为中心,将其作为观山水胜景的支点,展开对周围景色的描摹,“路穷”“山破”“海门”“湖尾”这些“雄观”之景营造的意境恢弘壮阔,突出了垂云亭所建位置具有极佳的视野;紧接着描写诗人举目望去,“烟村”“鸟鹊”“渔樵”营造出冲融萧散的意境,以“微景”作收束。下句“道人真古人,啸咏慕嵇阮”,则是以古人之神承“雄观”宏阔之景,以古人之形承冲淡之“微景”。在这里“烟云”对于意境的烘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很显然的。又如《游何山》云:“云含老树明还灭,石碍飞泉咽复流。遍岭烟霞迷俗客,一溪风雨送归舟。”[2]2487身处缥缈冲淡之境的“俗客”随着归舟远逝,心性仿佛也被浸染,现实中的追名逐利者在诗画中完成蜕变,回归自我。另外,“水云”“云山”等词也常出现在苏轼其他的山水诗中。
苏轼的山水诗除了借助“烟云”烘托冲融缥缈的诗境外,还融入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对此进行了创新和变革,他在水墨冲淡的背景下加入了碧色的元素,使得其山水诗呈现出“不古不今”的样貌,而这一创变灵感的源泉也不应忽视相关绘画理论的启迪之功。如前所述,北宋前期的李成和后来继承李成一脉的画家奠定了北宋绘画风格的基调,但是在苏轼看来对艺术的践行不可囿于一家,而应该兼容并收,并在此基础上自出新意。《王晋卿所藏著色山二首》其一就肯定了王诜在北宋以水墨山水擅场的背景下创作唐代的金碧山水,表现了对他所画著色山水的赞许。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亦云:“汉杰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为之不已,当作着色山也。”[3]2216所谓的“不古不今”是不专于古,亦不专于今,实则是既古又今,唯有此,方能锤炼而后稍出新意。此论与郭熙一脉相承,郭氏云:“人之学画,无异学书,今取钟、王、虞、柳,久必入其仿佛。至于大人达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专门之学,自古为病,正谓出于一律,而不肯听者,不可罪不听之人,迨由陈迹,人之耳目喜新厌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为大人达士不局于一家者,此也。”在冲淡背景下加入碧色这一理念在苏轼的山水诗中也有所体现。如其《南都妙峰亭》云:“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烟鬟。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2]1256“翠壁”与“烟鬟”相对,冲淡的背景下借一缕碧色来点缀。《游道场山何山》云:“出山回望翠云鬟,碧瓦朱栏缥缈间。白水田头问行路,小溪深处是何山。”[2]383在缥缈之中又透着绚烂。《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云:“江流镜面静,烟雨轻幂幂。孤舟如凫鹥,点破千顷碧。”[2]1024诗中的碧色不单单是诗人眼前的实景,而是诗人有意识地冲破水墨的迷蒙淡雅,在视觉上注入色彩并突破原有范式所限,为北宋的山水诗、画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诗与画拓展内涵的方式:全景式构图
传神的山水画绝非仅对自然景观的客观描摹,而是能够引发观者的画外之意,即由观画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时还能引发观者对自身的反省、对现状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这不仅丰富了绘画的内涵,也使画作超越有限的尺幅,具有了延展的特性。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云:“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看此画令人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此画之意外妙也。”[13]0576b即是对这一创作宗旨的最好诠释。如何才能做到令人观画生意呢?郭熙认为要“所养扩充”。“何谓所养欲扩充?近者画手有《仁者乐山图》,作一叟支颐于峰畔,《智者乐水图》作一叟侧耳于岩前,此不扩充之病也。盖仁者乐山宜如白乐天《草堂图》,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乐水宜如王摩诘《辋川图》,水中之乐饶给也。仁智所乐岂只一夫之形状可见之哉!”[13]0577a意即好的画作,能引人有所思有所想,在深处触动观览者的心弦。苏轼在评王维之画时也说“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2]154。“得之象外”与郭熙所说“画之景外意”是一个意思,而这种表现效果离不开对画面的完整呈现。
苏轼在创作题画山水诗时,也非常注意这一点,借助完整的画面意境挖掘画外之意。如在《〈虔州八境图〉八首》引中云:“《南康八境图》者,太守孔君(孔宗翰)之所作也,君既作石城,即其城上楼观台榭之所见而作是图也。东望七闽,南望五岭,览群山之参差,俯章贡之奔流,云烟出没,草木蕃丽,邑屋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观此图也,可以茫然而思,粲然而笑,嘅然而叹矣。”[2]761-762观此图可思、可笑、可叹,概也是由于画家做了全景的呈现,“群山”“奔流”“云烟”“草木”“邑屋”“鸡犬”应有尽有,所含扩充,故有画外之意。再来看苏轼的山水诗,不少作品也是通过全景式的构图来体现画外之意。如其《留题仙都观》云:“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空山楼观何峥嵘,真人王远阴长生。”[2]20这首诗以写仙都观为主,同时对其周围的景物也进行了描绘,山前之江水、山上之松柏、江中之舟客,眼前完整的景象引发了诗人对于宇宙的思考进而联想到王远、阴长生等隐士,触发了诗人对于归隐的深思。
苏轼“诗画一律”的艺术观使他在创作诗歌的同时也尽可能汲取本前贤与本朝绘画创作与理论中的精髓。而郭熙作为苏轼的前辈,其绘画实践及相关理论颇具启发意义。首先,表现在画面的视域及空间布局以平远之势展开,并以“平远”视角为基础,通过对山水阴晴明晦变化的呈现丰富山水的表现形态。其次,选取“烟云”这一最具有代表性景物,借此烘托出冲融缥缈、萧散平淡的意境;最后,则借助完整的画面意境呈现画外之意,使览者品得“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这些绘画技法和相关理论显然都对苏轼的山水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可贵的是,苏轼能够在此基础上自出新意,如其在水墨冲淡的背景下喜欢加入碧色元素,使得山水诗的创作呈现出“不古不今”的面貌。此外,苏轼山水诗对郭熙画论的借鉴还表现在对四时之景不同的表达以及对景物“步步移”“面面看”的全方位视角等等,限于篇幅,兹不赘述。苏轼山水诗对绘画技法和理论的借鉴一方面以实际行动有力践行了其“诗画一律”的艺术观,同时也使其山水诗的创作达到了“诗中有画”的妙境,并对后人的山水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堪称研究诗歌与绘画两种艺术形式彼此交融的绝佳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