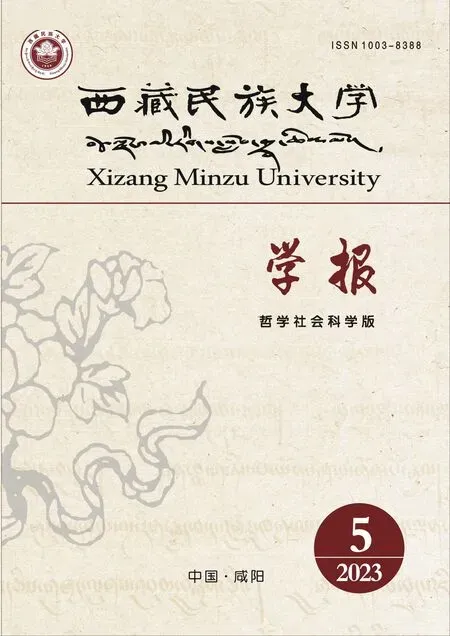人类学视野下对20世纪前半叶在藏尼瓦尔人的考察
马生福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062)
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唐朝时期尼泊尔赤尊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元代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建造北京妙应寺白塔等史实见证着中尼两国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千百年来,中尼两国人民跋山涉水,为两国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大批尼泊尔人通过中尼边境地区进入中国西藏从事商贸活动。进入民国后,受英国殖民主义者影响,西藏地方的内地商人势力逐渐式微,英印商人、尼泊尔商人在商业贸易中的地位上升。根据史料记载,这些尼泊尔商人绝大多数属于被誉为加德满都谷地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创造者的尼瓦尔民族。20世纪前半叶,尼瓦尔人跨越巨大的地理障碍,在我国与尼泊尔的跨喜马拉雅贸易和文化、宗教与艺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 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尼泊尔国内封建和专制并行的拉纳家族独裁统治结束,海门道夫(Fürer-Haimendorf)、休伯特·德克莱尔(Hubert Decleer)、杰拉德·托芬(Gérard Toffin)等西方学者开始对尼瓦尔人进行相关研究,内容多涉及尼瓦尔人的宗教信仰与种姓制度、节日与仪式、“库玛丽活女神”崇拜等内容。近年来,一些曾经赴藏经商与生活的尼瓦尔人及其后裔相继出版了一些记述20 世纪前半叶尼瓦尔人在藏经历的书籍,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卡迈勒·拉特纳·图拉达哈(Kamal Ratna Tuladhar)所著英文图书《前往拉萨的商队——旧西藏的加德满都商人》(《CARAVANTOLHASA:AMerchant ofKathmanduinTraditionalTibet》),德布·绍瓦·堪萨卡·希尔克(Deb Shova Kansakar Hilker)所著英文图书《夏木嘎布:噶伦堡和加德满都的拉萨尼瓦尔人》(《Syamukapu:TheLhasaNewarsofKalimpong andKathmandu》),凯萨·拉尔(Kesar Lall)所著英文图书《在拉萨的尼瓦尔人商人》(《THENEWAR MERCHANTSINLHASA》),达摩·拉特纳·亚米(Dharma Ratna Yami)所著英文图书《来自西藏的回复》(《ReplyfromTibet》),贾加特·比尔·辛格·堪萨卡(Jagat Bir Singh Kansakar)所著尼文图书《一百多年前的拉萨》(《LhasaMoreThanaHundredYears Ago》)等。这些作者自己或其父辈曾于20 世纪前半叶在西藏活动并与西藏社会各界密切交往交流,其记录虽然有一定的偏见和局限性,但也不乏真实性与客观性,作为他山之石,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尼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及贸易和文化往来的历史。国内关于在藏尼瓦尔人的研究至今鲜见,本文拟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在藏的尼瓦尔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群体做初步研究,希望抛砖引玉,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尼瓦尔人入藏
自清初开始,尼瓦尔人就在从事我国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零星民间跨境贸易。有清一代,一统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先后发动过三次侵藏战争。19世纪末开始,尼泊尔境内的部分尼瓦尔人因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及在尼泊尔国内受苛捐杂税的盘剥等原因影响而离开尼泊尔,赴藏经商、生活。
(一)清朝时期廓尔喀王朝三次侵藏战争与尼瓦尔人入藏的历史背景
18 世纪后期,尼泊尔境内的廓尔喀民族统一了尼泊尔,建立了沙阿王朝,又称廓尔喀王朝。尚武的廓尔喀人在统一尼泊尔过程中不断征战,领土不断扩张。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让廓尔喀人的野心大大膨胀,他们一度将扩张目标指向了中国西藏。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受西藏噶玛噶举派的第十世红帽系活佛却朱嘉措唆使,廓尔喀军队以贸易和边界纠纷为由入侵西藏,占领了聂拉木(又称“库提”)、宗喀(今西藏吉隆县治)和济咙(今西藏吉隆县吉隆镇)。西藏地方政府“许银赎地”和廓尔喀官员私订条约,许诺向廓尔喀“每年一次付银三百秤”[1](P291),廓尔喀军队撤兵回国。乾隆五十五年(1790),廓尔喀派人入藏索要赎地银两,西藏地方政府在付给一年银两后拒绝支付,希望与其重新谈判。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军队以西藏拒不付款为由,再次入侵西藏,并一度攻到日喀则,在扎什伦布寺大肆抢掠。第八世达赖喇嘛和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相继向乾隆皇帝求援。接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求援后,乾隆皇帝派福康安、海兰察等率大军入藏增援。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军攻克济咙,全面收复被侵领土,随后攻入廓尔喀境内,兵临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廓尔喀遣使求和,并派遣大臣到北京投诚进贡,许诺永不侵扰西藏。咸丰五年(1855),在英国的蓄意挑拨下,廓尔喀派兵占领了西藏济咙、聂拉木等地,西藏军队不敌,向清政府求援。时值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清廷忙于绞杀这场农民运动,同时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北京,清廷无暇顾及西藏,急于息事宁人,遂命驻藏大臣出面调解。时逢十一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僧俗百姓也不愿继续作战。[1](P456)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驻藏大臣赫特贺的主持下,咸丰六年(1856)3月,双方签订了不平等的《西藏廓尔喀条约》(又称《塔帕塔利条约》)。该条约规定:“西藏年付廓尔喀赎金一万卢比;廓尔喀商民在西藏不抽商税、路税及其他项税捐;廓尔喀派高级官员一员,驻在拉萨;廓尔喀准在拉萨开设店铺,任便售卖珠宝、衣着、粮食及其他各种物品;拉萨辖区内廓尔喀商民如有争执,不容西藏官员审讯[1](P457)”等等。根据该条约,廓尔喀商民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等,这是作为廓尔喀王朝居民的尼瓦尔人开始进入西藏经商和生活的历史背景。
(二)尼瓦尔人赴藏经商与生活的原因探析
尼瓦尔人赴藏经商和生活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廓尔喀王朝时期,尼泊尔境内对贸易征收重税。对此,乔治·波格尔在《出访西藏记事》中提到: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廓尔喀王公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筹集军费开支,其中就包括对贸易征收重税,以随便找来的借口,对商人大数额的罚款。很多商人被剥夺了财产或受到苛捐杂税的盘剥,只能选择离开尼泊尔[2](P285-286)。第二,尼瓦尔人在政治方面受到排挤。从13 世纪初到18 世纪中期,是尼瓦尔人统治的马拉王朝时期,廓尔喀政权成立后,尼瓦尔人在政治上受到排挤。《西藏廓尔喀条约》签订时廓尔喀人就曾明确提出“廓尔喀派高级官员一员,驻在拉萨,但不得派尼瓦尔人”[1](P457)。20 世纪20 年代长期在拉萨生活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其所著《西藏志》中写道:“尼泊尔人侨寓拉萨,率皆集族而居,为数颇众,在孜塘、日喀则、江孜、拉孜以及工布州各地,亦有尼泊尔人之足迹,唯数目较少。在廓尔喀人未得政以前,统治之民族为尼瓦尔人,移居西藏之尼泊尔人即此族苗裔也。”[3](P145)第三,尼瓦尔人在宗教方面受到迫害。19 世纪中叶以后,尼泊尔国内正值拉纳家族开始实施军事独裁统治之际,拉纳家族对内实行愚民政策、对外忠实听命于英国,导致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拉纳家族掌握尼泊尔权力后,借印度教压制佛教,使印度教在尼泊尔发展到近乎唯我独尊的地步,而尼瓦尔人则多信奉佛教,当时的尼瓦尔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亦受到迫害,佛教僧侣被驱逐出境,随后在政治高压下,许多尼瓦尔人渐渐改信了印度教。第四,尼瓦尔人的民族性格偃武修文,不喜军事,据尼瓦尔人自述“尼瓦尔人性格平和、开朗,经常被廓尔喀人在内的其他民族嘲笑胆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直到1950 年,尼瓦尔人都被拒绝在廓尔喀军队中服役”[4](P12)。正是在这些多重因素影响下,一部分尼瓦尔人选择离开尼泊尔,来到中国西藏经商和生活。
二、在藏尼瓦尔人的人口、宗教信仰和种姓制度
尼瓦尔人是尼泊尔众多民族之一,以其经商才能和艺术造诣而出名。据说,遍布加德满都的古建筑绝大多数均出自尼瓦尔人之手。元代时期,来华的尼泊尔著名艺术家和建筑家,中尼传统友谊的推动者和贡献者阿尼哥,就是尼瓦尔人。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 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记载他在拉萨见到的尼瓦尔人时曾写道:“商店门前站着脸色惨白的尼瓦尔人,他们的祖先来自尼泊尔,若干世纪以前就在拉萨定居了。他们头戴平顶棕帽,身上的赤褐色长袍比喇嘛袍的颜色更深一些”[5](P186)。
(一)在藏尼瓦尔人的人口数量、职业与分布
20 世纪前半叶在藏的尼瓦尔人人数因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及时局变化时有不同,目前未见精确统计数据。根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大典时观察,1940年时“拉萨市有尼泊尔人千余,均业杂货商,商店共约150 家,资本百余万,此外江孜、日喀则等各大埠,均有尼泊尔人经商,全藏尼人总数约在3千”[6](P173)。陪同吴忠信前往西藏出席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的朱少逸记载:“尼泊尔人侨居西藏者数约3 千,散处拉萨、江孜及日喀则、哥大克(今阿里地区噶尔县)一带,以拉萨人数最多,占全体三分之二,拉萨一带有尼泊尔商店150 家”[7](P26)。根据中国民族学会原副秘书长李坚尚的记载,1950 年—1960 年期间,拉萨、江孜、泽当、亚东、聂拉木、充堆(今山南市扎囊县境内)、岗噶(今日喀则市定日县境内)均有尼泊尔商人分布[8](P23-24)。
在藏尼瓦尔人大多具有丰富的跨国贸易商业经验和西藏地方性知识,他们曾在拉萨、日喀则江孜和聂拉木、山南泽当和扎囊等地从业。在藏尼瓦尔人将拉萨作为常居地,频繁往返于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之间,建立起了跨国商业网络,业务集中于布料、毛皮、金银首饰等。尼瓦尔人从尼泊尔到中国西藏的跨境贸易路线和在藏的经商状况,及其公共空间与社会交往等内容笔者另有专文论述[9]。
(二)在藏尼瓦尔人的宗教信仰
尼瓦尔人多信仰佛教,也有因受信仰印度教的拉纳家族影响而改信印度教的,甚至有部分尼瓦尔人是二者兼信仰。这两种宗教互相渗透,彼此和平相处,两种教徒都积极参加对方的宗教庆祝、宗教仪式和其他活动,并尊敬对方崇拜的神灵[10](P90)。在西藏经商的尼瓦尔人既参加佛教的节日庆典活动,包括去藏传佛教寺院礼佛,也会举行仪式庆祝印度教的节庆。查尔斯·贝尔在《西藏志》中写道:“尼瓦尔人之中崇信佛教者亦众,无论何日,皆可见其在拉萨各大庙宇中礼佛。”[3](P145)
(三)在藏尼瓦尔人的种姓制度
受到印度教的强大影响,尼瓦尔人接受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尼瓦尔人的种姓制度中姓氏有高低贵贱之分。尼瓦尔佛教徒中有古巴朱、瓦吉拉查尔亚、萨克亚、巴雷、什雷斯塔、乌赖等种姓,尼瓦尔印度教徒中有代奥婆罗门、巴塔婆罗门、贾婆罗门等种姓[11](P284-285)。尼瓦尔人佛教徒的种姓内部又有等级划分。比如在拉萨经商的多属于什雷斯塔(Shrestha)、乌赖(Uray)种姓。乌赖种姓内部又有堪萨卡(Kansakars)、图拉达哈(Tuladhar)、塔姆拉卡(Tamrakars)、斯塔皮特(Sthapits)、巴尼亚(Baniyas)等姓氏。20世纪前半叶,拉萨著名的尼泊尔商店哥惹夏①的经营者卡鲁纳·拉特纳·图拉达哈(Karuna Ratna Tuladhar)即为乌赖种姓图拉达哈②姓氏,至今仍在营业的拉萨尼瓦尔人商店夏木嘎布③的创始人巴珠·拉特纳·堪萨卡(Bhajuratna Kansakar)即为乌赖种姓堪萨卡姓氏。受拉纳家族影响,20 世纪初尼瓦尔人的种姓意识较强,限制与不平等种姓的人通婚甚至吃饭喝水。但是赴藏经商的尼瓦尔人一旦离开尼泊尔国境,种姓差别已没有明显的影响,即使是吃碰过别人嘴唇的食物也不再会成为禁忌[12](P65)。
三、在藏尼瓦尔人的仪式
尼瓦尔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周期会举行不同的仪式。仪式作为凝聚尼瓦尔人的工具形式,承载着集体的历史记忆,强化了尼瓦尔人的历史文化认同。
(一)萨甘仪式
尼瓦尔人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仪式是萨甘(sagan),这是一种备受尊崇、适用性极强的仪式,在庆祝新生儿出生、生日、婚礼等生命周期事件时均会举行萨甘仪式。萨甘仪式上首先会对雕刻在苏昆达(sukunda)油灯上代表幸运之神象神甘尼什(Ganesh)的形象进行祭祀;然后给接受仪式的人献上鸭蛋或鸡蛋、熏鱼、米酒、肉和扁豆等食物。萨甘仪式的程序、食物的材料可能因家庭传统和地域的不同而变动,20 世纪上半叶在西藏因为鸭蛋比较罕见,举行萨甘仪式时则是用肉饼代替鸭蛋。尼瓦尔人从尼泊尔出发将要去西藏经商时、到达拉萨接受已在拉萨的尼瓦尔人迎接时、结束经商之旅返回尼泊尔之时都会举行萨甘仪式。
当尼瓦尔人离开家乡去往西藏时,会戴上象征欢乐和吉祥的红帽子,出发前会给家庭成员,特别是给年幼的孩子一些现金作为礼物。从尼泊尔出发和抵达拉萨时,尼瓦尔人都会跪下来非常恭敬地用额头去碰触近亲长辈的脚,这是一种尼瓦尔人传统的问候或告别长辈的仪式[12](P65)。
当尼瓦尔人结束在拉萨的生意,准备返回尼泊尔时,首先会前往拉萨的各主要寺院,在佛像前供奉哈达,并祈祷他们能够平安回家。留守者将利用这一时机了解谁将离开拉萨,并向任何企图在未偿清债务的情况下就离开的人索赔[4](P131-132)。
(二)成年仪式
尼瓦尔人的男孩子要进行一种叫作卡塔普迦(Kayta Puja)的成年仪式,这个仪式是典型的法国人类学家范热内普认为的过渡仪式。在这个仪式中,尼瓦尔人的男孩子将被授予一串佛珠和一条缠腰带,仪式结束后,他将被视为成年人,成为他们父系和种姓的正式成员,从此可以开始读书、习武或经商。尼瓦尔人的习俗中,只允许男性赴藏经商,接受过成年礼的尼瓦尔男子就有资格赴西藏从事跨喜马拉雅贸易了。在藏经商的尼瓦尔人一般是以家族为基础,大家庭成员、堂表兄弟和亲戚们都被吸收在一个商店之内,一个尼瓦尔人在西藏经商的时间通常是三年,但实际上很多人待的时间长达八年甚至超过十年之久,直到有兄弟或亲戚从尼泊尔来替换他们为止[13](P20)。
(三)婚礼
婚礼是尼瓦尔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仪式之一。关于尼瓦尔人的婚礼,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尼瓦尔女孩二次婚和第一次结婚需要嫁给一种叫“贝尔果”(bel)的果实的象征性结婚的风俗习惯[10](P107)。20世纪初,尼瓦尔人的婚姻多由父母包办,也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于尼瓦尔人家庭来说,很多年轻夫妇都是在婚礼当天第一次见面。根据尼瓦尔人的习俗,在为儿子寻找合适的新娘时,与相关家庭直接接触是不合适的,因此媒人会在两个家庭之间穿梭,两个未来姻亲间唯一的联系就是通过媒人。一旦两个家庭同意让他们的孩子结婚,这对未来夫妇的星座就会被带到家族占星师那里。如果星座不匹配,媒人就要寻找另一位准新娘。尼瓦尔人的婚礼非常昂贵和复杂,繁琐的仪式至少需要四天才能完成,因此长期以来,为了节省开支,大多数尼瓦尔人的家庭会在同一天让他们所有的适龄儿子结婚,所以经常会举行双人婚礼,同一场婚礼上亲兄弟或堂兄弟会同时和各自的妻子喜结连理。通常尼瓦尔人的孩子们很小就会结婚。然而,新娘在结婚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父母身边生活的,她会定期被召集参加夫家的节日和宗教仪式。年轻的新娘住在夫家时,会和丈夫的姊妹们住在一起,年轻的丈夫则和兄弟们住在一起。只有当新娘年满16 岁后,才允许她与丈夫同房,从此开始长期居住在丈夫的家里。结婚的头几个月、甚至是头几年,年轻的丈夫如果需要离开家庭赴藏经商,把年轻的妻子留在父母身边是很常见的事[4](P72—73)。尼瓦尔诗人拉克希米·普拉萨德·德夫科塔的叙事诗《穆娜与马丹》[14],就讲述了新婚妻子穆娜在丈夫马丹离开尼泊尔前往西藏经商后的孤寂和对丈夫的思念。尼瓦尔人的男子长期在藏经商,也有与西藏的藏族女性结婚,在尼泊尔之外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生活的。这种跨境婚姻关系中所生的混血子女中的儿子称为卡扎拉(ཁ་ཙ་ར།),被认为是尼瓦尔人,而女儿则被认为是藏族人。
(四)净化仪式
对于从西藏长途跋涉返回故土的尼瓦尔人,尼泊尔国内的尼瓦尔人认为由于他们与来自陌生地方的人长期交往后远道而来,可能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污染,因此需要和家人保持社交距离,经过一场“自我隔离”的净化仪式后方能和家人团聚。从西藏返回的尼瓦尔人不允许到家中一楼以上的地方,不能接触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到家后的十五天时间里他需要“自我隔离”,独自一人睡在空房间中,每天只吃一顿饭。事实上,这种制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在尼泊尔家中等待亲人归来的尼瓦尔人为了早日和长期分离的亲人团聚,采取了一种投机取巧式的做法,即家庭成员共同分享隔离期,比如一个男子在执行“自我隔离”时,他的妻子、姊妹可以同时进行“自我隔离”,各自替他履行五天的义务,以期尽早会面。等隔离期满后,会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宴会,并由家族祭祀主持举行萨甘仪式,以驱赶可能跟随旅行者从遥远的陌生地方远行而来的邪祟[4](P151)。据说从西藏返回的尼瓦尔人在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长途旅程中丢失了种姓,所以隔离期结束后,他们必须从当地政府获得一张证明他们已经找回了自己种姓的文件,方能允许他们重新融入当地社会。1962 年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爆发,绝大多数尼瓦尔人都从西藏返回了尼泊尔,没有人再从事跨境贸易,这种“自我隔离”的净化仪式也就因此被废止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尼瓦尔人开始回忆起这一仪式,认为这种“自我隔离”的净化仪式,实际上有助于在人口稠密的社区中防止传染病的传播④。
四、在藏尼瓦尔人的历史记忆建构
尼瓦尔人从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来到西藏,主要在拉萨、日喀则、江孜、聂拉木、吉隆、亚东等地经商,尤以拉萨为主。赴藏经商与生活的尼瓦尔商人群体为了适应在西藏的生活,建构了一位名叫“僧诃罗萨陀波怙”(Simhalasarthabahu)的伟大祖先的历史记忆,以此来增强族群认同。尼瓦尔人称尼泊尔和西藏之间的大宗贸易由尼泊尔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尼瓦尔人僧诃罗萨陀波怙所开创。他被当作一个地方性的神灵来供奉,在加德满都的泰米尔区有一座专门供奉他的巴格旺神庙(Bhagwan Bahah)。尼瓦尔人认为拉萨八廓北街上的佛塔⑤是为了纪念僧诃罗萨陀波怙开创尼泊尔与西藏之间贸易的功绩而建,凡是新来拉萨的尼瓦尔人都要去该佛塔对僧诃罗萨陀波怙的神像和其内的大黑天护法神及象神甘尼什的神像进行供奉[13](P62)。尼瓦尔人认为僧诃罗萨陀波怙曾在其他商人和同伴的陪同下,在西藏各地游历。他的雕像出现在了他曾游历过的一些地方,包括扎囊境内的强巴林寺[15](P99)。在加德满都,每年的法尔贡月(即尼泊尔历的第11月,大约在公历3 月)满月日后的第二天,他的神像会被游行队伍带去加德满都阿山街和因陀罗广场,这是庆祝他从西藏归来的历史性节日[4](P139)。
有一则尼瓦尔人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僧诃罗萨陀波怙曾被化身为飞马的观音菩萨从伪装成漂亮女人的罗刹女手中解救了出来。该故事称:“很久以前,传说中的西藏尼瓦尔商人的传奇祖先僧诃罗萨陀波怙带着一群人到拉萨经商。到达后不久,他们遇到了一群美女,并被她们迷住了。他们把生意忘得一干二净,整日沉迷于声色犬马。一天晚上,观音菩萨在油灯的火焰中显现在僧诃罗萨陀波怙面前。菩萨警告他,这些美丽的少女其实是罗刹女伪装的,他们应该迅速逃走。观音菩萨会变成一匹有翅膀的马,带着整个队伍飞越雅鲁藏布江。但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回头看,他们就会被恶魔吞噬。当女人们睡着的时候,僧诃罗萨陀波怙悄悄地召集了他的朋友们在破晓时分偷偷溜了出去。他们急忙赶到江边,那里有一匹马正如约定的那样等着他们。他们都爬上了马背,然后马起飞了。当女人们醒来时发现商人们已经走了,她们追着商人们跑,恳求不要把她们抛下。她们凄厉的尖叫声打破了逃亡者的自制力。商人们无视在到达彼岸之前不要回头的忠告,转过头去看了他们的情人最后一眼。于是,这些可怜的家伙们都摔死了,只有僧诃罗萨陀波怙没有回头,平安地回到了加德满都”[13](P57-58)。尼瓦尔人称这则故事在《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མིདབློ་ཟ་མི་ཏོབློག་བོཀབློད་པ།)》和《玛尼宝训(མི་ནགི་བོཀའ་འབོམི།)》(《玛尼全集》)中都有记载[16](P108)。
《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是一部成文于4 世纪末或5 世纪初的大乘佛教经典,其汉文译版由印度来华僧人天息灾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译出[17](P1029-1030),藏文版于8 世纪中期到9 世纪初期由藏族大译师襄·益西德译出[18]。《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第三卷中有一则“观音化身圣马王救度菩萨”⑥的故事,内容大致如下:释迦牟尼佛往昔为大商主时,与五百商人入海求宝,遭遇罗刹女“变发剧暴大风,鼓浪漂激其舶破坏”,被迫漂至师子国。五百罗刹女化现童女,各择其一为夫,享乐丰足。于是,罗刹女们个个与一商人归自所居,寻欢作乐。大商主(即释迦牟尼佛的前生)也与罗刹女的首领啰底迦囕配为夫妻,丰足饱满,感觉快乐无异于人间。罗刹女得遇新欢则将前一次掳来的商人囚禁于铁城,啖而食之。大商主夜探铁城,攀升瞻波迦树,被囚商人告言,罗刹女“日日食啖百人”。大商主承啰底迦囕相告,可随圣马王离开此境。于是,大商主与五百商人俱升马上。“诸罗刹女,忽闻商人去,口出苦切之声,即驶奔驰趁逐,悲啼号哭叫呼随后”,众商人贪恋美色,“回首顾眄,不觉闪坠,其身入于水中,于是诸罗刹女取彼身肉而啖食之”,终葬身于罗刹女之腹,唯大商主一人得还。当时的圣马王,即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化现,而大商主则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
该佛本生故事与尼瓦尔人传说中僧诃罗萨陀波怙的故事骨架极为相似,只有细节略为不同,《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中被救的大商主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其流落的地方是师子国,即僧伽罗,今斯里兰卡;而尼瓦尔人传说故事中被救的大商人是僧诃罗萨陀波怙,其被救是在西藏拉萨。与《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类似的“宝马救人”主题的佛本生故事还可以在《增一阿含经》⑦《出曜经》⑧《佛本行集经》⑨《撰集百缘经》⑩及《大唐西域记》⑪中找到,故事情节又不尽相同。
可以说,尼瓦尔人通过将这样一个佛经中常见的佛本生故事“本土化”,以关于传奇的或虚构的英雄僧诃罗萨陀波怙的记忆,一方面使尼瓦尔人赴西藏经商与生活带上浓厚的奇幻元素,对族群成员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有助于尼瓦尔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他们直面跨喜马拉雅山贸易旅途中未知灾难的勇气。
五、在藏尼瓦尔人眼中的西藏社会与生活
作为他者,20 世纪前半叶在藏经商和游历的尼瓦尔人对当时西藏的社会与生活也有所记述。
(一)旧西藏的农奴制
1959 年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广大农奴人身安全时时处处受到威胁,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20 世纪前半叶,长期生活在拉萨的尼瓦尔人记述了旧西藏残酷的刑罚。旧西藏的监狱不供应伙食,而是让犯人戴着脚镣、手铐沿街乞讨,乞讨不到食物的囚犯们只好挨饿,尼瓦尔人卡迈勒·拉特纳·图拉达哈在《前往拉萨的商队——旧西藏的加德满都商人》一书中写道:“囚犯们每天被释放一次去乞讨食物,因为政府无力养活他们。他们两人一组戴着手铐,人们可以看到囚犯们站在街头巷尾乞讨。一些囚犯被迫在脖子上戴一个木项圈,他们的罪名写在肩上的宽木板上”[13](P74);在旧西藏三大领主凭借对农奴统治的绝对权力,为了惩罚农奴设立有监狱或私牢,滥用刑具,对农奴随意施以酷刑,尼瓦尔人努切·巴哈杜尔·巴杰拉查亚在自传中曾记载“我在西藏遇到的最令人厌恶的事情是对罪犯的残酷惩罚。他们被扒光衣服,在大街上游街示众,并在大批人群面前被残酷地鞭打”[15](P104);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广大农奴受剥削、压迫极为严重,尼瓦尔人玛尼·拉特纳·堪萨卡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人们经常在街道中间看到罪犯,他们被扒去衣服,用绳子捆绑并被鞭打。那些犯了重罪的人,他们的头从一块大木板上的洞里伸出来,成了一道奇观”[19](P115)。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由此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尼瓦尔人关于旧西藏残酷刑罚的记载也从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旧西藏农奴的生活状态和封建农奴制的黑暗落后。
(二)西藏的天葬
天葬是藏族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丧葬方式。尼瓦尔人在藏期间对天葬进行了观察,将被天葬的尸体戏称为“摩诃萨埵”⑫(Mahasattva Raja),“当有人死亡时,他既没有被埋葬,也没有被火葬,而是被天葬,尸体在城外的一个地方被喂给秃鹫。一个特殊阶层的低种姓藏人承担了将尸体切碎这项令人不快的任务,然后再扔给饥饿的秃鹫”[4](P131)。天葬葬俗作为一种生命终结礼仪,能在西藏长久延续,有其自然和社会基础,在藏的尼瓦尔人长期与藏族人交流交往,深受藏族人影响,也有尼瓦尔人去世后就地进行天葬的个例,1935 年6 月,哥惹夏商店的老板普什帕·桑达尔在西藏去世后,就地举行了天葬,“由于普什帕·桑达尔的病情开始恶化,他决定返回加德满都。在离开拉萨四天后,他死在了马背上。人们把他的尸体带回拉萨,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举行了天葬。尸体被剁成碎片,喂给了秃鹫。他去世时享年50岁”[13](P31)。
(三)西藏的婚俗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传统婚姻类型包括: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尼瓦尔人观察到了20 世纪前半叶西藏的一妻多夫和入赘婚姻的情况。德布·绍瓦·堪萨卡·希尔克在《夏木嘎布:噶伦堡和加德满都的拉萨尼瓦尔人》一书中写道:“藏族兄弟共娶一个妻子,这是很正常的,而且似乎没有引起家庭矛盾。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个兄弟留在家里,因为其他兄弟会长期在外工作或寻找工作。如果在妻子的房间里有一个兄弟过夜,他的鞋子会被谨慎地放在房间外面,以示不受打扰。这个愿望得到了其他所有人的尊重”[4](P131);尼瓦尔人努切·巴哈杜尔·巴杰拉查亚曾以藏商桑都仓的英语家教的身份到访西藏,他在自传中称:“在西藏,婚姻方面的习俗分为两大类。通常情况下,通常是几个兄弟合娶一位妻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住在自己的家里。但也有年轻女子嫁给一个单身男子,然后把他从自己家带走和她一起生活的情况。这种入赘婚姻中的丈夫被称为玛巴(མིག་པ།)。”[15](P94)当他发现桑都仓的家庭是一妻多夫家庭时,就一妻多夫制婚姻形态下的家庭关系问题对桑都仓兄弟几人共同的妻子进行了访谈,“桑都仓兄弟共同的妻子称他们的家里充满了友好和安宁,他们的生活非常和谐,适应良好。她解释说,(一妻多夫)这种情况实际上有助于使她成为一个绝对公正的妻子,她也能够对她的四位丈夫一视同仁。她相信一妻多夫制实际上使妻子拥有了一颗宽广而博爱的心。”[15](P93)尼瓦尔人记录的一妻多夫制这种婚姻形态,在一定时期内顺应了部分藏族地区居民的生活需要,实行这种婚姻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土地和家庭财产的完整性、便于家庭集中劳动力、有利于提高他们家庭的社会地位,同时可以避免兄弟之间因分家产生冲突。
结 语
20 世纪前半叶,在藏的尼瓦尔人通过经商,与西藏社会各界维持了交往,产生了实际互动,通过日常生活和对西藏人风俗习惯的接触,尼瓦尔人逐渐了解了西藏文化和传统。20 世纪中期,受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在西藏经商与生活的绝大部分尼瓦尔人返回了尼泊尔,开始在尼泊尔本国寻找商机,从事商贸活动。
1955 年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废除了《西藏廓尔喀条约》,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两国高层开启互访,双边关系的稳定也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了中尼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往来。从前由尼瓦尔人进行的贸易规模有限、商品结构较为单一的民间性质的中尼贸易,也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建设,变为了中尼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交流。今天,我们对20 世纪前半叶生活在西藏的尼瓦尔人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增强对中尼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积淀的认识,促进中尼两国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
[注 释]
①哥惹夏Ghorasyar,藏语为གབློ་ར་ཤར།,意为“东方的庭院”,原店址位于拉萨市八廓北街。
②图拉达哈Tuladhar,原词来源于梵文,意为“天平的持有者”“执秤者”。
③夏木嘎布Syamukapu,藏语为ཞྭ་མིབློ་དཀར་པབློ།,意为“白色的帽子”,店址位于拉萨市八廓北街。
④Kamal Ratna Tuladhar,Self-quarantine,Kathmandu style[EB/OL].加德满都邮报:https://kathmandupost.com/columns/2020/08/30/self-quarantine-kathmandu-style?fbclid=IwAR0Q BsDqi-7br70MYVFr_TTXSVUj_ynNuBPEGgTo3WCJqQCRw LC4CGGNbPg.
⑤该佛塔名为“噶林各西”,西藏人认为该塔内供奉的是商人之神村本·罗布桑波的头盖骨,因为有了他的护佑,拉萨的商业才能繁荣昌盛,长久不衰。据说村本·罗布桑波是宗喀巴大师同时代的人,原籍康定,因护持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举办传召大法会有功,被宗喀巴大师封赠为“商人之神”,该佛塔今已不存。见廖东凡《雪域众神》,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⑥(宋)天息灾译:《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卷三,《大正藏》第20册,第56页中-57页下。
⑦(东晋)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四一《马王品》,《大正藏》第2册,第769页中—775页中。
⑧(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二十一《如来品之二》,《大正藏》第4册,第718页下—724页下。
⑨(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四九《五百比丘因缘品》,《大正藏》第3册,第879页上—882页中。
⑩(汉)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九《声闻品》,《大正藏》第4册,第244页中—249页下。
[11]董志翘译注,《大唐西域记》卷十一《二十三国》,中华书局,2012年,第637—640页。
[12]摩诃萨埵舍身饲虎是最著名的佛本生故事之一,参见孟瑜《谈舍身饲虎本生的起源问题》,《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