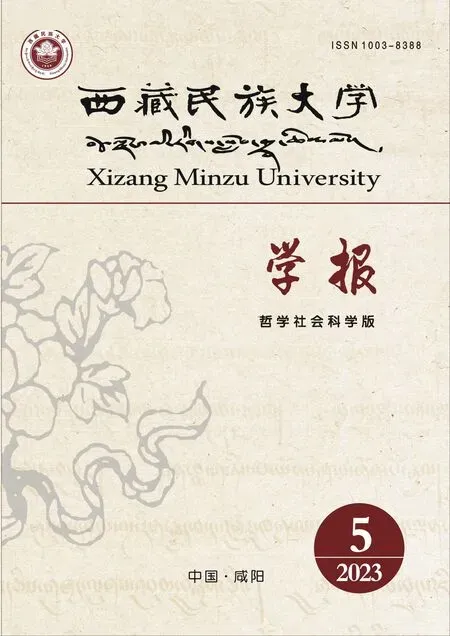论吐蕃四茹的“域岱”
曾柏亮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位处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藏南山原湖盆谷地区(简称藏南谷地),是孕育藏族及其古老文化的原始中心圈。[1](P27-37)①藏族历史上唯一统一政权——吐蕃王朝,即由这一地区雅隆河谷的悉补野氏建立。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曾在藏南谷地设立名为“域岱”(ཡུལ་སྡེཆེ།)的基层组织。探讨“域岱”相关问题,有助于直观认识吐蕃基层管理的具体情况,对进一步了解藏文明形成亦有重要意义。
熊文彬[2](P51-58)、于巴赫(H.Uebach)[3](P997-1003)、武内绍人[4](P855-856)、杨铭[5](P48)、杜晓峰(B. Dotson)[6](P147-154)、陆离[7](P147-148)、完玛多杰[8](P116-126)等学者对“域岱”已进行过一些探讨,主要集中在“域岱”性质、分布及其与敦煌西域地区“将”的关系等方面,“域岱”形成过程及在吐蕃政权中的作用等受关注较少。本文拟在吐蕃初期构建军政体制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域岱”内涵、创设及其与“东岱”关系等具体问题,以期将相关研究引向深入。
一、“域岱”的内涵
“域岱”见载于《国王遗教》《弟吴宗教源流》两部史籍。《国王遗教》载:
吐蕃境内诸王所辖“东岱”之地区,人口根据“弥岱”进行统计。上部象雄建有13个“东岱”,下部苏毗设有13 个“东岱”,其军队用以守卫唐蕃边境。蕃地分为四茹:伍茹、约茹、叶茹和茹拉。在叶茹的山谷里有16个“域岱”:“羌浦”“哲雪”“桑桑”“达德”“达日”“牟多”“节”“贤塔”“香”“门卡尔”“客热”“朗卓”“巴葛尔”“粗尔学”和“聂莫”,以上是叶茹的16个“域岱”。“囊论”对茹拉的16 个“域朱”统计如下:“白 玛”“切 垄”“定 日”“色 域”“阿 里”“巴 竹”“止 仓”“色吉域”“章垄”“夏卜垄”“娘惹”“娘堆”“藏细”“日卧”。伍茹的16个“域朱”为“堆垄”“帕尔杰”“垄雪”“墨竹”“当木”“帕郎木”“恩兰”“热”“征”“玉空”“卫”“萨科尔”“雪公”“彭域”“绒雪”“扎”。约茹的16 个“域朱”为“塔波”“阿热卜”“贡波”“雅隆”“昌岱”“聂”“罗若”“达木墟”“扎垄”“多雄”“羊卓”。[9](P185)
上文四茹蕃地有别于上部象雄与下部苏毗,指吐蕃政权发迹的核心区域藏南谷地。于巴赫[3](P999)、杜晓峰[6](P147-148)指出上述四茹之下的“域岱”“域朱”(ཡུལ་གྲུ།)都是地名,又据茹拉“域朱”由负责民政事务的“囊论”(ནང་བློབློན།)统计,认为“囊论”参与“域岱”的管理,进而判断“域岱”的行政性质,并将之译为“行政区”(administrative district)。与《国王遗教》直接记载地名不同,《弟吴宗教源流》记载四茹下辖领土各有16个“地方官”(ཡུལ་དཔབློན།),统称为“十将”(སྡེཆེ་བོཅུ།)②:
所谓“十将”,是指吐蕃各茹都有16 个“地方官”。在茹拉的十六个地方官分别是方官”“色隆巴地方官”“娘达隆巴地方官”“赤塘巴地方官”“塘章地方官”“奴布地方官”“右隆巴地方官”“东隆巴地方官”“娘堆巴地方官”“根邦隆巴地方官”及“巴荣地方官”。叶茹16 个地方官,分别是“强普地方官”“桑桑地方官”“桑噶尔地方”“官东隆巴地方官”“跌隆巴地方官”“坚隆巴地方官”“夏隆巴地方官”“切隆巴地方官”“达那隆巴地方官”“辛塔地方官”“措娘地方官”“达奴地方官”“藏雪地方官”“乌右地方官”“尼木地方官”及“扎亚地方官”。卫茹的16 个地方官,分别是“堆龙地方官”“帕杰地方官”“隆雪地方官”“墨竹地方官”“当雪地方官”“萨根地方官”“热夏地方官”“巴朗地方官”“艾朗地方官”“昌域地方官”“乌德地方官”“色曲水地方官”“昌波地方官”“聂隆巴地方官”“桑地方官”“扎绒地方官”及“彭域地方官”。约茹的16 个地方官,分别是“昂热地方官”“弓波地方官”“岗巴地方官”“亚达地方官”“钦隆地方官”“直昂地方官”“若巴地方官”“罗若地方官”“本巴地方官”“当雪地方官”“库亭地方官”“扎隆地方官”“杜雄二地方官”“扎隆巴地方官”“克苏地方官”及“亚卓纳木松地方官”。[10](P16)
两部史籍中“域岱”“十将”共有22 个可相互对应,“域岱”“域朱”即为“十将”。[2](P51-52)“域岱”长官即“地方官”,又称为“域本”。《贤者喜宴》载“域本之职责,系以法治理小地区”[11](P35),说明“域本”管辖的“域岱”是四茹下设的次级领土单位。《弟吴宗教源流》载“域本的职责是成为各地法律的根本,监督地位高的人,保护地位低下者的利益”[10](P20),即委派“域本”目的在于确保吐蕃政令制度贯彻于“域岱”。熊文彬曾据此指出“域岱”“十将”是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此言诚是。[2](P52-53)
“囊论”是吐蕃三大职官系统之一,意为“内臣”,承担国家财政税收、统计人口、供应赞普王室及中央行政事务等职能。[12](P61-63)[13](P89)[14](P62)[15](P85-86)敦煌西域古藏文文书中地方官的信函多写给“囊论掣逋”(ནང་བློབློན་ཆེཆེན་པབློ།),反映地方行政事务主要向“囊论”呈报,地方上“囊论”职官包括负责财政收支的“岸本”(རྔན་དཔབློན།)、负责后勤供应的军需官“资悉波”(རྕིརྕིགིས་པ།)以及负责牲畜管理“楚本”(ཕྲུ་དཔབློན།)等。[12](P63)[14](P86)史籍载“域本”为地方七官之首[10](P20)[11](P35),也属“囊论”职官系统。由是观之,“域本”是确保吐蕃政令下达至地方、负责当地行政事务的最高长官,“域岱”是“域本”管辖的地方区域,亦即四茹下设的基层行政区划单位。
“域岱”中有诸多以“隆巴”(ལུང་པ།)为名者,熊文彬指出“隆巴”本义指河流处或流域,逐渐演变出沟谷、地方的引申义。[2](P56)于巴赫认为“域岱”中有许多著名的河谷,多位处山谷地区。[3](P999)多杰(G.Dorje)、杰尔博(T.Gyalbo)、哈佐德(G.Hazod)等学者曾考察“域岱”的地理位置,并详细绘制了相关地图,直观地反映这些地区位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及其支流河谷地带,杜晓峰据此指出“域岱”是由地方官员管辖的农业区。[6](P148-154)[16](P200-207)
藏南谷地地貌结构表现为高山、深谷与盆地相间,气候垂直变化明显,在部分日照较长、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的河谷山麓地带,具备发展农耕经济的有利条件。[17](P135-137)[18](P15-16)[19](P51-52)吐蕃早期被称为“六牦牛部”,以雅隆悉补野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以畜牧经济为主业,布德贡杰时代农业技术开始快速发展,农耕经济在吐蕃经济结构中的地位逐步提升。[20](P2-3)随着主要生计方式由牧业向农业转变,藏南谷地人群自发地向热量较好、适宜农耕的河谷地带聚集形成定居聚落。[21](P135-136)在分裂的小邦时代,人口集中的河谷地区逐渐成为诸小邦的政治、经济中心。③农耕经济发展促使藏南谷地先民生活走向定居,也使得统一的吐蕃政权建立后,根据定居聚落划分行政区域成为可能。
综上,“域岱”是吐蕃根据藏南河谷定居聚落设立的基层行政单位。“域岱”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具体过程,将在下节详述。
二、“大行政安排”与“域岱”创设
“域岱”创设的时间,武内绍人[4](P856)、熊文彬[2](P58)均认为大致在7 世纪下半叶,但未详细讨论。作为吐蕃四茹下设的统一行政区划,“域岱”应当形成于吐蕃茹制创设之后。乌瑞(G.Uray)曾据《吐蕃大事纪年》中茹的相关记载,指出藏南谷地四茹至晚于733 年即全部存在。[22](P31-53)山口瑞凤从吐蕃制度形成的角度,认为茹制构想始于654 年,并将四茹建立时间前推至大相噶尔·东赞掌政时期(654-676)。[23](P871)笔者以为,“域岱”形成时间与山口氏所论四茹建立时间基本吻合,与噶尔氏所推行的“大行政安排”密切相关。
雅隆悉补野氏历经三代赞普经营,以武力统一藏南谷地的诸小邦以及藏北高原、唐古拉山南北的象雄、苏毗部落,建立起军事部落联盟性质的吐蕃政权[24](P124-126)。初创期的吐蕃,正如杜晓峰所言“由一群与赞普利益相同的地方统治者组成”[25]。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开始创设行政区划,将各小邦地方以新的领土单位纳入统一管理。史籍载吐蕃曾在本部、象雄、苏毗、齐布和通颊等地任命五位“执政官”(ཁབློས་དཔབློན།)[11](P31-32),学者指出上述五地是为五大“行政区”(ཁབློས།),其划分年代可上溯至7 世纪30 年代中期,标志着新国家领土结构取代旧小邦边界划分的历史进程的开始[26](P32-45)[27](P38)。后吐蕃又划分“十八势力”[11](P32-33),将特定领地分配给特定氏族,在正式承认原小邦部落领主地方特权的基础上,将其领地转变成国家行政单位[6](P363-374)。
650 年松赞干布去世,继任者芒松芒赞赞普年幼,大相噶尔·东赞掌政。噶尔氏秉政后奉行以吐谷浑为目标的东向拓展战略,由此打破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与唐朝所缔结的睦邻关系,唐蕃双方在河源、西域进入严峻的武力对峙。④这一时期噶尔氏创设诸多稳定内部、整备军事的制度,其中最重要者为“大行政安排”。⑤《吐蕃大事纪年》载:
及至虎年(654)。赞普驻于美尔盖。大论东赞于蒙布塞拉宗集会,他将人口区分为“桂”(རྒོབློད།)和“庸”(གཡུང།),并为创立“大行政安排”(མིཁབློ་ཤམི་ཆེཆེན་ཕོབློ།)制作了户册。[27](P85)
“མིཁབློ་ཤམི་ཆེཆེན་ཕོབློ།”,王忠[28](P37)、范文澜[29](P458)译为“大调发”,认为是“以田数为基础的封建负担”。王尧、陈践译为“大料集”[30](P145),黄布凡、马德译为“大调集”[31](P39),均参考汉文史籍相关记载将之视为吐蕃清查户口、检阅兵丁、征集赋税的战前措施。乌瑞指出“མིཁབློ།”与《贤者喜宴》中“ཁབློད།”“ཁབློས།”等词同义,意为“政策”“制度”“国家措施”。[25](P18-19)据于巴赫的解释,“ཁབློད།”原意为“秩序”“正确的秩序”“世界秩序”,对国家而言指“行政”“制度”“机构”[32](P21),故上文杜晓峰将“མིཁབློ་ཤམི་ཆེཆེན་ཕོབློ།”译为“大行政安排”。山口瑞凤则释为“大征兵征发制度”,即根据军事需要区分、编制“桂”(军)和“庸”(民),并分别征派兵役、民役的制度。[23](P883)张弛指出“大行政安排”是吐蕃“围绕征调兵员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统计户籍、区分军户与民户、检索户籍、征调入伍等”。[33](P38)
7世纪中叶噶尔氏主导东向进军青海地区的历史背景下,为应对与唐争夺吐谷浑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吐蕃通过“大行政安排”,构建起专为战事的军政体制。[23](P907-909)区分“桂”“庸”是“大行政安排”的前期措施[33](P38),也是吐蕃政权军事化的第一步[32](P22)。这一举措将吐蕃社会成员区分军、民,并为满足在游牧地带的作战需求,设置类似游牧千户组织的“东岱”(སྟོབློང་སྡེཆེ།)编制军人⑥,分由地方氏族首领统辖[24](P122-124)。噶尔氏以战争利益为绳索,通过设置统一的基层组织,将分散地方氏族势力捆绑于吐蕃军政管理之下。但藏南谷地农耕定居的藏族先民,不同于以移动、分散为生计特征的北方游牧者。⑦游牧民族以十进制形式将地方民众组织千户的做法,推行于农业区域则不得不受定居聚落大小的限制。换言之,吐蕃虽以游牧千户形式编制军队,清查户口、征调兵员、征集粮草赋税等军事整备事务,仍须以自然形成的定居聚落为单位展开。为此,吐蕃在农耕聚落设置“域岱”作为新的行政区划单位,委派民政长官“囊论”“域本”管辖,以保障军事行动所需的兵源、物资。又据《弟吴宗教源流》:
所谓“十将”,是指吐蕃的每个茹都有十六个“地方官将”(ཡུལ་དཔབློན་བོཅུ།)。所谓“十岱”(སྡེཆེ་བོཅུ།),是指吐蕃每个茹有八个东岱、一个小东岱和一个禁卫军,共为十个。[10](P15)
“十将”是“域岱”的总称,“十岱”是东岱、小东岱及禁卫军东岱的总称。乌瑞指出藏文史籍所载吐蕃法律、组织等制度,可追溯至654 年噶尔氏推行的“大行政安排”。[26](P23-32)“十岱”“十将”并提,似乎也可说明“域岱”“东岱”创设同步进行,二者均为“大行政安排”的内容。
综上,“域岱”在吐蕃初期构建军政体制与统一行政区划的进程中形成,“域岱”创设是“大行政安排”的具体举措之一。
三、藏南谷地“域岱”与“东岱”的关系
吐蕃为实施对外扩张而设“域岱”“东岱”,厘清藏南谷地“域岱”“东岱”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认识吐蕃核心区域基层管理的具体情况。
关于“域岱”“东岱”的关系,学界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熊文彬认为“域岱”即“庸民部”(གཡུང་གགི་མིགི་སྡེཆེ།),吐蕃区分“桂”“庸”后将之分别编制,“桂”的组织“桂东岱”(རྒོབློད་ཀྱིགི་སྟོབློང་སྡེཆེ།)为军事建制,“庸”的组织“庸民部”是行政建制,“域岱”“东岱”为茹之下平行设置的同级行政组织。[2](P55-56)于巴赫据《弟吴宗教源流》所载各茹“域岱”数量(16)是“东岱”的两倍(8),认为“域岱”即《吐蕃大事纪年》所载的“五百户”(ལྔ་བོརྒྱ།),是“东岱”的下级行政组织,每个“东岱”(千户)包括两个“域岱”。[3](P999-1001)岩尾一史指出两种观点均证据不足,只能停留在假说层面,但他没有详述具体不足所在,也没有对这一问题继续深入。[34](P494)杜晓峰曾论及“域岱”是与“东岱”不同的领地单位,但也未作进一步阐释。[6](P147)
据第一节所引,《国王遗教》所载“域岱”总数为57,其中茹拉14、叶茹16、卫茹15、约茹12。⑧四茹下辖“域岱”数量不等,而《大臣遗教》所载各茹“东岱”数量均为9 个。[35](P57-59)《国王遗教》与《大臣遗教》同为史籍《五部遗教》的内容,后者“东岱”数量并非前者“域岱”的两倍。又据《吐蕃大事纪年》:
及至蛇年(693)。赞普驻于辗噶尔。夏,于“董畿之虎园”集会议盟,任命“五百”夫长(ལྔ་བོརྒྱ་ཆེཆེན་པབློ་བོསྐོབློས།)。[30](P148)
及至羊年(707)。……冬季会盟由大论乞力徐于温江岛召集之。改五百长为小千夫长(ལྔ་བོརྒྱ་སྟོབློང་བུ:རྗེཆེར་བོཅོབློས།)。[30](P150)
“五百长”即“小千夫长”,亦即藏文史籍所载“小东岱”的长官。“小东岱”与“东岱”同属于“十岱”,二者性质相同,只是所辖军人数量不同。证实“五百户”“域岱”等同,尚需更充分的证据。
《国王遗教》载“བོབློད་ཁམིས་རྒྱལ་པབློ་སྟོབློང་སྡེཆེའགི་ས་ཁུལ་ན།།ཡུལ་གྲིགི་མིགི་ལ་མིགི་སྡེཆེའགི་གྲིངས་བོཏོབོ་པ།”。[9](P184)熊文彬汉译为“吐蕃王朝千户所辖之地,为计居民而设mi-sde(མིགི་སྡེཆེ།)”,据此认为“misde”是“与其语义学内容相称的地方行政组织机构的专有名称”,并将其释为“域岱”的异称;“mi-sde”同于“庸民部”,与“庸民部”对应的“桂东岱”是军事建制,因而“弥岱”“域岱”属行政建制。[2](P53)
藏文“མིགི།”(mi)意为“人”,“སྡེཆེ།”(sde)意为“品类”“群体”“集团”,“མིགི་སྡེཆེ།”本义为“人群”。[36](P1471)上述《国王遗教》中的材料,于巴赫译为“吐蕃境内诸王所辖东岱之地区,人口根据“弥岱”(མིགི་སྡེཆེ།)统计(登记)”[3](P999),杜晓峰译为“至于吐蕃东岱诸王的领土,以及这些地区耕地人口的统计”[6](P205)。据二氏译文,“弥岱”只是统计人口的形式,不具有地方行政机构组织的含义。
又《国王遗教》载:“保卫唐蕃边界的‘东岱’,听从‘苏毗弥岱’(སུམི་པའགི་མིགི་སྡེཆེ།)的命令,受命管理“弭药”(མིགི་ཉག།)地区的边界。”[9](P184-185)“弭药”即党项[37](P5292),在松赞干布时期已臣服吐蕃,其地毗邻吐谷浑、位处唐蕃边界地带。若据熊氏“东岱”“弥岱”平行设置、分属军事和行政建制的论断,在以防卫唐蕃边界为目的的军事安排中,军事建制“东岱”反而受命于行政建制“苏毗弥岱”,孰不合逻辑。
《弟吴宗教源流》载:“‘岱本’(སྡེཆེ་དཔབློན།),是‘弥岱’的长官。”[38](P252)“岱本”一词见于古藏文文书P.T.1283(2)《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
自默啜而西,蕃人称之为突厥九姓,九部落联盟之首长(སྡེཆེ་དཔབློན་ཆེཆེན་པབློ།),名之为“回鹘都督”。
其北,有“拔悉蜜”五部落。“拔悉蜜”部落长(སྡེཆེ་དཔབློན།)即可汗大位。
“合督葛”部落,酋长(སྡེཆེ་དཔབློན།)“颉吉尔高尔俟斤”。[39](17-18)⑨
《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是吐蕃北方居民的资料汇集,反映8-9 世纪藏族先民对北方近邻部族的认识情况。[39](P16-17)游牧部落首领的权力“建立在一个移动社会的机制上”[17](P44-45),其权威主要体现在对牧团的逐级支配。根据游牧民族权力的这种特点,吐蕃将回鹘、突厥等部落首领称之为“岱本”。吐蕃效仿游牧民族千户组织设置“东岱”编制军人,“东岱”内部各级长官也统称为“岱本”。《谐拉康碑》西面碑文载:“其(娘氏)部落“岱本”(སྡེཆེའགི་དཔབློན་པབློ།)之职,仍予世袭承传。”[40](P116)为维持军事部落联盟政权的稳定,吐蕃内部常以缔约盟誓的方式确定、巩固、约束君臣、部落、家族之间的关系或职责,并立碑石刻以使誓约永固。[41](P7)娘氏在“约茹”坐拥巨大势力,其成员不仅任职“东岱”长官,还担任约茹上部四个“东岱”的指挥官。[42](P523)正因娘氏成员在“约茹”各级军事组织中世袭任职,赤德松赞赞普与娘·定增埃盟誓所立的《谐拉康碑》中才会以“岱本”之名统称之。
“岱本”既然可用以称呼“东岱”各级长官,“岱本”管辖的“弥岱”,自然也可指“东岱”内的军人。上引《国王遗教》材料中“‘东岱’地区人口按‘弥岱’统计(登记)”,指将一定数量的人口编入军事组织“东岱”,而非设置“弥岱”这一行政组织;“保卫唐蕃边界的‘东岱’,听从‘苏毗弥岱’的命令”,意为将吐蕃其他地区征派而来的军队交由苏毗统一管理,并非军事组织受命于行政建制。因此,仅从语义判断“弥岱”等同于“域岱”或“弥岱”等同于“庸民部”,同样猜测居多而实证不足。
“域岱”“东岱”的关系,在《弟吴宗教源流》有十分明确的记载:“此时,‘十将’法和‘十岱’法是吐蕃之总法(ཁྲིགིམིས།)。”[10](P15)“ཁྲིགིམིས།”基本义为法律,可组成国法、法规、法令、法典等词,与古汉语“律”含义较为切合。[43](P4)据敦煌古藏文法律文书,吐蕃时代的“法”既包括“以正罪名”“正刑定罪”的律的条例,也包括“以事成制”“设笵立制”的令的内容。[44](P122)藏文史籍中“ཁྲིགིམིས།”不仅指律令,还涉及吐蕃行政区划、赋税征收、军事安排等内容,因而具有政策、制度的含义。[45](P70)“十将”“十岱”是吐蕃之总法,即“域岱”“东岱”同为吐蕃的基本制度。
吐蕃四茹下设的“域岱”是据地理环境下自然形成的聚落而设立的行政区域单位;“东岱”是由一定数量军人构成的军事组织,军事集合点或驻扎点位于交通要道、战略要地或按大方位设置[2](P56),以为其提供兵源的“域岱”所在地为其征兵区域。“域岱”辖区大小与人口数量受自然环境及人口迁徙的影响,而“东岱”军人成员数量是固定的,一个或数个“域岱”中征派一千(户)“桂”组成“东岱”。藏文史籍记载部分“域岱”与“东岱”同名,是因为这些“域岱”规模较大,足以单独提供一千人的兵源。
藏南谷地“东岱”以“域岱”为资源汲取单位,“域岱”为“东岱”提供军需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吐蕃早期军事扩张的制度基础。
余 论
吐蕃政权建立之前的小邦时代,藏南谷地因自然条件与农耕技术发展,在河谷地带形成了若干定居聚落。7 世纪中叶,噶尔氏为加强中央集权以实施向外拓展政策,在这些聚落设置“域岱”作为基层行政区划单位,以“域本”为管辖“域岱”民政事务的地方长官;同时为适应在游牧地带的战争需求,效仿游牧民族千户设立“东岱”,作为编制“域岱”人口的军事组织。“域岱”“东岱”在吐蕃构建军政体制的进程中同步创设,二者是平行设置、不同性质的基层组织,共同服务于吐蕃军事拓展的政策,藏南谷地基层管理实施行政、军事分立的双轨制。
藏文史籍记载“东岱”不仅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领地划分单位。⑩据古藏文文书,噶尔氏创设“大行政安排”约一百四十年后,吐蕃统治的于阗、敦煌地区出现名为“将”(tshan)的组织,学者指出“将”源自吐蕃本土的“地方官将”(“域岱”)[5](P44-49),是“东岱”的下级组织[4](P848-862)[7](P137-170)。“东岱”性质及其与“域岱”关系的变动,反映吐蕃军事拓展过程中基层组织的变动,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讨论。
[注 释]
①4世纪以前象雄文明率先兴起于西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后因气候变迁等原因逐渐衰落,西藏文明中心东移至藏南谷地。参见许若冰.从象雄到吐蕃:气候变迁与西藏文明中心的东移[J].中国藏学,2022(6):108-116.
②“十将”并非十个将,而是指多个将。杜晓峰指出单位数量与具体数量不一致是藏文史籍中类似列表的共同特征,即通常试图将大量单位放入一个预先设定的结构中。参见Brandon Dotson. Administration and Law in the Tibetan Empire:The Section on Law and State and its Old Tibetan Antecedents,D.Phil.Thesis,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Oriental Institute,University of Oxford,Trinity Term,2006,p.134.
③佐藤长曾指出农耕的存在是堡寨建设、维持的重要因素。小邦首领以高处的堡寨为中心,统治高山、河谷间从事农耕、畜牧的定居人口,当是藏南谷地诸小邦的实态。参见[日]佐藤长著,金伟等译.古代西藏史研究[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9:530.
④雅隆悉补野氏统一各小邦后,西藏高原内部分裂势力得到整合,社会渐趋安定。自然环境对人口增长的制约,迫使吐蕃向外扩张寻求更多的生活资源;又因吐蕃是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军事联盟政权,为巩固内部稳定而不得不向外扩张以保证各部落贵族的利益;地理环境以及吐蕃政权性质等因素外,吐蕃君臣耻居人之下、其他君主必须臣属于赞普的观念也是吐蕃军事扩张的重要原因。受地缘、文化等因素限制,吐蕃王朝的扩张只能东向进行。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位处沟通西域绿洲、关中盆地、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的关键位置,是吐蕃东向经略、巩固国防的必争之地。参见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第二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113-156;林冠群.论唐代吐蕃之对外扩张[A].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21-226;林冠群.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关系[A].林冠群.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182-198;陈柏萍.吐蕃东扩略论[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42-47;[日]松田寿男著,周伟洲译.吐谷浑遣使考(下)[J].西北史地,1981(3):97-98;安应民.略论噶氏家族专权时期唐蕃之间的吐谷浑之争[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2):30-31;陈楠.公元七世纪中后期唐、蕃对吐谷浑的争夺[A].陈楠.藏史丛考[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98-102。
⑤“大行政安排”之外,《吐蕃大事纪年》还记载噶尔氏652年抚服“珞”“赞尔夏”,653 年“大论东赞于‘祜’定牛腿租。达延莽布支征收农田贡赋”,655 年“写定法律条文”,656 年“征收牛腿税”。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45.
⑥托马斯(F.W.Thomas)较早指出吐蕃军队与匈奴的相似性,图齐(G.Tucci)也认为西藏军事制度与北方蒙古、突厥等游牧民族类同,推测吐蕃军队中有万、千、百、十户等组织。佐藤长认为古藏文文献中虽未记载万户、百户、十户的事例,但从确切记载的千户用语可以推测类似组织存在,吐蕃采用此种军事体制很可能是受北方民族影响。类似观点在戴密微(P. Demiéville)、石泰安(R. A. Stein)、切格莱迪(K. Gzegledy)的论著中也有所提及。陆庆夫、陆离更具体地指出吐蕃军事编制中的十进制形式源自突厥。参见Frederick William Thomas.TibetanLiteraryTextsandDocumentsConcerningChineseTurkestanPart I: Literary Texts,Royal Asiatic Society,1935,p. 285; Giuseppe Tucci.Tibetan PaintedScrollsⅡ,Roma: Lalibereria Dello Stato,1949,p.738;[日]佐藤长著,金伟等译.古代西藏史研究[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9:525;陆庆夫,陆离.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63-64.
⑦从人类学的视角,游牧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为应对热量密度低且充满变化的自然环境,游牧民须时常移动、分散以利用变动无常的水草资源,及时躲避各种风险。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45-93.⑧《国王遗教》中约茹的“域岱”未列举完全。.
⑨材料中藏文据今枝由郎转写的拉丁文回译,转写见Yoshiro Imaeda,Tsguhito Takeuchi,Izumi Hoshi et al.(eds.).Tibetan Documents from Dunhuang,ILCAA,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07,pp.179-180.
⑩《贤者喜宴》记载了各“茹”的边界,可以确定“茹”的行政区划属性。“茹”之下部分“东岱”名称与西藏地区现代地名相同,反映“东岱”是区划单位,也是学者确定“东岱”所在地理位置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