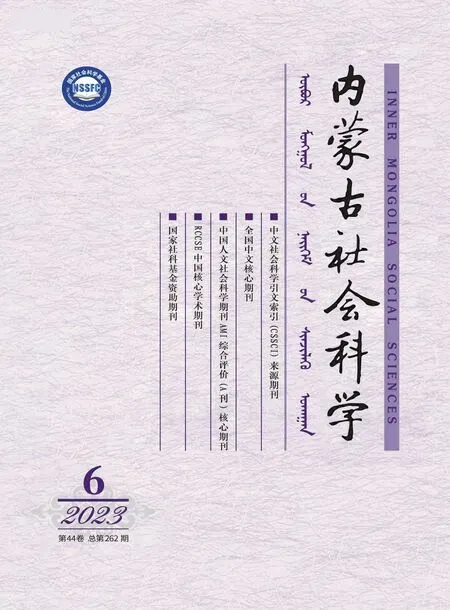北部边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崔思朋
(内蒙古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核心与紧要任务,但兼顾到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就需要有区别地对待不同区域及不同民族的特殊性。(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9页。由于各民族分布地域不同,彼此之间差异显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陆域边疆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历史上“农耕区的西北、东北先后成为匈奴、氐、羌、柔然、突厥、回纥、铁勒、薛延陀、沙陀、吐谷浑、党项、蒙古以及濊貊、肃慎、挹娄、夫余、乌桓、鲜卑、室韦、库莫奚、豆莫娄、乌洛侯、地豆干、勿吉、奚、契丹、靺鞨、满等非农业民族或部族的活动区域”[3](PP.298~299)。生活在北部边疆的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疆域内其他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如赵武灵王时期的“胡服骑射”弱化了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冲突,推动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互动与互鉴融通,展现了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4],增强了生活在北部边疆的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民族之间的交融。顾颉刚说:“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如“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5]。因此,生活在这一北部边疆的各个民族在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梁启超在20世纪初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6](P.4)继而又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7](P.82)随后,孙中山提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8](PP.528~529)、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5]、傅斯年提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9](P.125)等观点,逐步确立了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元统一的“共同体”(2)英国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指出,共同体“似乎从来没有用负面的意涵,并且不会被赋予明确的反对意涵或具区别性的意涵”,而是“具有‘直接、共同关怀’的意涵”。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1页。的基本结论。
历史上,中国疆域内出现过的各个民族在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共同缔造并形成了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历史走到今天并继续走向未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影响下,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或是被其他文明取代的国家,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延绵不绝、经久不衰。中华文化扎实之根脉、醇厚之积淀,恰如有源之水,滋养着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创造、新发展,给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最深厚的历史根基。”[10](P.292)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确保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之根本,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一脉相承。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其间经历了无数“天灾”与“人祸”的考验,更是多次直面危亡,但中华民族都能以华夏儿女所特有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英勇顽强的精神进行抗争,在危机中崛起,在多难中兴邦。
如距离我们最近的晚清近代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中屡屡失败,并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3)中国即便在中法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但同样签署了不平等的和约。,国内也掀起了多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在内忧外患局面的猛烈冲击下,中国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许多仁人志士投身到救亡图存的事业中,但终究因对中国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及缺乏正确理论指导,没能成功。(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实现民族独立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正确道路。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说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1](P.35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要“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12](P.355)1938年中共中央又提出要建立“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13](P.760)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4]。中国疆域内出现过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并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历史作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经历了无数磨难与危亡之际的考验,中华各民族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的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维系着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因而A.J.汤因比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15](P.294)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虽然出现过对立冲突乃至于兵戎相见,但始终保持着多元一体的格局继续向前发展,对此费孝通指出,各民族在相互“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及“分裂和消亡”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6]。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其“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17](P.150)。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国疆域内出现过的所有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基本概括,且深深地融入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维护及巩固着共同体并发挥其在党和国家民族工作中的作用,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目标。换句话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是不断巩固和加强广大民众对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8]但由于各民族所处地理位置与本民族文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及作用不尽相同,这就需要我们有区别地对待不同区域及不同民族的特殊性。
二、北部边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突出历史贡献
目前北部边疆已发掘的人类文明历史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窑遗址到青铜器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朱开沟文化,跨越了数十万年,同黄河与长江流域一样有着悠久的人类历史。伴随着中国疆域不断向外拓展,越来越多的民族融入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内,但中国四周分布有高原、山地、沙漠及海洋等多种自然实体,使中国疆域呈现出相对封闭的空间特征。(5)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中国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久远,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山脉、沙漠和辽阔的太平洋所隔断。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吴象婴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9页。这也导致边海与边高原地区成为古人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唯有农牧交错带的正北方、西北方,非农耕民族的游牧生活所依托的草原与荒漠,成为疆域伸缩的舞台,以疆土为背景的武力争雄与文化交融几乎可称这一地带上演的历史主剧目”[19]。因此,在中国广阔的陆域与海域边疆中,北部边疆尤为特殊,不仅在史前时代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及中华民族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之一,而且是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安定的关键所在,中原农耕民族与诸草原民族在这一地带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碰撞与交融。北部边疆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区位,北部边疆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
(一)北部边疆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疆域内就已出现了存在一定差异但又紧密联系的区域性人类活动与人类文明早期形态。作为中国早期人类重要分布区域之一的内蒙古地区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30余处。如大窑遗址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遗址中发现了一处罕见的大型石器制造场,出土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锥状石核等石器具有细石器特征,与华北地区细石器存在一定关联。[20]细石器起源于华北地区并以华北地区为中心扩散至周围广大地区,传入北部边疆后取得了一定发展也体现出此时期北部边疆与其他区域人类之间的密切交流互动。又如萨拉乌苏遗址,学界有关中国现代人起源存在“近期出自非洲说”和“多地区进化说”两大观点,其争论的关键点之一是早于6万年前的中国是否存在具备现代人特征的古人类,河套人化石属于晚期智人(距今约14~7万年),虽保留一定原始性状,但体质特征已接近现代蒙古人种,具备现代人特征。[21](PP.226~227)河套人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古人类是本土起源,同时也表明北部边疆作为中国早期人类起源的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奠定了多元一体特征。
新石器时代内蒙古地区已发掘的遗址有100多处,影响较大的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海生不浪文化及老虎山文化等,尤以红山文化的跨越时间最长、影响也最深远。如“牛河梁遗址”出土了大型祭祀中心,里面存有规模宏大的庙、坛、冢等,其中有一处圆形三重大坛,外圈直径是内圈直径的2倍(内直径11米、外直径22米)[22],与首见于《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图”所示外内衡比值相同(6)七衡图将太阳周日视运动轨道设想为七条同心圆,由内到外分别为一衡、二衡……七衡,两衡之间空隙为“间”,直线距离相同,太阳每移动一衡相当于1个月,从一衡移动至七衡后再回到一衡需要1年(12个月)时间。参见程贞一等译注《周髀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4~89页。,表明人类文明起源时期北部边疆的一些文明要素对后世人类文明发展产生的影响或存在着关联。红山文化还出土了大量玉器,以玉龙最具代表性。北部边疆带有龙元素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兴隆洼文化的石块堆塑的龙、赵宝沟文化的龙游云端图案及红山文化后期龙纹的抽象化等。对龙的崇拜和以玉为贵的思想是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特征,在距今55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普遍形成了对龙的崇拜和以玉为贵的理念,也出土了与北部边疆极为相似的龙形玉器,这些人类遗址虽然相距甚远,但却存在如此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各个人类文化区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交流,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及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基础。[23]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区之间的交流互动推动了各区域人类逐渐形成了相互依存且不可分离的关系,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部边疆人类文明渐渐汇入中华文明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上的交流互动也表明北部边疆与其他地区存在密切往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北部边疆逐渐过渡至青铜器时代,西方学界曾将青铜器视为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准之一(7)中外学界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界定标准并不一致,一些西方学者把城市、文字、青铜器视为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将中华文明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中国而言,将社会分工、礼仪规范、人口增加与集中分布导致出现的城镇聚落、文字记录及历法或法规、阶级分化等纳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界定标准,由此判定中华文明起源至少可以推至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参见崔思朋《中华文明起源视域下的北部边疆》,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2期。,但青铜器时代已是中华文明进入完善甚至是早期阶段。北部边疆的青铜器文明具有深远影响,如“鄂尔多斯青铜器”,目前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北、辽宁、河南、新疆及北京等地的数十处遗址中均出现了带有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征或样式的青铜器,只是以上各地出土的此类青铜器与当地其他类型青铜器混杂分布,数量及种类较少,年代也晚于鄂尔多斯地区最早青铜器的出现时间,应是受到鄂尔多斯青铜器文明的影响。[24]北部边疆还出土了与龙相关的青铜器,如“蟠龙盖罍”,是西周早期盛酒器,目前全国共发现4件,内蒙古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1件,四川彭州2件,湖北随州1件。由此推知,商周时期带有“龙”元素的青铜文化已传播至很多地区。[25]在三个距离较远地区发现的极为相似的“蟠龙盖罍”说明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早期就已经在意识上与其他区域有了某些一致性,说明新石器时代之前北部边疆与其他地区就已存在交流互动的事实,这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基础。
自青铜器时代开始,“游牧”逐渐成为北部边疆的主要文明形态。《史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牲畜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26](卷110P.2879)游牧需要对草原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进行精准把握与合理利用,以有效维持草原民族生存发展与草原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如五世纪的科尔沁地区,契丹部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27](卷100P.2223)。至六世纪时,因契丹人数十年发展游牧经济,当地自然环境有所恢复。《北史》载:“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真君以来,岁贡名马。献文时,使莫弗纥何辰来献,得班乡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28](卷94P.3127)
综上可见,北部边疆在人类文明起源时期以原始农业为主,至青铜器时代,因自然因素波动影响出现了由原始农业向畜牧业的过渡。随着青铜器时代以来农业分布范围逐渐南退,在北部边疆南部区域形成了农牧业交错分布的过渡带,这一区域也成为农耕与草原民族碰撞、交融最活跃的区域,两种文化彼此汲取、互相注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二)北部边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部边疆及以北地区是辽阔的欧亚草原带,欧亚草原带从东亚的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西欧的匈牙利,是历史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地理大发现以前,尽管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美洲地区的文明和商业也很繁荣,但基本上处于各大陆地区的内部交流状态。欧亚大陆(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区)内部由于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补充,其联系更加紧密,商品贸易交流更加发达。[29](P.34)但生活在欧亚草原带的草原民族也与临近的农耕民族之间存在着对立冲突。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它为由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向外伸展的各文明中心进行交往提供了一条陆上通道。靠大草原养活的游牧民们总是赶着他们的牧群,到处迁徙,并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攫取北京、德里、巴格达和罗马的财富。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30](P.59)这种草原民族与邻近农耕民族之间的对立冲突在中国北部边疆最为显著。北部边疆所处的地理区位使其成为中国疆域波动及各民族碰撞与交融最频繁的区域,同时也是各中原王朝国家治理尤其是对边疆民族地区施政的核心区域。
赵现海将“北中国亚洲内陆与北方平原接壤地带”称为“核心边疆”,并指出,“核心边疆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扩张权力、统一全国的‘地理阶梯’与‘经济过渡区’,可以合称为‘过渡阶梯’”,“为得到核心边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方族群在这一地带投入了最多的精力与资源”。[31]“核心边疆”即包括北部边疆的主体区域,这一地带同时受到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的高度重视,是双方争夺的重点区域,由此影响到农牧业的分布范围,直接体现在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波动上。一般而言,当中原王朝处于强盛时期,往往在实际控制这一地带时会推行农业,从而向北方及西北方拓展了北方农牧交错带分布范围;相反,若是草原民族强盛时期,游牧经济也会随其控制区域向南拓展,出现相同方向的波动,导致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南缩。但也存在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双方在碰撞与交融过程中,草原民族会接受农业(以农耕区出产各种物资为主),通过贸易获取、武力掠夺或自身发展一定的农业等方式满足这一需求,由此促进双方的交流融合(8)王方晗就汉朝与匈奴之间的交往指出,汉朝的“农作物渗透到了游牧文明中,作为罕见珍贵的外来产品深受匈奴贵族的喜爱,不仅成为饮食的一部分,也在墓葬文化中占据了特殊的礼仪性位置”。参见王方晗《汉代黄河河套区域农业发展与边疆农牧文明的互动与融合》,载《民俗研究》2021年第6期。,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至关重要。随着秦汉以来中原王朝控制疆域向周邻地区拓展并与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之间碰撞与交融的增多,东、西、南三个方向的陆域边疆分布范围因地理环境制约逐渐稳定下来,北部边疆的范围波动逐渐凸显并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活跃的区域。此后,“中原王朝疆域的伸缩变化,主要是与北部干旱和半干旱区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之间”[32],也即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及物资而导致的,几乎贯穿于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并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疆域波动。韩茂莉将中国疆域形成过程划分为“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19],第二与第三阶段均围绕着北方农牧交错带展开。第二阶段出现在秦汉时期并一直持续到明代,北方疆域围绕着北方农牧交错带出现多次南北波动;第三阶段出现并完成于清前中期,一直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战败导致领土遭到侵略。但在第三阶段,中国疆域突破了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地理界限,向北方农牧交错带以北及西北地区大幅度拓展,北部边疆也成为秦汉以来各中原王朝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清人张曾对此有这样一段论述:“云朔以北,沙漠以南,为华夷交界,从古战争之地,见诸史策者最多,不独一州一邑,难以几及。即以一行省之大,亦无如此事蹟之繁,记载之富者。廿一史汗牛充栋,边事每居十之二三,西北边防较别处尤重,此间属南北管钥,中外强弱之势,即以其地之属南属北定之。三代以前,远难稽考,自赵主父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之后,迄我朝臣服土默特蒙古以前,干戈代兴,几无虚岁,非若他志,于兵戈一门,寥寥数纸可以尽之。”[33](PP.317~318)北部边疆作为历史时期中原农耕区与草原游牧区的中间过渡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部边疆及西北地区的稳定与清朝的有效治理对于中国疆域形成的意义重大。格鲁塞评价道:“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既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34](P.670)直到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疆土之前,清朝疆域不仅辽阔而且完整。因而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在北部边疆的碰撞与交融持续不断。在此过程中不仅促进了中国疆域的形成,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北部边疆因其地理区位而强化了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
三、北部边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国情基础上的。今天的中国是由汉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及一些未被识别民族共同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把历史上那些出现在中国疆域之内但又消失的民族也算在内,那么中国的民族数量则更多。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一书中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并论述了这一特征是中国能够保持高度统一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关键所在。[35]秦汉以来,作为绝大部分历史时期的中原王朝统治者,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长期稳步地深入到其他民族之中,建立起汉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其间虽然不乏对立冲突乃至于兵戎相见,但由此也建立起了各民族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网络,并把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形成了更加紧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北部边疆及生活在本区域的各民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是古代中国繁荣昌盛的基础
北部边疆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西方学界多将长城视为中原王朝防御草原民族的边界线,而且这样线性割裂双方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历史记述中也普遍存在(9)马立博指出:“在遭遇新的环境和族群时,汉人和他们的编年史家总会陷入这样的叙述模式:蛮夷和他们的环境就应该被驯服和教化。持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将汉人描述成一股积极进取的力量,而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其生活的环境,则仅仅是被改造的对象。在这种‘自然—文化’二元结构中,以汉人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总是将汉人置于‘自然’之上或之外,而‘自然’则是终将要被汉人‘教化’的,其他的族群和环境也都应该接受汉人的改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参见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6页。,导致我们在相关历史解释中出现困难或矛盾。西方学界对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内陆亚洲”学说,此学说奠基者拉铁摩尔指出,“中国的长城线是世界的绝对边界之一”[36](P.17)。近代日本企图瓜分中国领土时也大肆鼓吹长城以外非中国,如田村实造等借助美国学者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提出了“北亚历史世界论”,人为地把长城以北的草原民族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来,为日本侵略中国开脱罪责。[37](P.624,648)很显然,这种线性割裂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就需要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探寻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各个民族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有力回击那些分裂中国、歪曲中国历史的不当言论。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强盛王朝的出现离不开对边疆地区尤其是北部边疆的有效治理。正如巴菲尔德指出的,“中原与蒙古高原交界地区占据了其北部边地的中心”[38](P.23)。他进一步解释道:“从蒙古高原的边缘向南俯瞰中原,则以长城为界。很难确定这里的边界线,因为它横跨着一个过渡区域,这一区域既生活着游牧民,也生活着农民。尽管这里没有牧地以吸引游牧民,但是中原的富庶使得这块边地成为将草原各处的部落吸引过来的一块磁石。对草原民族来说,中原是财富的宝库,这是一块边地市场欣欣向荣而粮食、衣物以及俘虏源源不绝的地区。它还是能从中原王朝那里当作礼物勒索到的诸如丝酒之类奢侈品的来源。”[38](P.23)随着秦汉以来中国疆域范围向周边地区拓展,中原王朝与生活在北部边疆的各民族逐渐发生关系。强盛时期,中原王朝治理下的北部边疆地区长期维持着和平稳定局面,尤以秦与西汉、隋唐及清代最为显著,这三个时期的中国均建立起了强盛的大一统王朝,同时也是北部边疆较为和平稳定的历史阶段。
尤其到了清代,清前期统治者注重开发边疆,大大改变了“重中原,轻边疆”[39](P.105)的传统观念。正如康熙所言:“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40](P.677)清朝将整个蒙古草原视为北部边疆,这是清朝与以往中原王朝治理北部边疆的最大不同。随着清朝对蒙古问题的有效解决,北部边疆及以北的蒙古草原上的和平稳定局面长期存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土地开垦及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北部边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亦如雍正言:“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41](P.99)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进一步指出:“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42](P.5)
北部边疆和平稳定局面的出现促进了生活在此区域中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推动了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繁荣发展。王钟翰指出:“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创制、执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但超周、秦、汉三代,甚至连显赫一时、地跨欧亚二洲的大元帝国亦瞠乎其后。”[43](P.225)邹逸麟也认为:“清代前期统一帝国的形成,是将两三千年来,形成的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三大经济区融合在一个政权之内,是三大经济区的民族在长期相互交流、融合的自然结果。”[32]以上有关清代中国疆域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较高评价,缘于清朝对北部边疆的有效治理,体现出北部边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奠定了北部边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二)北部边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以今内蒙古地区为主体区域的北部边疆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历史上,北部边疆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尤其到了清代,随着汉、回等民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并与当地蒙古族及其他民族的深度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多数、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存的社会状态,这是今日内蒙古地区多民族聚居的基础。
内蒙古地区位于祖国正北方,外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边境线长达4200多公里,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区域特色与民族文化特色鲜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内蒙古有汉、蒙古、满、回、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49个民族,在全区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8935537人,占78.74%;蒙古族人口为4247815人,占17.66%;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865803人,占3.60%。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715150人,减少3.64%;蒙古族人口增加21722人,增长0.51%,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增加36262人,增长4.37%”[44]。当下内蒙古地区仍然是多民族聚居区,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稳中有增。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北部边疆不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同样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工作,充分肯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在民族工作中做出的成绩。习近平总书记三次(2014年1月27—28日、2019年7月15—16日与2023年6月5—8日)到内蒙古考察调研,连续5年参加全国人大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审议。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内蒙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在促进民族团结上具有光荣传统,长期以来拥有‘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要倍加珍惜、继续保持。”[45]这些都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内蒙古地区的高度重视。
内蒙古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疆民族地区,不仅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早探索者与践行者,在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更是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也必将承担起重要的历史使命。对此,“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着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46]。这就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北部边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需要我们立足现实、充分重视北部边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愈是整合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愈丰富,愈有生命力,而一个文化体系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它的整合能力就愈强”;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整合各民族文化特质”,使中华民族“如滔滔江河,川流不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47](P.240)各民族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纽带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共同体内部,“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48]。中国辽阔的北部边疆及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直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这也决定了北部边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