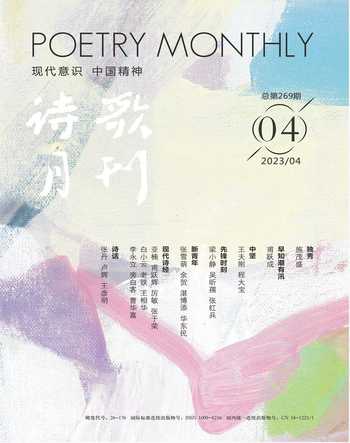在霍山(组诗)
在佛子岭水库
大坝高耸,从这让人眩晕的高度俯瞰
水面遥远如万劫不复的一跃——
刹那的悬想,让人心头战栗,而手心
在用手机拍下水面时,有隐约的颤动
高处不胜寒,我们行走,在心的跳动和
似有若无的风中。无人谈论历史
怎样用钢铁之心和凡人之手,建造起
这让后人心惊的高度。我们说笑着
为此刻无可置疑的安全,和并不存在的
危险。有人极目远眺,谈论水里的鱼虾
和远处岸边的一座小屋。屋檐低矮
仿若置身七十年前的岁月,人影不见
几只雪白山羊,在坡地啃食发苦的青草
它们聚拢又散开,如时间易逝的水花
它们咩咩连声,如历史虚渺的回应
在月亮湾作家村
砖墙冷硬,拒绝岁月的抚慰
在其冷硬之上,有灰白笔迹:
这是一个时代
最后的执拗。那些油灯下的面孔
从皱纹的曲折里延伸出道路
有的锄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有的镰刀与磨刀石拉扯之后
在麦子耿直的脖颈上一试锋刃
闪亮的刹那,有叹息从鼻孔升起
有烟尘在脚下的土地制造一片
短暂的迷雾——时间是怎样过去的?
当这灰白的字迹仍旧盘踞在
冷硬的墙头,被风吹,被雨淋
但拒绝消失——它注目一群群人
不断老去,衰朽,注目一群群人
不断出生,成长,在年轻的日光里
重复陈旧的故事:所有的故事
都不会白白发生,都不会了无痕迹
它们必将被写下来,被装订成册
这无数的册页,此时就在这墙后
一排排的书架上。它们可能被遗忘
被篡改,但它们始终在那儿
以依稀真实的面目,深埋在
暗藏着焰火的薄薄纸面之上
在石斛种植园
山坡缓慢爬升,松林疏密有致
松风如涛,日光斑驳,在这堆积的寂静里
石斛矮小,碧绿,以轻柔的呼吸
铺展身姿。它们不以土壤为食
只以木屑和人间的露水喂养自己
日积月累,黏稠的汁液,在鼓胀的
躯体里辗转,微涩?微酸?回甘?
多少旧梦重回,那时它们出现在
皇宫,王府,或钟鸣鼎食之家
如今它们在寻常百姓家,被托付
健康,长寿,和更多祝福——而此刻
寂静如斯,我们说话也不觉压低声音
看它们在时光里缓慢生长,在错置的
季节里,结几粒绿果,开几朵白花
在河边
河水潺潺,有人在岸边浆洗衣服
一段流水,几棵大树,几片竹林
还有一座吊桥的摇摆,一齐将时间的指针
调慢,停滞,往回拨——河边的人走了
又回来了;河边的人年轻过,但老去了
多少故事,在河边发生,结束
多少故事,昨天的今天的并无不同
你从旧故事里伸出手来,拈一朵蒲公英
送至我面前,刹那的犹疑,吹一口
微小的风,蒲公英洁白的思绪便四散了
只余几畦菜蔬,一架丝瓜,绿着
在这初秋时节,在这短暂的交错里
甫跃辉,云南人,现居上海。参加《诗刊》社第37届青春诗会、《十月》雜志第12届十月诗会。著有诗集《去大地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