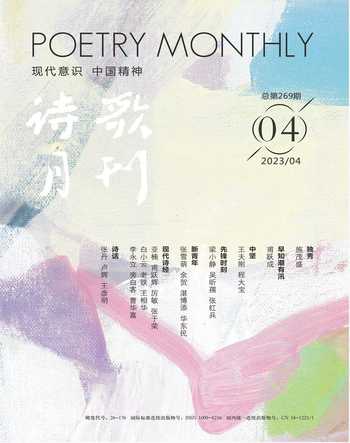野山楂(组诗)
程大宝
潋滟与空蒙之间
残花孤寂如持戒,如
静心打坐,等果实
楫棹不可等,芟荑可等
歌谣不可等,心音可等
看,那些匆匆者必有落英能踏
那些驻足者定有影像被删除
无心人,请你给我一张处方
在潋滟与空蒙之间
旗幡
你不要说什么都不知道
她已经越来越近了,距离
我难以确定。你看她
手势如风,仿佛自己吹拂着自己
自己告诫着自己,因而
一次次被灌满,一次次被撕裂
一次次凸显、消散
那是悲愤的断裂力
那是因爱所及之轻微的内省力
一闪念
一闪念,花蕾显现裂痕
仿佛羽毛划过你猝不及防的臉
你会忍不住回过头
一闪念,花朵开出裂痕,你
终于说出隐忍许久的心里话,就像
一位遗产继承权的放弃者,忽略了
其间发生的所有故事,全凭
落英诉说、保存
一闪念,青涩静默凸显,像
一个清澈的小沙弥
弥合全部裂痕
昙花
昙花叫不醒深睡的人
明月也不行,明月是昙花的内心
在黑夜里突然打开,然后
对我有所交代
时刻短暂,不能细琢
只有开出伤感,开出深刻
才能窗影摇曳,似有玉人来
才能一半给她,一半留给自己
完全阐解明与暗的关系
匆匆而去,像是
认定了去看一个人
一盆兰花
窗前一盆兰花,我
带你回家,带你在书房
读出你不为人知的阴影,读出
你的沉默,你的倔强,你的惆怅
还有那深涧中没有发出的
高耸白杨的嗓音,以及越过岁月的
大面积的钟声。其实
那是爱,是不愿惊动任何的摸索
是周际此物及他物之间的惜悯
是一刹凛冽的闪念
请允许我站在孤寂芳香的一边
使用回忆以及纯粹的虚妄
令它短暂重生
白描
栀子花快开了
苍白的,真实的,像
一出悲剧
如果有一些爱的成分
栀子花会继续开
开新芽探头的颤栗
开墨绿渲染的心思,什么
都不说,只是越来越白。那些
花蕊深藏的原罪,让你站在
困梦将醒的边缘,仿佛置身
空阔幻境的海滩,直到
栀子花开成一群群跃起的鱼
会不会在暗夜抛洒香气
那是以后
野山楂
我现在没有故乡,我
随着无序的脚步到处行走
我做过错事,所以
我落叶。我有时心存善念
所以,我开花
我结果子,是为了给自己一个
交代,有虫子啃噬
那是我们都应该有的印记
有风雨来临,我在枝头
用酸涩荡着渴求的秋千
春之吟
春光明媚,我怜惜审美
怜惜山水喧嚣藉由的疲惫
我知道,千重山万道水
只是草履上泥土的记忆
只是你我深处不可踩踏的禁地
只是几片飘零落叶的轻抚
几声肆意鸟鸣的慰藉
几行没有破译的文字
落叶飘零
你我都曾路遇飓风
漫天树叶飘零,我们突然想起什么
但又什么都不能忆起
只见他们飘起,落下,惊魂未定
像失散的孩子,拉不住风的手
像七月十六日的今天
随时挣脱,又进入必经的明天
包河边的小院若隐若现
不时敲响的钟声与风纠缠在一起
那些树叶仿佛被牵引
一片片倚靠在墙角,像
等待训导和皈依的人
一颗新芽
我走过的路上突然顶出一颗新芽
昨天那里还孤寂如一篇初稿
今天就听到词语出走的节律
也许是一种常见的交换吧
它把土地的夙愿转变成可见的表达
那么,就让我蹲下来看看它
它好似远离了自己的同类
像一只孤独的小羊
独自贪婪而哀怜地站立
它有两片椭圆的、翠绿的眼睛
有盲人和失聪者的坚信
世间有黑漆漆的温暖和冷冰冰的笑靥
楼下的香樟树
从七楼看一片树林
看它们相拥或者覆盖
有几点白鹇、乌鸫和灰喜鹊的标注
对应着点点重叠纠缠的云朵
在晴无的天穹
反复斟酌,反复删减,反复修改着
天空中阔大无序的文章
其中一棵香樟树
像高举着半握的拳头
积蓄了绵韧的修正之力
用低伏的影子充填着周边的虚空
像我们用旧的日子
留有温度,叮嘱和包浆
像括号,像宽容
向晚河边的柳树
柳树冒领一个过路人的身份
向晚时踮起脚照河面的镜子
多么像翘首等待又极力掩饰的人
总有人知道原因,但他们不说
这个冬天,抱火而眠者其实不是
为了抵御寒凉
也不是不戴面具,是躲藏在所有人的面具之后
词语中也有电阻,所以我们懦弱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小彷徨藏匿在即将到来的
大彻大悟。在这个大中,我们可以荡漾
荡漾一天叫徜徉
荡漾一季是忧伤
温暖的背面
雪花能从没关紧的窗户缝隙走进来
我们不可能,我们睡得那么熟
雪花能把全部的自己变成眼泪
我们不可能,垂泣的声音那么轻
雪花啊,她又吸走所有的寒,成为
冰,我们也不可能,她总在温暖的背面
我经常念起的孩子
坐在草地上
没有比这更切深的柔软的体验了
风吹过来,一棵棵小草转向我
像我们永远的辨识
而后顺势靠在我身上,是我
经常念起的孩子
竹林中折返
折一竿竹,折断山坡不舍的牵扯
折断内心虚空的余音袅袅
竹动如手势,竹静似冥想
乘余温尚存,训鸟人没有走远
青涩如羞愧
去皮,打磨,钻几孔迫不及待张开的嘴
灌满台词与历史剧的场景
去除妖娆和摇摆,打马踏浪而过
怀揣竹笛的人,没有风过竹林
你就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