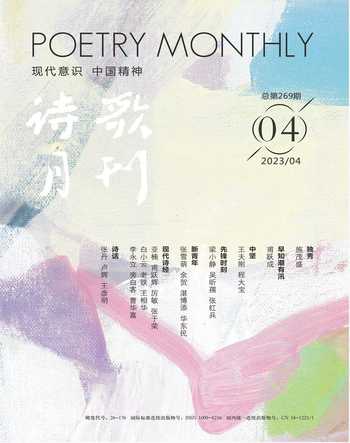第一首和最后一首
施茂盛
唯有诗是这样的,第一首的降临总是像天赐一般。它从一个灵感而来,或者是闪过脑海的一个碎片,被我们的一个词、一个未加修饰的句子所捕获,尔后在我们各不相同的语调中被确定下来。这是诗和其他文本不同的地方。它不需要铺陈,甚至不需要谋划。它就是这样毫无防备、毫无预兆地把这一馈赠给予诗写者。也只有诗写者,才有如此机缘获得这种慰藉。我因此也相信,是那个“更大的存在”依然认定这个世界需要诗写者,认可这个世界诗写者的存在,才会有诗写者的这个命运。我甚至感到,那个“更大的存在”已经向诗写者交代了使命和目的地。我把它看作是那个“更大的存在”对诗写者的眷顾。每天,诗写者是沿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在掘进,就像每天向他所指引的方向不断掘进已经成为每个诗写者的宿命。
对于诗写者来说,他的第一首一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它是一次突然的打开。从此以后,每一位诗写者才真正来到诗写的轨道。我的第一首也大抵如此。虽然我已经不能清晰地记起它的样子、记起它的每一行句子,甚至都忘了它写的是哪个主题,涉及哪些场景、哪些意象。但它发生的过程,它从我脑海中走出来的过程,我还能记起。我相信它肯定和我生活的这座小岛、这个小镇有关。我的第一首必然来自于我在这座小岛、这个小镇生活的某个瞬间,来自于某个瞬间的一次停顿、一次定格。诗写者之于诗,不仅仅只是机缘巧合,还是一种因果关系。我想,正是因为我生活在这座小岛、这个小镇上,我才会在某个微风徐缓的早晨或夜晚,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并从此加入了诗写者竞走的行列。但我说不出究竟是这一首还是那一首,是我的第一首。这也正好是我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或许对于一个诗写者来说,任何一首新写出来的诗,都是他的第一首。
而我要表达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我的第一首或者所有的诗,虽然都和我在这座小岛、这个小镇上的生活有关,但它肯定不是生活现场的临摹和模仿,甚至都不是生活划过我身体的伤痕和印记。在这座小岛、这个小镇上,我有自己养家糊口的职业,有自己对职业的态度。更早的年纪时,还喜欢时不时邀上一二好友,小酌或快饮一番。日常中,内心向善,乐意助人,散漫而随性。当然,我也经历过自身难以摆脱的茫然与无奈,经历过任何一个人会经历的刺和钉子。但这些都不是我的诗,或者说,它不足以构成我认为的、我要书写的诗。诗一定是突破了生活现场的界限的产物,它跃出生活本身要去完成的是进入一个未知领域的使命,这个未知领域才是它的目的地。一旦它抵达,它就成为一个自足体。它所展示的,应该是经过语言之“思”锻造过的,应该是聚精于神的,也应该是言不可及、言而不及和言之不尽的。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是诗与其他文本有所区别的根本所在。这才应该是诗的“善”。诗的“善”,就是诗的“真”的全部。我多么希望,我记不起的那第一首已经领悟了这一要义,而所有的诗全部涵盖在了这第一首中。
那么,这最后一首呢?是不是有这最后一首?布鲁姆在《论诗人们最后的诗》中,曾把诗人“最后的诗”归类为三种:字面意义上的诗人最后的诗;意图去宣告终结,尽管诗人在这之后依旧活着并继续创作;对于一段诗歌生涯的想象性总结。按照布鲁姆的说法,我的最后一首似乎还未出现。首先,诗写是言说和触及我隐秘世界的“器”,它让我摆脱生活的各种陋習,让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好奇和兴趣,让我在生活现场得以自我提炼与涵养,它几乎满足了我在两个迥异世界平行飞行的所有良愿,其中也难免包含了对日常所携带的遗憾的补偿,所以诗写是我余生必然将继续的一个技艺活。再有,在我的诗写中,我一直都把每一首当作第一首,把所有的诗写都汇聚到这第一首中,构成我的第一首的一部分。每一首向我降临时,我都希望它是不断有所精进的那一首,我还没有准备好用一首自认为可行的诗作为总结,以完成带有自我色彩的某个体系的构筑。况且,我的诗写没有达到源头性的高度,也没有要为其他诗写者提供参考的冲动。我之于诗写并无野心,更多的是一种情怀。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自我试探、自我触及、自我愉悦、自我阅读和自我省思而已。
但近两三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在我的诗写中,那“最后一首”的影子时不时地在某处晃动。我还不能很清晰地归纳和表述它。或许因为在我的诗写中,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新的主题闯入了进来。习诗以来,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诗写所触及的素材、场景、镜像,绝大部分来自我生活的这座小岛、这个小镇,以及与之形成某种适度的紧张、对峙、映照和呼应关系的对岸那座城市。所有诗的逻辑、取舍和确立,都围绕这些而关联、生成。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推进的诗写纬度,是一条横向诗写的路线。总体上它是向内的、闭环的,并未摆脱地域性诗写的界限。有一天,我的诗写出现了神奇的一幕,一些新的元素和新的“思”涌向我,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诗写。它已经完全不同于我之前那种横向的、需要照顾现场的广度和覆盖面的诗写。它是一种纵向(经度)诗写。它是开放的、繁复的、螺旋状的,又是混沌的、浑然的、单一的。它更多关注的,或是对秩序的玄秘生成、或是对物(实和虚)经由语言的赋形、或是对日常细节的神性的诗写。它与前者构成了我现在的诗写坐标,给我带来了新的诗写场域。
这个变化,也必然让我的诗写状态和诗写风格发生变化。或许,那个“更大的存在”在告诫我,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中年写作后,我可以过渡到晚年写作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也有更多信心迎接这一刻的到来。或许在晚年写作中,我所谓的“最后一首”也会在某一时刻得以呈现。这不是布鲁姆所说的“字面意义上的诗人最后的诗”,而是终于确立了与晚年写作相协调、相呼应的一种风格后,对自己整个习诗经历的最后总结。但这“最后一首”,仍是我的第一首,仍是构成我的第一首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