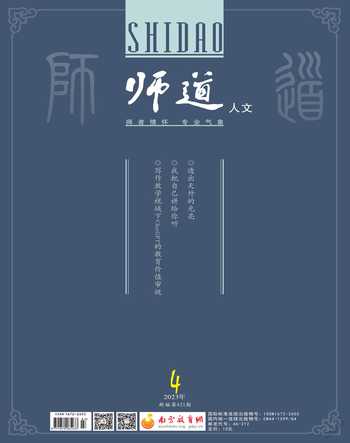刊林撷思
首先,写作活动本身是一种建构“自我”的方式。张江曾在“公共阐释论”中引述伽达默尔的观点,指出阐释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对话。其实,一切意义活动,也即一切符号传递行为都是一种对话。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活动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建构“自我”。绝大多数符号表意活动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即符号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但在文本叙述活动中,由于叙述行为缺少了一般意义上的对话活动中在场的他者,意义的传递对象被“自我”取代,写作即文本叙述活动成为作者与自己之间的对话,因此,叙述者叙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作者和自己对话并借助文本而调整自我、修正自我的过程。写作行为其实是一种镜像式的自我修正,赵毅衡说:“任何思想、判断、推理、想象、感悟等心智活动,实际上都是有两个自我之间的协调,而不是纯然的‘自我意志。也就是说,自我符号不纯粹是我个人的表意活动,它也是一个意义过程。我,通过符号解释对象化的我,来理解我自己。”个体通过文本叙述行为即写作而达成了建构“自我符号”的结果。
其次,作者文本是多种文本支撑的结果。“作者文本”本身是靠社会、历史、文化前文本及作者生平、日记、书信甚至作品等诸多同时期伴随文本的支撑而形成。虽然与作品不同,作者这一文本并不具备无限敞开的结构,但它的意义是未完结的。这种未完结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作者所具有的人格结构不能被完整还原。由于作者个体是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物,那么作者思想或人格的解读就是一种回溯的研究。作者作为一个鲜活个体却是时时刻刻处于与周围世界的交流之中,这些因素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追溯的。作为一个他者,我们接近作者的思想或人格依靠的只能是那些散落于历史之中的非人格化的文本片段(包括历史和社会文本)。由非人格化的文本片段追溯人格化特征,这决定了我们所了解的作者永远是一个不完全的人物,是一个充满空白的文本。一封被公开的私信,一篇新发现的声明,一段被人遗忘的日记,甚至一段友人的临终回忆,都可能立刻改变我们对于一位作者的认知,那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作者本就是一个充满了推断和猜测的“作者文本”,我们只能依靠对种种伴随文本的解读从而不断地接近,却永远不能完整地还原。第二,作为作者的伴随文本的作品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文本。既然“作者文本”是多种文本搭建的结果,而作品本身又具有未完成的特点,“作品文本”自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一切书面文本都可能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对于一些特殊的作者来说,日记与作品之间的界限常常非常模糊。(中略)
再次,“作者文本”受文学史影响。“作者文本”还受到了文学史制约,文学史先期地创造了“作者文本”产生的条件。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以往的某种文学传统有联系,在文学史中,这种联系往往被视为文学这一客体自身发展规律的表现。文学史在本质上并不是作家史,而是作品史或者说是作品的创作史,因而作者实际上是文学史叙述所产生的副文本。在这种文学史叙述模式中,“作者文本”就是以其自身内化了文学史而产生的一个人格存在。所以,是作品决定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评价,而不是相反。(中略)事实上,文学史本身就是“作者文本”的一个前文本。对于批评家来说,由于文学史构成了作家文本的前伴随文本,因而也决定了他们批评活动的视域;换句话说,一个批评家只有在了解了文学史之后才可能对作家做出评价,而了解了文学史则意味着批评家先期地理解了“作者文本”的释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家在“读”到一个“作者文本”之前,就已经在文学史中理解了这个文本。许多情况下,由于批评家视域的差异,同一个作家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批评家那里可能具有迥异的人格,即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批评家那里可能呈现为几种完全不同的“作者文本”。也就是说,“作者文本”在遇到批评家之前,已经事先“被生成”了。
——摘自张明《重审“作者已死”:论作为“伴随文本”的作者与作品》,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3期
以一个核心家庭为例,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这样,家庭语言也就分为两类。一类是夫妻话语,其内容既与他们工作、生活所涉及的幅度相關,也有一些属于二人世界的情感性内容;其形式既有与社会生活通行用语或行业用语的相一致的话语习惯,也有少量个人化或两人间的独特创造。另一类是亲子话语,这是以儿童为中心所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在内容上涵盖儿童身体和目光所触的人、环境与事物,有时也扩展到家长认为或想象为儿童关注的不在场的人与事物。在表达形式上则依据儿童语言能力进行简化、短语化或加工重组,一般都伴随着身体和目光的注意力引导、话音拉长或节律化的强调以及不断重复的特征。
亲子话语与夫妻话语所遵循的“语法”完全不同。亲子话语不考虑现行语言的规范性、准确性,虽依然具有一定的结构性特征,但在许多时候都更重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价值。家长们容易对儿童咿呀学语过程中所吐出的某些特殊语词或话语结构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将它们纳入亲子话语体系之中,使之在家庭语言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对这些特殊语词或话语结构的关注,对儿童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对儿童话语建构与创造能力的重视与激励,家长对这些词语和结构带有感情色彩的重复引用,还可以让儿童返身确认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因此,围绕着儿童成长的家庭语言就呈现为一个有趣的语言圈层现象,靠近核心的内圈层是亲子话语,而外围的夫妻话语则将儿童的语言环境与外部的社会语言联系在一起,并为儿童语言发展起到良好的过渡作用。内圈层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儿童语言的创造性、生成性;外圈层的主要功能则在于确保儿童语言的规范性、丰富性。正是因为这两个语言圈层的共同作用,家庭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及影响程度远胜于其他任何机构。
应该说,以亲子话语为主的内圈层语言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家庭语言的类型与品相,尤其是其中充盈的语言创造性活力(不仅是儿童的语言创造,还包括许多家长围绕儿童的成长表现所激发出来的语言创造),更标志着家庭语言繁盛时期的到来。外圈层的夫妻话语一方面直接承继了婚前恋人话语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往往直接映射夫妻双方在社会生产与生活过程中的认知与情感经验,与家庭外部的社会结构、语言结构具有较强的同质与同构性。只有内圈层语言的形式与内容都纯粹产生于家庭关系内部,因家庭内部新生命的诞生而产生,具有简单、有效、具身的能指特性以及相对封闭、私密、指称性大于陈述性的所指特征,凝聚着家庭主体精神情感特质与创造力量。因此,内圈层语言可以反映出家庭的精神本原,不仅体现出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功能,而且有助于增进家庭团结,在音声相和中积淀血缘之上的文化价值。
因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空间内部自由走动,家庭语言使用并不受空间功能分割的限制,内外圈层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容易相互嵌套,从而对儿童的语言成长产生复杂影响。(中略)
内圈层语言对于0~3岁儿童来说,在确保儿童安全感、同一感、幸福感、价值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尤其是从关键期理论出发,它的结构与样态对儿童的语言发育乃至终身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一般来讲,内圈层语言过度稀薄,不容易营建儿童成长必需的互动性语言实践环境,会导致一定的语言缺氧;而内圈层语言过厚,也会导致语言信号单一刺激过量以及丰富性、变动性不足所带来的语言醉氧。(中略)
由于一个家庭所赖以依存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往往来自家庭外部,强大的社会因素可以通过语言压力影响到家庭的语言圈层。一方面,过量的家庭外部语言使用可以直接减少家庭内部的语言总量,在伯恩斯坦的经典研究中,劳工阶层的家庭语言往往简单、缺乏交流。另一方面,外部社会压力往往迫使家庭成员通过外圈层语言的交流来共同寻求缓解或克服的办法,这种情况虽然不会减少家庭语言的总量,但会影响家庭内外圈层语言的配置。部分家庭教育中的“父亲缺位”,便是男性在竞争过于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压力下在家庭内圈层失语的结果。
——摘自苏尚锋《关注儿童成长中的语言圈层现象,重视家庭语言教育》,《语言战略研究》2023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