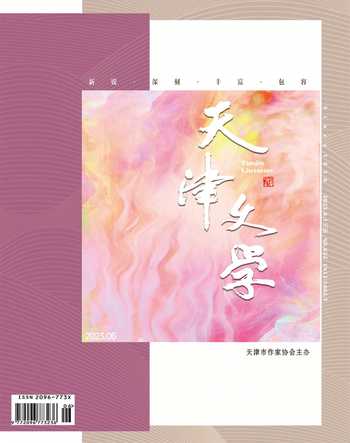开在珠峰脚下的花朵(外二篇)
绒辖沟嵌在珠峰的最底部,像一朵待放的花朵,在人们的等待中终于开了。
在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在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在珠峰自然保护区,雪山夹峙出一条长55公里的深沟,海拔在这里从7340米跌落到2100米,落差5000多米,这就是绒辖沟——喜马拉雅南麓的“五条沟”之一,敢与亚东沟、陈塘沟、樟木沟、吉隆沟相媲美。
绒辖沟谷深沟长,高山上的劲风,吹走珠峰的雪花,落满绒辖沟谷,形成与世隔绝的“雪中孤岛”。尤其是在通讯不发达、道路不通畅的年代,每遇大雪封山,长则半年,短则几个月,山里人出不来,山外人进不去。现在,虽然道路宽敞,但要想进入沟底,还得提前几天预约,等到铲雪车清出道路上的积雪后,方可进入。今年三月,我有幸进入绒辖沟蹲点调研。被两座大山夹峙而成的绒辖沟,每座山被亚热带温和湿润的气候一分为二,半山腰以上是终年不化的皑皑积雪,半山腰以下是众多植物泛起的春意盎然的绿波。
这样的景致,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园。翩翩起舞的蝴蝶,在花丛中漫天飞舞,描绘着绒辖裸露的春色。从不停歇的蜜蜂,与田间一锨一镢挥汗劳作的人们,一起舞蹈。长尾叶猴和熊猴在冷杉与红杉之间跳跃,像是从冬天跳出来的精灵,欢快无比。雪豹和黑熊出没在羊群里,捕猎时还追逐到牧人的跟前。岩羊、兔狲、苏门羚、麝等动物在雪山山尖眺望,从这座山翻越到另一座山,时不时扬起雪沫。猎隼和大鵟盘旋在空中巡视猎物。纵纹腹小鸮、雕鸮、藏雪鸡、棕尾虹雉在柳叶沙棘里“咯咯”地觅食,不知名的鸟儿穿梭在青刺尖、垂枝柏和藏南槭中“叽叽喳喳”地叫着春天。
和煦的春风,吹开了一束束桃花、一树树李花、一丛丛杜鹃花、一朵朵格桑花……那些花儿,开在珠峰脚下的雪窝里,开在雪山的层层包围之中,开出了雪山的圣洁;那些花朵,也开在人们的心上,开出了人们的期盼,开出绒辖沟的诗意和风韵。
绒辖沟的村民们忙碌在春天里,像潺潺小溪冲破冬雪的禁锢,哼着春曲,欢唱在田野,漫步在沟渠。他们背靠珠峰,固守着那份孤寂中的圣洁,感染着来自城市性情浮躁的人们。这里,每个人的双眼,清澈如水,在阅尽孤独后,把心里想说的和不想说的都告诉世人。
绒辖虽然偏远,但与世界紧密相连。寻幽探秘的游客纷至沓来,绒辖与日喀则,与拉萨,甚至与全国各省市都有了或多或少的联通和牵挂。村里的姑娘卓玛说:“开春了,要把自家开办的民宿拓展到每家每户,让每户腾出一间房屋托管给我,经营家庭旅馆,成为全村的一号房东”。卓玛性格开朗,活泼上进,见到客人唱酒歌,见到路人唱山歌……八方游客都喜欢与她交往。
在这里娶了藏族媳妇、被县里授予“民族团结家庭”的四川小伙说:“开春了,要组建一个农牧民施工队,组织村民们干活致富……”
单身女子央金说:“开春了,要找一个男人,一起上山采挖虫草,多一个劳力,多一份收入。”
过去靠着墙根晒太阳的贫困户尼玛脱贫后说:“开春了,要去山外打工,争取多增加一些现金收入。”
在外经商的玉珍说:“开春了,在拉萨开的藏餐厅,生意更好了。”
孤寡老人多吉说:“开春了,曾经收养的孤儿回来接我到城里生活了。”
正在放牧的青年学生梅朵说:“开春了,去内地西藏班高三学习的任务更重了。去年,有一位师姐,在高考后就回家放羊了,她考上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是县里的干部送上山的。我也希望今年高考后,有人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给我送到山上来啊!”
这会儿,绒辖小学的学生正在朗诵课文:“春天来了”。
绒辖沟的春天来了。她从雪域的寒冬醒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的人们,心里总是装着春天,心中总有一朵开不败的花朵。
于礼嘉
观色林湖
唐古拉和冈底斯冰川,孕育了扎加藏布、扎根藏布、波曲藏布等众多河流,也孕育了格仁、吴如、错鄂、仁错贡玛、恰规、孜桂等众多湖泊。湖泊与河流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陆湖泊群。在众多的湖泊中,最大的莫过于色林湖,被冰川孕育的河流跋涉千里,都汇入了色林湖。它位于西藏羌塘高原南部、申扎县以北,是西藏最大的深水湖,也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
湖边的老人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色林湖一直在“长大”,湖面扩张了百分之四十左右,湖边的一些草场被淹没,居民的房屋和牛栏被湖水渐渐吞没,有的已举家迁徙。据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表明,至2010年,色林湖的面积已增加到2349平方公里,“长大”的主要原因是降水量增加。
在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色林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魔鬼”,每天要吞噬千万生灵。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一路降妖除魔的莲花生大师降伏了色林,命令他到岗尼羌塘南面的浩瀚大湖中虔诚忏悔,不得残害水族,并把大湖命名为“色林错”,意为“魔鬼湖”。由于“魔鬼湖”少有人来,湖边成了藏羚羊、藏野驴、棕熊、藏狐等野生动物憩息的乐园。
那次,行至色林湖,正入冬季,湖照残雪,似烟似雾,氤氲天涯。端详色林湖的姿容,湖面明净澄澈,湖水幽深,湖边冰花绽放,不染俗尘,让人沉醉。一只幼小的藏羚羊,跪乳报恩,催生出生命的恬静与斑斓。
站在高处眺望,湖面广大,近处湖水粼粼,远处平展如镜;湖色越远越深,由近及远,银白、淡蓝、深青、墨绿,界线分明;湖水的绿由深及浅往周围扩散。墨绿、翠绿、葱绿。澄澈、恬淡、绮美。太阳的光辉倒映在湖面上,泛着金红色的光芒,像涂了一层霞红的胭脂。碧玉般的绿和胭脂般的红,交融在一起,优美而宁静。
湖水倒映的一景一物莹洁无比。湖中有天,蓝天如湖;湖中有云,云如浪花;湖水映山峰,峰如指柔。
湛蓝的天空与湖水融为一体,像两面镜子,一个悬于空中,一个嵌入地面,相互对照,相互颠倒。蓝,从湖水中滴落出来,干净纯粹,广阔深邃,如梦如诗,让人目眩神迷,让人心生孤独,又让人得到心灵洗礼、灵魂升华。
倒映在湖中的云,一会儿洁白,一会儿乳白,一会儿雪白;白得发绿,白得发蓝,白得发青。微风掠过湖面,湖中的云朵更加飘逸、轻柔、达观和洒脱。
倒映在湖中的雪山,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收起了山的峻峭与逶迤,囊括了山的高、雄、险、峻。湖水把众山搂入怀抱,也搂入了山上的皑皑白雪、山腰的淡淡薄雾、山下的茫茫草原。这时,在湖的面前,所有的山都是渺小的,不管山是斜倾而来,还是拔地而起,都收起了它的豪放与张扬。
我站在一望无际的湖水面前,渺小得像湖中的一朵浪花。
于日喀则
加布拉冰川
路遇加布拉冰川,冰塔矗立,冰凌四方,直指冷艳的天空。仿佛要诉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听说这些冰川,由上百、上千甚至上亿万年的积雪、浓雾、冰雹侵蚀和堆积演化,经反复挤压孕育而成。
肃立在冰川下,让我仿佛回到了冰世纪。波涛似的冰川像汹涌的特堤斯海,浩荡而又磅礴;又像一道道蓝色的火焰,从远古的雪山飘来,闪烁在冰林里。冰缝犬牙交错,冰洞林立,宛如童话世界的城堡。我像螳螂探路、企鹅移步,小心翼翼地踩在冰川鲜活的舌头上,听冰川下的冰窟窿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仿佛要驮着冰川逃出雪山,扑向大地人间。
近观或者远眺加布拉冰川,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目所能及的冰川是亿万年前的冰雪吗?手所能触的是亿万年前的时间吗?这海拔5000多米的高度,托起的千里冰川,是在静守一方澄澈与清凉吗?是谁把冰川纪浓缩成亘古的冰雪让人切近,抖落俗尘?又是谁把凝固的雪花融化成水让生命延展?难怪人们亲切地称冰川是雪山上的“固体水库”。
仰望加布拉冰川神韵,不禁想起它旁边的卓奥友峰,也称“乔乌雅峰”,藏语的意思是“首席尊师”。它海拔8201米,是位于中尼边界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有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和西山五条山脊,峰体常年被积雪和冰川所覆盖。加布拉冰川就在卓奥友峰的北侧,是绵延21公里的现代冰川。海拔5700米以上的峰面上,形成了一些消融区,冰塔林突兀而立,触目皆是,形态各异,梦幻非常。其间,还有幽深的冰洞、曲折的冰河,壮丽的奇观令人目不暇接。卓奥友峰把加布拉孕育成了深不可测的山谷冰川以及平顶冰川、冰斗冰川等。在冰塔林的下方,还孕育了一个长2.5公里的冰面湖泊,仿佛是镶嵌在天际的镜子,秉承洁净与晶莹,映照着万年冰心的誓约。
1954年,四名奥地利登山运动员就是踏着加布拉冰川,登上了卓奥友峰峰顶。我们来到加布拉冰川已是2022年3月下旬。这个时节,狂风依然大作,卷起的沙尘飘浮在洁白无瑕的冰柱上,被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气温,冻成一排排“泥人”,像出征的勇士傲立在蓝天下。
冰川,在漫长的岁月里结晶而成,又渐渐消融,成为江河湖泊,供人们繁衍生息。在人们感叹冰川消融过快的今天,我只能双手合十,以敬仰之心仰望它,期盼一场场雪,丰满它的身躯,永不消亡。连绵不绝地用冰层深处的融泉,流淌清冽与甘甜,滋养人们的身心。
于日喀则
舒成坤,重庆人,军旅生活5年,荣立三等功三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集《雪魂》《雪花无尘》。
责任编辑:王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