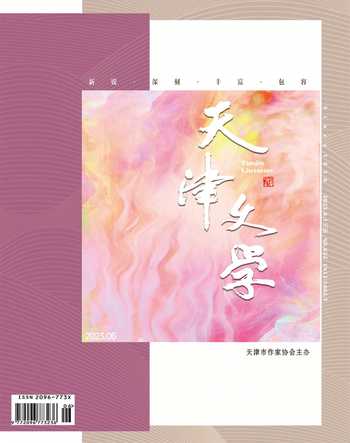我的中学生活
我中学六年都是在“北京三中”读的(这是一所男校,不收女生)。初中时作为“学员”我参加了课外兴趣小组——“理化小组”;高中三年又担任该小组的“辅导员”。从此与“理化”结缘,终生不辍。大学期间进北大化学系选读物理化学专业(又是“理化”);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在当地(嘉定)对外名称叫“理化所”;工作后期曾调入“理论室”从事理论化学研究工作……可以说,我终身没有跳出“理化”二字。不单是我,一位和我同时担任理化小组辅导员、颇有兄长风度的董为毅同学最终也因此以“理化”为职业,先考入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留校当老师。还有一位比我低两届的理化小组学员程印槐同学随后也考入北大化学系。可见,这种早已深入内心的“理化情怀”足可贯穿我们的一生。
“志趣”可能与先天有关。按着志趣行事能够顺风顺水,彰显特长,事半功倍。参加“理化小组”对我而言纯属兴趣所致,与课堂教学完全不搭界。我在理化小组活动中感受到极大的乐趣,特别是高中阶段,担任理化小组辅导员后更是如鱼得水,拥有了很大的自主权!
有一次我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一本很久以前出版的(竖排本,没准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关于科学小知识的书,厚厚的一大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科学小制作。其中有一个叫“天气预报管”的小制作极大地吸引了我。我们依据书中配方,用无水酒精把十几种化学药品按照比例溶解在一个粗大的试管里,上层是透明的饱和溶液,没有完全溶解的固体药品沉积在底层,试管口再用一个大软木塞塞紧,并用针戳一个孔,以保持内外相通。然后安放到一个为测量气象而专门制作的“百叶箱”中。神奇的现象出现了!每当刮大风前试管固体界面则出现羽毛状晶体;下雪之前,界面上又会出现白色的小圆球……为此我们还专门在校门口过道处立了一块天气预报的小黑板,按照划定的空格填上每天的温度、湿度、气压、最低温度、最高温度。最底下一栏则是根据“天气预报管”中显示的晶体形状,写下“近日有大风”等预报项目。有一次,一群北京师范大学即将毕业的实习生老师们经过小黑板,看到下面居然还设有“预报”一栏后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当时在我们国家“天气预报”尚不予公开(不像现在每天都会有天气预报),他们很是诧异:这些中学生到底是根据什么“预报”的?
当时正值人造地球卫星准备发射时期,我们应时举办了介绍人造卫星的专题讲座。全是由我们几个辅导员搜集资料,亲自讲解,并伴有幻灯图片。我们还筹备了一场全校性的天文報告会。真的挺好玩,开会前还“鸣放礼炮”,以示“隆重”。台上架了一门迫击炮模型,然后是一瓶瓶用氢气配制的“爆鸣气”,鸣放时瓶口对着酒精灯一一点燃爆鸣。挂在舞台右边的“节目单”只是一张白纸,会议正式开始时,用喷雾器对着它一喷立即显出清晰的字来。为了这次会,我们还专门请来了著名的科普作家郑文光先生来作关于月球的报告。演讲开始前,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套上头盔,身着“宇航服”扮演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二十多年后的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真的实现了脚踩月球土壤的“登月”)。我们开展这些大型活动都是以“理化小组”名义举办的,告知一下校领导,其他细节都由我们自己来考虑安排。当时就我们几个辅导员在那里忙活,校领导只是知道这回事,不过问,很信任我们,让我们享有充分的自由。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中学生活还是比较宽松,充满乐趣的。我的同学也各有各的兴趣,各随己愿地选择了不同的兴趣小组,同样也是只凭个人兴趣爱好,与课堂教学内容完全无关。其中我的好友赵健同学参加了航空模型制作而且还获得全国航模比赛第四名,为此,他受到邀请,中学毕业后可以直升西安航空学院。还有一个同学制造一台纯手工的电影放映机……真是五花八门,各显其能,各得其乐。
记得高中上物理课,学到了“法拉第常数”,即每克分子(摩尔)所携带的电荷为:96500库仑∕摩尔。我当时突发奇想,若是将一个“元电荷”的微观电量乘以阿佛加多罗常数(6.022×10的23次方)应该也可以得到这个法拉第常数。经过计算,我得到的结果是96450库伦∕摩尔,两个数值很是接近。对这一计算结果,我和周围的同学都感到非常惊奇,立即一齐去找物理老师告知这一结果。我的物理老师是一位北京市名望很高的老师,他听了我的叙述后见怪不怪,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就对喽”。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将微观电量与宏观电量采用不同单位换算而已,但这一计算还是让我兴奋不已。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这还是第一次试图将宏观与微观直接联系起来。目前由美国国家标准局确定的权威数据:法拉第常数是96485.3386±0.0083库伦∕摩尔。当时我曾将这一计算过程随手写在物理课本空白处。大学一年级入学时,因当时年级里专门设有一个“工农班”(由“调干生”组成),其中有些同学没系统学过中学物理,要借一批中学物理课本。我遂将这本书上交,结果没还回来,又不知在谁手里。由于书中记载了这一推导过程,失掉了还觉得挺可惜。
当时的校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我高中时利用寒暑假参加了市里举办的摩托车、跳伞以及军用步枪射击等国防体育项目的训练。摩托车训练采用的捷克生产的红色“佳瓦”摩托车。跳伞是在北京东郊的一座跳伞塔训练的,此塔将伞提升到40米,一拉伞绳,降落伞带着人直接飘落下来。其实从跳伞塔跳伞,落地速度要比从飞机上跳伞落地速度还要快,因此对下肢的冲击力也更大(飞机跳伞着地之前,伞在空中飘浮了一段时间,已经达到了匀速)。
军用步枪射击用的是七九步枪。这种训练是非常艰苦的,正值暑假,连续两个星期的训练全都是趴在地上练习瞄准。解放军教官也趴在直角位置用专门的“瞄准镜”予以纠正。因直接趴在草地上,从家里出来预先都要穿好长袖制服,为此我还曾经中暑。家里出发后在强烈太阳光底下纵贯四分之三个北京城,骑了半个多小时自行车,刚到射击场就站不起来了。解放军卫生员赶来给我服用了一瓶“十滴水”才缓过来。经过枯燥而艰苦的训练,最后终于迎来了实弹射击,每人三发子弹,用的是1米宽的“一号甲环靶”,射击距离为100米。临射击前,对枪的“后坐力”略微有点忐忑不安(据说枪托若没顶紧,后坐力可导致肩部脱臼)。射击时从容卧倒,稳稳握枪,静静瞄准,在不知不觉中扣响扳机,“砰”的一声,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枪居然打了9环,然后依次是8环、9环。3枪总共26环(只是没打出最高的10环,心中略感缺憾)。
中学时代的生活也是刻苦的,每天晚上11点准时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钟被闹钟准时叫醒。中午回家匆忙吃饭争取再睡上半个多小时。天天如此,周日也不例外。有时回家做作业中遇到数学难题,又非要把它做出来,上床时间偶尔推迟。但这种生活也是充实的、主动的、充满自由的,没有精神压力,没有背后催促,没有课外补课班,没有纯粹为“高考加分”而硬性参加的“兴趣班”,想干什么完全由自己决定。对比今昔,心里总感觉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否缺失了点什么。而每个中学生又被某种无形绳索捆绑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什么志趣爱好、天分特长、灵性慧根、好奇探究以及未来的发展潜能,都被升学压力压缩得无影无踪。时至今日,虽说七十年过去,但当年那种紧张、丰富、自主、自由、快乐的中学生活还是令我怀念。
詹克明,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其中1959年5月—1961年8月在北大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教研室任助教);1964年10月7日毕业分配到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退休。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