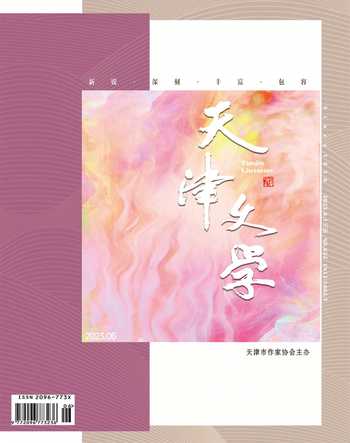山火
郑皓文
投着玩的,在家待着闲着也没意思。网上净是写东西的,五花八门,我也总看。最近新文章应该不少吧,跟井喷一样。她说。
我说,你写的东西让我想起来许多事。你住哪?
春园里。
啊?
春园里啊。
咱一个小区?我站起来走到客厅窗台,你几号楼的?
是吗?我十三号,我看看哈。我给你开开灯,给你发个电报。她笑了几声,声音像是在烟灰缸里蹭上了一大团灰。
我转身走到厨房,透过几块小巧玲珑的玻璃向外窥视。十三号楼是前几年新开发的,外墙很有设计感,像构思出来的某种机甲崭新地伫立着,预备对付未知的危险。目前还没怎么住人,仍在孤独地放味儿。大家都怕甲醛。我望去,一片黑暗,只有几格子光亮。我像狙击手一样盯着那栋楼。没有新开灯的住家,也没有灯光闪烁的住家。
我说,没看见啊。
她说,你把语音挂了,我给你录一段。不会啊,这么明显。
我把语音通话挂掉。半分钟后她发来一段视频。屏幕上一直转圈圈,我走到窗台它才加载出来。我看到狭窄的被瓷砖包围挟持的空间。一只白色衣架从屏幕左下角冒出,伸到中央,拨弄远处的开关,频率很快,好像生怕灯掉不了闸。房间最终暴露在惨白的灯光下,灯在视频以外虚弱地捯气儿。我刚辨认出来那个衣架是一只细得吓人的手。
我发语音说,我看了半天了,你这样我不可能看不见。你确定住在春园里,春天的春,家园的园?
对啊。她随即说了一条街道,就这旁边啊。
我退出微信,打开导航。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微信。我说,有两个春园里,我住的是城西的,你住的是城北的。
她说,哦对,刚想起来,我之前打车还走错过。我从单位到家用不了二十分钟,那天开了一个小时,我还和司机吵了一架。我这脑子。
我笑了。我说,咱这算不算有缘呢。
她说,算。后面跟了一朵行将枯萎的玫瑰花。她也笑了,但我不清楚,大概笑了吧。
我说,你那边没事吧?要是有事你先去忙。
她说,我这没事。
我说,没去吃饭?
她说,每年年夜饭我都不去吃。太乱了,年年都是那些亲戚,还没有在饭局上认识的人熟,闹腾得让人没心思吃饭。也没意思。
我说,我也不乐意掺和这些,上一次去吃还是因为刚找着工作。要是没事就和我聊聊天吧,一个人不是无聊到一定程度是不会在除夕晚上工作的。
她又在手机那头笑了笑,但我还是无法看到,这笑容就还只能是一个几率。
我把手机放下,点上眼药水,感受大量细小的针头去扎我的眼。药水在眼球表面转动,手机的振动声不间断地传来,填充我的耳道。电脑兀自开着,散热装置呼呼地运转,苍白的屏幕在黑暗里显得很咋呼。我关上,让黑暗包容地涌入身旁的缝隙。
她说,行啊。编辑好干吗?
我说,好干确实是好干,下肢瘫痪半身不遂都能干,要说难吧也够难的,一个月弄不到几篇来稿,就得用之前的废稿,反正得把一大本杂志填满,估计作者写得都没我改得辛苦。杂志已经快死了。
她说,明白,卖不出去。送都送不出去。
我说,反正也没人看,我就应该印一整本脏话。
发笑的几率又在屏幕那头出现。
我听见玻璃碎裂的声音,没等走到窗台,又传来很大声的叫骂。有人喝多了找茬儿,在黑暗中推搡,门卫疲于应付,麻木地扛着那人的肩膀拉到小区外面,碰上门禁,再走回小传达室喝一口半凉不热的茶水。
她说,我也是。事都简单,但一个指标就能把人逼疯。你我都是潜在的疯子。
微信沉寂下来。我打开电脑,屏幕乍明,黑色的字符包上一层朦胧,好像要长眠于无边的惨白中。我看着最后一段:
绝望四处安家繁衍,爬行着、逼视着要毁灭一切。然而我就看见温馨的夕阳般的橘红下,一团黑影正缓缓蠕动,好像从强压下逃逸出来的灵魂。
单说文笔已经足够扎实,我已经很久没在投稿栏中看见这种成熟的文风了,很久很久。她说的应该不假,经常看文章,但我很难相信网上庞杂的文章能培育出这种文风来。我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让整件事在脑中浮现。
重现。
我走到楼下买了一打啤酒,三盒便携小菜。差几块钱能满减,又拿了一盒口香糖。来个袋子吧,我说。五毛一个,响应国家号召,老板淡然地半睁着眼点了点印着二维码的塑料片。我把口香糖揣进口袋,左手提着啤酒,右手抓着三盒菜,菜盒叠起来很厚,撑得虎口要爆裂。老板走到门口扒开塑料帘,新年快乐,您慢走。
到家后我把啤酒放下,从冰柜里翻速冻饺子。翻了半天,只翻到两盒。我心想,有就行,不就为图个好兆头。锅里满水,倒上饺子。倒的时候我隐隐听见有几声响动,不像饺子入水,没怎么注意。过了会儿又有隐隐的响动溢出,听着像敲门。我走到门口,门外有个幽灵一样的身影。我说,谁啊。
幽灵说,找你来了。
我说,我刚才没告诉你我住哪啊?她走进门,手指上挂着一提白色的冒着热气的滑冻状物体。她说,这之前就是我家。楼下饭馆那买了点饺子,你还没吃吧?我说,我刚煮上,你等会儿。她说,需要换鞋吗?我说,你看我家这状态像需要换鞋的地方吗?她笑了笑,真实的笑,但很难听,像在烟灰缸里蹭过。我走进厨房,半数饺子已经破开口子空虚地咧着嘴。几团肉馅在水面潜浮着,像团团自由的灵魂。
她咬了一口自己带来的饺子,皱了皱眉说,味儿远不如以前了,我住这儿时每年过年我都在他家买。我抿了抿嘴。她问,你笑什么?我说,你让我想起一个故事,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听过吗?她一边对付小菜的塑封封皮一边说,没听过,讲讲。我说,他俩是朋友。有一天呢下大雪,这个王子猷看着满天的大雪突然就想见见戴安道。她干笑一声,真朋友啊。我说,他就带上仆人出门上船,划一晚上到了戴安道门口,他扫一眼门口就要回去,仆人说你有病啊,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完了?我说,完了。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觉得他有病。我说,王子猷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羲之你总得知道吧?她说,知道知道,大书法家。我还知道他是东晋的呢。她嘬嘬牙花,五代十国,乱世啊。我说,所以你想出啥来了呢?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一个人伟大,并不耽误他儿子有病。
我换了个话题,你怎么确信我住这?她没接话,掏出来一个灯笼,我匪夷所思这么个灯笼是从哪掏出来的,刚才进门的时候我一直就没看见她还带着个灯笼。灯笼外罩着劣质塑料壳,艳红、艳黄,印着惊悚的图画,小孩拜年,提着的红色礼品袋印得朦胧不清,像是提着一颗血肉模糊的头颅。灯笼意在吓跑年兽,而不是吓跑人,但小孩子却提着这种能把大人吓死的劣质灯笼跑来跑去。她拨开开关,灯笼疯狂旋转起来,夹杂着诡异的音乐,拜年小孩在灯笼上跑了起来,像是要找谁索命。她把它放到地上,看其旋转,很是入神。我借机打量了一下她。四肢修长,显得脑袋硕大,令人忽视其瘦弱的本质;嘴角不时抽动一下,幅度很小,也许是灯光的问题。眼睛在看灯笼,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在看,视线愣愣地向着前方。
她突然开口,我小时候玩的就是这种灯笼。提着满街跑。我说,你不觉得它挺吓人的吗?那个灯笼还在旋转,黄色的挂穗四散趴在地上,好像下一秒就要变成触手捅进地板。她又看了片刻,点了点头说,现在看来,是有点恐怖。她走过去关上。
我打开一听啤酒递给她,你喝吗?她伸出手来,又很快缩回去了。我说,不放心就算了。她说,我是开车来的。我收回手啜了一点,一口口地喝下去。我又去柜子里找出几瓶濒临保质期的杏仁露什么的给她喝。她试图拉开拉环,看上去很费劲,手指头绞在一团,被压得毫无血色,我帮她打开。她喝了半罐,脸上有了被屏住的笑意。我说,你有什么想笑的就笑。她说,我这么些年一个人过年,和你才认识几个小时,就和你吃上年夜饭,很讽刺。我看桌上,饺子和菜已经去了一半,显得这话很突兀。我们在沉默中把剩下的菜慢慢吃完,时间越到后面越显漫长,像完成一件艺术品的最末尾。
吃完饭她开始在我的房间里巡视,她走路很快,看上去步子迈得不大,频率也不高,但就是走得很快。她一边走一边揉肚子,嘴里念叨,怎么这么凉。我家住顶楼,屋内冰凉,手紧贴着暖气片才能感到一丝暖意,它隐隐约约地存在于深处,像森林远方若有若无的火光。房间里除了床和书柜没有其他装饰,这让她很不理解,插着腰点评了一番,好像自己是将要住进来的旅客。她随手从书架上抽出本书,翻看几页放回去,再抽出另一本翻看。
她拿着一本小册子停住,慢慢走到沙发前坐下从头看起来。我看书不会去折书页,用两只手捏着两角,书看完还和新的一样。她直接把书页连封皮折到后面,这让我很不舒服,书封上势必会留下纵贯的折痕。她坐在那里,完全没有停止阅读的意思,偶尔挪一下腿。
我走回书房,打开电脑。那些字又蹦出来,在我眼前喧嚣。
我把那根棒棒糖棍儿捡起来。棒棒糖是老牌子,熊头样式,然而什么都不剩了,棍儿的边缘还剩一点糖渣和牙印。还有在表面形成保护膜的唾液。
这种棒棒糖是老县里糖厂做的,我还去过那个老糖厂,门口的栏杆锈得糠透了,不能碰,轻轻一抓就会从中间断开,也划不破手,一攥就比细沙还碎。门卫趴在小屋里睡觉。棒棒糖由纯糖做成,没有别的香精,吃完嘴里发酸发涩,感觉嘴皮都在惊恐地往回抽搐。我每次都会反复把糖从嘴里拔出来,上面的图案会变得更浅,我就满足了,如此反复。可见我很小就开始享受消逝的乐趣。图案我一直以为是一张狗脸,去糖厂问人说是熊,可我一直坚持熊没有这么长的耳朵。我嗜此糖如命,与年龄极不相符,有钱就买来吃,一度身形臃肿,牙齿阵痛。一直到十六岁的一天,我对这种糖的兴趣戛然而止。
十六岁之前的日子单一而燥热,夏天有没完没了的知了。我坐在栏杆旁操纵着棒棒糖的消逝并因此而感到喜悦,不管不顾地坐在一堆锈渣上,使裤子变成茶褐色。这一切并不能长时间地停留,我在消失棒棒糖的时候,也让时间一点点流失着,只不过当时的我还感觉不到,踩蚂蚁时我感受不到生命的消逝,天亮了又暗我感受不到时间的消逝;只有那点糖化成甜浆使我嗓子一紧,我才清晰地感受到流逝的过程。棒棒糖和我浅薄的生活粘在一起。
我从稿件中抽回神来。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食指、中指、无名指分别指向三个维度,构造出空间坐标系,那本小书就架在三根坐标轴间。她说,这是谁写的?我看挺好。她翻开封皮。豪,豪尔豪,豪尔赫,博尔赫斯。这姓读完肺里痰都给清干净了。
我说,博尔赫斯的《阿莱夫》,富有哲理,博尔赫斯总是启发我写作。她说,我基本看得懂,但我不明白写这些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写东西就是记录,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偶尔换个形式。当然这篇玩意就是我瞎编出来的,我活到现在还没遭过哪的火呢。我向窗外看去,已经过了十一点,家家灯火通明,人们都在忙着抢红包。我说,你喜欢就送你了。我看见书封上一道长长的无法挽回的折痕。
一道黑影闪过,我下意识地抬头看,看见一条青绿色的长裙。我盯着看,看了很久,好像发现了一小团森林。我再低头时,融化的糖和着唾液滴在地上,有几滴落于裤子表面,形成浅黄色的星星点。我用手去擦,那些糖点扩大四散,腻乎在手指间。我又掸了掸,便抬屁股跟在青绿色长裙后面。我裤子前方是一团快凝成糖片的星点,后方是大片的茶褐色,两手黏黏糊糊,捏着还剩一点的棒棒糖,尾随着长裙。我知道结局只会有两种,我自己先放弃,或者长裙逼我放弃。裙摆轻轻荡漾,像是一艘行驶着的游艇引我向水流深处,水草的清香传来,让我如痴如醉。
我向左侧看,看见一大条绳子。绳子有小指头粗细,看上去韧性很足,有时候那些女生跳皮筋跳断了,差使男生去找能替换的,男生就会十分不耐烦地拿来这种绳子,筋道,不比皮筋差。右边是一大提橘子,新鲜的橙色和青绿色长裙交相辉映,看上去很舒服,不扎眼。我稍稍向上移了移眼珠,看见一段细长白皙的手腕。长裙走得很快,两条腿隐隐在缝隙中裸露几个瞬间。我紧紧跟随着,好像追随一场龙卷风。
有人雇我和朋友们去打了场架。根本没用多少力气,对手不堪一击,露出无辜的眼神,仿佛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打架。打完架我们去饭店用雇主给的钱大吃一顿,随后在楼顶上和其他孩子打牌。楼房七层封顶,下雪时能覆盖一层最洁白的雪砂供我娱乐。时值夏天,正有一些风迅疾地掠过,我们心情宁静,不时伸出手按住即将被吹走的纸牌。我掌握十几种扑克玩法,每玩必赢,还是照样玩,可见我的无聊。我把牌摔在地上,起身去楼顶的边缘。油漆褪得差不多了,露出破碎的水泥。我伸脚使劲一踢,它们纷纷而下,楼下传来几声闷响,不知道砸到什么了。
只要我想跳下去,不会有任何人来阻拦我。家庭支离破碎,父亲老早就弃家而去,听说现在还活着,家庭美满,过得不错。学业更没戏。我的生活就像走在一条路上,周遭都是水泥和灰土,前面啥也看不见,好像截止于此。我要是愿意再走几步,它就再向前延伸一点,两旁依旧是水泥和灰土。我跳下去了,我的那些朋友也许会跟着我一起跳下去,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和我一样百无聊赖。一个女生挪上来,手里捏着一张纸,在我脸上擦拭,拿下来时我看见上面一大团脓血。把痘碰破了,她说。她把嘴凑上来寻找我的舌头,我把头扭过去。
我对她说,如果我现在跳下去,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跳?
她把我的手放开,你犯什么病?
于是我把头伸向楼下看了看,平着头闭上眼。
一股焦煳味从故事里飘出来。
她觑着眼睛,要么听得十分认真,要么十分不认真,要么快睡着了。我说,现在这个故事有两种选择,一种很有讲头,一种很没讲头。你要听哪种?她没回答我,果然处于恍惚状态。我把她晃醒,重复了一遍。她说,这还用问,当然是听有讲头的了。
我睁眼顺着焦煳味传来的方向看去。对楼顶层开着灯,我又看见了那条青绿色的长裙,在屋子里飘来游去,像一条自由的水草。但有一丝不寻常的亮光一闪一烁,照得人眼看不真实,好像是水光,把脸伏在水底向上望,就能看见满眼这样的粼粼的水光。水光永远是碎的,但是水光很快地连贯起来,连成一片了,全是水藻的延伸和铺展方式。我就眼看着水光蔓延。水光蔓延。一片!一片了!
青绿色长裙舞蹈起来。下摆扬起,四散舞动。
一丛自由的水草,一匹自由的野马,一条自由的长裙。
舞蹈幅度扩大,飞速地旋转起来,带起四下的风和其创造的焦香扑打在我的脸上。舞蹈幅度扩大,变成颤抖,变成抽搐,变成不知其意的摆动。舞蹈幅度扩大,渐渐离开地面,长裙的上半身消失于我的视线,只有两只苍白的脚腕依然轻浮地、轻柔地、轻蔑地舞蹈给这个世界看。舞蹈幅度扩大到极点,于是悬浮着结束。
亮光继灯光后再次照亮了整间房子。我看见了一场山火,跳过缓慢的准备阶段,爆发。爆发。一场伟大的山火。长裙悬浮其间(一场伟大的山火),永不倾倒(一场伟大的山火),好像本来就该这样似的。绝望四处安家繁衍,爬行着逼视着要毁灭一切。然而我就看见温馨的夕阳般的橘红下,一团黑影正缓缓蠕动,好像从强压下逃逸出来的灵魂。
我看着这一切,大笑着鼓掌,然后一跃而下。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我,讲完了?我说,对。她又沉默了一会儿。
临走时,她手揣着兜问我,所以那个没什么讲头的故事是什么?我说,之所以没讲头,是因为我什么也没看见,黑烟很快就涌上来,我连眼睛都睁不开,就回到他们打牌的地方坐着了。然后我就听见了人们的呼救声。我再看那里时,房子已经烧得不剩什么了,里面的东西都难辨。但我还是分辨出来一团蜷曲的东西。那条充满韧劲的绳子绕过应该是脖子的部分,向前延伸,好像脐带。我开始呕吐,没有消化完的晚饭变了模样倒在我的面前,被橘子的纤维包裹,橘子是青绿色长裙发现我的跟踪从右手的提袋里拿出来递给我的。我走下楼顶,考上了一所平庸的大学,选择了一份无奈的工作,再后来的事你差不多都知道了。她低下眼眉。
还记得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吗?
她说,王子猷挺有病的,其他不记得了。
我说,我一直很羡慕王子猷。
她说,那你有没有后悔过?
我说,一直没有。
她裹上衣服离开了。
我坐到餐桌旁,把剩下的啤酒都喝完。我看看表,马上就要除夕了,窗外已经有远近的焰火在燃放。人们纷纷从餐桌走到阳台,面目模糊。我也远远望着那些焰火。我缺少了什么吗?什么也没,或者说,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好侥幸。我让那些短暂的幻影隐匿,独自哭了一会儿。
手机突然震动。我拾起来,她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谢谢你的故事,尽管那是我写的。我也有一个故事,现在我决定讲给你听。按你的说法,这个故事也有两种选择,一种很有讲头,一种很没讲头。你要听哪种?
有讲头的,我说。
我把手机放下,走到窗台,面临午夜。四处的焰火燃起,飞速地蹿上天空,绽出各自的颜色。有一团距我很近,飞起然后火星四散,把房间映得明亮,把我映得明亮。我看着这一切,大笑着鼓掌。
在除夕的午夜,满天的焰火中,发生了两起火灾。两起火灾发生在本市两处重名叫春园里的小区,分别位于城西和城北。
责任编辑: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