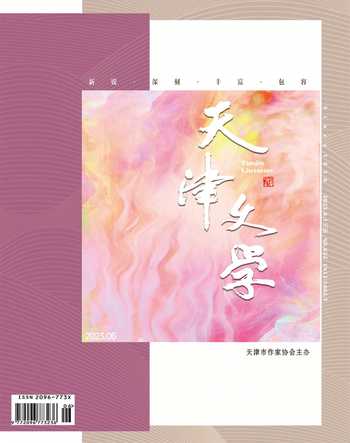我的外公是一只飞鸟
外公生病了。他坐在院前的桃树下,望着天空。
“你在看云吗,外公?”我问。他摇头,指着一群飞过的鸟。
“我认识它们,”他笑,自信地讲,“我曾和它们一起飞过。”
“外公,你曾经是一只鸟?”
“对哦。”
太阳晒着,风吹着,我坐在外公脚边的小凳上,听他讲起以前。
陶匠有只灰陶罐
东西村的杏树下,以前住着一位年轻的陶匠。
每天黎明,公鸡一打鸣,陶匠就起床,赶去黄泥地,背回最好的泥。天麻麻亮时,他吃过饭,开始做陶碗、陶勺、陶钵和陶罐。
烧陶的小窑,是陶匠的爷爷的爷爷留下的。东西村和南北村,东西镇和南北镇,还有更远地方的村镇,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陶匠家的陶。
赶集的日子,年轻的陶匠挑着陶器,去街上卖。落担后,他只随便一站,大伙儿就都围过来。
大家也不挑。有什么好挑的呢,每只陶都好。陶碗拿回去,盛粥,当茶碗,或是装糖果、坚果,即使什么都不装,摆在灶头或桌上,也怪好看的;那陶勺呢,勺柄上绕着一朵小花,或是卧着一条鱼、一只蚂蚱,放进水里,花会开,鱼会游,蚂蚱会跳;钵啊罐啊,就更不用说了,什么东西放进去,十天半月后,都新新鲜鲜的。爱美的女人,采了野花,插在罐里,放在窗台,几月过去,花仍美美地开。
陶匠生性寡言。别人夸他陶做得好,他只笑笑。
卖了陶,买了油盐酱醋茶,陶匠往家赶。他很少在街上和别人喝茶讲闲。大家喜欢他。有人托了媒,想将闺女嫁他。陶匠摇头,说爹妈去世早,家底薄,等攒攒钱再说。
可是,这年冬天,他成亲了,娶了一位名叫蓼姑的女孩。有人说,她是遇大荒,从异地乞讨到东西村的——讲到这,外公原本眯成一条缝的眼睁开,冲我眨巴眨巴,笑笑地说那都是瞎扯,他最清楚蓼姑从哪来的。
“说起来,还和你的太爷爷有关呢。”外公慢悠悠道。
太爷爷?爸爸的爷爷?爸爸对我讲过他,说他是木匠。不过,在以前,一个人除了是木匠,还是农夫,是渔夫,是养蜂人,是焗瓷人,一个人会的东西可多了。
外公告诉我,太爷爷除了是木匠,还是东西村的捕鸟人。
东西村后有东西林和东西山。有林有山,就有鸟。不但有,还多得很,常见的鸟儿,稀罕的鸟儿,一团一团地飞。太爷爷闲时,一听鸟儿喳喳叫,心就慌,背上鸟笼,拎起捕鸟网,就往林里走。
太爷爷的耳朵灵,眼睛亮,耐心好,最厉害的是,他跑得特别快。看中的鸟儿,他可以一直追啊追。鸟在天上飞,他在地上追。
鸟飞得累了,落在树上,他跑到树下,将捕鸟网一伸——鸟落进了网。
太爷爷喜欢稀罕的鸟,三文鸟、独眼雀、白乌鸦、四脚乌、菊斑鸟、铜钱鸟、绣花鸟、麦穗雀……菊斑鸟敛翅时,像朵含苞待放的菊花,飞起时,像一大朵盛开的龙须菊;绣花鸟会在自个的巢上,用叶絮织出好看的花,它叫的声音也好听,像针脚在缓缓地绣花,啄食过的草叶,像是一张张镂空的小手帕;麦穗雀呢,喜欢盘飞在原野,早春时,和麦苗的颜色一样,嫩绿嫩绿的,然后,变成浅绿、深绿,到五月时,浑身的羽毛会变得和麦穗一样,黄澄澄的。
陶匠除了做陶、吃饭、睡觉、卖陶,就是去捕鸟人家中看鸟。
鸟儿们装在笼里,笼挂在门前的檐下、院中的树上。各种鸟儿叽叽喳喳,扑扇着翅膀,像开在檐下树间的一簇簇鸟花。
每次去,陶匠都会带一件陶。他用它们,换得一只只稀罕的鸟。
他将鸟儿们都放了。他喜欢看它们飞在空中。
捕鸟人的一只只鸟,变成一件件陶。
一件件陶,一溜排地搁在堂屋中,等着以后的以后再卖。
后来,捕鸟人带着戏谑的口吻告诉别人,自己早预感到陶匠将是东西村最后一位制陶人。谁也不知这话的真假。
一天,捕鸟人网到一只从未见过的鸟:通体蓝色,没有一根杂羽,“滴溜滴溜”的叫声,像小铃铛被风摇啊摇,最好的是那双黑豆似的眼珠儿,骨碌一转,惹得人心窝窝暖暖的,想要笑,又想要哭。
陶匠迷上了这只鸟。
他拿来做得最好的碗。碗底卧着一条鱼,放入水,鱼会活泼泼地游来游去。捕鸟人不换。
他拿来做得最好的钵。钵壁上,绕着一圈圈的云纹,阳光落在里面,一小团一小团的云会在钵里跑来跑去。捕鸟人不换。
他又拿来做得最好的罐。罐身上,爬着一根豇豆藤,月光照着时,藤会迅速开花、结果,像变戏法。捕鸟人不换。
捕鸟人说,这鸟稀罕,你得拿稀罕的东西换,比如那只灰陶罐。一听这话,陶匠掉头就走。
灰陶罐是陶匠的爷爷做的,灰扑扑的,笨憨憨的,可无论是干瘪的果,还是蔫了的花儿,从罐里再拿出,都会变得饱满新鲜。村里人都稀罕这罐。孩子们更喜欢。他们常拿了坏掉的果啊瓜啊,往罐里放,再往外掏。
罐是陶匠家的宝,谁都知道眼馋没用,可……可这捕鸟人——唉!
陶匠回家后,一夜没睡,耳边是“滴溜滴溜”的鸟声,眼前晃着那雙黑豆似的眼,心窝窝里是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忧。
早晨,他抱着罐,站在了捕鸟人的院里。
打开鸟笼,那鸟儿停了“滴溜滴溜”,偏起头,将陶匠看了又看。然后,扇翅,飞出,在他的头顶盘旋了一圈又一圈。陶匠将它痴痴地看。后来,他将头一低,转身回了家。
鸟儿跟着飞进陶匠的家。
陶匠开始做活,鸟儿开始“滴溜滴溜”地为他唱歌。
“这儿不是你的家。”陶匠对它讲。鸟儿不唱了,落在他的肩,又将他看了又看,从嘴里喷出一小簇火焰——像一朵红色的小花,落在陶匠的指尖。
火焰,不热不烫,暖暖的。
“谢谢你。”陶匠说。他将火焰放在喝水的杯沿上,继续埋头做陶。鸟儿见了,这才拍拍翅,飞走了。
晚上,陶匠躺在床上,歪头看那簇火焰,心里很暖,不再觉得孤单。
第二天,他用泥抟出一只鸟。第三天,他又抟出一只鸟。从那以后,他每天抟一只鸟。那些鸟,都像那只会吐火焰的鸟儿。他将它们放进窑里,烧出一只只陶鸟。这事,谁也不知道。
放在阁楼窗口的陶鸟,在风经过时,偶尔会“滴溜滴溜”地叫。
他做的陶上,有花,有草,有鱼,有虫,没有鸟。鸟儿属于更大的天地,他不想让它们只住在陶上。他为陶鸟们都捏了翅膀,希望它们能飞。可它们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阁楼。
就在他烧制好第一百只鸟儿的那天,一位衣衫褴褛的女孩,晕倒在村头。他看到她的第一眼,就知道是那只鸟儿回来了。
她的眼睛,和那只鸟儿一模一样,看得人心里暖暖的、酸酸的,像发酵后的面团。
女孩留在了东西村,成了他的新娘。她叫蓼姑。他喊她鸟姑。
外公讲到这里时,有些疲惫。我给他端来妈妈泡好的刺榴茶。他的脚浮肿了,一按一个小窝窝。
“这都怪我以前飞得太高太久,落在地上后,没好好适应呢。”外公调侃。可妈妈讲,是他心脏不好。对啦,那个灰陶罐——
捕鸟人得到的灰陶罐!就是放在屋角落,搁放了许多核桃的灰陶罐吗?外公笑眯眯地点头。
难怪妈妈说放里面的东西,能存很久很久。等一等,桌上正好有个蔫掉的橘子,让我试一试,就试一下。
呃,橘子放进去,拿出来——还是蔫蔫的?外公鼻里哼一声,说这罐到了你太爷爷家后,就不好使啰,也不知是认主,还是知道他没安好心眼。
“他怎么没安好心眼?”我没好气地问。
“他呀,得到这罐后,就不再捕鸟了,你想想,你好好想一想。”
妈妈在菜园拔萝卜,我跑去问她。她抬头,看看我,看看外公,笑笑地说:“也有可能是灰罐累了,没有力气再让东西变得新鲜嘛。”
“也就是说,它以后还可能像以前那样神奇啰?”
“嗯,所以你玩的时候当心点,别碰着它。”
我点头,拼命地点头,真想灰陶罐早点儿又变得神奇,那样我就可以将蔫掉的桃啊橘啊,还有坏掉的花生啊板栗啊,都放在里面。更更好的是,小山、阿毛该多馋我家有这个罐啊。
外公似乎瞧出我的心思,朝我招招手,问我还想不想听他继续讲。
当然想听啦。
牧鸟人
陶匠和鸟姑很恩爱。不久,鸟姑怀孕了。他们忐忑又开心。忐忑的是,他们都没做过爸爸妈妈。开心的是,他们就要做爸爸妈妈了。
村里的孕妇们,肚儿胖胖圆圆的,胎儿的手脚像游泳,在肚里轻轻地划过来划过去;鸟姑的孕肚呢,小小的,胎儿在里面——好像在飞,轻轻地飞,有时好像还能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儿叫,肚里该不会飞出一只小鸟儿吧?鸟姑开玩笑道。
是鸟也没有关系,陶匠认真讲。
已经过了预产期,孩子还迟迟不肯出来。这让小两口不知该怎么办。村里的老人們也不知道。
一天,在田地里劳作的人,看到一位长长的长长的人,迈着缓慢的步子,从东西山的那边,从东西林的上空,朝村子远远地走来。一阵风过,他像一面旗,又像一棵高高的树,左摇右晃,忽而被风扯长,忽而被风缩小。而他身上那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也忽地被扯得很阔大,又忽地贴紧他的身子骨。
等他走近,人们才看清,他身上站满花花绿绿的鸟。
“嘘!”他一声呼哨,铺天盖地的鸟儿雨点般,向四面八方飞去。那件花花绿绿的衣服,没有了,只剩一件赤褐色的长衫。
他弯下长长的腰,向目瞪口呆的村民们问好,也向站在门前的陶匠和鸟姑问好。
过了一会儿,飞出去的鸟儿们,“呼啦啦”地一大片,像从天空坠下的急雨,又像是一条急遽而下的小河,纷纷落回他的帽上、衣上、腿上、鞋上,密密麻麻,花花绿绿。最后,他只有一张微笑的脸,露在外面。
村里的老人曾一辈一辈地讲,有牧鸟人来过。没想到他又来了。
牧鸟人很和蔼。孩子们喜欢坐在他的掌心,被他托举到半空,像一位位小国王,巡视过他的鸟群。他甚至允许他们用小手摸它们。
每只鸟儿,都是村民们不曾见。它们的羽翼是透明的绿,是纯粹的白,是比墨更深的黑,是比火更亮的红。捕鸟人看得直掉口水,尽管他已不再捕鸟。
晚上时,所有鸟的羽翼都亮起来,像一小块一小块的田野在燃烧。一直看着牧鸟人的陶匠和鸟姑,看着看着,像走进梦里面,变得恍恍惚惚。牧鸟人发现了他俩,托举那些孩子一样,将他们轻托在掌心。与此同时,鸟姑开始阵痛——
一个男孩出生了。
对,是一个男孩,不是一只鸟。
男孩在牧鸟人的掌中,不哭不闹。后来,牧鸟人俯下身,朝男孩轻轻一吹,男孩粉嫩的胳膊变成翅膀,小小的脚丫变成细细的鸟足,小嘴巴变成尖尖的鸟喙——
男孩变成一只绿色的小鸟。
他朝栖息在牧鸟人衣服上的鸟群飞去。陶匠和鸟姑,也变成两只鸟儿,落在小鸟的身边。
黎明,牧鸟人打了个呼哨,所有鸟都朝天空飞去。男孩、陶匠和鸟姑,也拍拍翅,飞起。
一只黑鸟告诉他们,鸟儿们分为金部、水部、火部、土部和木部。金部的鸟儿需练习往岩石里飞,水部的得练习往溪里、河里、泉眼里飞,火部则拼命地往高空飞,土部呢,则是往泥里飞,木部是往树木里飞。
很快,鸟儿们飞入河心、岩石、大地、高空、树木。最后,只有陶匠一家,在田野上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不久,当牧鸟人的呼哨由远而近,绵长悠远地随风散入天地各处时,鸟儿们纷纷从河心、岩石、大地、高空、树木中扑翅而出,飞落向牧鸟人。
陶匠一家,也飞落向他。牧鸟人将他们放到地上。一落地,他们变回了人——那男孩,“哇哇哇”地大哭起来。
讲到这,外公的胸口“呼哧呼哧”响,像拉风箱。可他对我摆摆手,说那是翅膀缩回的地方,一激动,它们就想重新长出来。
我看着外公涨红的脸。
他慢慢恢复平静,冲我眨眨眼,说:“你现在知道了吧,我就是大家说的‘还没学会走就学会飞的家伙。”
我正啃着的胡萝卜,掉在了地上。
四脚鸦和大脚女
外公的名字叫晨风。有一种鸟也叫晨风。老外公,也就是那位陶匠,说这名是牧鸟人取的。
和别的孩子不同,外公不哭,爱笑,爱唱,六个月会走路,八个月会说话。
老外公检查外公的腋下,没发现翅膀。
三岁多时,外公隐约感觉有只鸟飞在附近。很快,它露出形体,近似透明,只在阳光照着时,才会被他隐约看见。不久,那鸟透明的羽色变成浅灰,变成深灰,变成一只黑色的鸟。
它看着他。
“那里有只鸟。”他讲。老外公顺着他的手指,却什么也没看见。
鸟不叫。它酷似乌鸦,长着四足。
老外婆也看不见。她病了,病得很重。外公害怕,知道黑鸟的到来和老外婆有关。
他想赶它走。可它像一阵烟、一阵雾,影影绰绰,无法驱赶。
四脚鸦飞进屋时,老外婆已瘦弱成一个婴孩,只有一双眼睛仍乌黑明亮。她抓着外公的手,久久地看他,像是要将他的每根头发都记在心上。
四脚鸦落在了她的肩上。那簇在老外公杯口燃烧很久的无名鸟的火焰,熄灭了。
妈妈去哪了?外公问。
她变成一只鸟飞走了,老外公回答。
外公知道,是四脚鸦带走了他的妈妈。他想变成一只鸟,追上它,带回她。可他的心太沉重了,身也太沉重了。他的双臂没有变成翅膀。
原本三个人的小院,顿时显得很大很空。寡言的老外公,话变得更少。外公没说话的人时,就和路过的风、墙角的花、经过的鸡鸭说话。渐渐地,他懂得了它们的语言,也能听懂风和雨的歌。
他给老外公唱歌、讲蚂蚁搬家。老外公听着听着,大颗大颗的眼泪,掉在正制的陶上。这些陶,烧出后,一沾水,就碎。而那些他忍住泪,制出的陶,烧出后,轻轻一碰,也碎了。
老外公找出一副货担,一头挑着外公,一头挑着以前制的陶,开始走村。
父子俩一直走啊走,翻过一座座山,穿过一座座林,走过一个个村。陶器早卖完了。好像该回家了。可父子俩停不下来了,就那么一直走呀走了下去。
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外公不用坐货担了。一开始,他还会牵牵老外公的手,慢慢地,他便撒开脚丫,一个人蹦蹦跳跳地走到了他的前面。他有时走得很快,很急,像在飞。
一天,父子俩走累,正想歇息,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旋风般从他俩身边刮过——那刮起的风哟,像一双巨手,推搡着他俩,跟在了那女人的身后。
后来,那女人停在山坡。她深深地,深深地吸一口气,浑身顿时像一座发酵的馒头山,开始长啊长,长成一大团圆圆滚滚的东西。然后,她脚往上一踮,双手往上一举,变成一股大风,朝天空刮去。
大風忽而使劲地吹着天空中的云,忽而在林中横冲直撞,忽而摔打着原野里的庄稼。后来,她累了,落回地上,变回了那个又高又胖的女人。
她沮丧地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
父子俩朝她走去。
她吃光了他们所有的饼,喝光了他们所有的水。然后,才抬起头,看着他俩。
她头发黄而稀疏,鼻子塌,牙齿龅,眼睛泪汪汪,像在哭——嗯,有点丑丑的。可她身上有股味道,让外公想起老外婆。他靠着她,安静地坐下。
她告诉父子俩,她叫“坏脾气的大脚女”。一瞧,哟,那双脚,果真像两只小船。
大家都怕她。没人娶她。她很孤单。老外公也孤单。他们坐着,对看。
“娶我。”她讲。
“好。”老外公话一出口,突然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回家了。
山里有位小老头
外公吃药。他的药又多又苦。看着他喝,我直吐舌头。外公故意“吧嗒吧嗒”地咂嘴。
“不难喝呢。”
“喝了,你就会好了吗,外公?”
“才不是,这药啊——喝了,会让我又长出翅膀。”外公笑呵呵地讲。
妈妈做饭时,我问她,婴儿可以六个月走路吗,大脚老外婆真的能变成风吗。妈妈笑笑,说锅子里熬了青菜粥。
我没见过大脚老外婆。可我听妈妈讲过,说她……说她是一个秃子。
外公说,她一开始只是头发有点少,成为秃子嘛,那是因为——
她脾气坏。
还记得吗,别人都叫她“坏脾气的大脚女”。刚和老外公成亲时,她其实像换了一个人,说话的嗓门变低了,走路的声音变小了,生气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外公常和她一起,去菜园,去麦地。他们相处得很好。
老外婆做事利落,一片麦地,一弯腰,只看到一柄镰像闪电,所到之处,黄澄澄的麦齐刷刷地倒。她的力气也大,一地的麦,用一根大扁担,三五趟就挑完。
老外公不做农活,只做陶。他做得认认真真,烧出的陶,很结实,比以前还好看,可碗,啊勺啊,钵啊,罐上的鱼啊,花啊,草啊,云啊,都不会动了。他让外公学做陶。外公不肯。
不久,外公有了一个小弟弟。嗯,我该叫他舅爷啦。
有了自己的宝宝,老外婆是不是对外公就不好啦?外公说,她对他仍很好。只是,她和老外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她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会变成一阵狂风,刮来刮去,会将树摇得东倒西歪,会将老外公做的陶都摔坏。
“妈妈,别生气,长大后,我给你做一双船鞋。”不过,只要外公这么一说,大脚老外婆就会慢慢停下来。
老外公开始迅速衰老,身子矮下去,背弯下去,发须变白,眼睛昏花。有人说,他一定是不小心冲撞了山老头。
据说,山老头掌管着东西山,住在一个阔绰的山洞洞里,常背着一个大布袋,游走在四乡八野。他脾气怪,看谁顺眼,会送好运好礼,看谁不顺眼,会使坏。
外公怀疑山老头拿走了老外公的时间。当他感觉到四脚鸦又飞在附近时,决心去找山老头。
山大,路难,他没找着山老头。回家的路上,他边哭边看飞过的鸟,想要变成它们。
他再次试图赶走四脚鸦。它不躲不避,不惊不惧,安安静静,像一团暗光,一碗黑水,照着你,映着你,棍啊,棒啊,落在它身上,就像落在一个能看见却无法触碰到的地方。
老外公去世后,老外婆开始掉头发,脑袋中央变得白水蛋一样光光的。
她成了秃子。村里的小孩看到她,开始唱:
大脚女,秃秃秃。
变成风,呼呼呼。
一阵秃来一阵风,
害得花猫钻灶孔。
老外婆气得不行,变成风,“呼啦啦”地刮到这家,掀翻别人晒的豆,“呼啦啦”刮到那家,扯了别人晾晒的衣,顺带还将一群鸡刮上了树。
“妈妈,别生气,我去给你找草药。”外公对她讲。他听村里老人讲过,东西山的悬崖上,长着姜草。抹了那草的汁,石头能发芽,光头能生发。
天寒,地冻,外公在山里走了一圈,还没寻着悬崖呢,却迷了路。夏天的山里,怕兽;冬天的山里嘛,怕冻。
外公不怕。他带着火镰呢。
他找了避风地,堆起火,掏出糍粑,放火上烤。一会儿,糍粑烤得“滋滋”响,散出好闻的糯香味儿。他不慌不忙掏出准备的白糖,撒在鼓鼓的糍粑上——
嗯,真香啊,连火舌也抻长,想要尝一口。就在这时,“喀嚓”一声响,一个七寸高的小老头从树后跳出来。
“糍粑归我吃。”小老头毫不客气道。他戴着一顶黄小帽,穿着红袄红裤,雪白的胡须一翘一翘,雪白的寿眉下红彤彤的鼻头像山楂。
外公将糍粑递给他。
外公掏出一把板栗,扔进火里烤。板栗被火烘得热,“噼里啪啦”,敞开一件件硬壳衣,散出香喷喷的栗肉香。
“板栗归我吃。”小老头嚷嚷道。外公将板栗一颗一颗剥给他。
外公又掏出一小壶酒。
“酒归我喝。”小老头兴奋道。
“那可不行。”这次,外公拒绝了他。
“糍粑和板栗都可以,为什么酒不可以?”小老头跺脚,气呼呼地问。
外公说,糍粑是他做的,板栗是他捡的,可那酒却是老外公制陶的钱买的。
“不过,你可以和我一起喝。”外公说。
“好吧,就当你是邀请我哦。”小老头不情不愿地讲。
于是,两人围着火,喝起酒。酒好,喝得人轻飘飘。光喝酒没意思,小老头提议玩牌。
没有牌?好办!小老头掏出一根细木棍,朝着头顶树上残存的叶子绕一绕,叶子变纸牌,一张张掉在火堆旁。他们玩了一把又一把。每一把,都是外公输。
外公提议玩别的。他问小老头还会什么。
“我会的可多了。”小老头笑嘻嘻地讲,胡须一抖一抖,变得忽长忽短。他将脚跺一跺,瘦小的身体忽地变得圆滚滚,像是一圆桶;他将脚跺两跺,圆滚滚的身体忽地变得扁扁的,像是一簸箩;他将脚跺三跺,扁扁的身体拉得长长的,像是一张席。
轮到外公了。
外公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吧。
“父亲挑着陶,挑着我,走村时,遇到一群孩子和一条狗。那狗凶,追着我们撵,孩子们一见,忙追狗。跑啊跑,父亲带着我,跑不动了,他灵机一动,猛地一掉头,朝那狗跑去。狗傻了,等反应过来,父亲已跑到孩子们中间。”
“这不是一个笑话。”小老头尖叫道。
“还没讲完嘛,”外公慢悠悠道,“这时,那狗说话了:‘你傻啊,我追你,是想和你的儿子玩;他们追我,是要我和他们玩。现在好啦,你儿子只能和他们一起玩了。说完,那狗就走了,再也没出现。”
小老头搔搔头,问:“除了讲笑话,你还会啥?”
外公指着燃烧的火堆:“我看到里面有只火鸟,还听到它在唱歌。”小老头歪头瞧了一会儿,说:“我没看见,也没听见。”
“只是你没看见没听见,也许我讲了关于它的故事,你就能看见,就能听见。”
“深林里,有一种无音鸟。不知道的人,以为它生来是哑鸟,不会鸣唱。林中的树们却全都知道,这鸟只要在最喜欢的树上筑巢后,就会敞开喉咙,尽情歌唱。
它的歌声像从天空走下,让听见的人和兽都变得醉醺醺的。它筑巢的树,甚至会拔出脚,在大地行走。
鸟和树,会一直在一起。直到某天,鸟累了,钻进树里,树才会停止行走。而那树,若是被砍伐后,扔进火里,熊熊燃烧,鸟就会重新醒来,唱起生命里最后一首歌。”
“瞧,我们多幸运,正巧听到这只鸟儿最后的歌。”外公说。
小老头一仰头,喝尽壶中最后一滴酒,咂咂嘴:“你是一个有趣的人!我问你,若有人想送你一只母鸡或一只公鸡,你要哪只鸡?”
“母鸡下蛋,公鸡打鸣,都好——我要那只弟弟会喜欢的鸡。”
“两只鸡,一只下鸡蛋,一只下金蛋,你要哪只?”
“穷的时候,要下金蛋的;富的时候,要下鸡蛋的。”
小老头背着手,绕着火堆转了一圈又一圈,说:“吃了你的糍粑和板栗,喝了你的酒,听了你的笑话和故事,让我再来难为难为你。”
嘿,有这样的人吗。可外公不介意,笑笑地点点头。
眨巴眨巴眼,火堆旁,站着三个一模一样的小老头。
“猜猜,谁是我?”三个小老头的胡子都一翘一翘的。
“山老头是你,你是山老头。”
“刚才吃喝你东西的是谁?”
“吃我东西的是口福老头,喝我酒的是无忧老头,听我笑话和故事的是快活老头。三个老头是山老头。”
“哈哈,有意思,有意思,”三老头变回了一个老头,对着外公手舞足蹈地讲,“快说,快说,你到这林里做什么。如果你对我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
“我来找姜草。”
“哈哈,我知道,我知道,山下的村里有一个秃头女人。”小老头拍腿大笑,“那东西不在东西林里,不在东西山里,在那东西河里。”
小老头告诉外公如何才能采到姜草。
“现在好了,你心里的事解决了,我们一起跳舞吧。”小老头拉起外公,绕着火,嘣嚓嚓跳起舞。两人越跳越高兴,周围的树啊草啊灌木啊,也都跟着,嘣嚓嚓地跳起来。
“说说,说说,你还有什么事吗?”俩人跳累了,跌坐到火堆旁时,小老头又问道。
“我不知道以后该做什么。”外公实话实说。
“好办,做我的货郎,卖了钱,你三份,我七份,买鞋穿,买花戴。”
做货郎?外公一翻身,看着小老头:“你怎么知道我想做货郎?”
“这个嘛——我是山老头呀。”
大鱼看守着姜草
妈妈熬了小米青菜粥,炒了莴笋。都是外公和我喜欢的。
吃着喝着,外公忽然问我,如果天天一样的饭菜,我会选大鱼大肉,还是选粥饭和泡菜?
大鱼大肉,嗯,我喜欢大口吃肉小口吃鱼,可天天一样啊,那……还是粥饭和泡菜更好点。
外公说,他选的和我的一样。
吃过饭,外公小睡了会儿。妈妈说,他需要多休息。可他一醒来,就吵着要出去转一转。妈妈要我陪着他。
我喜欢跟着外公,到处转一转。
外公以前住的老屋,门前的杏花开了,绕着栅栏的打碗花也开了。他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后,每天都要回家看看的。
“你舅爷说不定会回这养老呢。”嗯,这话嘛,外公已经说了一次又一次。舅爷在城里住着大房子,做着大生意,美得很,回这?
看了老屋后,我们往河边走。一路上,外公和我指认着野花玩。
“蒲公英。”我说。
“太阳脸。”外公说。嗯,一听,就是他胡诌啦。
“紫花地丁。”
“紫星星。”
“荠菜。”
“小碎米。”
“哎呀,外公!”
外公先是呵呵笑,继而一阵急咳,慌得我忙给他捶背。
“不要叫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另取一个,这样才好玩。”外公说。好像……有点道理。
于是,我们指认了狐狸花、獾尾巴、豆娘花、鸭子草、羊眼树。
瞧,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陪外公了吧。对了,你知道他在哪找到姜草的吗?
就在这东西河里哦。
山老头说,姜草由河里的水族们种植,一条大鱼日夜守着,要想采到,得在星星最多的晚上。
外公知道河里什么时候星星最多。
桃熟月,四面八方的星星,会齐聚到东西村的上空,趁夜深人静时,溜进河里洗澡玩耍。这秘密,他从小就知道。
看守的大鱼被游来游去的星星们迷住了。碧绿的姜草,在一河的星光下,像穿上银闪闪的外衣。可是——可是,这个外公,并没有按山老头教的,趁机采走姜草。
他等着大鱼看完星星。
“你为什么不趁机偷偷采走呢?”大鱼问。
“我想,你也许会同意我采。”
“看来你是想试试自己的运气啰?”
“不,我是想试试向别人提出请求的胆量。”
“好吧,我会送你一束姜草,但不是因你有胆量,而是因为你的诚实。”
外公带回了姜草。
老外婆秃头的地方,长出乌黑的发。那她后来为什么又秃了,甚至变成了光头呢?这啊——你听下去就知道了。
外公决定去当货郎。
山老头住的山洞洞里,堆满各种各样的货物,会自己捣碎东西的蒜臼子,会跳舞的小锅子,种下就发芽的花种子,跳跃出水花儿的木勺子,会“咿咿呀呀”唱歌的小凳子,还有会跳来跳去的小扫帚。
山老头随便外公挑,随便他选。他还送他一副货郎担。那担,什么东西都可放里面,多少东西也装不满。
就这样,外公当起了货郎。我从小就知道,他卖的东西好,价格公道,一见他挑着担从村口回来,满村的孩子都会围向他。
生病前,妈妈和姨妈就不要他再走村卖东西。外公不肯。她们怕他辛苦。外公说,卖东西好玩,不辛苦。
“要走好多好多的路吗?”我问外公。
“才不是,”外公弯下腰,神秘兮兮地对我讲,“有时候,我走着走着,水会带着我走,云会带着我走,风也会带着我走。”
我瞪大了眼。
“因为我走着走着,就会变成一只鸟儿嘛。”外公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一只挑着货担,飞着的鸟儿?这可真新鲜。
廖小琴,笔名麦子。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丰子恺图画书奖、信谊图画书奖、四川文学奖特别奖等,作品入选具世界影响力的“白乌鸦书目”,进入“年度优秀童书”“年度桂冠童书”等。有《大熊的女儿》《棉婆婆睡不着》《我的外婆在乡下》《走出黑森林的男孩》等书出版。
责任编辑: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