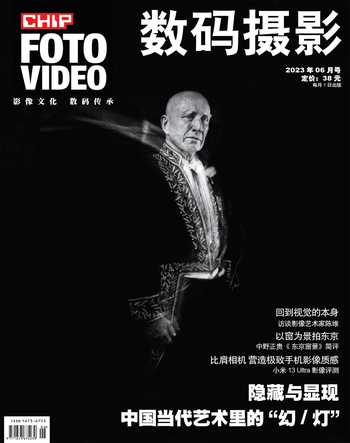芳菲中的幽径
苏葵



记得是在一个吹着风的下午,去看了展览《延展与隐匿——俊朗之径》。李俊和黎朗,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这两位居住在成都的摄影艺术家都曾获得过许多国内外的重要奖项。他们的作品无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此前,我也在其他的展览上见过,但未曾设想过他们会以双个展的形式来呈现自己作品。
对这个展览,我其实有很多的期待和想象。正如展览名称所言——“延展”“隐匿”,当他们的路径与思考在同一语境下发生碰撞与交流时,会形成怎样的关系?又带给我怎样的感受?
展览的地点在成都的蓝顶美术馆。进入展厅, 首先进入视线的是“延展与隐匿——俊朗之径”这几个大字,虽然简单,但看上去却很劲道,似乎在暗示:展览“不多言多语、不花里胡哨,干净利落,充满力量”。现场也的确给予了我这样的感觉。展览并不是以某位艺术家的创作脉络为线索来依次展开——而且,就算是一组作品,有时也是以一种近乎“散文”的方式来排列。此外,展厅除了固定的长展墙外,策展人还在空间中间搭建了很多短展墙,这些展墙都有多面——例如有的展墙就呈Y字型,这就让作品的展现方式变得很灵动。事实上,展览确实没有把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分成两个场域来展出,而是以打散的方式,让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交织”和“并列”。并且,展墙的特性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固定、严密的观看路线,无法给予观众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看了这面墙后,下一面你应该看向哪里?”观展顺序多样且可变,这或许也给观众带来了“挑战”,毕竟观众有时过于依赖这些信号,从而可以更容易、更快速地把握整个展览。但现在,当信号变得模糊后,就意味着展览意义的构建更多的需要观众的反复观看和思考。对于此前从未看过黎朗和李俊作品的观众而言,他们或许需要更认真地观看这场展览,以此才能厘清艺术家的作品线索,如果一瞥而过,可能都无法清楚眼前作品属于哪位艺术家,更不用说理解整场展览了;但对于之前已较为熟悉他们作品的觀众而言,这种展现方式无疑也让他们得以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观看艺术家们的作品。毕竟,交错的作品呈现、不固定的观展路线,可能让他们很难像观看其他展览那样,看完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再看下一位,而是不停地交叉,感知和思维处于一种快速切换的状态里……重要的不仅仅是艺术家自己的作品体系与表达脉络,作品在联结后的语境中所产生的共振与差异,也同样——甚至更为——关键。我想,这或许就是李俊和黎朗双个展之意。
其实看了这两位艺术家的双个展后,我的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词——“存在”。虽然,存在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可以用来囊括的对象和范畴有很多,但在我看来,他们的作品都是在表达对“存在”的思考。并且,这种思考所传递出的强度是较为强烈的——黎朗的作品,无论是在其父遗物照片或者肖像照片上不断书写其父在世上生活过的日期,还是在墙面上用铅笔书写其父曾生活过的30219天中的每一个日期,然后再用刻刀将这些时期刻掉……它们都指向了他对于父亲的存在的思考——就像他在自述里所写,他不愿意只是在父亲的墓碑上刻上出生日期与死亡日期,中间的破折号就概括了父亲的一生,他想要知道父亲到底在世界上活了多少天,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很重要,所以他夜以继日地书写,写下了他的父亲生活过的每一天的日期,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一次次地完成了自己对于父亲的回忆和想象。这个系列不仅让人感触于黎朗对于父亲的深刻情感、以及用重复书写对于遗忘的抵抗,也感触于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作品仿佛在询问每一位观众——人是如何“存在”着?一个人是如何存在着又是如何在他人的记忆里存在着?我们如何回忆那些已不存在的人,又是如何构建存在着的生活?那一个个具体的日期和这些日期中发生的事情是否就构成了一个人的一生?这种对于“存在”的思考,也出现在他的其他现场作品中,例如作品《某年某月某日》,他在“一趟往返有四千六百公里的高速火车上,以统计学采样的方式拍摄窗外的景观,跟随火车纵贯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度,穿过城市、乡镇、农村、丘陵、平原和荒野”。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思考现实是什么。他把对现实的旁观和对风景的旁观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正如“某年某月某日”这个标题一般,在他看来,昨天、今天、明天最后都会以“某年某月某日”的形式存在,而这种旁观也在数个周而复始的“某年某月某日”中持续地进行着——这也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隐喻。
李俊的作品同样表现出了对于“存在”的关切,只不过他更多的是从“纯物”的角度来切入。在作品《无常时》里,李俊在自己的家里发现了灰尘所形成的痕迹,于是便拍下了这个系列里的第一张照片,此后,他开始有计划地去“培养灰尘”,在灰尘将物件和物件的周遭覆盖后,他再将物件移开,此时,物件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缺席而变得隐匿,反而是在灰尘的作用下,其原先放置它的地方被留下了印痕——物件没有直接出现在图像里,却又是切切实实地存在于图像中,物件的“不在”反而更加深刻地印证了物的“存在”/“曾经存在”。在这里,看得见的、逐日逐月积累下的灰尘,也隐喻着看不见的逐日逐月流逝的时间,李俊不仅是在深思物的存在以及物之于“存在与缺席”间的深刻辩证关系,也是在向我们发问:存在是如何“存在”,“存在”与“不存在”是否真的处于对立状态?“不存在”是否也是一种“存在”?
此外,对于“存在”的思考,在李俊的作品《物影》中也延续了下来。他拍下了物体和物体的影子,却又运用数字技术将物体抹掉,于是只留下了物体的发光和阴影。如果说,在作品《无常时》中还有标题来暗示那些缺席的物件是什么,那么在作品《物影》中,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晓李俊的拍摄对象是什么?如果说,在作品《无常时》里我们还能看见,还能感受到具体的“形象”,那么在作品《物影》中,具象的物似乎已经“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抽象的影子。而这种“抽象感”,在作品《记之暗面》中也存在着——艺术家将之前由相机拍摄的图像重新放入相机的内部,这些图像被光线穿透,然后会在底片上感光成影。这依然是对物的存在的探讨——图像作为物和作为物的图像,这一次,李俊还对相机的图像生产机制进行了反思。并且,在作品《记之暗面》完成后,李俊又把零散的底片重新组合,这些片段化的底片、物件作为他个人的视觉档案被重新并置,以此隐喻了他自己的存在状态和他所感受到的世界。可以说,李俊的作品通过物将我最终引向了对“存在与虚无”、对一种普遍性的存在状态和境遇的思考。
当然,虽然这两位艺术家都在关注存在,但在我看来,他们的路径却有所不同——一个侧重于从抽象到具象,另一个则侧重于从具象到抽象。黎朗的艺术实践,在我看来是比较“具象”的,这种具象体现在他重复书写日期的行为上,他父亲的一生,对于观众而言,原本是抽象和难以直感的,但通过书写父亲存在过的一个个日期,却能让我们的感受具像化,从而能真正具体地感受到一个人的“曾在”,感受到他父一生的重量。此外,这种具象也体现在黎朗对具象化的表达的偏好上,作品《一九七四》正是以他出生的那年作为记忆元年,通过“三百九十张幻灯片循环播放和回忆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四个故事的画外音,以及对一九七四年大事记的梳理和直接在墙上对记忆文本的书写”,重构黎朗对于记忆元年的想象。甚至,就算是未曾直接表露具体日期、看起来似乎有些“抽象”的作品《某年某月某日》,也正是因为可以指向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每一天,指向最后都以“某年某月某日”形式存在的每一天,而拥有了具象的意义。“某年某月某日”并不是遥远的一天,也不是存在于历史中的和我们不相关的一天,而是我们每个人已经经历、正在经历或者即将经历的每一天。对于日期的重视,对于每一个日期的独特性和重复性,对于人在每一天、每一个日期中的存在状态的关注,都体现了黎朗将抽象的“人的存在”命题转化为具象、可感经验的尝试。他让我们对较为宏大的“人的存在”议题的思考,从一个个具体的“日期”出发,并落脚于一个个看似平凡的“日期”上。尽管日期作为文字具有抽象性,却并不停留于抽象,而是带着我们走进了对那些具体日期背后所发生的具体之事的想象里,进而推及到对我们自身所走过的日子,以及在这些日子中所经历的事件的回忆和反观。
而李俊的作品,在我看来,其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对具体物的意义的思考,而是将具象的日常之物抽象化,通过对它们的某种“共性”/“精神性”的提炼和呈现,进而完成了對“存在和虚无”命题的诠释与表达。这一点,在从作品《无常时》到作品《物影》的细节转变上便可见一斑。正如前文所言,作品《无常时》还存在着文字暗示画面中的缺席之物,只留下了印痕的物是什么,以及它们和艺术家之间在日常语境下所产生的关联——例如作品《一个人用的》。并且,画面也具有一定的日常性和具象化——它们都是李俊在家里拍摄的,我们透过画面中的陈设、缺席之物所处的位置,其他物件的摆放都能感受到艺术家日常所处的环境,一个具象化的独一无二的空间。但作品《物影》却将物进一步的抽象化,没有任何文字再来暗示曾经在场的物为何物,它们和艺术家有什么关联,这或许就成为了只有艺术家知道的秘密;物所处的地方也从家——一个特定的环境转变成高度抽象的由纯黑色背景与纯白色台面构成的场域。相较于作品《无常时》,作品《物影》的画面显得更加干净、整洁,此外,作品《无常时》里的图像呈现了大量的、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而作品《物影》却似乎有意识地将这些痕迹去除。在这里,物的日常功用、价值或许愈发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物在“存在与缺席之间”所体现出的张力与“精神性”。因此,李俊的作品并不完全是要聚焦于某个/某类具体的物,表达对具体之物的思考,而是要通过对“物”的关注、表现和提炼,最终完成对“存在与虚无”这一哲学命题的反思。在作品《记之暗面》中,那些看上去有些抽象的画面,实则都是曾经拍下的具象图像在被光穿透后所形成的。这里的“物”依然从具象走向了抽象——它们曾经表达了什么、叙述了什么,在光的作用下,都似乎重新回到了“粒子”的层面,回到了存在的“存在本身”。所以,从作品《无常时》到作品《物影》再到作品《记之暗面》,他的路径是从具象出发,最终到达抽象,到达对那不可言说、难以言说之境的存在的观照。
然而,无论是具象或抽象,最终抵达的都是艺术家和观看者的内心。观看这场展览就如同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看完后,虽然原路返回,一切都没有变化,但在这一来一回之间,内心却逐渐充盈。黎朗与李俊的作品,带领着我们走进了那条“俊朗之径”,在那条“俊朗之径”上,“存在”正向存在着的一切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