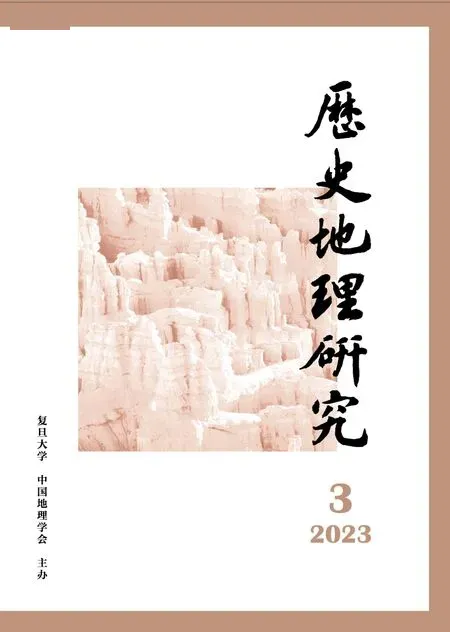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及影响
——以河流水系为中心
霍仁龙
(1.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2.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成都 610065)
近代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图测绘活动。一方面填补了世界地图上的空白,提高了西方国家对世界地理事物的认知水平;另一方面也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领土扩张提供了丰富的情报(1)J. P. Sharp, Geographies of Postcolonialism: Spaces of Power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9;[英] 丹尼尔·克莱顿: 《批判性的帝国和殖民地理学》,[英] 凯·安德森等主编,李蕾蕾等译: 《文化地理学手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35—561页。,重新塑造了被殖民地区的政治与地理界线(2)M. H. Edney,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D. V. Zou, M. S. Kumar, Mapping a colonial borderland: objectifying the geo-body of India’s Northeas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1, Vol.70, No.1;[美] 通猜·威尼差恭著,袁剑译: 《图绘暹罗: 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形成了一种殖民主义的权力
话语(3)[美] 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 《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宋念申: 《地图帝国主义: 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赵光锐: 《论20世纪上半叶英帝国的西藏知识生产机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19世纪,英国不断派遣军事调查队、测量员、间谍和边疆官员等到中国西藏东南地区(4)本文所研究的西藏东南地区主要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下及其主要支流: 察隅河、丹巴河、西巴霞曲流域,面积稍大于今天被印度非法占领的地区。进行非法测绘活动,其中,河流水系是重要的测绘内容之一。至19世纪末期,英国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认知逐渐清晰,地图中的空白不断被填补,形成了相对较为完善的地理认知体系。此外,英国对西藏东南地区的测绘活动也为20世纪初期“新外线”和“麦克马洪线”等非法边界线的炮制提供了情报基础(5)[英] 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 《中印涉藏关系史: 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 1904—19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71—372页。,影响深远。
国外学术界多将英国在中国西藏的地图测绘和调查活动看作是探险和“发现”未知世界的过程(6)G. Sandberg, The Exploration of Tibet: Its History and Particular from 1623 to 1904, London: W. Thacker &Co., 1904;[美] 约翰·麦格雷格著,向红笳译: 《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瑞士] 米歇尔·泰勒著,耿昇译: 《发现西藏》第2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英] 彼得·霍普柯克著,向红笳等译: 《闯入世界屋脊的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L. Petech, China and the European travellers to Tibet, 1860-1880, T’ong Pao(通报), 1976, Vol.LXII.,尤其是印度本土间谍班智达在西藏的秘密测绘活动引起了较多的关注(7)D.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and Central Asia,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8; J. Stewart, Spying for the Raj: The Pundits and the Mapping of the Himalaya, Stroud: Sutton Publishing, 2006; R. Dean, Mapping the Great Game: Explorers, Spies &Maps in Nineteenth-century Asia, Oxford &Philadelphia: Casemate, 2019.,部分研究也关注到英国利用地图测绘等为手段蚕食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8)[英] 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 《中印涉藏关系史: 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 1904—1914》;D. V. Zou, M. S. Kumar, Mapping a colonial borderland: objectifying the geo-body of India’s northeas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1, Vol.70, No.1.。国内相关研究梳理了中国及西方国家在西藏的地图测绘史(9)黄盛璋: 《中国地图有关中印边界的画法的分析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第1—6页;房建昌: 《清代西藏的行政区划及历史地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清代西藏历史地图的编纂、史料及方法》,《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354页;孔令伟: 《钦差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图测绘与世界地理知识之传播》,《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21年第92本第3分;赵光锐: 《界划西藏: 20世纪40年代英国有关西藏地图的“政治规范”》,《史林》2022年第4期;陈发虎、王亚军、丁林等: 《1949年以前青藏高原探险和科学考察活动情况》,《地理学报》2022年第7期。,尤其关注地图中边界线画法的演变过程(10)牛汝辰: 《地图测绘与中国疆域变迁》,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戴超武: 《中国和印度有关地图边界画法的交涉及其意义(1950—1962)》,《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但国内外学术界对19世纪英国在西藏东南地区的地图测绘过程,尤其是对河流水系这一自然地理事物的测绘过程及其影响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利用英属印度测量局档案、近代英国所绘西藏东南地区地图资料、调查报告等,以河流水系,即雅鲁藏布江下游主河道及三条最大的支流察隅河、丹巴河、西巴霞曲为中心,研究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进行非法测绘的时空过程、阶段性特征,及其对这一地区地理知识体系初步形成和英国殖民侵略等的影响。
一、英国早期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
地理认知(1824年前)
西藏东南地区主要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形北高南低,雅鲁藏布江由东流折向南流后纵贯整个地区,成为这一地区最大的河流。雅鲁藏布江流至印度阿萨姆地区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丹巴河(Dibang)、察隅河(在印度称为“鲁希特河”,Lohit)、西巴霞曲(英文文献中称为“苏班西里河”,Subansiri)三条主要支流先后汇入布拉马普特拉河,构成了西藏东南地区的主要河流水系,也成为近代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和印度阿萨姆地区测绘的重要内容。(11)J. T. Walker, The hydrography of south-east Tibet,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8, Vol.10, No.9.
1824—1826年,英国通过第一次缅甸战争和《杨达波条约》(Treaty of Yandaboo)从缅甸手中夺取了新的领土阿萨姆(12)C. U. Aitchison, A Collection of Treaties, 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Vol.1, Calcutta: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892, p.198.,使得英印东北部与中国西藏有了直接接壤的地区。在第一次缅甸战争之前,英国还未能到中国西藏东南地区进行实地测绘,其对这一地区的地理认知主要来自康熙《皇舆全览图》在国外的转绘与传播。
法国传教士在清康熙年间主持编绘的《皇舆全览图》,是我国首次利用西方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全国性地图。(13)翁文灏: 《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1930年第3期;[法] 杜赫德著,葛剑雄译: 《测绘中国地图纪事》,《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212页;冯宝琳: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白鸿叶、李孝聪: 《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康熙五十三年(1714),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被派往西藏进行测绘活动,从青海西宁进入西藏,到达拉萨,进而到达冈底斯山和恒河源。但这次测绘活动遇到策妄阿拉布坦叛乱,测绘队伍被迫返回。根据喇嘛的测绘结果,传教士编制了《皇舆全览图》中的西藏部分。(14)白鸿叶、李孝聪: 《康熙朝〈皇舆全览图〉》,第52页;孔令伟: 《钦差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图测绘与世界地理知识之传播》,《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21年第92本第3分。18世纪30年代,巴黎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15)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hiese-Tartary, Corea and Thibet, London: J. Watts, 1736.,第一卷所附“中国、中国鞑靼与西藏总图”,即1734年由唐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主要依据康熙《皇舆全览图》改绘(以下简称“唐氏地图”),成为18世纪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西藏地方的重要参考(16)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唐氏地图中雅鲁藏布江由西北流向东南方向,最后流入阿瓦王朝(Awa),这也导致后世许多西方地理学者认为雅鲁藏布江的下游为伊洛瓦底江。(17)R. H. Phillimor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3, 1815-1830, Dehra Dun: The Office of the Geodetic Branch, Survey of India, 1954, p.57.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福克斯版本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以下简称“福克斯地图”)中,中文标注雅鲁藏布江流入姓烟县昂河。
唐氏地图分别采用以北京为零度经线和巴黎为零度经线的经纬度系统,研究时需要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为零度经线换算度数。在唐氏地图中,雅鲁藏布江在21°W附近消失。据韩昭庆研究,《皇舆全览图》以北京太和殿为大地原点,即中央经线所在地的0°经线(116°23′27″E),在其东为东经,其西为西经。(18)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故唐氏地图中雅鲁藏布江消失的地方应位于95°23′27″E附近。雅鲁藏布江在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的实测经度约为95°21′36″E(19)经度实测数据来自天地图,https://map.tianditu.gov.cn/。,与唐氏地图绘制情形较为相似。所以,虽然唐氏地图中雅鲁藏布江下游标注为流入缅甸,但经度却显示其下游应流入布拉马普特拉河。
雅鲁藏布江以东,唐氏地图中绘有更布河(Kenpu),自北向南流。福克斯地图中将这一河流标注为“噶哥布藏布必拉”,“必拉”为满语,河流之意。(20)万依主编: 《故宫辞典》,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547页。唐氏地图中更布河消失处的经度换算约为96°23′27″E,察隅河在由南流折向西流处实测经度约为96°55′12″E,这与唐氏地图中的更布河较为相似,故其应为察隅河。
唐氏地图中将雅鲁藏布江西部的河流标注为乌姆曲(Omchu),乌姆曲的西部支流标注为“Lopra Kachu”。在福克斯地图中,这一河流标注为“母母撮必拉”,西部支流标注为“罗普拉喀初必拉”。唐氏地图中乌姆曲消失处经度可换算为94°23′27″E,与西巴霞曲在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处的实测经度94°15′36″E较为相似,故地图中的乌姆曲应为西巴霞曲,而地图中西巴霞曲的西部支流应为坎拉河。
总的来说,18世纪初期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已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河流水系进行了初步绘制,唐氏地图中雅鲁藏布江下游虽标绘注入缅甸,但推算其经度却发现与其流入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位置相似。察隅河、西巴霞曲等主要支流的地理位置和大体流向也都进行了标绘,形成了西方世界认识中国西藏东南地区地理知识的基础。英属印度测量局也认为“第一幅基于系统勘测的西藏和喜马拉雅山脉地图是1733年唐维尔所绘”(21)按: 这里指1733年唐维尔所绘法文版地图。R. H. Phillimor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1, 18th Century, p.70.。
1765年,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瑞纳尔(J. Rennell)对布拉马普特拉河进行了测量,并提出布拉马普特拉河与雅鲁藏布江是同一条河流的观点。(22)J. Rennell, An account of the Ganges and Burrampooter River,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71, 1781. Memoir of a Mogul Empire, London: M. Brown, 1788.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多将该河绘制成一条500英里长的、自北向南流的小河流。(23)R. H. Phillimor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1, 18th Century, p.78.在1788年瑞纳尔所绘《最新权威印度斯坦或莫卧儿帝国地图》(24)J. Rennell, A map of Hindoostan, or the Mogul Empire: from the latest authorities, 1788.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和1801年阿罗史密斯(A. Arrowsmith)所绘《亚洲地图》(25)A. Arrowsmith, Asia, 1801. 大卫·拉姆齐地图网站藏。中,阿萨姆地区位于印度版图以外,雅鲁藏布江的走向基本承袭了唐氏地图的画法,其下游走向则主要依据瑞纳尔的观点,连接布拉马普特拉河。西巴霞曲和察隅河的走向亦与唐氏地图相似,但两图都误将察隅河下游绘制为流向缅甸。
除地图外,这一时期英国对印度或阿萨姆地区的地理类论著中也多提到阿萨姆北部山区的河流水系。1820年,W. 汉密尔顿(W. Hamilton)在《印度斯坦及周边国家的地理、统计与历史描述》中,认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为雅鲁藏布江的下游,雅鲁藏布江从源头一直向东流,在96°E附近转向南方,出现在阿萨姆地区。(26)W. Hamilton. Geographical,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Description of Hindostan, and the Adjacent Countries, Vol.2, London: John Murray, 1820, p.14.但F. 汉密尔顿(F. Hamilton)在同年发表的《阿萨姆记》中通过对长期居住在阿萨姆地区的或是逃难到孟加拉的阿萨姆人进行访谈等,仍认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为鲁希特河,从北向南流,并在布拉马昆德(Brahmakunda)流出山区,到达阿萨姆平原。(27)F. Hamilton. An account of Asam, with some notices concerning the neighbouring territories, Annals of Oriental Literature, 1820, Vol.1, pp.259-260.
总之,19世纪2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关于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地理认知主要源于唐维尔转绘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及其在西方世界的流传。18世纪后期,英国地理学家通过对布拉马普特拉河测量与研究,正式提出雅鲁藏布江下游流入布拉马普特拉河的观点,并得到了西方地理学界普遍认可,使西方国家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认识更进一步。(28)J. F. Michell,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 (A Topographic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port), Calcutta: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883, p.iii.
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及认知演变
地图测绘是帝国主义对新领土进行军事征服和行政管理的重要前提。(29)R. Dean, Mapping the Great Game: Explorers, Spies &Maps in Nineteenth-century Asia, p.72.1824—1826年,英国与缅甸发生了第一次缅甸战争,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英国还派遣调查队对阿萨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详细测量。西藏东南地区紧邻阿萨姆,且作为阿萨姆主要河流的发源或流经地,自然也成为这次测量活动的重点关注对象。英国这一时期的测量活动获得了阿萨姆和西藏东南地区南缘丰富的地理知识,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英国在这一地区“不完全的知识”(30)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1832, Vol.17.,也为英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31)R. H. Phillimor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3, 1815-1830, pp.52-53.。
(一) 非法测绘活动
1824年,印度税务调查局派遣贝德福德(Captain Bedford)和威尔科特斯(R. Wilcox)组成针对阿萨姆及周边地区的调查队,“利用每一次可行的探险进入阿萨姆”(32)R. H. Phillimor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3, 1815-1830, pp.52-53.。调查队的任务主要有两项: 一是寻找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二是配合英国的军事行动,对新占领的阿萨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全面调查。调查队所携带的测量设备包括: 六分仪、指南针、伍拉斯通测温气压表(Woollaston’s thermometric barometer)和普通气压表等(33)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1832, Vol.17.。
1. 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
1826年,贝德福德到达巴昔卡(Pasial/Pasighat)(34)巴昔卡位于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中方一侧。Map of the countries shewing the sources of the Irawadi river and eastern branches of the Brahmaputra, 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1832, Vol.17.,当地珞巴人(英国称其为“阿波尔人”)拒绝其继续前进,贝德福德在巴昔卡停留两天后只能返回(35)J. F. Michell,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 (A Topographic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port), p.53.。此后,威尔科特斯应门布村(Membu,位于巴昔卡东北部8英里左右)的邀请溯底杭河(36)底杭河,Dihong/Dihang,英国对雅鲁藏布江下游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河段的称谓。而上,对底杭河下游进行了测量,但当地人同样拒绝威尔科特斯继续向山地前进(37)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1832, Vol.17; J. F. Michell,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 (A Topographic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port), pp.54-55.。总之,此次测量活动最远只到达巴昔卡附近,未能深入山区。
2. 察隅河流域
阿萨姆本地人和印度教传说都认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位于萨地亚(Sadiya)往东三四日程的布拉马昆德。(38)B. C. Allen, Assam District Gazetteers, Vol.8, Lakhimpur, Calcutta: City Press, 1905, p.5.1825年,布尔顿(Lieutenant Burlton)受命测量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但其到达27°49′N,95°52′E附近便无法继续前行。(39)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1832, Vol.17.
威尔科特斯沿察隅河—鲁希特河进行了三次测量活动。在第一次测量活动中,威尔科特斯发现了昆德(Kund,即“布拉马昆德”)所在地。他认为昆德只是鲁希特河从山地流到平原的位置,并非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在第二次测量活动中,威尔科特斯从昆德出发,经过两日路程到达迪加罗米什米人(Digaro/Tain Mishmis)(40)米什米人,Mishmi,英国对中国僜人等山地部族的称谓。所在地区,并得到两位部落首领的帮助。通过对米什米头人的访谈,威尔科特斯了解了鲁希特河上游察隅河的大体走向,此次测量活动最远到达特同村(Thethong)。(41)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1832, Vol.17.在第三次测量活动中,威尔科特斯成功劝说迪加罗米什米人让其通过村庄到米久(Mezho/Miju)米什米人所在区域,并最远到达察隅河由南流折向西流转弯处的金沙村(Jingsha)。(42)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1832, Vol.17; A. Mackenzi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Hill Tribe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Bengal, Calcutta: Home Department Press, 1884, pp.47-48.
3. 丹巴河流域
贝德福德沿丹巴河而上,最远到达丹巴河与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交汇处的尼杂木哈特(Nizamghat)。(43)尼杂木哈特的位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1960年所绘的《中国西南边疆图》。贝德福德发现5个米什米人聚落,共有80户、500人左右。(44)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1832, Vol.17.
4. 西巴霞曲流域
威尔科特斯访问了西巴霞曲流域的米里人(Miri,中国珞巴人的一支)地区。当地人告诉威尔科特斯,西巴霞曲的源头叫坎拉河(Kamla),有三个分支,主要源头发源于北部或东北部的雪山。威尔科特斯认为西巴霞曲就是唐维尔和瑞纳尔地图中标绘的乌姆曲。但由于当地人的反对,威尔科特斯未能深入山区。(45)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1832, Vol.17.
贝德福德和威尔科特斯等人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南缘的活动是英国第一次有计划、在军队保护下进行的非法测绘活动,测绘范围西起西巴霞曲流域,东到察隅河流域,此次测绘活动及绘制的地图,大大提高了英国对这一地区的地理认知水平。
(二) 地理认知演变
威尔科特斯等人完成对阿萨姆及周边地区的测量后,于1828年绘制了一幅比例尺为1英寸比4英里的阿萨姆地区地图。(46)《印度测量局历史记录》第3卷给出了1828年地图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部分“1828年上布拉马普特拉河地图”。R. H. Phillimor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3, 1815-1830.1832年,在威尔科特斯公开发表的调查报告中,附录了一幅在1828年地图基础上改绘的地图——“伊洛瓦底江源头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东部支流地区图”(以下简称“威氏地图”)(47)Map of the countries shewing the sources of the Irawadi river and the eastern branches of the Brahmaputra, 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Vol.17, 1832.,本文即以1832年修改之后的地图为对象,研究这一时期英国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地理认知演变。
威氏地图的地理范围包括21°N—32°N,90°E—100°E,除阿萨姆地区外,还包括了中国西藏东南地区南缘。威氏地图的图说中详细阐述了地图的绘制过程及数据来源:“阿萨姆地图是一幅最近在测量局长办公室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的缩略图,这幅地图来自威尔科特斯自己的调查和贝德福德(Bedford)、约翰斯(Jones)和拜丁福尔德(Beddingfeld)的调查活动。”此外,还有费舍(Fisher)、伍德(Wood)、布坎南(Buchannan)等人进行实地调查、测量与访谈等的贡献。所以,威氏地图是19世纪30年代前英国对这一地区地理认知的一次总结,具有一定代表性,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这一地区地图绘制的基础。(48)R. H. Phillimor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5, 1844-1861, p.311.与前述唐维尔、瑞纳尔等人的地图相比,威氏地图的主要贡献是理清了雅鲁藏布江及各主要支流的下游流向和主次关系,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威氏地图将该河段标注为“底杭河”,流入阿萨姆平原后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Lohit or Brahmaputra)。威尔科特斯认为雅鲁藏布江不可能从伊洛瓦底江出海,延续了瑞纳尔关于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是一条河流的观点。(49)R. Wilcox, Memoir of a survey of Asam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executed in 1825-6-7-8, Asiatic Researches, 1832, Vol.17.
第二,在察隅河—鲁希特河流域,这一时期的测量活动证实了察隅河下游为鲁希特河,改变了以往所认为的察隅河下游为伊洛瓦底江,以及鲁希特河的源头为布拉马昆德的观点。(50)W. Hamilton, The East-India Gazetteer (2nd ed.), Vol.1, London: WM. H. Allen and Co., 1828, p.67.威尔科特斯虽然最远只到达察隅河由南流折向西流处,但通过对当地人的访谈,他在地图中将察隅河河道绘制到28.5°N以北,对察隅河沿岸一些重要地点的位置和名称等也有标注,如瓦弄(Oalong)、日马(Riuma)等。
第三,底杭河与察隅河之间的地区增加了丹巴河这一重要支流。但因他未对丹巴河中上游进行测量,故中上游标注“推测的河道”。
第四,底杭河以西绘制出西巴霞曲的走向,改变了以往地图中乌姆曲的称谓,标注为“苏班西里河”(Suban Shiri)。西巴霞曲的主要支流克鲁河和坎拉河走向也被相对准确地绘制出来。
1828年W. 汉密尔顿(W. Hamilton)所著的《东印度地名志》一书中,仍坚持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为察隅河—鲁希特河,认为其源头可能与怒江(Loukiang)和伊洛瓦底江(Irawady)的源头相似。汉密尔顿认为一些地理学家所主张的底杭河或西部的河流(指西巴霞曲)与雅鲁藏布江是一条河流的观点是不可信的,因为底杭河的尺寸太小,河道狭窄,且可通航的河道有限。(51)W. Hamilton, The East-India Gazetteer (2nd ed.), Vol.1, pp.67-68, 286, 511.1841年,罗宾逊(W. Robinson)虽然认同底杭河为雅鲁藏布江的下游,但他同时也怀疑,底杭河的河道才100码宽,与雅鲁藏布江这一大江下游应有的尺寸不相符。(52)W. Robinson, A Descriptive Account of Asam, Calcutta: Ostell and Lepage, British Library, 1841.
1858年出版的《东印度公司治下领土地名志》一书中仍将察隅河—鲁希特河看作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起源于喜马拉雅山约28°30′N,97°20′E,向西流后汇入丹巴河和底杭河等,但同时,该书也认为底杭河即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是布拉马普特拉河最远的源头。(53)E. Thornton, A Gazetteer of the Territories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of the Native States on the Continent of India, Delhi: Low Price Publications, 1858, pp.143-144.
总之,在19世纪前期,英国通过对阿萨姆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测量,基本确定了西藏东南地区南缘主要河流的河道流向和主次关系。雅鲁藏布江与底杭河或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关系问题虽然得到主流地理学家的认同,但仍存在一定争议。
三、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
非法测绘及认知演变
19世纪,英、俄两国在亚洲内陆进行了激烈的“大博弈”。俄国为了侵略中国西藏,在19世纪中后期先后派遣了13支考察队,以“科学考察”为名,大肆搜集西藏情报。(54)详见邓锐龄、冯智主编: 《西藏通史·清代卷》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0—478页。随着俄国的扩张,英国更加迫切地想了解中国西藏的地理环境,以对抗来自俄国的压力,“对这些地区进行探险及制图是十分重要的”(55)[美] 约翰·麦格雷格著,向红笳译: 《西藏探险》,第242页。,“这些地区”指中国的西藏和新疆。
1876年,英国借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另议专条规定英国可“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56)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50页。。按照列强“机会均等”的原则,俄、美、法等国也同样具有这一权利,形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在西藏游历和探险的高潮。(57)周伟洲: 《19世纪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在我国藏区的活动》,《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190页。
从英印东北边疆地区的局势来看,19世纪中后期,阿萨姆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周边山地部族的“侵扰”,矛盾不断激化,印度迫切希望突破“内线”的束缚,向北部山区扩张。(58)J. F. Michell,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 Calcutta: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883, pp.iv, 4.加之此时印度测量局已经完成了对印度次大陆的测量工作,开始将测量目标转向西藏高原(59)Matthew H. Edney,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成为这一时期英国进行地理测绘和情报搜集的重点地区。
(一) 班智达的非法测绘活动
19世纪中后期,为了获得更多西藏情报,同时避免英国人在西藏调查时受到阻挠或可能有生命危险,印度大三角测量局(the Great Trigonometrical Survey of India)的蒙哥马利(T. G. Montgomerie)在印度北部的台拉登(Dehra Dun)对印度本地人进行测量训练,并利用这些人与西藏人具有相似的外貌和宗教信仰,让其以到西藏朝圣等名义对西藏进行非法和秘密测量,这些人被称为“班智达”(Pundit)。这些班智达在19世纪中后期对中亚、西藏等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与测量,获取了大量情报。(60)D.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and Central Asia.
班智达在西藏进行秘密测量时,一般会携带以下工具: 九英寸的六分仪,用来进行纬度观察;西藏茶碗,用来装置水银槽;棱镜罗盘,用来测量远处山峰的方位;小型罗盘,用来测量一般道路的方位;念珠,用来计步;转经筒,用来藏匿野外工作记录;无液气压计和沸点温度计,用来测量海拔。(61)J. T. Walker, Four year’s journeyings through Great Tibet, by one of the Trans-Himalayan explorer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5, Vol.7, No.2.
1. 南姆·辛格在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活动
南姆·辛格(Nem Singh,代号G. M. N)是一位锡金僧人,受过很好的教育,略懂一些英语,在大吉岭的公共事务部(Public Works Department)做苦力监工,时不时为大吉岭法庭做翻译。1878年8月,在经过专业的培训后,南姆在金塔普的陪同下从大吉岭出发到西藏执行秘密任务,其目的是测量泽当以下的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
南姆先到拉萨,从拉萨南行到达泽当,顺雅鲁藏布江东行,最远到达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后的甲拉西登(Gyala Sindong,位于今墨脱县加热萨乡(62)中国地图出版社编: 《西藏·墨脱县》,中国地图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附近,并被当地人告知雅鲁藏布江最后会“流入一个被英国统治的地区”(63)H. J. Harman, Report on the exploration of Nem Singh in Eastern Tibet, 1878-79, S. G. Burrard,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8, Part 1, 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 1865-1879, Dehra Dun: The Office of the Trigonometrical Survey, 1915, pp.211-212.。
南姆在对雅鲁藏布江流域进行秘密测量后,印度大三角测量局对其测量过程进行了记录,并依据其测量结果绘制了《西藏雅鲁藏布江南部低地地区推测图》。(64)Conjectural sketch of the country to the south of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Great Tsan-Po River of Tibet, S. G. Burrard,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8, Part 1, 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 1865-1879.从该图中可以看出,雅鲁藏布江河道自泽当始,至甲拉西登,包括大拐弯处,都已被南姆测量完毕并绘制成图。
印度测量局认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雅鲁藏布江不可能流向西巴霞曲,而只能流向底杭河。(65)D.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and Central Asia, p.212.然而由于南姆并未能沿雅鲁藏布江而下,以证明雅鲁藏布江的下游就是底杭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故雅鲁藏布江下游之谜仍未能完全解开。(66)R. Gordon, Report on the Irrawaddy River, D. Waller, The Pundits: 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and Central Asia, p.225.
2. 金塔普在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活动
金塔普(Kintup,代号K.P.)是一名锡金裁缝,曾于1878—1879年随南姆到达甲拉西登测量。由于金塔普不识字,不能进行文字记录,所以印度大三角测量局的哈曼(67)哈曼(Captain Henry John Harman),1872年起负责大三角测量局工作,1877—1978年负责米里山区(Miri hill)的测量,1878年负责印度测量局大吉岭分部。曾测量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流量,以证明其是雅鲁藏布江的下游。决定派一名中国喇嘛和金塔普一起进行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测量工作。这次测量工作的计划是从甲拉西登继续沿雅鲁藏布江南下,最后到达阿萨姆。如果这一计划行不通,哈曼还设计了一个灵活的办法: 让金塔普准备大量做了记号的圆木,顺江放下,并通知哈曼在底杭河注入阿萨姆的出口处拦截,如果发现一根圆木,则证明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是布拉马普特拉河。(68)H. R. Thuillier, General Report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Department Administer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uring 1886-87, Calcutta: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888, p.lxxxix.
1880年金塔普和喇嘛离开大吉岭,经江孜到达拉萨,8月底到达泽当,1881年3月到达甲拉西登,后因未能找到可以去南方的路,只能返回。在东久宗(Tongjuk Dzong),喇嘛将金塔普偷偷卖给了宗本作奴隶,直到1882年3月金塔普才成功逃脱。而后金塔普决定实施哈曼的第二方案。金塔普制作了500根圆木,在白马岗的背崩(Bipung)每天放50根圆木到雅鲁藏布江里。但因哈曼已经离开了印度,导致这一计划也未能成功。(69)关于金塔普的测量过程可参见[英] F. M. 贝利著,春雨译: 《无护照西藏之行》,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版,第4—7页。
在放了圆木后,金塔普再次尝试顺雅鲁藏布江南下,最远到达甲拉西登以南100英里左右的岸来特(Onlonw/Onlet)。在岸来特,因珞巴人不允许来自北方的人通过他们的领地,金塔普被迫按原路返回。1884年11月,金塔普回到大吉岭。因金塔普没有受过专业的测量训练,他回到印度两年后才由印度测量局的人将他的测量结果记录下来。(70)H. C. B. Tanner, Kintup’s Narrative of a journey from Darjeeling to Gyala Sindong (Gyala and Sendam), Tsari and the Lower Tsang-po, 1880-1884, S. G. Burrard,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8, Part 2, 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 1879-1892, pp.329-338.
根据金塔普的测量结果,1887年大三角测量局绘制了《坦纳上校关于雅鲁藏布江河道报告地图: 来自1886—87年K.P所提供信息》(71)Sketch map to illustrate colonel Tanner’s memorandum on the course of the Sangpo from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K. P in 1886-87, H. R. Thuillier, General Report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Department Administer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uring 1886-87.,在《印度测量局档案》中也附有一幅印度测量局绘制的《根据金塔普在1880—84年搜集到的情报所绘雅鲁藏布江河道图》(72)Sketch map illustrating the course of the Tsang-po from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Kinthup in 1880-84, S. G. Burrard,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8, Part 2, 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 1879-1892.,两幅地图关于雅鲁藏布江河道走向的信息基本相同。金塔普不识字,没有笔记记录,所以他的测量结果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这两幅地图中,虽然甲拉西登以下的雅鲁藏布江两岸标注了大量村落地名,但河道仍然用虚线表示。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对这一地区再次进行非法测量时,才证实金塔普对地名、距离的描述基本都是正确的。(73)H. R. Thuillier, General Report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Department Administer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uring 1886-87, p.lxxxix; J. A. Field, The history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pper Dihong,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13, Vol.41, No.3.
3. 克桑在察隅河流域的活动
克桑·辛格(Kishen Singh,代号A—K)来自库玛翁地区。1878—1882年,克桑到西藏的秘密测量活动的主要任务是从南向北纵穿西藏,跨越昆仑山,进入蒙古并进行测量,回来时则要选择与原路平行的其他道路,以测量更多区域。印度测量局局长沃克(J. T. Walker)特别指示克桑要避免到中国内地,因为这些地方的地理情况已经测量过。(74)③ J. T. Walker, Four year’s journeyings through Great Tibet, by one of the Trans-Himalayan explorer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5, Vol.7, No.2.
克桑于1878年4月从大吉岭出发,9月到达拉萨,在拉萨停留了一年时间。1879年9月,克桑加入一支由100人组成的商队前往蒙古,穿过羌塘高原,到达青海,最远到达甘肃敦煌附近。在返回途中,克桑取道康区,经德格,于1882年2月到达打箭炉,接受了传教士比特(Bishop Biet)的建议,经里塘、巴塘,到达察隅河流域。在察隅地区,克桑测量了察隅河的东部支流桑曲,南部最远到达沙马村(Sama)。在沙马村,克桑被告知如果他沿察隅河到阿萨姆,会被米什米人杀掉。③1882年7月9日,克桑沿察隅河的西部支流贡日嘎布曲(Rong Thod Chu)而上,穿过冰川和阿扎公拉(Ata Gang La),到达今八宿县,对所经地区进行了详细测量。因天花流行,沿帕隆藏布到工布再到拉萨的道路被封闭,克桑只能沿冷曲而北,至洛隆宗,从洛隆宗经工布,于10月8日到达泽当,经过江孜,在1882年11月12日回到大吉岭。
克桑的整个测量活动持续了4年半的时间,总行程达到2 800英里,其中有1 700英里是以前未进行过科学测量的。1884年,印度测量局大三角分部根据克桑的测量结果,绘制了《1879—1882年间A—K在西藏和蒙古的探险修正图》(75)Revised sketch map illustrating the explorations of Kishen Singh in Great Tibet and Mongolia in 1879-1882, S. G. Burrard, 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Vol.8, Part 2, Exploration in Tibet and Neighbouring Regions, 1879-1892.,包括三幅分图,详细描绘了克桑的行程路线及其测量结果。克桑第一次对察隅河的两条主要支流,即桑曲中下游和贡日嘎布曲进行了测量,绘制出了相对准确的河道走向,最南端测量到沙马村。此外,克桑的测量路线还进一步证明了雅鲁藏布江不可能越过察隅河而流向伊洛瓦底江。它只能向南流,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同一条河(76)J. T. Walker, The hydrography of south-east Tibet,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8, Vol.10, No.9.。
(二) 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尼达姆的非法测绘活动
1882年,英国设置了萨地亚助理政务官(Assistant Political Officer at Sadiya)一职,以发展与喜马拉雅山南麓山地部族的关系,确保印度东北边疆的稳定。1882—1905年,尼达姆(J. F. Needham)担任第一任助理政务官,其间取得了被印度政府颇为赞赏的“成绩”,如《1928年萨地亚边疆区地名志》就如此评价:“尼达姆先生通过他的远征与发现,获得了一种国际声誉,他在1882—1905年间的工作为当代阿萨姆东北边疆的局势奠定了基础。”(77)R. Reid, 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on Assam from 1883-1941, Delhi: Eastern Publishing House, 1942, p.181.尼达姆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活动主要集中在察隅河流域。
1885年12月—1886年1月,尼达姆对察隅地区进行了非法调查,此次调查的目的是: 探查察隅河—鲁希特河的源头、发展与米什米人和西藏人的关系。1885年12月12日,尼达姆在没有军队保护的情况下,带着三个边境警察从萨地亚出发,溯察隅河而上,在距离日马(Rima)一英里的地方被西藏官员阻拦,被迫返回。(78)G. L. S. Ward, Military Report on the Mishmi Country, Simla: The Government Central Printing Office, 1901, p.11.
尼达姆测量了察隅河—鲁希特河从萨地亚到日马的部分河段(79)Mr. J. F. Needham’s journey along the Lohit Brahmaputra, between Sadiya in Upper Assam and Rima in South-Eastern Tibet,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Supplementary Papers, 1889, Vol.2; R. Reid, 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on Assam from 1883-1941, p.185.,在“鲁希特—布拉马普特拉河草图”中(80)Sketch map of the Lohit Brahmaputra, Mr. J. F. Needham’s journey along the Lohit Brahmaputra, between Sadiya in Upper Assam and Rima in South-Eastern Tibet,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Supplementary Papers, 1889, Vol.2.,这一河段被准确绘出。尼达姆的地图中还首次标绘出西藏人和米什米人的分界,为英国利用部族分界线作为中印边界提供了所谓依据。(81)[英] 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 《中印涉藏关系史: 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 1904—1914》,第426页。
尼达姆的测量与班智达克桑的测量对接,证明了克桑地图中关于察隅河流向的正确性,完成了对于察隅河下游的完整测量。(82)Mr. J. F. Needham’s journey to the Zayul Chu,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6, Vol.4.尼达姆在报告中说:“我非常自豪且满意地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地理问题。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支流,从萨地亚一直到距日马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我非常自信地确定,在这之间不存在与雅鲁藏布江相似的河流,所以雅鲁藏布江一定在萨地亚以西注入布拉马普特拉河,据我看来只有底杭河。”(83)R. Reid, 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on Assam from 1883-1941, p.185.
除察隅河外,尼达姆也对丹巴河的部分支流进行了测量。丹巴河的东部支流因通河(Ithun)流域分布着贝贝吉亚米什米人(Bebejiyas)。1899年,贝贝吉亚米什米人劫掠了萨地亚东北方向16英里处的一座村庄,其中3人被杀、3人被掳走。1899年12月,英国对贝贝吉亚米什米人进行了军事远征,尼达姆任政务官。远征军到达丹巴河的尼杂木哈特,烧毁了因通河沿岸的部分村庄。在远征军到达的地方,尼达姆测量了808平方英里的地区。(84)G. L. S. Ward, Military Report on the Mishmi Country, pp.13, 15-16.
(三) 地理认知演变
1878年,印度测量局派哈曼对底杭河、鲁希特河、丹巴河和西巴霞曲的径流量进行了测量,“以明确每条河流的径流量大小,另外,也可以为这一有趣且重要的地理问题(即雅鲁藏布江的下游流向)提供证据”(85)J. T. Walker, General Report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1877-78, Calcutta: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879, pp.16-17.。据测量结果,底杭河的径流量远远大于其他三条河流,这也增加了底杭河为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可信度。1881年,在印度统计局长的亨特(W. W. Hunter)主编的《印度帝国地名志》中,认为虽然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还未被实地探查证明为同一条河,但一般都已认可两条河为上下游关系。(86)W. W. Hunter,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Vol.3, London: Trubner &Co., 1885, pp.93-95.
1887年和1888年,沃克(1878—1883年任印度测量局长)发表了两篇文章: 《西藏的怒江(潞江)是伊洛瓦底江或萨尔温江的源头吗》(87)J. T. Walker, The Lu River of Tibet: Is it the source of the Irawadi or the Salwi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7, Vol.9, No.6.和《西藏东南部的水文学》(88)J. T. Walker, The hydrography of south-east Tibet,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8, Vol.10, No.9.,结合英国测量员、间谍班智达、边疆地方官员等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测量结果,系统论述和概括了此时英国对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认识。沃克的两篇文章都附有地图,《西藏东南部与周边地区地图》和《西藏东南部水系图》,因1888年沃克对这一地区的河流水系较1887年的文章有了新的认识,故两者有冲突处以1888年的论述为准。
1. 雅鲁藏布江与底杭河的关系
受唐维尔地图的影响,许多西方地理学家仍然坚持雅鲁藏布江下游是伊洛瓦底江,如在1885年,戈登(R. Gordon)主要依据三个理由坚持这一观点。一是伊洛瓦底江为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且径流量大;二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与唐维尔的地图;三是来自阿萨姆人的证据,即当地人认为没有河流连接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89)R. Gordon, The Irawadi River,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5, Vol.7, No.5.
而沃克在文章中着重介绍了金塔普对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测量活动,认为虽然金塔普当时缺少测量设备,也不能进行文字记录,但在这一地区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使得他对地点之间的距离与方位记忆深刻,能令印度大三角测量局绘制出相对可靠的地图。沃克认为,在班智达对察隅河、雅鲁藏布江进行大规模的测量后,可以确定雅鲁藏布江的下游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2. 鲁希特河的源头问题
沃克认为,班智达对察隅河及其北部地区的测量进一步证明了雅鲁藏布江不可能流入伊洛瓦底江。戈登则认为沙马和布拉马昆德之间的地区尚未被实地测量,雅鲁藏布江有可能流经这一地区,并最终汇入察隅河,流入伊洛瓦底江。1885—1886年尼达姆的测量结果证实了察隅河为鲁希特河的源头,解决了戈登提出的问题(90)J. T. Walker, The Lu River of Tibet: Is it the source of the Irawadi or the Salwi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7, Vol.9, No.6.,也证明了在怒江以西的西藏地区没有河流可能成为伊洛瓦底江的源头(91)实际上,伊洛瓦底江发源于察隅县伯舒拉岭南部,注入云南贡山县,再向西流入缅甸的克钦邦,成为伊洛瓦底江的东部源头恩梅开江。。沃克认为班智达A—K调查所得的贡日嘎布曲和桑曲分别是察隅河的西部和东部源头,而察隅河又是鲁希特河的源头,基本上廓清了察隅河的主要源头和中下游河道的走向。
3. 丹巴河的源头问题
沃克将英国对丹巴河下游的测量与唐维尔的地图相结合,认为丹巴河上游是唐氏地图中的更布河。进而他根据山地部族的描述,认为在察隅河的源头附近有一条称为“Kala-pani”(意为“黑水”)的河流,向西汇入底杭河。恰帕隆藏布(Nagong Chu)发源于同一地区,有同样的流向,其含义也为“黑水”,故沃克将帕隆藏布视为丹巴河的东部支流,两条河流在汇合后流入布拉马普特拉河。
尼达姆在读了沃克的研究后,并不认同沃克关于丹巴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部的看法。他提出,居住在丹巴河沿岸的米什米人多次说他们在去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西藏聚落时,会路过丹巴河的源头,证明丹巴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坡,并不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部。(92)J. F. Needham, The hydrography of south-estern Tibet: the Dibong River,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889, Vol.11, No.7.
4. 西巴霞曲
沃克地图中绘制出了西巴霞曲的两条主要支流,即坎拉河(Kamla)和克鲁河(Khru),因未对西巴霞曲的源头进行测量,故错将坎拉河作为西巴霞曲的源头,发源于泽当南部的泽古错(Tigu tso)。
1900年,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绘制的“西藏及其周边区域地图: 基于最新信息”(93)Tibet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compiled from the latest information, 1900.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修正版,借鉴了沃克地图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绘制方法,将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绘制为一条河流,但仍将雅鲁藏布江下游,即甲拉西登以下至格邦(Kebang)用双虚曲线表示。此次关于丹巴河的绘制方法,修正了沃克所认为的丹巴河源头为更布河的看法,仅保留帕隆藏布作为丹巴河的源头;关于察隅河,完整绘制出了察隅河中下游河道的走向,并将察隅河的两条上游支流桑曲和贡日嘎布曲的具体走向绘制出来,因桑曲的上游还未被实地测量,故用虚线绘制;关于西巴霞曲,仍沿用沃克的绘制方式,将坎拉河作为西巴霞曲的源头,发源于泽古错,上游用虚线表示。
总之,到19世纪末,英国通过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活动,基本构建了对这一地区河流水系的地理知识体系,但关于雅鲁藏布江与底杭河的关系、丹巴河和西巴霞曲的源头等问题,直到1911—1913年间英国对这片区域进行大规模非法军事行动时才最终通过实地测量得到解决。(94)参见[英] 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 《中印涉藏关系史: 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 1904—1914》,第262—270页。
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所进行的地理测绘活动本身即具有侵略性质,是其建构殖民主义权力话语、重塑被殖民地区的政治与地理界线的重要手段。(95)D. V. Zou, M. S. Kumar, Mapping a colonial borderland: objectifying the geo-body of India’s Northeas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1, Vol.70, No.1.20世纪初期,英印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企图将西藏变为保护英印东北边疆的“缓冲国”,以削减俄国南向扩张的影响。加之,中国也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控,英国认为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外线”“从战略上来说是不牢靠的”,将“外线”向中国一侧推移,将英国的影响扩大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最终炮制“一条自然的与更加安全的边界”是当务之急。(96)Government of India to the Marquess of Crewe, Simla, 1911-09-21, IOR, L/P&S/20/FO/87-3.
1910年10月,印度总督明托(Minto)认为:“中国人在日马的活动和我们与东北边疆地区相邻部族区域的未来关系问题导致了区域性的焦虑。对于中国人的前进,军事当局认为现在的观点是不健全的策略。”故而提出所谓的“新外线”(new external boundary),“我们倾向于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将外线扩展到可能必要的地方,以保证在外线以内或以外没有除我们之外的其他国家力量与部族之间发生关系或交流,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确保一个缓冲区”(97)Government of India to Viscount Morley, 1910-10-23, IOR, L/P&S/20/FO/87-2.。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结果则为“新外线”的走向提供了重要情报。
1906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再次出版了《西藏及其周边区域地图》修正版。1913年10月23日,正在召开西姆拉会议的麦克马洪在《备忘录》中明确写道,将1906年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绘制的《西藏及其周边区域地图》用在西姆拉会议,并将复本交与了中国与西藏地方代表(98)A. H. McMahon, Memorandum, 1913-10-23, IOR, L/P&S/10/342.,并以此为基础标注出多条边界线,最终形成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走向(99)[英] 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 《中印涉藏关系史: 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 1904—1914》,第408—409页。。
结 论
近代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图测绘活动,是其殖民扩张的先导。客观上,帝国主义的这一行为也促进了西方人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填补了世界地图中的空白。19世纪,英国派遣测量队、间谍、边疆官员、探险家等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测绘活动,其中,河流水系是其测绘的重要内容之一,为英国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单方面划分中印边界线等提供了情报基础。
英国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非法测绘与认知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地理认知主要来自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改绘及其在西方的传播,对雅鲁藏布江、察隅河、西巴霞曲等河流的基本走向有了相对准确的绘制。18世纪中后期英国地理学家瑞纳尔在对布拉马普特拉河进行测量与研究后,提出雅鲁藏布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是一条河流的观点。第二阶段为19世纪前期,英国派遣测量队在阿萨姆及西藏东南地区南缘的测量活动,基本确定了雅鲁藏布江、察隅河、丹巴河和西巴霞曲的主次关系及下游河道的流向问题,奠定了此后相关地图中关于这一地区河流水系绘制的基础。第三阶段为19世纪后期,通过间谍班智达、英印边疆官员的测量活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察隅河的上游至下游、丹巴河的中下游、西巴霞曲的中下游地区均被较为准确地绘制在地图上,这一地区的河流水系知识不断得到完善。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丰富知识也为1910年“新外线”和1914年“麦克马洪线”的炮制提供了情报基础,成为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