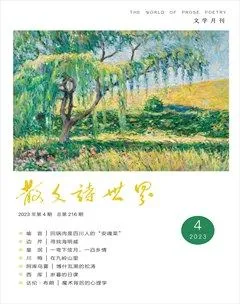陌生的因缘
朱灿
阅读卡夫卡,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客体,是海德格尔笔下那个熟练木匠手上“上手”的锤子,而非那个木匠。木匠能沟通、能共情、能思维、能做一些自认为能做的认识世界的事,而作为“客体”的存在,好像不能,“客体”好像只需要“存在”,其他的,都不用管也不必管。作为“人”的卡夫卡是确乎“存在”过的,而作为“锤子”,似乎至今都缺乏一个熟练的能“上手”的木匠,这样的木匠,可能以后也不会有吧。
一千个读者能找到一千种进入卡夫卡世界的方法,能有一千零一个卡夫卡,这除了证明“卡夫卡”本身的丰富性以外,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这一千个读者,可能是围绕着卡夫卡打转,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卡夫卡世界”,或者卡夫卡所折射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和读者“自我”,而非真正进入卡夫卡的世界呢?
于是,在千千万万的进入方式中,明明消失的距离,又无端端从不知道的地方出现在“我们”和“卡夫卡”之间,如杂花生树,乱欲迷眼。这切实存在的“距离”的意义,似乎也就变了,它不再是为了“消失”而“存在”,而是为了“提醒”而存在,“提醒”我们“卡夫卡”的存在,作为一个“客体”的卡夫卡的存在。但这儿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何要“提醒”我们,“提醒”之于我们的意义为何?
解决这个问题,得先转回到那个“锤子”上,如果很难成为一个熟练的木匠,便只好怀着好奇与无知的心绪,去看看,一把“客体”的“锤子”是如何成为“锤子”的,它的把手出身的那棵树,长在怎样的地方,是酸性的土壤还是碱性的土壤,抑或纯粹的山石夹缝中,它又经历了多少东南西北风,又是如何被斧钺砍伐,它的锤头又是从哪座山上选择的什么矿石以我们不知道的形式被挖掘运送再煅火炼就而成?等等。等到这些疑惑都彻底解答了,“提醒”的意义也就显明出来了。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把“客体”的“锤子”便会出现在活生生的“后死者”的生命里,成为一把不为了砸开任何冰山的锤子,它仅仅就是它自己——将自己显明出来。一个生命中有着另一个“客体”显明出来,此一生命也就有一可靠的锚点,一切实的参照,幸甚至哉。
施塔赫的《卡夫卡传:关键岁月》,呈现了这柄“锤子”关键的成型时期。看似事无巨细纷繁复杂的文本,不难发现的是,卡夫卡在这样的“关键岁月”里,与之相应的关键对象,是家人、恋人、朋友、文学。施塔赫的《关键岁月》把这几者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个清楚的结果就是,前三者,都让位于第四者。如果再把这几者用人这一物种惯常的概念性、抽象性的表达方式来阐述,则是——亲情、爱情、友情和文学成为了卡夫卡“关键岁月”里的关键对象。而最终,在友情的助推下,亲情、爱情让渡给了看似与普通个体毫无关系的“文学”这一对象上。作为看重血缘和家族传承的人这一物种来说,友情在个体的整个家庭生存结构中,似又要稍低于亲情、爱情,友情因其为友情,其所蕴含的疆域之宽又非他者所能比拟,它是个体在生命、家庭、社会关系中的缓冲带,极具宽容性的背后其实也极具陌生性。进而言之,在卡夫卡这一生中,爱情、亲情这些可作为普通人一生的重要元素,都在另一个兼具宽容性和陌生性的力量的帮助下,让渡给了“文学”。此后,如卡夫卡所言,“我即文学”。而“文学”之于个体,因其看似抽象而遥远,分明更为陌生。在剥离掉那些共性的关系后,一个不可回避的情况出现了——陌生,成就了卡夫卡。而卡夫卡,亦成全了陌生。卡夫卡进入窄门,走向了陌生深处。卡夫卡,即陌生。
文学之子,总以文学为是。但这也不过是只存在了41年的卡夫卡博士一生最浅层的生命邏辑。卡夫卡究竟为何会投向文学而非他一直工作且成果斐然的保险工作呢?那样,世上会多一个更优秀的公务员,而少一个更优秀的作家,当然,这样的“多”与“少”也仅仅是面对后人,而非卡夫卡本人。那么,于他本人而言,为何投向了文学?为何一再地诉说家人带给他的陌生感、恋人的无可理解的回应?或者说,是怎样的条件,促成了卡夫卡与文学产生关系,而非与其他产生关系呢?
在《关键岁月》所呈现的整个的卡夫卡的生命里,家人和恋人所带给他的感受,那一封封寄出和未曾寄出的“不知疲倦”的书信,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渴望理解,渴望关注的人。其实,更应该看到,那都是我们,那就是我们,是我们这个物种穷其一生所渴望的东西——理解与关注是陌生的对立面,是非陌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显然,这些渴望,都没有达成。倾覆的巴别塔预示着绝天地通,也自然预示着绝人人通——天地自然终归大过个体,如李零言,大道理管小道理。当这些不可达成的东西已如万古冰山横亘在生命的北极时,卡夫卡彻底地走向了“陌生”——既然不可理解,便让“陌生”恒久“陌生”。而这“陌生”在卡夫卡的生命里,则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了。陌生,是文学该有且必有的品质。因走向了这恒久的“陌生”,卡夫卡把人类在世上的共性性质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极致,把我们所认可的人生中必须的关系,推向了一个彻底的“无”的状态。卡夫卡成为了一个从“有”活到“无”的人的范例,甚或,是唯一一人。
非常卡夫卡式的阅读印象是,我们又分明在他笔下看到了那些注定的事,那些技术对人的侵蚀,那些社会结构对个体生活与生命的解构,等等,正一件件生发在现代人的生命里。一个分明陌生的人,写出了一件件我们异常熟悉且日复一日重复的事,一个彻底的“无”完整地呈现了一个无尽的“有”的荒谬。以“有”而对“无”,我们面对卡夫卡的每一次阅读每一次靠近,何尝不是第一次抓冰块的奥雷里亚诺上校的感觉——它在烧——而那分明就是痛。
这巨大的陌生感和无边的“无”,是伴随卡夫卡那不可言喻的孤独感而来的,是不是走向孤独深处,就是走向生命深处?孤独和生命有什么本质的关系呢?我们的群体性和向心性,我们对孤独和陌生的似无缘由的恐惧和排斥,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这些,似乎都在卡夫卡身上得以显明,它们隐没在那41年的岁月里,却在此后漫长的无尽的岁月里散溢开来。卡夫卡于是成为了经典,这个经典不再是一个“经典作家”,而是作为一个“经典”的存在着的人。我们似乎都能在卡夫卡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但毫无疑问,这个存在本身也是庞大的,他不只是面向某一个人,而是面向了“全部的人”。于是,这本《关键岁月》的另一个意义也凸显了——不执著于作品、作家、读者的关系,而是完整性地去呈现作家这个个体的生命,在寻求“完整性”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发现了此一个体的“完整性”又恰对照着作为整体的“全部的人”,于无知无想无意识中,便呈现了这样的结果——写一个卡夫卡,就呈现了“全部的人”。进而,在阅读中,不难产生这样的感觉:分明见到一个人,又分明见到一切人。
如果想在这本传记中找到只属于文学作品性质的阐释,是不会失望,但不会是最主要的,如果想在这本传记中找到传主的逸闻趣事,是不会失望,同样却不是最主要的。施塔赫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打开的完整的生命体,那么,唯有打开自己,才能面对他,面对他,同时也就面对了自己,通过卡夫卡,于万万人中,于万万年间,看到了一个人——自己。看似是与卡夫卡相遇,其实何尝不是于苍茫天地亘古洪荒中,与自己的相遇。以“完全的人”烛照细微之自我,于无尽中见有限,于有限中,见及此生此世当前当时之自我之珍贵,于是,此生的悲喜,此生的哀慈,此生的孤独,此生的幸运,此生的陌生,此生的熟悉,此生的有,此生的无,此生的一切,一切的一切,便都通了。生生之谓易也。
我们能复原近乎一切的细节,而这所有的细节,却再也不能让我们这个物种产生另一个卡夫卡。这是施塔赫心知肚明的一件事。这也是这部传记作品本就不打算为之的一件事。文学的化学反应并非为了发明什么再造什么,而是为了呈现——毕竟,生命等候的,首要是发现而非发明,卡夫卡亦如是。于此,“锤子”显明出来了,相遇本是生命的题中之义,作为木匠、铁匠、泥瓦匠、教书匠的“我们匠”与“锤子”相遇了,一切的事,就都顺理成章了。
我看卡夫卡的照片,最醒目也最吸引我的,只是他的耳朵,黑白的照片里,视力每况愈下的我确实看不出文学的眼睛,但那双耳朵,那么大的那双耳朵,卡夫卡,这个连乒乓球落地都能引来不适的人,明明是一个那么喜欢安静的人,长得那么大的一双耳朵,似乎在努力听一切能听到的声音,更似乎,一切的声音,都能肆无忌惮地进到他的耳朵里——世界是多么的热闹,世界是多么的喧嚣,造物之力,真是怪哉。家里老人说,耳朵大的人有福,以前以为是耳朵大那个人有福,看看卡夫卡,他好像算不得有福,能读到他的人,算。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德]莱纳·施塔赫著,黄雪媛、程卫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