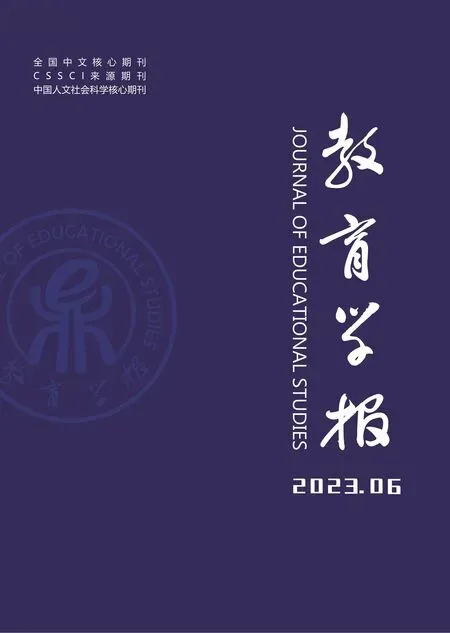儿童教育的乌托邦建构与展望
——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述评
孟令军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儿童的世纪》(TheCenturyoftheChild)一经问世,就引发了欧洲教育学界的关注,被称为“一本充满活力的书”[1],此后被翻译成26种语言[2]。作者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年)也因该书被冠以“改革措施运动的先知”[3]、“北欧女子的先觉”[4]、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片土地上第一个女人”、“妇女政权论者”[5]、“儿童世纪的先驱”[6]、“永恒的女祭司”[7]、“现代的圣布丽姬”[8]等多种称号。她的儿童教育思想在德国、英国、瑞典等欧美国家广泛传播,[9]随后经过翻译影响到了日本[10]、中国[11]等多个亚洲国家。
一、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
欧美学者比较重视爱伦·凯的教育思想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研究。《爱伦·凯,她的生活和工作》(EllenKey,HerLifeandHerWork)一书介绍了爱伦·凯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以及她所主张的教育思想(1)参见:HAVELOCK ELLIS.Ellen Key,Her Life and Her Work[M].trans A.E.B.Fries.New York &London:G.P. Putnam’s Sons,1913.。《儿童权利的世纪》(TheCenturyoftheRightsofChildren)则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儿童的世纪》做出解读,认为该书揭示了一种新的儿童文化的发展方式,并讨论了儿童被爱的权利、选择父母的权利以及淘气的权利等。[12]《限制或解放:爱伦·凯对学校、宗教教育的看法》(Limitorliberation:EllenKey’sviewonreligiouseducationinschool)讨论了在当时政治—宗教框架下爱伦·凯对宗教和学校教育的态度,特别对宗教教育给儿童带来的是限制还是解放做出细致探讨。[13]第二,对爱伦·凯著作的书评。如《爱伦·凯所著的〈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by Ellen Key)简要介绍了《儿童的世纪》的思想内容和主要观点。[14]第三,把爱伦·凯的教育理念与其他教育家进行对比研究。如《爱伦·凯和鲁道夫·契伦论战争、和平和一战后欧洲的未来》(Ellen Key and Rudolf Kjellén on war,peace,and the future of post-First World War Europe)考察了同为瑞典公共知识分子的爱伦·凯和鲁道夫·契伦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揭示了他们的政治背景和世界观。[15]《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之辩》(Debating Individualism and Altruism)讨论了一战前德国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温和团体,特别是格特鲁·伯伊默对爱伦·凯作品的批评与接受,并讨论了两位对宗教作用的不同态度。[16]
国外对爱伦·凯教育思想的研究较为多元,无论是对其教育思想的探讨还是对比研究,都呈现出研究多样化的趋势,并且从研究时间上看也是比较持久的。不过仍需要看到的是,在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研究中,其所研究的范畴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两方面,即便是有文章关注到了爱伦·凯的宗教教育,也没有把它纳入到整个儿童教育思想的框架内加以讨论。
(二)国内研究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译介,爱伦·凯的“母性论”“新性道德”等思想传入中国,对我国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解放思潮[11]和五四新文化运动[17]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就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研究主要可分为译介研究和专题研究两部分。在译介研究方面,沈泽民翻译了《恋爱与道德》(2)参见:爱伦·凯著,沈泽民译:《恋爱与道德》,上海书局1925年版。,爱伦·凯批评了传统的婚姻观念,主张自由恋爱,建立新型家庭关系;朱舜琴翻译了《恋爱与婚姻》(3)参见:爱伦·凯著,朱舜琴译:《恋爱与婚姻》,光明书局1926年版。,以爱为基础的恋爱是构建幸福家庭的基础;黄石翻译了《母性复兴论》(4)参见:爱伦·凯著,黄石译:《母性复兴论》,民智书局1926年版。,该书把母性作为女性的自然属性,民族、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都与母性息息相关。在评介方面,瑟庐的《爱伦·凯女士与其思想》[18]简要概括了爱伦·凯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茅盾发表的《爱伦·凯的母性论》[19]164-173论述了她的母性观。此后,有关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的评述多集中在教育研究史中,如滕大春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第四卷)、张斌贤主编的《外国教育史》、单中惠编写的《西方教育思想史》等。在国内,专题研究爱伦·凯的著作和论文相对较少,学术论文有庞德禄的《爱伦·凯的教育思想述评》[20],杨洁、闫娜的《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探析》[21]和吴明海、李功雨、梁芳的《爱伦·凯“儿童的世纪”教育思想及其借鉴意义》[22]三篇,硕士论文有张霞的《爱伦·凯教育思想研究》(5)参见:张霞著:《爱伦·凯教育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版。和雷蕾的《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思想》(6)参见:雷蕾著:《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思想》,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版。两篇。
就国内研究来看,其研究范畴同样集中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两方面,而忽视了对宗教和社会教育两个维度的考察,研究不够整体全面。同时,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具体研究中也存有可商榷之处:从家庭教育上看,学界关注到了爱伦·凯提出的新型家庭教育模式,但没有对其主张的“女内男外”的家庭结构做出深入分析。此外,爱伦·凯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认可所有的家庭教育,她批判了两种家庭教育,当前学界对此关注也不够;从学校教育上来看,当前学界看到了爱伦·凯提出的新式学堂以及对体罚教育的反对,不过就此认为爱伦·凯“推行新式学校教育”[21]的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另外,从教学模式上来看,学界关注到了爱伦·凯提出的开放式教学,但认为她“否认班级授课制,否认教师的指导作用”[20]的观点也有悖于她的思想主旨,爱伦·凯不曾否认班级授课制以及教师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爱伦·凯著作的文本细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和深化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思想,并指出它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建构与展望,以期丰富对爱伦·凯教育思想的研究。
二、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前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传统教育不适配社会需求等因素影响了教育思想、制度和实践的发展。科学知识被纳入教育中,儿童身心发展成为教育关注的重点。教育由原来的古典教育转向了科学教育,出现了新人文主义教育、主知主义教育、幼儿园教育、全人类教育等新的教育思想。新人文主义教育主张教育应是无功利性的,它反对崇尚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派和功利主义派;主知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赫尔巴特提出儿童的关联理论,认为教育应加强对儿童的管理,以培养有序的道德观念;幼儿园教育则强调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重要性,福禄培尔主张儿童在游戏中发展;全人类教育思想反对等级学校,主张普及教育。
19世纪后半期,欧洲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对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知识的进步,特别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为“新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新教育思想批判了传统教育,它更注重儿童个性自由的发展,爱伦· 凯的儿童教育思想就是新教育运动的一部分。雷迪认为学校应促进儿童身心的自由发展,教师与儿童之间应是真诚的信赖关系。德可乐利批判了传统教育过度关注课本知识、学科细化等弊端,他主张生活教育,认为儿童应从生活中学习。新教育运动注重把现代生物学、心理学的学科纳入教育教学中,重视儿童的自主性,在教学中也更加强调科学教育。[23]
通过对欧美教育史中“儿童研究运动”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思想和教育思想史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在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出现之前,新人文主义教育对审美、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关注以及对教育的无功利性的关注与爱伦·凯对“未来学校”的畅想和对功利化教育的批判是一致的;幼儿园教育对学前教育的关注和爱伦·凯重视儿童教育也有相似性;全人类教育思想主张的教育同等化和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观点与爱伦·凯主张的为所有人建立“高级意义的学校”“终身学习的学校”和新型宗教教育的提出也有承续性的关系。雷迪主张的真诚信任的师生关系与爱伦·凯对教师灌输知识的抨击内在逻辑相符;德可乐利反对学科细分与爱伦·凯强调教育回归生活和自然是相同的。可以说,爱伦·凯提出进入的新世纪(即1900年以后)是“儿童的世纪”,这一观念的提出并不是凭空而来,它顺应了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潮的发展规律。
此外,从瑞典历史发展来看,19世纪后半期瑞典进入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妇女和儿童成为主要廉价劳动力来源。同时,19世纪的瑞典对“家庭价值观”仍比较重视,如《瑞典家庭杂志》和《家庭之友》等新杂志的发行,它们宣扬并标榜家庭和睦的价值理念。瑞典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和对家庭价值观念的重视形成了冲突。这一点也体现在爱伦·凯既主张妇女独立又强调妇女要有母性气质并回归家庭等方面。在学校教育方面,瑞典的宗教教育与学校教育关系密切,十六七世纪,教会实际上成为了国家的一个部门,民族主义和民主的教育理念也使宗教教育得到了深化。[24]5在1842年颁布的《公共教育法》(the Law of Public Education)中,它确保了7~13岁儿童获得基础教育的权利,其教授范畴包括读、写和算术,以及路德教基本信条等。[25]在瑞典青年运动中,赫丁(Hedin)和伯格(Berg)于1879年和1882年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人会议上批评了学校教育中学习宗教教义的授课内容。随后,在1897年第四次工人会议上,争取学校与教会相分离,把学校而不是教堂作为教授知识的教育场所。1904年文法学校委员会的成立,取代了大教堂负责课程教授的教育职责。[24]11-13可以看到,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的提出符合了时代发展的教育诉求: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要使妇女走出家庭,获得工作的权利,不过它又动摇了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路德教在瑞典国内依旧占有主流,宗教教育与学校教育相分离的理念也开始崭露头角。因此,19世纪瑞典的社会状况为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它是针对瑞典工业化发展向教育提出新要求所做出的反应。
三、爱伦·凯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一)家庭教育的缺位
家庭教育在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思想中占有核心位置。家庭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前端,在生活中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影响着儿童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她首先批评了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模式:“无论父母只为自己的利益存在,还是为孩子倾其所有,其结果都是可悲的。”[26]173家庭教育既不是在生活中只关注自我利益也不是牺牲自我,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以有意识的教育教化和无意识的家庭气氛共同建构起来的。从受教育群体上看,学校教育需要关注多数学生的发展需求,难以顾及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而家庭教育面对的是单个或少数儿童,在时间、精力等方面更为充裕;从教授内容上看,学校教育以学习科学知识为重心,家庭教育以培养品性为主;从教育影响上看,学校发挥作用的时间和场所有限,而家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场域,在时间上是持续不断的,在空间上又是无所不包的。
(二) 机械化和功利化的学校教育
爱伦·凯批判了传统学校教育中引以为傲的秩序、方法、制度、纪律等内容,她表示这种不从儿童角度而是从教育者角度制订方针、政策的学校教育是“教育犯罪”。她指出当今学校教育的病症:“在教育儿童时,最大的错误仍然是把‘儿童’当作一种抽象的概念,把他当作一种无机的或个人的材料。”[26]145传统教育中“教”与“学”不是双向互动,而是单方面的灌输,学校教学是流水线式的重复生产,它培养出来的是缺乏生机的工业产品。统一的纪律要求限制了儿童个性的发展,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被成批次地制造,这种专业化、统一化的教育加工生产方式是对儿童个性发展的戕害,是对受教育者样态多样化的忽视。
爱伦·凯对知识和教育做了区分:知识可以通过不断积累获得,它是固定的、无机的、中立的;教育与观点相关,它是变动的、有机的、引人向善的。当前学校教育是知识的讲授而非教育的学习,机械式的学校教育忽视了学生的情感需求和价值引导,“教育”中“育”的一面被抹杀了,只剩下知识的“教”。爱伦·凯批评了机械化和功利化的学校教育,指出这培养的只能是缺乏思辨能力的工业产品。
(三) 社会教育的缺失和僵化的宗教教育
体罚和雇佣童工是社会教育缺失的主要体现。爱伦·凯批判了驯化儿童的体罚教育,它既不道德又容易滋生暴力。“体罚对受体罚者和施体罚者都是一种羞辱,它是无效的。”[26]328体罚作为教育的手段,它直观地表现出教育的强制性和规训性。在爱伦·凯看来,体罚引发的是奴性思维,它使儿童变得唯唯诺诺,不敢表现自我,是对自我意识的否定。此外,体罚只能带来不良的结果,体罚的效力是短暂的,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儿童的邪恶意志,甚至会加剧儿童的逆反心理,强化其邪恶感。体罚最严重的后果是对道德观念的错置,它以强制的方式规训儿童的言行,从根本上否认了儿童具有独立意识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凡不符合社会的行为统统以惩罚的方式强行驯服,这会使不道德、不正当和非正义的观念变得道德、正当和正义了。
爱伦·凯坚决反对雇佣童工行为。工业化发展加剧了对工人的需求,机械式的操作工种被分配给更灵巧的儿童,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并使上层阶级的奢靡放纵与下层社会的贫困潦倒相对立。从儿童教育来看,雇佣童工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发展;从社会发展来看,它加剧了社会内部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在宗教教育方面,爱伦·凯批评了把基督教教义视为绝对真理的教育理念:“在影响人类的所有错误教育中,最危险的错误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的孩子被教导把《旧约》中的世界视为绝对真理。”[26]285在知识方面,人们从对基督教的感性信仰转为对自然科学的理性认识,宗教所教导的知识和科学知识完全相悖相离;在观念意识方面,资本主义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也与基督教宣扬的爱人如己理念大相径庭。此外,在婚姻方面,基督教主张结婚应遵循上帝的旨意,宗教婚姻是对爱欲的抑制而非净化,所培养的是责任而非爱,这也与自由婚恋观相矛盾。宗教想要发挥教育的作用势必要做出适当调整,它“不应该以孩子需要基督教为借口把孩子培养成基督徒”[27]297。
四、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以爱和母性为基础的家庭教育
1.以爱为基础的恋爱观
爱伦·凯认为,传统恋爱观“以强制为基础唤醒了灵魂和感官上的敌意”[26]35,它不会带来幸福的婚姻。她主张人们应自由恋爱,只有在爱情中才有可能孕育出优秀的儿童。爱伦·凯把儿童置于恋爱婚姻中的重要位置,自由恋爱的前提是对儿童负责,儿童是恋爱的主导。
2.以母性为基础的婚姻观
以母性为基础的婚姻观是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中最重要,也是被讨论的最为广泛的一部分。爱伦·凯认可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不过她又是谨慎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世界历史上所有争取自由运动中最重要的运动。不过它是将人类引向更高还是更低的方向,这是当今最严峻的问题。那些无条件地主张前者或后者的人,是做了不成熟的判断。”[28]60爱伦·凯看到了妇女解放运动带来的权利自由,不过它在使女性获得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权利的同时也动摇了家庭的根基,在宣扬自由独立之余又带来了自私利己的潜在风险。
爱伦·凯批评了妇女解放运动带来的混乱和无序,指出这“很容易陷入一种毫无道理的利己主义之中”[26]64,妇女解放运动带来的最坏影响就是对母性的忽视。她认为儿童发展是高于女性自由的,女性拥有选择工作的权利,不过一旦她想要或将要成为母亲时,她就应考虑这份工作对儿童造成的可能危害。爱伦·凯进一步指出当前女性气质中存在的问题:“早期对女性气质的定义忽略了女性存在中的人类普遍因素,而现在对女性气质的定义忽略了女性存在中的女性因素。”[28]104传统思想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这是对女性气质中人类普遍性的忽视,而妇女解放运动过度强调了两性之间的共性而忽略了女性的特性。
爱伦·凯从人格原则分析了女性的气质。人格原则的形成受智力动机、道德动机、情感动机和审美动机的影响,只有四种动机相协调时人格才能获得整全,“这种和谐一直是最优美的女性所特有的”[28]105。为此,“妇女必须以一种更加完美的方式来完成她迄今为止最崇高的任务:生育和养育新一代。”[28]187爱伦·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赋予了女性获得的整全人格,女性具有调和四种动机的能力,这种完满借助生育得以传承,生育是女性的天然骄傲,是其殊荣的表现。
爱伦·凯认为性别分工是有其合理性的,如在一些重体力劳动上,女性天然不如男性。两性不是对抗关系,而是“两者相互补充和帮助”[28]16。部分女性主义者就此认为爱伦·凯的妇女观是保守的,这会导致女性重新回到家庭中,沦为生育的工具、家庭的保姆。(7)如芬兰妇女协会成员、国际知名女权主义者格里彭贝格(Alexandra Gripenberg)在剧本《肖像,或十一个女人》(Portraits,or Eleven Women)中就嘲讽了爱伦·凯的家庭教育,认为这严重阻碍了妇女解放和人类进步。参见Tiina Kinnunen.Fighting Sisters:A comparative biography of Ellen Key (1849-1926) and Alexandra Gripenberg (1857-1913) in the contested field of European feminisms[M]//Erla Hulda Halldórsdóttir,Tiina Kinnunen,Maarit Leskelä-Kärki,et al.Biography,gender and history:nordic perspectives.Turku:k&h,kulttuurihistoria,Turun yliopisto,2016:144.这种评价其实多少是有失偏颇的。诚然,爱伦·凯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是以温和的方式对当前家庭教育做出改良。在她看来,妇女解放的价值在于使女性获得选择的自由,独立女性和回归家庭二者并不矛盾。
爱伦·凯把女性分为作为母亲的女人和作为女性的女人,肯定了前者回归家庭的价值,批评了后者回归家庭的行为。对于女性来说,母性是根本性的自然法则之一,“即便是作为情妇,其最好的品质也与她天性中的母性密不可分。”[27]124同时,爱伦·凯把母性气质抬高至社会层面,认为这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母性气质与民族活力和国家发展密切相关联,一个民族的活力取决于女性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能力和意愿,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母亲。从自然法则层面上看,母性是女性所特有的自然属性,它是基本法则之一;从社会准则层面看,母性是民族、社会和国家得以持存的根基。
(二)以发展个性和注重生活为主的学校教育
1.注重儿童个性的发展
在爱伦·凯看来,学校教育应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无差别教育。所谓以儿童为中心,意味着学校“给孩子提供材料来构建自己的个性,让他完成这个构建工作。”[26]160-161无差别教育则意在表明教育的共性,教育不以性别、种族、信仰等不同而有所区别,学校教育应当是开放式的、包容的,它在敞开的环境中允许儿童平等自由地发展。
金属空气电池是燃料电池的一种,是以金属为燃料,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产生电能的一种装置,是新一代绿色电池的代表之一。金属空气电池与一般电池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只有一个电极储存能量,另一个电极依靠呼吸空气中的氧气来提供能量。金属空气电池就像大部分生物一样,要正常工作,就得呼吸新鲜空气。
当然,平等自由发展并不意味着无序发展,教育者在教学活动中仍有存在的必要,爱伦·凯认为教育者最主要的职责是陪护而非教导:“教育者最伟大的技能是暂时保持沉默。”[26]161教育者的失语不是不作为,而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对儿童的干预,在必要时提供保护。在爱伦·凯看来,学校教育是自由的守望,它提供的是一个自由的场地,一种无碍的守护,一份安全的保障。
2.教育回归生活的旨趣
在爱伦·凯那里,学校教育应回归现实生活。新型的学校教育应“依据孩子的特征、技能和需求而做出与现实生活世界相关的方法。”[29]爱伦·凯畅想了理想的学校教育样式:未来学校的考试是没有试卷的,教官会陪同学生走到户外,考察他们对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的理解;未来学校是被大花园所包围的,儿童在审美教育中得到心灵的净化;未来学校是带有礼堂和操场的,儿童可以享受艺术的洗礼和自由玩耍的愉悦;未来学校是被艺术环绕的,儿童的艺术感被艺术品所唤醒。[26]260-266她用诗意的笔法描绘了未来学校的状态,儿童在学校获得自然、生活、艺术的多重审美体验,从生活中获取知识,同时又把知识应用于生活。
基于此,爱伦·凯反对学科细化分类的教学模式,“不是每一门学科都要细分……要将艺术史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26]216把理性知识与感性经验相结合,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在现实生活中把所学知识加以利用,把知识融入现实中,在生活中使儿童的情感得到升华,审美得到提升。传统教育制度被彻底废弃、替代,以儿童个体活动为主旨的生活教育成为主流。在未来学校中,切实以儿童为发轫点,回归生活的教导,实现生活与学习的交融共存。
(三)建立法规的社会教育和新型宗教教育
1.社会立法教育
爱伦·凯进一步指出社会立法教育和新型宗教教育的重要性。在社会教育方面,她认为儿童的堕落与社会相关,“堕落的儿童是社会本身的产物,社会就像一个暴君,挖瞎了一个人的眼睛,然后殴打他,并责怪是他自己找不到路,它通过惩罚迫使他们走上‘美德之路’。”[30]323虽然爱伦·凯反对体罚教育,不过她也承认适当的疼痛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儿童不知道火的危险,那么在安全范围内使他碰触火并感受到灼伤感,在爱伦·凯看来这是合适的,因为它会使儿童对火有切身的体会和认知,可以减少以后的危害,不过这种体验应以保护为前提,不能带有风险性。
爱伦·凯批评了在儿童教育中社会教育的脱节,在她看来,法律法规的作用甚微,不过它又是不可或缺的:“在人类的改良方面,风俗和情感的改变总是最重要的。与之相比,立法的影响微不足道。……立法有它的作用。”[26]59她指出,在儿童和妇女保护方面,“当前社会意识的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有效立法。”[26]323爱伦·凯主张社会教育建立法律法规,以保护儿童免受体罚,减少雇佣童工事件的发生,通过制定抚养权以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
2.信仰自由的新型宗教教育
爱伦·凯对宗教教育的态度是复杂的。她认为,宗教教育要尊重儿童的自我需求,它是对教育的增补,不能是强行传道,以布道的形式对儿童进行宗教教化是不合适的。宗教教育要以激发儿童的兴趣为着力点,在尊重儿童意愿的基础上实现宗教教化。在爱伦·凯看来,宗教教育是可行的,但不是必须的。正如她所指出的那样,“自发的忏悔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一种深切渴望得到宽恕的欲望。但是,一种人造的情感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毫无价值的。”[27]131爱伦·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儿童拥有信仰的自由,也有不信仰的自由,“爱伦·凯的生命信仰并不强调脱离宗教的自由,而是强调信仰的自由。”[30]人们之所以弃恶扬善,并非出于宗教宣扬的善在天堂、恶在地狱的知识和道德,而是善本身就比恶更值得追求,这本身和宗教无关。
爱伦·凯提出的新型宗教观和原有基督教教义并不相同,她并不认可基督教所提倡的自我牺牲精神,“她的愿景可以被视为一种宗教的愿景,旨在拯救人类,即使它不是一种基督教的救赎形式。”[31]爱伦·凯的宗教教育始终以儿童发展需求为主旨,带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同时,她的宗教教育又是与时俱进的,借助达尔文进化论和心理学实验对基督教教义中不符合社会发展和科学知识的内容(如传统基督教的婚姻观、善恶观等)做了适当删改。因此,爱伦·凯建构的宗教教育观是复合的,它是一条“从基督教到生命信仰的爱伦·凯之路”[32],是个人主义、进化论等思想杂糅的儿童宗教教育观。
五、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的反思与启示
距爱伦·凯提出“二十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已有一百余年,儿童的身心发展日益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中的部分观念业已成为教育和社会领域的共识,如倡导儿童个性发展、反对体罚、强调跨学科教学等等。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已经成为当前儿童教育的传统惯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它的持续性深入研究稍有不足。爱伦·凯儿童教育思想的相关观念符合了儿童教育的发展规律,这使它被广泛地接受、采纳和运用,成为儿童教育活动的教学指导。从这一点来讲,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思想实现了从新式教育到教育共识、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践的范式转换,在教育学界出现研究式微的现象恰恰证实了它的成功。
不过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思想既包含对现实教育的批判,又带有对未来理想教育的憧憬。它是带有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是乌托邦式的教育愿景。这种儿童教育的理想范式一方面可以作为参照系,通过它我们可以反观和审视当前教育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它也寄托了爱伦·凯对理想教育的期盼,理想化的教育理念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和生活,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可以更新、转换人们的教育观念的,而人是可以改变社会和世界的。爱伦·凯提出的理想化的儿童教育理念是以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影响了教育理念和教学活动的革新。因此,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思想既具有当下性又具有未来性,它是通过对现实教育的批判来完成对未来教育的展望。
(一)理想化的家庭教育
爱伦·凯提出的以“爱”和“母性”为基础的家庭教育是很难实行的:“爱”和“母性”带有很强的感性情感,我们很难对这种新型家庭教育制订合适的标准,这为评判家庭教育是否为儿童的健全发展提供保障带来了实操上的困难。爱伦·凯赞成女性获得自由独立的权利,不过在这权利之上她又悬置了“母性”气质,主张女性应以“母性”特征为主,必要时牺牲个人权益。爱伦·凯提出的“长期以来所宣称的妇女个性的自治与仅通过妇女对生育的承诺而使人类变得更完美的预言是不相容的。”[33]无论是以爱为基础的恋爱观还是以母性为基础的婚姻观,它们都是爱伦·凯理想化的家庭教育模式,只提供了一种未来的可能,但在具体的实操性和可行性层面则需要打个问号。
(二)乌托邦式的未来学校
爱伦·凯的未来学校是带有鲜明乌托邦性质的,它是对未来的一种构想,“在‘家庭学校’之后的学校教育,爱伦·凯没有提出任何系统的方案。”[34]学校教育的受教育者是群体而非个体,它从源头上断绝了全面发展学生个性的可能性。在未来学校里,儿童的发展是自由的,是无蔽的,是敞开拥抱知识的,是面向自我和世界的。爱伦·凯用文学性的语言描绘了未来学校的美好愿景:“当方舟来到旱地时,人们不需要建造学校,而只需种植葡萄园,在那里,聘请的教师将成熟的葡萄带给孩子们。”[26]257理想的学校教育与生活息息相关,它没有围栏的束缚、没有知识的灌输,它从现实生活中来又回到现实世界中去,儿童在个性兴趣的感召下自由采摘知识的果实,它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教育图景。
(三)浪漫化的社会、宗教教育改革
爱伦·凯重视社会和宗教教育的作用,她的儿童教育观是立足社会的,“爱伦·凯是一个致力于改变社会的梦想家”[2]。不过她把希望寄托于情感良知,认为社会立法的效用甚微,这又注定了她是带有浪漫色彩的梦想家。她主张通过立法来减少体罚和雇佣童工事件的发生,不是立足现实对立法做出具体规定,而是把立法作为对情感良知的适当补充,爱伦·凯所提倡的,我们可以称其为浪漫的制裁。[35]立法是必需的而非必然的,它是当前社会不完善条件下不得已的折衷,是对道德良知觉悟不高的弥补。爱伦·凯提出的宗教教育是经过改良的新型宗教观,她把对上帝的信仰转换为对自我生命的信仰。她坚信终有一天儿童会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多重庇护下自由成长。到那时,新世纪的新宗教,即儿童的世纪将真正到来,而现在,这只是一些梦想家心灵中的一个希望。[36]
爱伦·凯主张的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它没有对现实制度的具体改革,对宗教教育的抨击力度也不够,它只是对情感教化不足的补充,是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她建立起爱与良知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理想的教育范式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一定程度上说,她的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改革是对遗憾现实的浪漫化补偿。
六、小 结
爱伦·凯从家庭、学校、社会和宗教四方面入手,系统阐发了她的儿童教育思想。在家庭教育中,她强调树立以“爱”为基础的恋爱观和以“母性”为基础的婚姻观;在学校教育中,她认为学校应尊重儿童个性发展,回归现实生活,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适合儿童学习的场所,教师在其中应扮演护佑者而非教育者的角色;在社会教育中,爱伦·凯认为立法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宗教教育中,她主张建立新型的宗教教育观,儿童具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这是混杂着个人主义、进化论等思想的新型生命信仰宗教观。不过,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浪漫成分,如她提倡的“爱”“母性”“道德”“良知”等都是教育活动中难以量化的标准。未来学校的构想和相信道德情感高于立法等也显示出她对未来理想教育的展望。因此,爱伦·凯的儿童教育是对其所处时代教育不足的反思与重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建构与展望,它在揭示出其所处时代教育存在不足的同时,又因浪漫化的构想成分而变得难以实施。